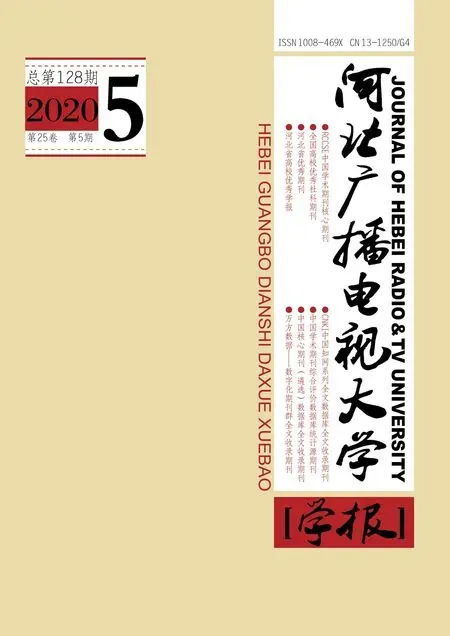韋斯· 安德森電影中后現(xiàn)代主義傾向的時(shí)空觀
徐斯然
(香港理工大學(xué) 中國文化學(xué)系, 中國 香港 999077)
韋斯·安德森是20 世紀(jì)90 年代美國獨(dú)立制片運(yùn)動(dòng)的重要成員,他的電影深受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思潮的影響,電影學(xué)者華倫·巴克蘭德(Warren Buckland)認(rèn)為韋斯·安德森的電影“與后現(xiàn)代主義密不可分且相得益彰”[1]。后現(xiàn)代主義在電影時(shí)空的表現(xiàn)上往往展現(xiàn)出其時(shí)間的無序性、時(shí)空的雜糅性,在時(shí)空的鏈接上“它不主張去舊更新,不斬?cái)嗯c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在中心二元對(duì)立中進(jìn)行拆解和間離,從而消解現(xiàn)代理性的權(quán)威”。[2]在其電影重疊時(shí)空的往復(fù)中,又試圖建立一種“游蕩者的時(shí)空觀”:“創(chuàng)造出一種錯(cuò)位的時(shí)空關(guān)系,他在代表現(xiàn)代性和當(dāng)下的時(shí)空中游走,但卻總是在往后、往過去看。他總是想要回到自己的記憶中去,而拒絕所有機(jī)械復(fù)制的圖像所提供的、所呈現(xiàn)的過去。”[3]
所以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中常常采用敘述倒置的手法,將當(dāng)下和過去的多層時(shí)空置于對(duì)讀的狀態(tài)之中,使人物所經(jīng)歷的外在時(shí)空轉(zhuǎn)化為自我的時(shí)空之中,其中包含著強(qiáng)烈的主觀性與虛構(gòu)性,但也正是如此,他的電影中深化了時(shí)間和空間的維度,在看似散亂的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中,尋找一種真正的鏈接——跨越時(shí)間與空間的個(gè)人情感交流。
一、媒介回溯產(chǎn)生的“深層時(shí)間”
在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中,他經(jīng)常以不同的傳播媒介作為時(shí)間回溯的工具,這些媒介包括戲劇、電影、書籍等。他以媒介介入的方式進(jìn)行不同時(shí)間的堆疊,形成時(shí)間的套層結(jié)構(gòu)。在他的電影中,時(shí)間絕不僅限于現(xiàn)在進(jìn)行時(shí)或過去進(jìn)行時(shí)這樣單一的線形時(shí)間結(jié)構(gòu),他通過時(shí)間的不斷回溯創(chuàng)造出一種“深層時(shí)間”,這意味著故事在復(fù)合歷史的發(fā)展中不存在一條基本線,你可以越出這條線而去尋找其他的星叢。并且這種套層結(jié)構(gòu)也并非簡單的疊加,在深層時(shí)間的框架內(nèi),他們展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流動(dòng)性:其具體表現(xiàn)為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的相互追溯、過去與過去之間的交互感染,這種戲劇性的追溯模式模糊了時(shí)間的界限,在打開故事時(shí)間深度的同時(shí),也擴(kuò)展了時(shí)間的維度和廣度。
1.重建歷史邏輯的小說想象
韋斯·安德森善于將電影的故事放置在一本小說的框架之中,以此來進(jìn)行異質(zhì)空間的想象。比如:《布達(dá)佩斯大飯店》中第一層敘事結(jié)構(gòu)始于一本名為《布達(dá)佩斯大飯店》的書;《穿越大吉嶺》中的杰克是一個(gè)作家,他構(gòu)想的小說不時(shí)地穿插在整個(gè)故事之間;《天才一族》更是把整個(gè)故事置于一本書的不同章節(jié)之內(nèi)。韋斯·安德森以小說的方式進(jìn)行故事前史的回溯和創(chuàng)造。究其原因,小說與歷史的相同之處就在于:它們都不斷地被重寫、修改。韋斯·安德森以小說的形式,利用人物的主觀視角重建了歷史的順序與邏輯,所以他的故事消除了垂直的歷時(shí)分界線,用大量的跳切鏡頭來阻斷敘事的連貫性,讓人們?cè)诠适碌恼鎸?shí)性和虛構(gòu)性之中游走。
《穿越大吉嶺》講述的是三兄弟在錯(cuò)置時(shí)空追尋心靈之旅的故事,這是韋斯·安德森第一次將家庭創(chuàng)傷作為探討的對(duì)象。與其他影片不同,《穿越大吉嶺》一直以線性時(shí)間的發(fā)展模式作為電影的基本時(shí)間線,劇中唯一一次時(shí)間倒敘發(fā)生在他們參加落水男孩葬禮的途中。這一時(shí)刻,影片回溯到了他們關(guān)于父親葬禮的集體記憶,正是這一“回憶”藏匿了他們彼此痛苦和不信任的根源。然而在此之前,杰克的小說已經(jīng)埋下了戲劇性的伏筆,在電影前半段的游歷過程中,杰克向兩兄弟介紹了自己新寫的小說:德國空軍汽車公司,在他們交談的過程中,杰克一再向他倆重申書中故事的虛構(gòu)性。但當(dāng)回憶重新上演,這個(gè)虛構(gòu)的故事卻成為記憶中的真實(shí),在參加父親葬禮的途中,他們?cè)诘聡哲娖嚬旧涎萘艘惶帒蛑o的表演。它既是記憶,同時(shí)也是虛構(gòu)性的戲劇表現(xiàn)。
一方面,小說可能是這次事件的戲劇化表達(dá),但也可能是真實(shí)記憶的自我反省。那一次,他們見證了父親葬禮中母親的缺席,發(fā)現(xiàn)了大哥在家庭關(guān)系上有所隱瞞,翻出了父親行李箱中那本還未被打開的書——杰克的《隱形墨水及其他故事》。小說的故事似乎看透了他們悲傷的深淵,對(duì)于這些角色而言,這些真相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根源,當(dāng)杰克一再重申故事作為小說的虛構(gòu)性時(shí),他其實(shí)是用小說掩飾其內(nèi)在的傷疤。所以現(xiàn)時(shí)的心靈之旅無法解決他們記憶中隱藏的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隨時(shí)間回溯到過去,直面創(chuàng)傷才是療愈創(chuàng)傷的必要前提。
在《布達(dá)佩斯大飯店》中,小說則建構(gòu)了一個(gè)新的敘事層次,這部電影可以說是韋斯·安德森電影中最復(fù)雜的構(gòu)圖形式。他在這部影片中進(jìn)行了深入的時(shí)間開掘,最深層是主體的故事事件,向上一層是老門童Zero(零號(hào))的回憶,再向上一層是作家對(duì)于故事的戲劇創(chuàng)作,最后是女孩閱讀之后的主觀理解。此時(shí),“作者、讀者、世界、文本等要素得到了綜合體現(xiàn),產(chǎn)生了復(fù)雜但有機(jī)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4]雖然觀看過程有著清晰的歷史邏輯,但在經(jīng)過層層人物主觀地?zé)o意識(shí)加工后,真實(shí)的故事性顯然已經(jīng)被小說化了。
所以布達(dá)佩斯大飯店本身是一個(gè)充滿象征符號(hào)的、被重建現(xiàn)實(shí)邏輯的虛構(gòu)的世界。“后現(xiàn)代主義電影空間一大特點(diǎn)就是深度的削平,即從本質(zhì)走向現(xiàn)象,從深層走向表層,從真實(shí)走向非真實(shí),從所指走向能指”,[5]這種深度的削平不是空間的壓縮,而是對(duì)宏大敘事的消解。所以韋斯·安德森將厚重的歷史表達(dá)集中于人物真實(shí)發(fā)生的情感關(guān)系之上,他講述了艱難社會(huì)中文明個(gè)人的故事:Zero(零號(hào))經(jīng)歷了歐洲戰(zhàn)前文化褪色的最后輝煌,在面對(duì)難以置信的混亂、暴力和貪婪的世界中,他們卻擁有一套自我的內(nèi)心秩序,這種秩序的建立使他們得以用純粹的態(tài)度表達(dá)自己對(duì)事物的正確理解,形成一種不以權(quán)力評(píng)判體系為標(biāo)準(zhǔn)的信任。古斯塔夫相應(yīng)地提供了某種優(yōu)雅文明的外觀,但正如臺(tái)詞所說:“古斯塔夫的世界早在他步入前就已經(jīng)逝去了,是他用超凡的魅力維持了這種假象。”他所在的酒店系統(tǒng)也是灰暗之中的明確光線,無條件地成為他越獄行動(dòng)的精準(zhǔn)指南,他們之間有一種深入的鏈接,即志同道合的人共享著一份職業(yè)。除此之外,古斯塔夫與Zero(零號(hào))形成了跨越種族、跨越階級(jí)、跨越是非評(píng)判的真正友誼,他們?cè)谶@個(gè)灰色世界中建立了最真誠的溝通,情感對(duì)于苦難的緩沖,才是韋斯·安德森穿透重疊歷史空間表達(dá)出的真正渴望。
2.戲劇舞臺(tái)主觀性的時(shí)間拓展
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中常常出現(xiàn)一個(gè)一體化的假定性戲劇舞臺(tái),它可以荒誕和假定對(duì)真實(shí)世界的書寫。紀(jì)錄片在它的電影中也被偽造成戲劇空間,使真實(shí)和虛構(gòu)形成一組悖論。對(duì)于舞臺(tái)空間上的含義,韋斯·安德森的電影更善于展現(xiàn)其時(shí)間上的延伸,戲劇舞臺(tái)也包含著一種主觀演繹,具有亦此亦彼的開放性。相對(duì)于小說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想象的空間,舞臺(tái)或者具有舞臺(tái)感的紀(jì)錄片形式則是一個(gè)實(shí)在的觀看空間。這種觀看空間包含著雙層時(shí)間,一個(gè)是舞臺(tái)表演的物理時(shí)間,它是線性的有序的;一個(gè)是主觀的心理時(shí)間,它是非線形的無序的,但它可以超越物理時(shí)間,將人物內(nèi)心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無限放大。
《水中生活》講述了一個(gè)海洋紀(jì)錄片導(dǎo)演的故事,電影的開篇以舞臺(tái)形式的畫面作為開場,紅色的幕布完成了空間的視覺閉合,假定性的戲劇舞臺(tái)是鏈接當(dāng)下與回憶的一個(gè)媒介,影片的開始意味著將視角引入回憶之中,在觀眾的“集體性注視”下,紀(jì)錄片導(dǎo)演史蒂夫(Steve Zissou)拍攝的影片《美洲豹鯊第一部》上演了。史蒂夫(Steve Zissou)的影片真實(shí)記錄了他充滿創(chuàng)傷的一次出海經(jīng)歷,他的摯友伊斯特(Esteban du Plantier)在和他出海尋鯊的過程中被鯊魚咀嚼吞下,在這次航行中犧牲,也為這部影片貢獻(xiàn)了最大的噱頭與爭議。
在“集體性注視”的劇院模式中,他的回憶性創(chuàng)傷接受了全體觀眾的審判,形成了他與觀眾溝通之間的不可調(diào)和,觀眾理性的冷漠造成了他心中的二次創(chuàng)傷,他不得不面對(duì)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欲望與傷痕,同時(shí)也造成他與回憶間的不可調(diào)和。他再次以同樣的路線出海尋鯊,進(jìn)行《美洲豹鯊第二部》的拍攝。這一過程其實(shí)是史蒂夫(Steve Zissou)尋找對(duì)抗和療愈心理的方法,它使得時(shí)間向未知的未來延伸,也向相似的過去回溯。
相比《水中之書》中紀(jì)錄片電影呈現(xiàn)出的回憶寫實(shí)主義,電影《青春年少》的戲劇舞臺(tái)則更多體現(xiàn)著一種對(duì)未來時(shí)間的想象。《青春年少》中的麥克斯是戲劇小組的導(dǎo)演,他對(duì)于戲劇情節(jié)的編排帶有一種現(xiàn)實(shí)無法滿足的期待感。戲劇舞臺(tái)切割了現(xiàn)實(shí)時(shí)間,存在著強(qiáng)烈的英雄主義情節(jié),每一句臺(tái)詞都要出現(xiàn)在對(duì)應(yīng)的劇情當(dāng)中,不能有絲毫的偏離,從而形成一出完美戲劇。
可現(xiàn)實(shí)中事情的發(fā)展卻常常背離他預(yù)設(shè)的軌道,他將戲劇想象中的劇情帶入現(xiàn)實(shí),卻常常深陷邏輯不合理的泥潭。他一直以戲劇中的節(jié)奏等同于生活中的節(jié)奏,戲劇中的時(shí)間等同于生活中的時(shí)間,所以當(dāng)他試圖將影片中的海洋生物帶入真實(shí)中,為心愛的人建一個(gè)水族館時(shí),他失敗了。他唯一和解的辦法只能將自己再次帶入虛構(gòu)性的戲劇空間中,他在生活中的遺憾,不被認(rèn)同的夢想以及少年炙熱的愛情理想,最終在他導(dǎo)演的戲劇中得到了實(shí)現(xiàn),他用戲劇和自我的欲望交流,在未來的戲劇時(shí)間中滿足了現(xiàn)實(shí)時(shí)間無法達(dá)成的期待。
二、“間性空間”融合的情感聯(lián)結(jié)
韋斯·安德森電影中的人物故事總發(fā)生在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空間之中,但是這個(gè)空間卻也不是單一的、密封的空間,空間之間也進(jìn)行相互的交流,是一個(gè)文化混雜的“間性空間”。“間性空間”這一后現(xiàn)代性概念是由哲學(xué)家霍米巴巴提出的,他“從承接索亞的第三空間入手,認(rèn)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續(xù)不斷地處在混雜性的過程之中,但恰恰是這種混雜性的第三空間才使得其他各種立場避免二元對(duì)立思維而得以出現(xiàn)”。[6]所以在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中時(shí)常出現(xiàn)多重空間之間的交流,這種交流既包括空間的流動(dòng),即空間的“里”與“面”形成的物體內(nèi)外的接觸與碰撞;還包括空間的組合,即“俄羅斯套娃式”的空間嵌入結(jié)構(gòu)。
眾多關(guān)于韋斯·安德森的電影研究理論都傾向于探討其電影中獨(dú)立空間的結(jié)構(gòu)意義,將間隔感披上神秘的外衣,疏遠(yuǎn)觀眾觀看的空間距離。但個(gè)性空間的塑造絕不意味著孤立,他包含著多元的文化中彼此獨(dú)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個(gè)體,正如邁克爾·夏邦所說:“距離并不意味著令我們遠(yuǎn)離情感,而是讓我們以更多的理性去思考和認(rèn)識(shí)它,使我們看到情感的整體性。”[7]
1.“里”與“面”的空間交流
空間的流動(dòng)性是韋斯·安德森電影的突出特點(diǎn),通常如果劇中人物靜止,那么相對(duì)人物所處的空間就會(huì)移動(dòng);如果空間靜止,那么人物就會(huì)流動(dòng);假使是靜止空間中的靜止的人物,攝影機(jī)的視覺鏡頭就會(huì)移動(dòng)。這種流動(dòng)的狀態(tài),塑造出空間與人物開放界面中的交流感。
移動(dòng)的交通工具是空間運(yùn)動(dòng)的最佳載體,它往往包含著“里”和“面”兩層,內(nèi)外空間在相互接觸時(shí)會(huì)發(fā)生交換和交流。《穿越大吉嶺》的夢想專列、《布達(dá)佩斯大飯店》的城際列車都是以火車作為流動(dòng)空間的移動(dòng)工具。火車本身有固定的軌道,它是一種有目的、有規(guī)則的行進(jìn)方式,但是兩部電影中的人物都沒有通過火車到達(dá)預(yù)定的終點(diǎn),列車在運(yùn)行途中由于不同原因戛然而止。《穿越大吉嶺》的火車偏離了軌道,行駛到一片荒蕪的沙漠之中,《布達(dá)佩斯大飯店》的火車兩次被軍隊(duì)攔下,因?yàn)閆ero(零號(hào))的移民身份而被迫中止行程。在火車停止運(yùn)行的時(shí)刻,火車內(nèi)部的“里”和外部的“面”發(fā)生了接觸和碰撞,里面是他們的心理秩序,外面是世界的客觀秩序,單獨(dú)的某種秩序都無法形成完整生命的真諦。
所以,當(dāng)意外悄然而至,“里”和“面”有了對(duì)話和沖突,他們才能從獨(dú)立的個(gè)體變成交互的整體,人物之間的內(nèi)在交流才真正形成。在《穿越大吉嶺》中他們走下列車,卸下與父親行李的不舍糾葛,脫下各自身份的面具,三人為參加葬禮一襲白衣走在沙漠中時(shí),真正的情感互換發(fā)生了,三兄弟第一次出現(xiàn)在統(tǒng)一的鏡頭中,他們邁著相同的步伐向前走,歌詞成為情感交流的媒介:“我們不是兩人,我們是一個(gè)人,你我來自同一個(gè)地方,那里是被拋棄者的故鄉(xiāng),所以我們同走在一條路上,我們不用說什么,直到到達(dá)最后的寧靜。”《布達(dá)佩斯大飯店》中的交流形式則略顯沉重,火車的“里”是文明世界最后的秩序,火車的“面”是摧毀秩序的戰(zhàn)爭體系,第一次文明與野蠻的交鋒是文明占了上風(fēng),第二次文明與野蠻的交鋒則是文明的最終摧毀,可是古斯塔夫與Zero(零號(hào))的情感正是在這兩次交鋒中得到了深入的連接,古斯塔夫的自我被建筑到Zero(零號(hào))的內(nèi)心中,得以在未來延續(xù)下去。
2.“個(gè)體”與“整體”的空間感染
韋斯·安德森電影中的空間是一個(gè)個(gè)體量不一、彼此獨(dú)立又互相依存的空間段落。空間的疊加和錯(cuò)層形成了不同空間之間的套層結(jié)構(gòu)。當(dāng)個(gè)體空間之間產(chǎn)生了重疊,就會(huì)形成空間感染,促成不同個(gè)體空間的交流。
這種“空間感染”的框架結(jié)構(gòu)在韋斯·安德森電影中以極高的頻率出現(xiàn),形成了他電影風(fēng)格的主體性,他也借此來表達(dá)情感的多樣性。在《月升王國》中,它被用來展現(xiàn)疏遠(yuǎn)的親屬關(guān)系。卡拉與父母分別處在三個(gè)不同的空間內(nèi),在影片的開場時(shí)刻,一組縱深鏡頭以疊加的方式將三個(gè)空間放置在統(tǒng)一整體內(nèi)。但是,整體的有機(jī)結(jié)合,卻并未形成三個(gè)人的整合,反而更加凸顯了個(gè)體間的孤獨(dú)與陌生。他們只是被血緣包裹的孤立個(gè)體,彼此缺少交流,更無法融入。
差異化空間截面的展示和組合也能形成空間之間的感染,《水中生活》的空間截面是船上的不同船艙,《布達(dá)佩斯大飯店》中的空間截面是酒店的各個(gè)房間,《穿越大吉嶺》中的空間截面是火車的節(jié)節(jié)車廂,這些具有差異性的空間最終都被組合到同一整體中。用空間的疊加建構(gòu)了“敘事起止的結(jié)構(gòu)性符號(hào),空間在不斷被割裂的同時(shí)又被多次粘合,同舞臺(tái)的分幕/換場一樣,每個(gè)獨(dú)立空間指向不同分幕的舞臺(tái)空間,人物角色的行為與關(guān)系隨空間流變,又讓敘事不斷變奏,造就了不同空間內(nèi)景觀與敘事的獨(dú)立,形成了不同情景內(nèi)的融合與聯(lián)系”。[8]
另外,眼睛也是一種空間交流的界面,它將物體分隔為凝視與被凝視的關(guān)系。通常來說,眼睛的看都不是純粹客觀的觀看行為,它包含著主觀價(jià)值的觀看視角。所以當(dāng)不同的人看向同一物體時(shí),觀看的結(jié)果可能出現(xiàn)不同的差異,所以不同視角的觀看本身就可以構(gòu)建出框架中的復(fù)合關(guān)系。當(dāng)個(gè)人的觀看視角變?yōu)橹丿B的觀看視角時(shí),就會(huì)出現(xiàn)“空間感染”,從而形成不同個(gè)體間價(jià)值觀的碰撞。《穿越大吉嶺》中的皮特就有著雙重的觀看視角,他佩戴著父親留下的眼鏡,所以他的觀看行為中便加入了父親的部分,他的自我認(rèn)同必須借助于父親的形象才能得以進(jìn)行。這種跨越了時(shí)空也跨越了載體的空間感染,必然指向的是內(nèi)心深處的和解與溝通,他們最終都無法脫離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連接,在遺憾和苦澀中追尋溫暖與安慰。
三、結(jié)語
后現(xiàn)代性是一個(gè)龐大而復(fù)雜的哲學(xué)命題,他與電影的溯源大概開始于20 世紀(jì)90 年代,憑借其多元性、去中心化、深度削平等特征成為電影導(dǎo)演施加隱喻的重要場域,這些視覺符號(hào)的運(yùn)用以及電影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新都極大地調(diào)動(dòng)了創(chuàng)作者與觀者之間的主觀能動(dòng)性,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不同切面進(jìn)行了深入的思考。韋斯·安德森電影中也展現(xiàn)出明顯的后現(xiàn)代主義傾向,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精巧的結(jié)構(gòu)、程式化的風(fēng)格,現(xiàn)實(shí)與虛幻交織、嚴(yán)肅與荒誕共存,尤其通過深層化、重疊化的敘事手法,在深度和廣度上拓展了對(duì)時(shí)空關(guān)系的理解。
但由于其碎片化的鏡頭語言風(fēng)格,以及跳躍性的敘事節(jié)奏,使人們通常把觀看視角集中在結(jié)構(gòu)本身,而忽視了其中的情感內(nèi)核,它們雖包裹著戲謔的表象,但無不隱藏著情感關(guān)系中的失落與遺憾。在看似錯(cuò)綜復(fù)雜、雜亂無章的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中,韋斯·安德森也在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治愈著自我的缺失,以獨(dú)特的電影視角表達(dá)著對(duì)世界的脈脈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