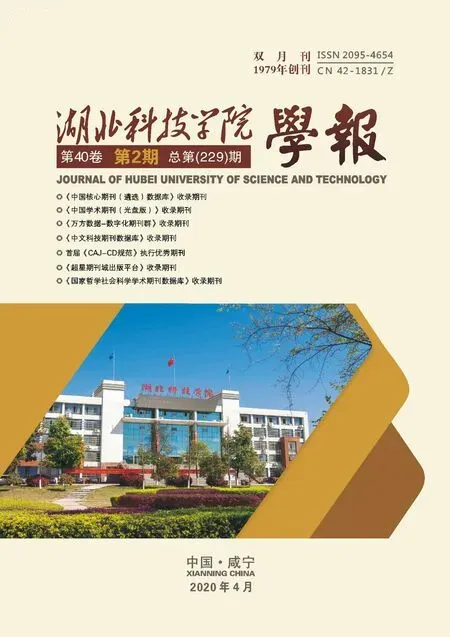辨析諸本,厘定史源
——評《千百年眼校釋》和《史源學視野下張燧<千百年眼>研究》
孫彩霞
(湖北科技學院 圖書館, 湖北 咸寧 437100)
《千百年眼》一書系晚明張燧的讀書筆記,共十二卷,500余個條目。在編纂體例方面,《千百年眼》著力會通,重視析疑;在內容風格方面,涉及歷史點評、史學評論、史實考證及史事敘述;在內容安排方面,以時間為序,由先秦到明代,貫通而作。張燧《千百年眼》刊出以后,因觀點新穎,敢于挑戰傳統思維,深受學人喜愛。在《千百年眼》的傳播上,從晚明迄今產生了各種類型的版本,版本之間亦有很多差異;在《千百年眼》的研究上,學界有一定的研究,亦有不少值得存疑之處。朱志先博士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開始接觸《千百年眼》一書,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十年的摸索探研,對張燧及其《千百年眼》進行了系統研究,并以《史源學視野下張燧<千百年眼>整理與研究》為題獲得湖北省社科基金資助,最終形成《千百年眼校釋》和《史源學視野下張燧<千百年眼>研究》姊妹篇,2018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細讀兩著,發現朱志先博士對《千百年眼》的整理與研究,在研究理路、史學價值方面頗有益于學界,茲略介紹其特點,以饗學界同道。
一、考辨諸本,校釋異同
《千百年眼》一書刊出后,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版本,其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甚至錯謬,不利于學界對《千百年眼》征引與研究。為使學界有一個相對完善的閱讀載體,作者以黃岡市圖書館所藏萬歷四十二年稽古堂本為底本,同時,參稽湖北省圖書館所藏萬歷四十二年本、四庫禁毀書刊中所收之萬歷四十二年本、日本明和四年擴充堂刊本、光緒十四年王惕齋銅版縮刻本、光緒二十八年清朱知雄校閱本、光緒乙已上海史學社印《重校本千百年眼》本、1921年上海進步書局本、《四千年史論驚奇》(《千百年眼》改名本)、1934年新文化書社印行樊爾勤校閱本、1934年大達圖書供應社印行周郁浩標點,沈芝楠校閱本、198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刊行賀天新標點本等,在詳細辨析各版本之間的差異、不改變底本正文的基礎上,將相關不同之處以頁下注的形式予以展示,對于能夠確證的則直接斷定,對于不能下結論之處則予以存疑,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清代印本《四千年史論驚奇》實際是張燧《千百年眼》的改名本,該書現藏于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對該書作者的著錄為“佚名”,這樣讀者很難知曉《四千年史論驚奇》與《千百年眼》之間的關系。僅北京大學圖書館顯示《四千年史論驚奇》作者為“張燧”,系民國文獻學家胡玉縉閱讀是書時予以校正。朱志先博士在查閱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四千年史論驚奇》時,將胡玉縉批注內容詳細過錄于《千百年眼》篇章的對應部分,這樣不僅便于學界了解《四千年史論驚奇》的真正面貌,同時,也有助于學者認識胡玉縉的校勘功夫。
198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賀天新標點本《千百年眼》,學界多征引此書。朱志先博士在校釋《千百年眼》過程中,通過不同版本的考索及史源考察,校正了賀天新標點本中一些不妥之處,如卷一《堯不誅四兄》“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族哉?”據蘇軾原文,“族”應為“俗”;卷一《帝堯善愛其子》“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本、黃岡市圖書館藏本、日本擴充堂本、王惕齋刻本,“痛”應為“痡”;卷一《井田不可行》“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本、黃岡市圖書館藏本、日本擴充堂本等,可知“所當周知也”與“農民每戶授田百畝”之間脫“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卷三《子胥、種、蠡皆人杰》“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釋也”,據黃岡市圖書館藏本及蘇軾原文,“釋”應為“擇”等。類似此種情況,朱志先博士通過不同版本的比對及史源考察,展示各版本之間的差異,并糾正了相關版本中的一些錯謬,為學界提供了一部相對完善的《千百年眼》研究載體。
二、厘定脈絡,析其傳播
萬歷四十二年(1614),《千百年眼》出版時,由晚明聞人鄒元標作序,鄒元標稱《千百年眼》寫的太精彩,“起古人相與論辯,亦必心服”“超天地而獨存”。光緒十四年(1888),浙江書商王惕齋在出版刊印《千百年眼》時,邀請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孫點為《千百年眼》作序,孫點贊譽此書,“縱橫十萬里,網羅美備,持論尤極平允。其抒寫心得,獨具只眼處,足令閱者驚其新穎,得未曾有。然核其事實,按之情理,并無一毫偏倚于其間,洵杰作也”。且稱此書在中原已難覓,是王惕齋在日本發現《千百年眼》,將其重版以饗海內。清代著名考據學家俞樾在《千百年眼·序》中言此書可與劉知幾《史通》、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相媲美。朱志先博士指出《千百年眼》所載內容觀點比較奇特新穎,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甚至將其列為禁毀書,加之鄒元標、孫點、俞樾等學人富有煽動性的序跋,使此書從晚明迄今,備受世人矚目。從傳播載體而言,《千百年眼》有二十多種不同的刊本;從刊載內容來說,有足本、節選本、改編本及小巧玲瓏的巾箱本。如此琳瑯滿目、形態各異的刊本,為《千百年眼》相關學術觀點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朱志先博士從傳播學的角度,在梳理《千百年眼》不同版本的基礎上,考察《千百年眼》在明清、民國以及該書在日本的傳播及其接受情況。乾隆年間,朝廷曾多次下令對《千百年眼》予以禁毀,但在當時士人周廣業的筆記《冬集紀程》中,可以發現其閱讀及評價《千百年眼》的內容,“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為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該括數年行止。后人誤認止為舍于逆旅。遂致異說紛起。有謂葬畢即求仕者。張燧《千百年眼》載許竹君曰: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其身乃不終喪于家。此說固謬。顧寧人謂為改葬。閻百詩謂終喪于家而后入齊為卿,并非。”朱志先博士指出“明清時期對《千百年眼》接受的形式是以抄錄其內容為主,說明這些學者熟識《千百年眼》之內容,同時又通過自己的著述,使《千百年眼》得以再傳播。其間亦有少量的評析(像胡玉縉進行系統批注的較少),褒貶不一”。
從1914到1935年,《千百年眼》先后由蔚成公司、進步書局、新文化書社印行、大達圖書供應社刊印七次,說明在民國時期《千百年眼》是非常受歡迎的。朱志先博士通過梳理,分析《千百年眼》的受眾對象,指出“《千百年眼》的受眾者,大概可分為一般讀者和研究者,在接受方式方面主要體現為:其一,抄錄與著錄;其二,征引與評析;其三,研究與創作。”像《滑稽時報》《讀史偶筆》《佛學半月刊》等期刊、筆記中對《千百年眼》的抄錄,袁嘉谷、劉咸炘、吳梅、顧頡剛等學人在著述中對《千百年眼》的征引和簡評,而聞一多、陳登原等學者將《千百年眼》相關內容靈活地融入到自己的學術創作中。對此種現象,朱志先博士論道:“從接受史的角度而言,此時期對《千百年眼》的接受可謂是層次高下、類型各異。有的著眼于抄錄其內容,有的潛心于研究其價值;有的是接受張燧其文而反對張燧其人,有的既接受其人又喜愛其文;有的是注明征引的明接受,有的是僅錄其文的暗接受,不一而足,各有千秋,構成一道《千百年眼》在民國時期傳播與接受的奇異風景。”
有關《千百年眼》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朱志先博士主要通過分析日本學者對《千百年眼》的征引、評析及研究,來考察其在日本的影響力。其中主要以林春勝、今關天彭為例,探討《千百年眼》在日本學界的接受狀況。通過朱志先博士這種梳理工作,有助于學界了解漢籍在域外的傳播接受情況。
三、史源考索,正本清源
陳垣先生在輔仁大學授課時,曾專門講授“史源學實習”課,讓學生對《日知錄》相關篇章進行史源學的梳理。陳垣先生這種史源考察,使我們明白在學術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中,注重考察史料源流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國傳統史料生成過程中,缺乏近代以來的學術表述規范,在相關史著中我們是難以直接發現其史料的淵源,自然也難以判斷哪些內容是作者本人的,哪些內容是作者征引他人的,在此境遇下,欲探求作者的學術思想或學術源流是比較困難的。
《千百年眼》一書是張燧的讀書筆記,是他在閱讀中對自己認為比較好的觀點予以完整摘錄,或者刪改選錄,很遺憾大部分內容沒有明確標明源自何處。從明清迄今,學人們往往被《千百年眼》中新穎的觀點所吸引,征引其內容,評判其價值,盛贊張燧學術水平之高,并以此來探求張燧之思想。朱志先博士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史源學方法,詳細梳理《千百年眼》中源自宋代蘇軾、蘇轍、羅大經、王楙、葉夢得、陸游、鄭樵、陳埴著述中的內容,以及《千百年眼》與明代學者楊慎、李贄、焦竑、王世貞、胡應麟、張大齡、陳繼儒、郎瑛等人著述之間關系,《千百年眼》中絕大部分條目,均被考出史源出處,并分析其原因所在。通過對《千百年眼》的史源學考索,使我們了解到《千百年眼》一書是如何生成的,在此情況下,為學界進一步研究《千百年眼》提供了有益參照。
像《千百年眼》卷一“堯不誅四兇”條、卷五“申公不知止”條、“霍光疏昌邑王之罪”條、卷六“晉室久亂”條等近十條是完全抄錄蘇軾之文而未予以標注。《千百年眼》卷二“季子之賢有定論”條、卷三“子胥、種、蠡皆人杰”條等八條是簡單刪改、節錄蘇軾之文。通過史源梳理,朱志先博士指出“張燧以其極具見識的學術眼光將宋人筆記、文集中的精彩部分予以節選、抄錄,并加以簡短醒目的標題,達到‘開卷而了然’的效果。不足之處,亦是張燧自相悖理之處,張燧力圖糾正明代‘影響剿襲,滿紙炫然’的文風,但是,《千百年眼》中有許多完整抄錄或刪節宋人著述內容,卻均未注明征引,頗為不妥”。有關張燧對明代學人著述的節選、完整抄錄和簡單刪改,該著通過分析,歸納其特點是張燧比較關注明代匯編、類編,而不是源自相關單本著作。以及張燧雖身處湘潭一隅,但對國內文人的著述是非常關注的。
通過朱志先博士對《千百年眼》的史源考察,使該書相關條目的出處展現無遺,有助于讀者明曉張燧是如何剪輯史料編纂《千百年眼》。同時,也使學界管窺到明人著述之一斑,在利用、探究明代史料時應該以審慎的態度對待,不能采取拿來主義。
四、悉述其瑕,未掩其美
《千百年眼》一書經過朱志先博士悉心考索,逐條辨析,其著述性質昭然若揭,并非傳統意義的著作,而是張燧按照時代順序,將自己讀書過程中所摘錄的內容予以編排整理。嚴格意義來說,這些內容絕非張燧獨創,當然不能憑借這些內容直接來分析張燧的學術思想。該著沒有僅僅滿足于對《千百年眼》內容進行簡單的史源考證,而是從探究《千百年眼》是如何撰成的出發,來發掘其編纂思想。進而根據《千百年眼》從刊出到當代的影響力,來分析《千百年眼》的學術價值。通過這樣系統全方位的考察,對《千百年眼》一書可以說是做到了指其瑕疵,而不掩其美。
張燧《千百年眼》雖屬于讀書筆記,并非雜亂無章的隨筆摘錄,而是依時代順序,由先秦迄明代,屬于貫通之作,亦即張燧在編纂此書時具有極強的編纂意識。朱志先博士指出張燧“所摘錄的條目,比較關注一些跨時代的內容”“用貫通的角度找尋歷史的相似點及不同點”,即張燧所撰書體現其“會通”之意;張燧“善于從紛繁蕪雜的史著中選擇出與眾不同的內容,即具有犀利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學術識見意識”;《千百年眼》中“所抄錄內容絕大部分是對已有問題之批判,諸如歷史批評、史學批評及史實考證”“不僅有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相關制度的評判,亦有對史家、史著之批評”,具有明晰的批評意識;作者還認為《千百年眼》中明代部分關涉到明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制度的批判、政治軍事方面的總結,“張燧讀書摘錄中對當代史的關注,是其經世意識的重要體現”。
在考察《千百年眼》編纂思想的基礎上,朱志先博士分析其學術價值在于卓越的史識,將眾多頗具見解的觀點匯聚一起。如其所言,“張燧在閱讀史著時,依據自己的價值評判標準,選錄及整理了大量敢于突破傳統的學術見解。隨著《千百年眼》在學界的廣泛流傳,這些原本存在于稗官野史中頗有見地的新解,自然也會隨之得以傳播”。像明代賀詳《史取》、清人杭世駿《訂訛類編含續補》、阮葵生《茶馀客話》、法式善《陶廬雜錄》、尤侗《艮齋雜說》等著述中,均有因襲《千百年眼》之文,“正是通過明清學人對其的轉相征引、抄錄在學界得以廣播,一定程度上對于促進相關歷史知識的傳播不無裨益”。還有,通過金毓黼、袁嘉谷、吳梅、顧頡剛等人的表述,朱志先博士指出學界對張燧研究方法的借鑒;通過《新刻七名家合纂易經講意千百年眼十六卷》《易經千百年眼》《四書千百年眼》《人相千百年眼》《家相千百年眼》等以“千百年眼”理念所命名的書籍,分析張燧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鑒識對學界的影響。
另外,朱志先博士在整理與研究《千百年眼》一書的過程中,并未囿于成說,敢于對已有觀點提出自己的見解。譬如,學界一般認為張燧晚年東渡日本,且卒于日本。他根據相關史料進行層層分析,認為張燧并未去過日本,且卒于家。還有,聞一多的《二月廬漫記》,研究聞一多的學者多認為這是他少年時期的奇文,朱志先博士通過史源學梳理,辨析《二月廬漫記》與《千百年眼》之間的關系,更有利于學界對少年聞一多學術思想的研究以及對《千百年眼》學術價值的認識。
當然,張燧在撰述《千百年眼》時,是如何擇取史料,以及《千百年眼》一書在日本學界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千百年眼》研究中尚需進一步挖掘之處。總之,如該著在余論中所言,“希冀通過對此書的整理與研究,使學界能夠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千百年眼》一書的價值,且能以此為個例,在研究學術思想史、史學史時盡量多考慮一下資料的史源問題。盡量避免由于忽視對史料的考據,而導致一些史學研究走入誤區,出現一些不必要的失誤”。誠然,朱志先博士對《千百年眼》一書系統的整理與研究,解決了《千百年眼》研究中的諸多問題,頗有益于明代學術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