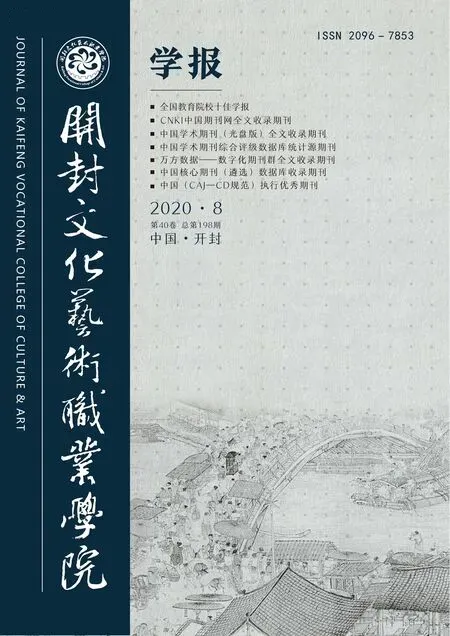論李進祥“清水河” 系列小說的美學意蘊
張一博
(北方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李進祥身為寧夏作家,對風土人情溫情書寫,昭示浪漫主義情懷;對故土深情回望,暗含堅守苦澀,流露對民族文化的眷戀。清水河、河灣村等地域文化符號,口弦、挦臉、花兒、方言等民俗文化符號,在小說中大量涌現,充實文本容量,豐富敘事空間,建構多元共生的審美世界,展現西北鄉土社會全方位景觀,凸顯地域文化特質,多重意象使地理空間成為隱匿人物情感的載體,豐富文本美學價值。
李進祥小說中鄉村與都市空間不斷切換與重組,展現出復雜文化屬性與多重審美意蘊,兩個富有對立意蘊空間的推進與轉移使文本跌宕起伏,讀者由單一地域空間達到審美空間維度,利于把握作者內在心理格調與美學追求。且小說中多元的敘事視角與精妙的敘事結構相互契合,共同賦予文本復調魅性與特異美學價值。
對異化倫理的憂慮與反思、對傳統家園的重建與守護、對傳統美德的呼喚與回歸,是李進祥小說的精神主線。筆者將從對美學意義的界定及發展歷程入手,分析文化符號隱喻的特異審美功能,探究美學形象在現代美育中的重構,挖掘李進祥小說中的美學意蘊,揭示其獨特審美取向,彰顯地域文化審美特色,使邊緣文化重煥生機。
一、美學意義的界定及發展歷程
柏拉圖的發問“美是什么?”,可謂美學濫觴。古代思想家對美與藝術在哲學層面的思考,可看作美學理論的萌芽。美學源于古希臘語“aisthetikos”,即“感官感受”, 由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首次提出。他的《美學》標志著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因此,他又被稱為“美學之父”。伴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誕生,美學研究開始有系統的方法論指導,但建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仍很漫長。
我國美學傳統淵源已久,但部分理論卻借鑒西方。學者認為:“如果五十年代美學浪潮在極左政治意識形態中產生,以知識分子啟蒙思想改造完成總體化規訓進程;那八十年代美學熱表征市民社會自我反思與文化啟蒙的‘解總體化思潮’,市民社會普世性與自由性文化訴求通過知識分子重拾話語權與美學從邊緣到核心進程,完成一次較大規模知識啟蒙。”[1]如今,我國美學研究日益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實踐美學為主流的當代美學體系,代表學者為朱立元教授。總之,美學是一門探究美的創造、發展與規律的學科,類屬哲學,被稱為“美的藝術的哲學”。
二、文化符號隱喻的特異審美功能
(一)地域文化符號隱喻的美學意蘊
李進祥在《永遠走不出的清水河》中寫道:“走不出清水河,像走不出一段愛情;走不出清水河,像走不出一種宿命。”[2]12“清水河”“河灣村”“克爾白”等地域文化符號別具韻味,呈現整體性與開放性地理結構,反映作者對地域身份認同。城鄉對立矛盾下,內隱作者渴望回歸鄉土、實現精神返鄉的情感訴求。
意大利哲學家維柯首次提出“詩性地理”概念,宣告地理并非客觀衡量與自然空間的物態現實,或僅對文化起外在承載、形塑的作用,而是其本身就充斥詩性、文學性與審美性,是人工打造的完美形式。受地域影響,李進祥的“清水河” 如同馬金蓮的“扇子灣”、查舜的“梨花灣”、漠月的“阿拉善”。不同地域元素蘊含著作家熱愛家園的共同情感,賦予作家寫作性靈與底氣,嵌入底層人物生存狀態與精神維度,張揚生命活力與圓融,以可視化空間形態闡釋文學規律與文化意蘊,形成文本內蘊審美張力。
李進祥引領讀者走進西北地理空間,感悟特色文化,探究作品美學構成與藝術形態,彰顯了民族精神的時代意義,實現了寧夏文學去邊界化。地理文化符號融入作者情感寄托與審美理想,具備顯性象征內涵,對文本人物塑造、情節推動與情感表達均有顯著的意義,還建構起西海固獨特的地理空間,是寧夏詩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民俗文化符號隱喻的美學意蘊
挦臉、花樣子、干花兒等詞語攜帶泥土氣息,極具審美韻味,共同建構小說內部世界,豐富了西北文化內核,健全了審美機制,形成與清水河等意象匹配的文學地理意義上的身份標識。
《口弦子奶奶》中的樂器口弦,發出悠長嗚咽聲音,極具感染魅力;《挦臉》中的習俗挦臉,又叫開臉,即一種女性結婚前的儀式。飲食文化元素在小說中也時常涌現,如蓋碗茶、八寶茶等傳統飲茶風俗,也有油香、撒子、羊肉臊子面等地方特色美食。
小說方言也具民俗色彩,如害娃娃指女人懷孕,害口指孕婦口饞。方言不僅是文化傳承媒介,也是解讀民俗的重要符號,可以折射出說話人的婚姻觀、人生觀、價值觀。瑞典語言學家索緒爾說過:“民族風俗習慣會在語言中反映;另一方面,構成民族的也正是語言。”[3]58中國現代民俗學家王獻忠也說:“方言是地區民俗載體,方言研究對把握各地文化獨特性深層結構,有很大幫助。”[4]26
民俗文化符號不僅是文學書寫中的別致色彩,而且也為歷史提供素描,流露了特異美學情調,體現出地域文化的內在獨特性,異質文化通過民俗差異得以彰顯。同時,深受民俗文化基因浸潤的文本充斥野性生命力,煥發蓬勃生機,使民俗文化在現代化場域中發揮審美魅力,帶給讀者新奇審美體驗,易受大眾追捧。
三、美學形象在現代美育中的重構
美育又叫審美教育。德國著名哲學家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首次提出全面美育理論,從此,美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并開始影響到各國的美育理論。后來,我國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這對培育新時期以來的人文精神有助推作用。而德國哲學家康德說:“純粹審美判斷不是知性判斷,而是主觀愉快情感體驗,強調美的個體性,審美自由與審美無利害。”[5]71中西方異質話語因子孕育迥異美育理論體系,相互借鑒之下使美育學科臻于完善。而我國現代美育的發展自從進入新時期以來,便始終立足于中華五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同時積極借鑒西方美學文化藝術資源,完善本民族的審美品格,提升本民族審美境界,使美育學科呈現良性發展態勢。我國美育學科的發展除了從傳統文化尋根與對西方美學的積極借鑒,還得益于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李進祥立足西北地域的特異文化語境,通過對審美意象再發現,賦予其全新的藝術價值。讀者借審美意象從物質與精神壓迫中釋放出來,獲得審美愉悅,更好展開審美欣賞,從而在熏陶中獲得靈魂健全與人格完整,成功發揮文學美育功能,促進當下人文精神建設。讀者從現代化擠壓的都市空間中暫時抽離出來,獲得短暫的休息。他還通過塑造馬清、楊潔等人物群像,傾情書寫鄉村人倫,呼喚傳統美德回歸,發出渴望建設“美的人生” 的情感訴求,對真善美的迫切渴望彰顯出作家的普世情懷,借此完成一系列美學形象在現代美育中的重構,對中國夢美好藍圖的實現有極強現實意義。
結語
地域與民俗文化符號均體現出西北文化的獨特魅力,彰顯了民族文化的顯性時代價值。李進祥對地域身份認同感使小說深深扎根大地,帶著濃厚泥土氣息與厚重文化底蘊,蘊含飽滿的情感張力,鄉土意識在文本中的流露已十分明顯,極易喚起大眾內心深處潛藏的對故土極強的情感認知。
李進祥借“文學返鄉” 情懷建構“清水河” 原生態詩性家園,目的在于擁抱大地,更好實現人類在大地上詩意的棲居,使人在自然生命敞開中走向審美化生存,同時促進現代多元文化視野下鄉愁美學的生成,體現出小說新奇美學情調,使文本煥發出全新審美特性。
李進祥對西海固鄉村詩意空間的建構帶給大眾愉悅的審美享受,喚起都市之子久違的家園意識情感共鳴,進而拉近讀者與文本的距離,使小說超越了地域局限而引起普世情感共鳴,即身處都市卻思念故土的情感,從而使文本的情感濃度一度達到飽和,文本張力也達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