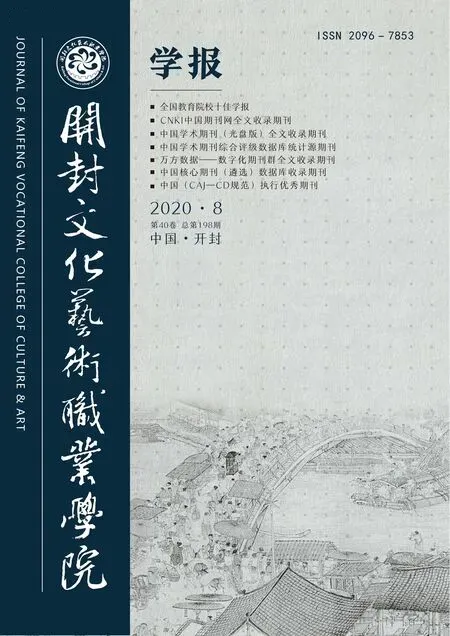自由間接引語“雙重聲音” 的認知語用分析
劉慧云
(廣州工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0850)
轉述者在被轉述話語中經常借用或保留被轉述者的視角,制造一種雙聲效果。這種“雙聲” 現象在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FID)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他明天會回來再次看望她(He would come back there to see her again tomorrow)。按照傳統語法, 該例中近指動詞“ 回來”(come back) 本 來 應 該 是“ 返 回”(return),“ 明天”(tomorrow)應該是“第二天”(the following day),但是,轉述者顯然借用了被轉述者原話的動詞和指示詞同時表達了兩者的視角,從而造成“雙聲”現象。對此,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且主要圍繞FID 的句法特征展開,對于其認知成因和語用意義卻鮮有提及。
一、FID“雙聲” 現象的認知理據
FID 的“雙聲性” 是 FID 的重要特征。就句法特征而言,FID 以第三人稱指代人物并采用過去時敘事,但沒有引導句。因為擺脫了引導句的束縛或出于某種語用目的,這一形式常常保留體現人物意識主體的語言成分,從而構成“雙聲” 效果。就其本質而言,FID 是半敘事半引語的混合體:在敘述過程中,敘事者有意放棄自己的敘事風格,轉而采用具有小說人物個體色彩的語言形式,形成一種看似某個人物的所思所想,實為敘述者話語的語言現象。FID的“雙聲性”反映了模仿的本質。在柏拉圖《理想國》第3 卷中,蘇格拉底把言語表現方式分為兩種:描述與模仿。描述是詩人用自己的言詞來轉述人物的話語,而模仿是直接展示人物話語。在模仿中,“詩人努力創造一種不是他在說話的幻覺”“一篇敘事作品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創造一種幻覺,一種效果,一種貌似‘模仿’的假象”[1]194,而這種模仿事實的幻覺是文本通過最大限度信息和最小限度信息的提供者才得以創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FID的“雙聲性”反映了模仿的本質。FID 的“雙聲性” 是敘事虛構作品文學性的最佳體現。Hawkes 認為,“文學性”是指文學作品特具文學價值的非指稱價值[2]71-73。從一般意義上講,FID 的文學性在于它在文學作品中較其他形式的語篇更常見,起到更關鍵作用。“或許是因為說話者難以口頭表現出FID 所特有的多聲并存這一特征,這種現象才似乎更適合于不出聲的書寫者。”[3]從學術意義上講,有學者把FID 的“雙聲性” 視為敘述虛構作品的主要特征。Bakhtin認為,長篇小說的中心傳統是由多聲(對話體)而不是單聲(獨白體)敘述文本構成的。這種多聲性既是通過并置文本自身的幾個聲音,也是通過在文本中“融入” 敘述話語獲得的。從這個角度講,FID似乎是一種更大的跨語言現象,其中各種不同聲音的共存創造了文本內部的多聲(復調)性,而說話者的語言音域的保留則是敘事話語與已存話語發生聯系,由此創造出文本之間的多聲(復調)性[1]208。就讀者來說,“雙重聲音” 是讀者在特定的文學語境中對語篇成分解讀的結果。閱讀現象學認為,文本相對于讀者來說必須達到兩個目的:其一,它必須肯定自己將被閱讀;其二,出于自身的利益必須延長讀者的理解過程,以保障自己的生存。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它會引進一些讀者所不熟悉的成分,增加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事實上,在FID 中,敘事話語與人物話語的界限有時確實難以分清,然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增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好奇心,延長了閱讀過程,幫助讀者能動地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
二、FID“雙聲” 現象的語用理據
任何話語行為都是有特定交際目的、交際對象、交際時間、交際地點等語用因素的創造性行為。“轉述是一種重復性行為,是轉述人在異時異地最大限度地模仿說話人的話語的行為。”[4]Leech 認為:“FID是由作者(敘述者)聲音介入讀者和小說人物話語之間的一種較自由的話語形式,使讀者與人物話語之間拉開了一段距離,容易產生譏諷或詼諧的效果。”[5]334也就是說,“ 敘述者在采用FID 轉述原話語信息意圖的同時有向受話人表明自己還有傳遞這種信息意圖的意圖,即交際意圖”[6]64。例如:
“那么,我認為,” 沃爾特先生說,“他的臉色大概和我侍從的護腕和坎肩一樣桔黃啦。”
謝潑德先生趕緊向他保證說,克羅夫特將軍精神矍鑠、身體健壯、相貌堂堂,只不過他的皮膚確實有點粗糙,但也不會太過分;他具有紳士思想,行為舉止彬彬有禮。在條款上他不會跟您設置障礙,-- 他只想有一個舒適的居所,能盡快住進去。-- 他知道,他得為便利付出代價;-- 知道一所配有家私的豪宅需要多少租金。-- 要是沃爾特先生一開始要價再高點,他也不會感到奇怪。-- 他問了宅邸的情況,-- 稱如果能狩獵就再美不過了,不能也無所謂。-- 說有時他會拿出槍來,但從不殺生;-- 真是個紳士!
——(簡·奧斯汀《勸導》第三章)
謝潑德先生是一位律師。對于卑恭順從的公務員謝潑德先生的話語,簡·奧斯汀一開始采用間接引語形式,然后通過省略從屬連詞和從句主語很自然地滑入FID。這里的口語體詞匯,尤其是這位小題大做的律師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紳士” 這一詞語以及連續使用的破折號等都是FID 的句法特征。在這里不僅有敘述者的干預,也有原話語的獨特風味。這位律師啰啰嗦嗦說了一大堆褒揚克羅夫特將軍的話,其信息意圖貌似在迫不及待地向人擔保他的為人,而其實際語境效果是讀者和謝潑德律師之間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疏遠了彼此,因而達到了說話者的交際目的:讀者有足夠的時間以旁觀者的眼光來充分體味人物話語的荒唐以及敘述者的譏諷。在這里,我們能夠領會作者的交際意圖:謝潑德律師這么做完全是為了他自己。
FID 的“雙聲性” 不僅能達到反諷的效果,也能激起讀者對人物的同情,增強語意密度。例如:
她不能回家;艾瑟爾在那兒。會把艾瑟爾嚇壞的。她不能坐在任何地方的長凳上;人們會過來問她問題……天哪,難道就沒有地方供她藏身,讓她盡可能長久地獨自呆在那兒,不打擾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擔憂么?難道這世上就沒有任何她終于可以嚎啕大哭的地方么?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帕克媽媽的一生》)
這是故事的結尾。帕克媽媽悲痛中倉皇離開文人的寓所來到街頭,再也不能自制,想痛哭一場,結果發現自己無處可去。這段話的信息意圖是:帕克媽媽辛勤勞作了一輩子,其悲涼的結果是在這大千世界中,竟然沒有一寸屬于她的土地。作者使用FID 轉述善良的帕克媽媽無助、無奈又絕望的心情。作為讀者,不難領悟作者的實際交際意圖:難道我們沒有聽到帕克媽媽的祈求、控訴與哀怨么?難道我們沒有感受到敘述者因這位老婦的悲慘境遇而憤憤不平么?難道不能喚醒我們對這位老婦的同情與憐憫嗎?
結語
FID 是小說家追求與模仿外在真實、內在真實以及內在真實與外在真實相融合這一過程的產物,而“雙重聲音” 是FID 帶給讀者的獨特閱讀體驗。在FID中,通過將敘述者目光和聲音附著在人物身上,小說家巧妙地實現內在世界與外在現實以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的互動。這種語言現象反映了人類語言中主觀與客觀、內在與外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限在某種程度上的化解與消融。研究FID 有助于了解人類如何有效利用語言來展示現代人內在感受的復雜與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