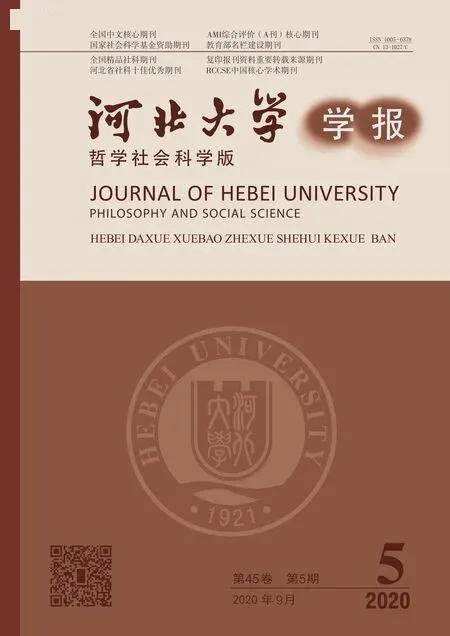章太炎對文學家魯迅及《狂人日記》的深度影響
郝 雨,田樂樂
(上海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上海 200444)
魯迅先生逝世之后,陳子展于1937年發表過一篇懷念魯迅的文章,其中追溯章太炎與魯迅的淵源道:“以章太炎代表進步的封建知識分子,作為其中一個殿后的人物;以魯迅代表激進的新興知識分子,作為其中一個先驅的人物;師弟兩人各代表過渡時代的一端,可以看出時代承前啟后的關系,好像歷史先生有意如此安排,這倒是很有意味的事情。”[1]179從章太炎的時代到魯迅的時代,這其中的曲折,確實是近代史研究中一個能以小見大的可貴案例。本文便欲從章太炎與文學家魯迅及其名作《狂人日記》的關系入手,考察新文化運動諸問題。
一、融會中西:1908年及之前的章魯師弟
近世以來,西學東漸。特別是晚明以降,以利瑪竇、徐光啟等人的文化碰撞為代表的中西哲學融會日益成為潮流[2]。至于清中期,這種融會的思想便十分成熟了,如章太炎祖父的經算老師,生于乾隆年間的項名達[3]18,其治學便“以推見本原,融會中西成法,以通其變,竟未竟之緒,發未發之藏為歸旨”[4]。在融會中西學術思想的基礎上加以超越,寓世界文明建設于中國建設,是近世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一大潮流。
晚清以降,國難日重,有識之士,如潮競起,援引西學,蔚為風尚,至于融會中外,超邁前圣,于近代諸人,已經不在話下。章太炎、魯迅所活躍的19晚期、20世紀初期,西方哲學流行的是從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到海德格爾的文明反思;至于東亞,也因為正處在危亡之際而興起了自我文化的批判,這兩種批判的合流,形成了人類史上一個大的文明批判浪潮。這個浪潮具體到中國,再具體到章太炎、魯迅,就是二人在批判中國禮教的時候,常受當時西方文明自我反思思想的影響,而將思維逸出,連著西方文明一同加以批判。這在魯迅,表現為他所說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5]57。在章太炎,則表現為他從批判宋儒的天理始,一直貫通到批判當時的公理:“驟言公理,若無害矣。然宋世言天理,其極至于錮情滅性,烝民常業,幾一切廢棄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飲食之事,放任無遮,獨此所以為異。若其以世界為本根,以陵籍個人之自主,其束縛人,亦與言天理者相若。”[6]
我們把這種立足于中國禮教批判而衍出人類文明批判的事實,總結為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
上面說的是形成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思想的大環境,繼續深入到章太炎、魯迅自身,我們接下來將探討二人形成這種取向的自身原因。
1903年,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直到1906年出獄,他讀了三年的佛經,出獄之后,他又有選擇地接受了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佛教對于世俗的批判,加上無政府主義對于人類文明的整體性反思,使得章太炎迅速地投入到禮教批判、文明批判之中。從1906年的《俱分進化論》開始,章太炎相繼發表的《無神論》《建立宗教論》《代議然否論》《人無我論》《五無論》等一系列文章,集中體現了其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的思想。在這之后,章太炎又將莊子哲學引入到批判思想之中。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章太炎是在1908年1月寫就、1908年4月25日發表的《無政府主義序》[7]中最早引入莊子齊物思想的,此后,章太炎快馬加鞭,1908年8月間,他又給魯迅等一眾學生講授《莊子》[8]170,講授內容經過整理發揮,就是后來出版的《莊子解故》《齊物論釋》①從章太炎在《莊子解故》序言中說的:“微言幼眇,別為述義,非《解故》所具也。”(見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莊子解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頁)一句話可以看出,《莊子解故》與《齊物論釋》是訓詁、義理的姊妹篇。。
《齊物論釋》是章太炎融會齊物哲學與佛教哲學②章太炎的佛學思想,根基是唯識宗、華嚴宗、禪宗,見郭朋、廖自新、張新鷹《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巴蜀書社1989年版,第354-392頁。而發的禮教、文明批判。章太炎之所以會借鑒莊子的齊物哲學,是因為莊子哲學與其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的思想路徑十分吻合。
比如《莊子·齊物論》中對于文明社會過分執著“言”“是非”而忽略“道”這一行為的批判,從當時的歷史來看,就是針對儒墨等家而發的[9]56;而莊子對文明社會所下的“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這一斷語,則是針對公孫龍子的指物論而來的[9]58-59。莊子常從對儒墨禮教的批判出發,衍為對于文明社會的批判。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儒墨禮教本身就是文明在一個階段的具體形態,禮教帶有文明社會的普遍性,所以章太炎才會說莊子“遠睹萬世之后,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而今適其會也”[10]3。莊子當然不是預言家,是文明與禮教的關系決定了其思想的超越性。
禮教是文明的具體形態。禮教批判,能使思想獲得在地性,即深深扎根于當時的歷史;而文明批判,則使思想獲得超越性,使其千載之后,依然具有活力。能實現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需要有大的見識,莊子有這個見識,章太炎有這個見識,其學生魯迅,也有這個見識。
從魯迅1907年、1908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中,都能看到其追蹤中西文化潮流,對中西文明所作的批判。至于這種批判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響,從魯迅逝世之前還在念及“俱分進化”、章太炎主持的《民報》等事可以看出,他是受了章太炎極大影響的③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載《魯迅全集》第六卷。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憶自己并不是愛章太炎的“俱分進化”,這是不可信的。魯迅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支持當時的革命而做的曲筆。比如他又說章太炎講的《說文解字》,他一句也不記得了,但事實卻是,他是認真做了筆記且精心保存的,參見《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具體說來,魯迅在《河南》上發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都與乃師章太炎的關系相聯[11]9-13,并且,這三篇文章從文風到內容,都受到章太炎深刻的影響[12]210-215。
至此,可得出一個結論: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是章太炎、魯迅師弟一以貫之的思想路徑。
二、會館魯迅的轉識成智與文學家魯迅的誕生
1912年5月6日,魯迅住進山會邑館(即后來的紹興會館)[13]1,一直到1918年《狂人日記》發表,這一段會館時期,被稱為魯迅生平“最弄不懂的部分”[14]45,竹內好便以此一階段為核心,構建了他影響深遠的“竹內魯迅”。竹內好認為,會館時期,魯迅形成了一生的主軸,他把這一時段沉默的魯迅看作“黑暗”;他認為魯迅在這黑暗中“自覺”——自覺有罪;他把這種黑暗與自覺叫作類似宗教性的“回心”;一以貫之地,他把魯迅的文學叫作“贖罪的文學”[14]45-46。
竹內好十分敏感,他覺察到了會館時期對于魯迅一生的重要意義,但是對于他所說的諸如“回心”“罪的自覺”“無”等等,總的來說,實在有些“玄學化”[15]181了。我們認為,會館時期確實是魯迅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但是其思想內容既不是“回心”,也不是“罪”,而是一種對于1908年之前所接受的知識的反思、沉淀、超越,我們把這種反思、沉淀、超越叫作“轉識成智”。
之所以給它命名為轉識成智,并不是故弄玄虛,這與魯迅此一時段的思想事實密不可分。如果不想使此時期魯迅的研究流入“玄學”(這里的玄學,義為空想,并不是魏晉玄學),最好的方法是考察能反映魯迅思想的日記與書賬。
查魯迅的書賬,他來北京后所買的第一本書是章太炎的《齊物論釋》[13]37,而且,從1912 年到1924年,魯迅書賬里只出現過兩種時人的思想類著作,分別是1912年購入的《齊物論釋》以及1913年購入的楊文會的佛學著作《等不等觀雜錄》[13]95。由此,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會館時期的魯迅仍然在延續著他對章太炎的學習,從《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到聽章太炎講課,再到學習《齊物論釋》,這是個一以貫之的過程。因此,我們就可以回答魯迅為什么在這段時期大量讀佛經、老莊了①從1912年到1924年,魯迅的書賬里,思想類作品,幾乎完全都是釋典與道家經典,見《魯迅全集》第十五、十六卷。——因為不深入莊子哲學、佛教哲學,魯迅便無法真正理解并超越他的老師章太炎。
通由章太炎這架橋梁,魯迅深入到了佛學與莊學之中,這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飛躍的契機,這就是轉識成智。
“轉識成智”,是唯識宗的理論。它指的是“由以分別為主、由‘我執’‘法執’的意識活動,轉變成為如實理解的無分別、無執著的智慧”[16]411。從普遍意義上講,轉識成智表達的是認識過程由知識到智慧的轉化[16]412。具體說來,知識,指的是對世界加以區分、分別并在此基礎上使用命題加以陳述的名言之域,而智慧,則是“有關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認識,關于性與天道的理論”[16]412-413。從知識到智慧,是認識過程的飛躍,它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知識作為基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對性與天道的探索中超越名言領域的知識,去領悟那貫通整個宇宙的無所不通的“道”。當人能夠開始獲得智慧,便能夠達到一種“理性的自覺”[16]420。這種理性的自覺,表現為一種在理性光輝照耀下的豁然貫通之感的直覺,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無論小大精粗,行動坐臥,種種直覺的、自發的行為都能夠達到一種與人的理性相符的境地。宋明儒者在這方面很有經驗,不妨征引一些例子:
仆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圣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冊書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后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圣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茲乎!”[17]83-84
以上是明儒陳白沙的自述,他的認識便經歷了一種從大量獲取知識到領悟性與天道的過程,最后陳白沙顯然是獲得了智慧。他獲得智慧之后的境界就是日用間種種行為都能夠與理性相符,同時,他的智慧也將他此前的知識融會,實現了一種對世界的整體、大全而非條理的把握。
上面我們說到,知識是分析、區別,是通過命題加以陳述的名言之域,那么,智慧能不能用名言表達呢? 歷史上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回答,而對于莊子來說,他認為世界不能通過名言領域的知識加以把握,只能通過智慧領域的詩與寓言加以暗示[18]220-222。即不通過條分縷析去說教,而將道理寓于藝術形象之中去啟迪人,使人自悟,從而獲得屬于自己的“作圣之功”。
通觀魯迅的創作,他1912年之前的作品,無論是科學知識論述、政論,還是文藝理論、譯作,幾乎全部是知識,沒有達到智慧的境地。而會館時期通由莊學與佛學對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探討,則能將魯迅接引到研究性與天道、通達智慧的道路上去。魯迅的成長過程便十分符合莊子的思想:不同于1912年之前以知識的形式把握世界,從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開始,魯迅一直都是以“文學家”的面貌用詩、寓言、小說、雜文等審美形式去把握世界的,而他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又無一不帶有深刻的哲理,我們也常能從他的文學中獲得啟迪。
能將文學與哲理結合起來,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能達到莊子與魯迅似的境界,則非有大智慧不能為之。千年前的莊子不能“預言”魯迅的成長,魯迅的成長只能反證出在此時段內他確實通由學習釋道思想經過了一個轉識成智的過程。
佛學與莊學對于終極原理的探討,使得會館時期的魯迅得以沉淀、超越他此前所獲取的知識,逐漸實現他的轉識成智。這種智慧使魯迅開始能夠實現對于宇宙與人生的整體、大全式的把握,也使得魯迅開始成為一個能以“詩”把握世界的人。文學家魯迅,就在這里誕生。
三、《狂人日記》與莊周夢蝶
這里需要再次強調一下,魯迅的轉識成智是追隨著章太炎而來的,是對此前所遭遇問題的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就是對禮教、文明的批判。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魯迅的自述以及受其影響的相關研究大多只關注反禮教的一面①魯迅的自述,參見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載《魯迅全集》第6卷。相關研究,以王富仁先生的研究最有代表,參見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特別是對《狂人日記》的相關闡述。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從大環境來說,與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過分重視外來文學影響而忽視“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19]233-272的研究方法有關。這種忽視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批判精神往往只能局限在中國,具體到魯迅,就是只局限在中國的禮教,而缺乏與世界文學的真正對話。從魯迅個人來說,新時期以來,他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野草》,思想內涵研究都有很大的拓寬,這一方面是因為魯迅在《野草》中傾注了他幾乎全部的詩學與哲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野草》表意模糊,易于發揮。但是魯迅的一些指向性明確的小說、雜文,思想內涵研究就很難擴大。比如,從1978年嚴家炎的《<狂人日記>的思想和藝術》[20]到2015年解志熙在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研討會上的發言[21],大約40年間,研究者對于《狂人日記》的關注點一直集中在禮教批判,中國的禮教批判。我們知道,魯迅早期的文章,強調“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即在對于中西文明的損益中建設中國,這種視野如此宏大,難道在魯迅回國后的作品,在《狂人日記》中沒有體現么?
我們的回答是:有。魯迅自己其實已經有過透露:“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22]247魯迅的這句表白說得十分清楚,他是將尼采等人對于文明的批判落實在中國的禮教上,這就是我們說的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
這種思想傾向集中體現在《狂人日記》的材源上。長久以來,研究者對于《狂人日記》材源的梳理都集中在外國文學上①汪衛東《<狂人日記>影響材源新考》,《文學評論》2018第5期,第52-57頁,及汪衛東、何欣潼《魯迅<狂人日記>與莫泊桑<奧爾拉>》,《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9期,第22-24、32頁。而忽略了中國方面,特別是魯迅認真學習的莊學、佛學以及章太炎的思想。以下我們來探討魯迅對于這些思想的吸收。
(一)《狂人日記》的狂愈主題對《莊子》夢覺主題的吸收
“夢”是虛幻的,它與現實世界相對,因此常被批判現實的思想家借來比喻“現實”的虛幻性,而“覺”則用來比喻了悟虛幻現實之后的狀態。比如我們熟悉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便是顯例。在中國,癲狂病因與夢同樣具有非現實的品格而經常被類比為夢,比如清代名醫王清任的著作《醫林改錯》中治癲狂癥的藥方便叫作《癲狂夢醒湯》:“癲狂一癥,哭笑不休,詈罵歌唱,不避親疏,許多惡態,乃氣血凝滯,腦氣與臟腑氣不接,如同作夢一般。”[23]59由莊子肇始的“夢覺”主題與后世的“狂愈”主題在中國哲學中本是一脈相承的。
莊子使用夢覺主題來批判禮教及世俗文明,精研莊學的魯迅所創作的“狂人”形象對此便有繼承。我們可以提供證據如下。
莊子在《齊物論》中批判儒墨所代表的世俗文明過分在乎利害、生死而忽略大道,他便將世俗文明比喻為夢:“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9]87。夢中哭泣,醒時反而高興,做夢之時,人不知道自己在做夢。狂人病時發狂,愈后做官。發狂,如同做夢,病愈,如同夢醒。
“夢之中又占其夢,覺而后知其夢也”[9]87。莊子認為世俗之人不斷發展自己的文明,其實不過是夢中做夢而已,只有真正夢醒了,才會恍然大悟。狂人發狂,發現他人吃人、歷史吃人,這在“大哥”等人看來,已經不可思議,但是狂人竟然還能繼續發現自己兄弟吃人,乃至自己也吃人。這狂中之狂顯然是對夢中做夢的借鑒。
“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9]87。莊子認為,只有真正覺醒的人,才會知道世俗文明乃是一場大夢,有些愚者自以為覺醒,其實不過是繼續做夢罷了。這些愚者的所謂覺,不過是遵守君臣禮教而已。因此世人皆夢,說別人做夢,其實不過是自己也在做夢。狂人發狂,世人皆說狂人發狂,但是世人遵從那禮教,才是真正的發狂;狂人病愈,狂人與親友都覺得是病愈,其實不過是回歸禮教,這仍是在發狂。狂人病愈,便去做官,這就是莊子說的“君乎,牧乎,固哉”。沒有真正的大覺,無論狂人是狂是愈,旁人覺其狂覺其愈,都只是在發狂、做夢而已。
(二)“大覺”思維與“救救孩子”
既然世俗文明中人無論是夢是覺,都只是在做夢,那難道就沒有解脫的方法么? 莊子的回答是,“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9]87。只有大圣的大覺,即對文明社會作徹底的反思,才是真正的覺醒。這種“大覺”類似于頓悟,也即對自我做徹底更新。
魯迅受此“大覺”思維影響十分之深。比如《狂人日記》的結尾,魯迅便認為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人,大家身上都帶著吃人的罪惡,因此最后只能呼喚救救孩子。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也說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魯迅為什么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自己就可以到光明的地方去,非得把希望放到孩子身上呢? 這種呼喚孩子的主題,一方面來自老子的“復歸于嬰兒”(《老子》王弼本第二十八章),另一方面來自尼采的“精神三變”,莊子則把這種狀態稱作“吾忘我”(《莊子·齊物論》)。
孩子在這些哲學家以及魯迅這里,都是一個象征,他象征著一種覺醒,意味著徹底忘卻、超越此前的自己,回歸一種純潔的心靈,即將展開一種重新開始。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狂人日記》的材源一大部分來自莊子、老子、尼采的思想。這些思想,統統指向對于人類文明的批判,期待一種文明的重新開始,魯迅則把它落在禮教批判之上。并且,《狂人日記》結尾所呼喚的真人、純潔心靈、文明的重新展開,完全可以適用于任何文明批判中,這已經不是禮教批判所能牢籠得住的了。
(三)吃人與心斗
對于文明批判,還有一點證據,那就是魯迅對于章太炎以及佛學的繼承。“吃人”是《狂人日記》十分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直接來源于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章太炎為了說明世界是善惡、苦樂同時進化,便指出人類文明的本質之一就是“吃人”:
虎豹以人為易與而啖食之,人亦以牛羊為易與而啖食之。牛羊之視人,必無異于人之視虎豹。是則人類之殘暴,固與虎豹同爾。虎豹雖食人,猶不自殘其同類,而人有自殘同類者。太古草昧之世,以爭巢窟競水草而相殺者,蓋不可計,猶以手足之能,土丸之用,相抵相射而止。國家未立,社會未形,其殺傷猶不能甚大也。既而團體成矣,浸為戈、矛、劍、戟矣,浸為火器矣,一戰而伏尸百萬,蹀血千里,則殺傷已甚于太古。縱令地球統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謀攻取者,必尤甚于疇昔。何者? 殺人以刃,固不如殺人以術,與接為構,日以心斗,則驅其同類,使至于悲憤失望而死者,其數又多于戰,其心又憯于戰,此固虎豹所無,而人所獨有也。[24]3
章太炎認為,虎豹作為動物尚且不吃同類,而自詡文明的人類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自相殘殺。禮教本身即是文明的一個具體歷史形態,魯迅對于禮教吃人的控訴來自章太炎對于人類文明吃人的批判。
不僅如此,章太炎還指出,相比遠古時期真刀真槍地相殺,文明社會“吃人”的方式是“心斗”——這來自莊子的思想。魯迅在《狂人日記》第七節中也說: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掛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愿,自然都歡天喜地地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幾下。[25]449
魯迅此處所描寫的“羅網”與“自戕”顯然就是對于莊子、章太炎“心斗”思想的繼承。
吃人與心斗在章太炎那里,是對人類文明的整體批判,魯迅則把它們落在禮教上。而且,章太炎認為重建文明的方法是:
世有勇猛大心之士不遠而復,吾寧使之早棄斯世而求之于視聽言思之外,以濟眾生而滅度之。縱令入世,以行善為途徑,必不應如功利論者,沾沾于公德、私德之分。康德所云“道德有對內之價值,非有對外之價值”者,庶幾近于“無漏善”哉! 何以故? 盡欲度脫等眾生界,而亦不取眾生相,以一切眾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既無別異,則惟有對內之價值,而何公德、私德之分乎?[24]13
這是章太炎對于佛教思想的繼承與發揮。他認為世俗文明世界已經很難改變,因此期待勇猛大心之士的“大覺”,他要求新文明于“視聽言思之外”,他期待文明的重新展開,這需要一種純潔的道德。從上文的闡述,我們可以發現,“救救孩子”的主題也來自于此。
(四)通史史觀與退化史觀
《狂人日記》中的史觀問題也頗有討論的意義。如何認識古代中國,這是橫亙在近代諸人心中的一個大問題,而《狂人日記》就是魯迅史觀的一個代表。季劍青指出,在《狂人日記》中,“歷史不是作為過程性的敘述,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對象化的存在而被狂人把握的”[26]。季劍青的覺察展現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魯迅對于歷史,是能夠達到整體性地把握,即“通”的境界的。
能否跳脫出瑣碎的歷史片斷而形成對歷史的整體把握,是判斷一個史學家是否能“通”的重要條件。司馬遷把它總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熟悉司馬遷這一斷語的魯迅不可能不在表達自己史觀時慎之又慎。并且,形成通史意識與達到“通”的境界在歷史學中是極難的,“綜觀諸大家,能有通識者,除家學淵源,智商特異外,下面三個條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心力之專致,閱歷之凝練,智慧之風發,方可接近這種學問最高而至難的境界——謂之‘通’”[27]。魯迅的學術淵源即是乃師太炎先生。
章太炎是中國近現代最先探索寫作新式“中國通史”的史學家之一[28],而從上文對于章太炎《俱分進化論》的引用中,我們可以發現,將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并把它歸結為“吃人”的,正是章太炎。魯迅之所以敢于對歷史作整體的把握以及將中國歷史的“吃人”特性表現出來,是因為其背后有章太炎的理論支撐。當然,魯迅此處對章太炎的化用也是一種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
而且,《狂人日記》對于章太炎史觀的吸收還不止于此。《狂人日記》第十節說:“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25]452魯迅認為,在以前的野蠻時代大概人都是吃人的,所以對桀紂時代吃人并不是特別批評,只說“還是一直從前的事”。他最反感的是中國沒有進步,此后一直吃人,特別是近代,也即他的當代,中國人還在吃人。聯系魯迅在《看鏡有感》中表達的對于漢唐氣魄、拿來主義的向往而鄙夷宋以后的國粹氣,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魯迅最為批評的其實是宋以后的歷史,這種史觀同樣來自章太炎——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認為中國自宋以后有退化而無進化[24]9。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與魯迅都是在世界歷史中進行比較才得出自己的結論的,章、魯的史觀具有研究中國歷史的世界視野。
綜上,從魯迅的成長史來說,《狂人日記》是魯迅此前思想的一種爆發式展開。魯迅是將其系統接受的章太炎、莊子、佛學、尼采對于人類文明的批判收束到禮教之中,才寫出《狂人日記》的。《狂人日記》寓文明批判于禮教批判,從中國來說,它具有極強的現實批判性,從人類文明來看,它確實是一部具有世界品格的作品。
因此,《狂人日記》遠遠不止禮教批判這樣簡單,它的每一個主題,諸如夢覺、狂愈,大覺,吃人、心斗等,都代表著對于人類文明的批判,從接受美學來說,它們作為能指,可以在任何時間喚起人們對于自己處境的反思,促使人類文明不斷地更新、進步!
四、馀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世界性
從魯迅對于章太炎的接受與超越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時代的轉換——從前五四新文化時代到五四新文化時代。所謂“前五四新文化時代”,我們不想給它一個嚴格的定義,而是把它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思想來源看待。從章太炎與魯迅的案例里可以發現,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并不是一場冒失的、突然的運動,也并不是一場僅僅局限在中國的運動,它是一大批前代思想家對于世界文明作出總結反思之后的思想結晶。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不管是隱還是顯,都與人類文明中、世界歷史中的眾多問題息息相關而且給出了解答,這也是我們后人應該總結繼承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