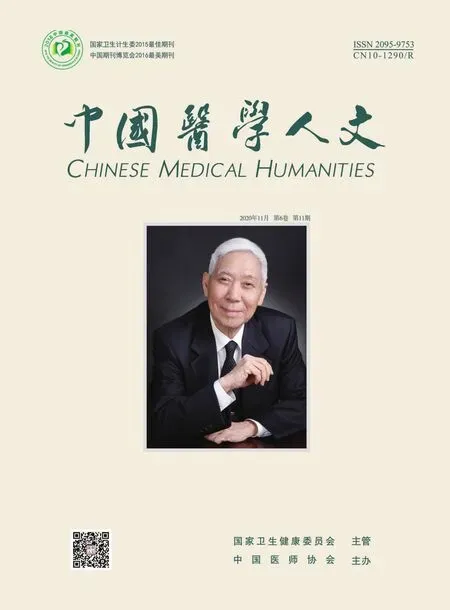沒有死亡就沒有美德
文/陳嘉映
編者按:2020 年9 月27 日下午,第四屆中國醫學人文大會醫學與文學論壇在京召開。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著名現象學家陳嘉映教授在會上作報告,他從哲學角度闡述了對死亡的看法。
中西方哲學家對死亡有很多思考,比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哲學這個活動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在為死亡做準備,或者是在練習死亡。20 世紀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認為我們整個生命是向死存在的。很大程度上,這些思考是希望人們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克服死亡恐懼有種種途徑。各種各樣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藏教等通常有不同的克服死亡恐懼的做法。而哲學家與他們不同,大范圍來講,哲學是通過思考來克服死亡恐懼的。從古到今也發展了很多不同的克服死亡恐懼的論證,非常突出的一條論證:靈魂不死。而蘇格拉底所說的練習死亡,也是和靈魂不死相關聯,這點需要我們聯系哲學慢慢地去領會、理解。德意志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提出的實踐理性的三共設中有一個就是靈魂不死,他也做了“炸彈性”的論證。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提出關于死亡的論證,即死亡與我們無關:當我存在,死亡尚不存在,當死亡存在,我尚不存在。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想法,《莊子》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莊周之作,其中《莊子·知北游》中寫到:“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元待也。皆有所一體,有元異道也。”后世的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對伊壁鳩魯的論證進行補充:我們跟死亡完全不相干,乃至于我們有時會想象死亡,但這種想象不合邏輯。因為想象中你總還是在場,你還是將活的自己放在其中,你可能什么也沒干,你可能躺在棺材里,而實際上你想象不出你死亡之后會怎么樣。盧克萊修用這個論證來支持伊壁鳩魯這樣一個基本命題:死亡跟我們生命是沒有交集的。
但是我們仍然會覺得死亡是遺憾、可憎、可怕的,這種感覺會不會因此被消除了呢?也不一定,那我們為什么不能消除對死亡的憾恨(這里是指遺憾的“憾”,恨鐵不成鋼的“恨”)?
有兩位哲學家對伊壁鳩魯的命題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其中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認為死亡之所以非常可憎,并不在于我當事人是否能“聽見”它,而是因為它剝奪了我當事人原有的能力。試想一下一個人正當盛年,突然發生一場事故。這場事故一下把他的腦袋撞壞了,但他并沒有死亡,之后他可能還會在生活中表現出傻樂的狀態,因為他自己感覺不到他有任何損失。雖然他自己生活在一個快樂的狀態中,但是那些愛他的人們會感到很大的損失。因為他正當盛年,有能力做很多事,而現在無法去做了。因此當一個人的能力和潛能不能得到發展和發揮的話,這樣一種損失才是我們憾恨的原因。實際上,一個人的狀態,無論是生是死,快樂與否,都不是以這個人的感知為標準。關于伊壁鳩魯命題的第二種進一步思考:一個叫歐利特的哲學家認為伊壁鳩魯的說法并不正確。因為按照伊壁鳩魯的想法:生命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到了死亡這一點,生命就受到了限制。而歐利特認為我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不斷移動的現在,我們是生活在希望和計劃里,生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你有希望,因為你正在做某件事,且你正在做的事是一個計劃中的事,而死亡之所以可憎是因為死亡打破了你的計劃,打斷了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整個計劃的完整性。
這兩種死亡觀的背后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時間觀。其中伊壁鳩魯認為時間是一個現在的線性移動。20 世紀初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提出“綿延”的時間觀,它非點的移動,是一種立體的時間觀。我們是生活在綿延之中,而非點中,我們的種種計劃、情感都有它特定綿延的界限。用通俗的時間觀念來說就是它們有特定的長度:一件事情可能在明天結束,另外一件事情在1 年后結束。有些人生計劃可能伴隨著我的一生,直到我們死去才會結束,而有些人生計劃并不是以我的死亡為終點。如宋代詩人陸游的《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他一生就希望統一北方,他的必生追求就綿延到死亡之外。
其實伊壁鳩魯的死亡觀中也有克服死亡、減輕死亡恐懼的辦法——“今朝有酒今朝醉”,即你永遠活在現在。這確實是我們在生活中克服死亡的一種辦法。但是這種伊壁鳩魯手把手教給你的克服死亡恐懼的辦法,它的代價非常大:一個立體的生活就會變成點式的、現在的、以移動式的生活,這樣生活的人叫單維或者一維的人,就是一個線性的人。另外我們面臨這樣一個處境:你用這種方式可能會減輕或者克服對死亡的憾恨,但是你不一定會接受它,結果就是讓你為了你所珍愛的東西(你的希望,你的計劃,你對世界對親人的愛)不得不接受死亡憾恨的一部分。
死亡對于我們人生正是起到了這樣一個作用,一方面他讓我們感到可厭、可憎、可怕,另外一方面它也使得我們周圍的一切珍貴的東西變得珍貴。如果沒有死亡的話,我們可能會有長生不老的想法,我們所珍愛的一切將不復存在,正因為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它才會是珍貴的。《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是全希臘人心中的英雄典范。亞里士多德說:據說只有在人間才有阿喀琉斯,天上的眾神里面是沒有阿喀琉斯的。因為希臘眾神是不死的,這是神與有死者(希臘中用來代替人的)的區別,也是人的一個本質。我們總是認為這是人不如神的地方。但是他反過來說:這是我們人優于神的地方,因為眾神中沒有阿喀琉斯,而終極的勇敢、終極的愛就是面對死亡,他們是不死的所以沒有也不需要這樣的勇敢。因此,我們人類珍愛的美德,我們珍愛的那些最深厚的感情,在那個意義上,人的有限性——我們作為人的缺陷或者遺憾,也正是我們人之為人的值得榮耀、值得珍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