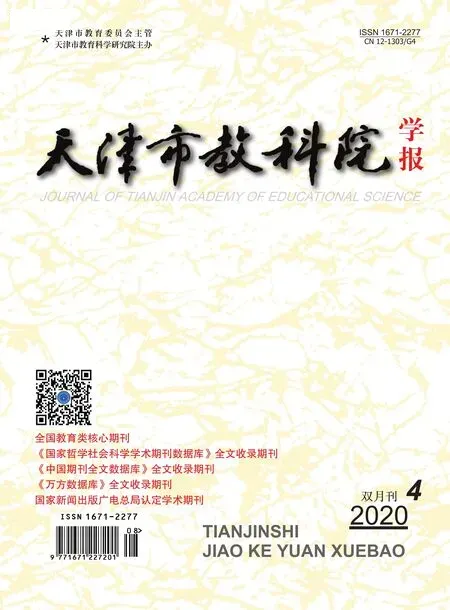學生自殺問題的教育學之思
李長偉,宋以國
無論是對個體亦或是社會而言,教育始終是一項回顧過去、立足當下并展望未來的事業。教育對個體的教化乃是以“生”為基礎的,如果說“生”是教育的起點,那換一個角度而言,“生”也是教育為之奮斗的目標。而這個目的就是成為“人”,成為一個具有人們所向往的完美品質和德性的理想狀態下的“人”,因為“‘人’是‘人’化的過程,所以‘人’總得去實現它自己”[1]。也就是說,“生”是為了更好地“生”。
如果說“生”是教育的底色,而教育又是一個朝向“生”和為了“生”的過程,那與“生”相反的“死”就應該是教育所極力規避的。當然,倘若受教育者在充分理智的情況下,為了更高的道德追求而慷慨赴死,這自然又是另外一種復雜的情況了。但受教育者的身份業已表明其是正在接受教育的個體,也就是說他的心智是不成熟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這樣幾個問題,即在多大程度上受教育者的理智是完全自主的,他的種種決定是否明智,他是否明了自己所要采取的行為將會給自己帶來何種后果。生此疑問,并非是要對種種“慷慨赴義”之行為予以任何的否定,相反,正是因為出于對個體生命的敬畏和珍惜,我們才難以草率地對此類行為一味地予以完全肯定。既然如此,那學生的自殺行為就更需要社會公眾予以關注和反思。因為與個體的“慷慨赴義”相比,學生的自殺完全是一種消極的和毀滅性的行為。雖然我們不能因此而對當下的教育現實予以完全的否定,但有鑒于當前學生自殺問題有擴大化為一種社會問題的趨勢,所以,對該問題予以探討既是理論需要,也是一種現實關切。
一、學生自殺問題的現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權威數據,自殺業已成為致使15~29歲青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這意味著自殺儼然已經成為一個需要我們給予密切關注的社會問題。[2]近幾年來,國內各地學生自殺的惡性事件不斷見諸報道,可見這一反常現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但學生自殺事件的特殊性卻使得在全國范圍內對中小學生自殺數據進行全面的整理和分析成為一項異常艱難的工作。作為國內較早關注這一現象的權威機構,21世紀教育研究院也僅在2014年和2018年發布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系列叢書中分別對2013年全年以及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間的全國中小學生自殺案例進行過全面的數據調查和分析。根據這兩份較為權威的調查報告,對國內中小學生的自殺現狀進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
其一,學生自殺人數呈遞增趨勢。2010年全國中小學生自殺案例為73起,2013年為79起。[3]而從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間全國累計共發生392起兒童青少年自殺案例,其中明確注明為中小學生的案例有267起。[4]
其二,學生自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長期高強度的學業壓力。導致中小學生自殺行為的原因從多到少依次為:家庭矛盾(33%)、學業壓力(26%)、師生矛盾(16%)、心理問題(10%)、情感糾紛(5%)、校園欺凌(4%),另有其他問題(6%)。[5]很明顯,家庭矛盾、學業壓力和師生矛盾是導致學生自殺的三大主要原因,但如果我們對部分案例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導致家庭矛盾和師生矛盾的深層次原因仍然是學業壓力。因為處于教育場域中的家長和教師也承擔著不同程度的學業壓力和教育壓力,而這種壓力和焦慮最終會部分甚至于全部轉移到學生身上,造成三者之間產生不同程度的對立情緒,激化家庭矛盾和師生矛盾。也就是說,學生始終是來自各方面學業壓力的最終承受者。所以,考慮間接作用的話,學業壓力可能才是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而對自殺學生年齡和學業階段的分析同樣也支持了這一結論: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自殺率開始攀升,而“13、14、15、16、17歲五個年齡階段的死亡及死亡未遂案例之和是8、9、10、11、12歲五個年齡案例之和的4.7倍。……中學生死亡案例與小學生死亡案例之比約為7.2∶1,中學生自殺未遂案例與小學生自殺未遂案例之比約為8.8∶1”[6]。種種數據都表明,中學生的自殺狀況比小學生要嚴重得多。這是因為,相比較小學階段而言,中學階段無論在課程量還是在課程內容難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這意味著學生所要面對的學業壓力急劇增大,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學生自殺行為的發生。
二、學生自殺問題的理性分析
經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即學業壓力是造成中小學生自殺行為發生的主要原因。但這一結論遠不能消除我們對于學生自殺問題所產生的全部疑惑,因為就某種意義而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7]。再者,“害怕死亡,是因為我們熱愛生命,至少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生存是值得繼續的。對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來說,怕與愛的根子都是生命的本能,二者無法分開”[8]。究竟是何種原因使得學子放棄人類所共同熱愛的寶貴生命,投向死亡的深淵?又是什么使得他們竟認為自己的生命不值得再繼續?因為學生自殺問題的復雜性和隱蔽性,僅從現實表面來思考這一“嚴肅的哲學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把握。
毫無疑問,學業壓力必定會給受教育者帶來不那么愉快的個人體驗。在肉體上,受教育者在學業壓力的督促下唯有披星戴月、伏案苦讀,自會飽嘗學習之辛苦;在精神上,學業壓力始終猶如一把“達摩克斯之劍”,時刻鞭策著學生,這使得學生精神心理始終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長此以往,對其身心自然會產生不良影響。既然如此,那身處傳統教育中的古代學子是否也面臨著同樣的學業壓力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相比較現代而言,古代教育資源十分有限,能夠進入正規教育機構進行系統性學習的學子數量十分有限,甚至于書籍在古代都是十分稀缺的教育資源。面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子必將更加珍惜,加倍努力,這無形之中加大了求學者的心理負擔。其次,古代物質資料十分匱乏,難以為普通學子營造舒適的學習環境,“囊螢映雪”“鑿壁偷光”和“頭懸梁,錐刺股”等典故都真實地反映了古代學子為求學而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肉體之苦。最后,古人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將讀圣賢書視為實現人生價值和抱負的唯一路徑,而“學而優則仕”和嚴苛的科舉制度又將讀書和從政為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加之古代階層之間流通路徑的有限性和嚴重的階層固化以及艱難的職業生存環境,使得學子將讀書和科舉視為實現階層流通的唯一路徑,最終造成了諸如“范進中舉”此類事件的發生。
由此可見,古代學子所面臨的學業壓力并不比當今學生少。傳統教育中的學子自殺問題似乎并不像現代教育中這樣嚴重,那他們何以就能忍受相比較今天而言更為嚴重的學業壓力呢?這意味著,除了學業壓力之外,一定還有某些更為深層次的原因與學生的自殺問題有關,而這些原因就隱藏在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本質性區別之中。
(一)由志業到學業
韓愈在《師說》中有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9]由此可見,就傳授內容而言,“道”的重要性要遠大于“業”和“惑”,是學子首先應該習得的內容。此處的“道”意味著古典哲人眼中永恒不變的真理和規律,意味著一種整體的和諧美滿,意味著人類自始至終都在追求的永恒之善好。而對于每個鮮活的個體而言,就意味著個人要認識世間之真善美,進而努力去實踐和踐行。也意味著學子要在師者所傳授的“道”的指引下,確立人生方向和道德價值觀,篤定人生之理想,實現人生之抱負。那么就此而言,這種以“道”為核心教育內容的傳統教育在其本質上乃是一種“志業”。“志業”是韋伯在其著作《學術與政治》中特別強調的一個關鍵詞,該詞在德文中對應著單詞“beruf”,但“beruf”一詞一般僅僅用來指職業,而馬丁·路德在翻譯圣經中的“beruf”一詞時賦予了其強烈的基督教價值背景,強調“奉神的旨意和召喚去從事某項偉大的事業”[10]。在此,我們可以將“志業”視為個體用理想和信仰去澆灌的一項為他人服務的事業,而不僅僅是一項謀生的職業。
由此而言,在古代學子眼中,學習乃是一項“志業”,也正因為“志業”所帶給個體的富有價值意義的人生體驗才使得其可以忍受“秉燭夜讀”所帶來的種種痛苦。所以,在古代學子的眼中,這種伴隨著“苦讀”而產生的痛苦是“得道”之路上必須經歷的磨礪,甚至是通往成功彼岸的唯一方式。因此,他們會勇敢地面對這種磨礪,絕不會以自殺的方式來逃避讀書之苦。而且,在讀書的過程中,在對“道”的追尋過程中,學子會逐漸建起自身的價值信仰和人生理想。而這種追求至善真理和實現人生志向的決心又會給予學子以克服困難之決心與毅力,斷然不會以自殺來終結對“道”的追尋。再者,“志業”中的“志”指的是“有志于”,也就意味著學子對“道”的不懈追求,而“道”所提供給學子的價值和信仰體驗使得其可以忍受學習過程中的諸多痛苦。也就是說,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可以給予個體以克服當下困境的力量。當“道”可以提供給個體以價值信仰之時,即使面對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難,個體也會有無盡的內在力量來捍衛自己心中的“道”,而絕不會為求一時之解脫而尋死。古有左丘明、孫臏、司馬遷,今有貝多芬、霍金、張海迪,他們沒有將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僅僅視為一種職業,而是當作一項融于自身生命中的“志業”來完成,這種追求和人生理想是內化于心的,因此,他們才能夠忍受世人難以忍受之痛苦,勇敢地并且好好地活下去。
由此可見,這種價值信仰所賦予個體的內在精神力量能夠有效地防止個體自殺行為的發生。但如果個體在內心深處難以建立積極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就自然無法提供給學子克服和忍受為學之苦的力量。因此,如何幫助學子真正認識、理解進而把握“道”和至善的價值理念,并引領學子踏上對“至善真理”的追尋之路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傳統師生之間所形成的“志業共同體”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所謂“志業共同體”,意指教師和學生在共同從事一項對“道”的追尋和探索的事業過程中所形成的親密關系體。在此過程中,師者要不遺余力地扶持學子,引導學子認識和內化“道”所內含的道德價值理念。因為“道”或者“至善”是終極的、永恒的存在,所以人類個體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很難完全把握住這樣一種超驗的存在。也就是說,“盡管教師的靈魂熱愛至善,追求永恒,但教師的生命畢竟是有限的存在,若要永恒地追求至善,就需要教師將自身的靈魂美德‘種植’到愛‘好’的學生身上”[11]。也就是說,雖然教師囿于自身之限制不一定能夠完全認知和把握這一永恒的“道”,但作為教育場域中最為接近“道”的人,教師有責任也有使命引領學生走上對真理的追尋和探索之路。而“人類真正的共同體,是那些尋求真理者,那些潛在的智者共同體,也就是說是全體渴望求知的共同體,人們不顧一切尋找的密切聯系正是在這里建立起來的”[12]。在此意義上,處于“志業共同體”中的教師和學生之間形成的是親密友愛的師生關系,這種“志業共同體”也能夠帶給學生個體以克服伴隨學習而產生的痛苦的勇氣和力量。最后,“道”貫穿于傳統教育的始終,甚至可以說,傳統教育過程就是對“道”和真理的不斷追尋和認識的過程。而后來人則需要在掌握先賢的思想基礎上開拓進取,繼往開來,唯有如此才能夠不斷加深人們對真理和至善的認識。“它意味著前后相續的每一代人都誠摯地融合到整體的精神中去,而后者則是經驗、工作和行動由之發生的文化,教育者的個人成就幾乎不被意識到。他服務于一項事業而無需進行實驗,他在人類的形成之河中游泳,這條河流一般來說是有規則的和連續的”[13]。這就使得教育場域中的教師和學子可以與眾多早已作古的至圣先賢在精神層面結成一種跨時空的“志業共同體”,因為他們都在從事同一項豐富人類精神文明的崇高事業,而眾多的先哲典籍就是教師和學生與先哲進行精神對話的媒介。在此過程中,雖然個體對這項偉大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個體得以“通過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無限性過程來獲得自我超越,實現不朽”[14],而對這種崇高的人生價值體驗的追求能夠使得個體直面讀圣賢書之苦。
如果說傳統教育的核心是“志業”,那么現代教育的關鍵詞則是降格化了的“學業”。很顯然,“志業”和“學業”在本質上是存在差異的,而這種本質上的差異就體現在“志”和“學”上。失去了“志”的“學業”難以使學生真正在精神領域建立起對崇高價值理念的信仰,對“道”的認識和追求更無從談起。也就是說,支撐著學生勇敢面對讀書之苦的精神價值體系崩塌了,這也導致了學生無法借助于任何內在的力量來克服讀書之艱辛。而此時于他們而言,自殺成為了終結當下一切無意義的學習之苦的最佳路徑。因為,前文業已提到,“志業”意味著學子將學習視為認識真理、塑造人生價值和實現人生意義的途徑,于是讀書和學習與個人的信仰追求和價值意義聯系在了一起,“志業”將學習與個體的鮮活生命力聯系在了一起。實際上,“志業”回答了個體“為什么學”這一重大教育現實關切:窮則獨善其身,飽讀經書,修身養性,以求圣賢之道;達則兼濟天下,出仕為官,匡扶正義,以求國泰民安。而當下教育現實僅僅將學習視為一種“學業”,“學”成為了主要的目的,學生“只圖考試過關,并且從應試的角度判斷所有的知識值不值得學習。把讀書階段看作是職業生涯開始前的痛苦煎熬”[15]。而這一目的既不能為學習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也不能解答學生關于“為什么學”這一現實疑惑。這也充分印證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今天,教育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不是教育工藝學方面的‘怎么做’,而是教育哲學方面的‘這樣做是為什么’”[16]。而一旦學生在精神層面失去了教育信仰和價值的支撐,肉體得不到自身精神維度上的支持,其自然難以忍受為學路上的漫漫求索之苦。然而,當學生無法從自身得到精神力量的支持以忍受讀書之苦時,還有另一種途徑,即從師者身上得到精神層面的關懷和力量。但遺憾的是,這一路徑在現實教育場域中也無法實現。因為“近現代教育的問題在于蔽于‘器’而不知‘道’”[17],也就是說現代教育將注意力集中于“器”的工具性價值層面,而忽視了對真理和善的追求。既然如此,就意味著將師者和學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粘合劑——至高無上的“道”——解體了,所謂的“志業共同體”也隨之土崩瓦解,雙方的關系也由精神性的相互依存關系轉變為物質性的契約關系。學生對教師所形成的普遍觀念是“他賣給我他的學問和方法,為的是賺我父親的錢,就像菜市場的女商販向我的母親兜售卷心菜一樣”[18]。而迫于學校追求升學率的巨大壓力,教師也在一定程度上將學子視為達成考試目標或升學率的工具,學生在教師眼中被“去人格化”而完全成為學習的機器。學生自身的精神發展和精神追求成為了教育所無暇顧及的角落,從而使得學生的生命得不到價值層面的關懷,因為“如果人被迫只顧眼前的目標,他就沒有時間去展望整個的生命”[19]。
(二)由自由到規訓
無論是古代亦或是現代,自由始終都是人們的永恒追求之一,既然教育是一項引領個人擁有整全生命的事業,那教育自然要給予受教育者以自由或者幫助受教育者實現自身的自由。若從這一角度而言,傳統教育給予學子的是“自由”,而現代教育給予學子的則是“規訓”。當學生面對無所不在的規訓之網而無力反抗之時,學生個體在精神和現實維度的個人空間會被教育壓力所無限壓迫,最終使得心智不成熟的學生將自殺視為反抗現實壓迫和爭取自由的唯一行為,而這也是造成學生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傳統教育在以“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對學子的言行舉止都有著嚴格的規定和限制,這當然表明傳統教育中的學子在行為方面是不那么自由的,但傳統教育所賦予受教育者的自由不是側重于行動的自由即肉體的自由,而是聚焦于精神層面和自我實現的自由,以此來正確地引導個人行為,踐行人生之追求。具體而言,處于“志業共同體”中的學子在師者的引領下,在求知欲的推動下能夠不斷地接近真理,徜徉在先哲的學術理念之中,并通過典籍與哲人進行精神的對話。他們將把握真理、見證永恒作為“志業”之目標,而事實上,他們在現實教育中也正是這樣行動的。因此,在實現人生目標的道路上,傳統教育之中的學子是自由的。再者,“自由是自我實現與自我導向的自由”[20]。也就是說,自由還意味著要“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思想、有意志、主動的存在,是對自己的選擇負有責任并能夠依據我自己的觀念與意圖對這些選擇作出解釋的”[21]。學子不但要將學到的為學做人之“道”融入自身的道德理念之中去,還要在現實生活中嚴格按照“道”所要求的道德規范來為人處世。這時的“道”于其而言已經不是外在的了,而是已經被潛移默化地內化為了自身的信仰和追求。要按照自己的原則和精神追求來實現自我,唯有如此才能夠更好地踐行“道”的理念,在此意義上,傳統教育給予學子的是實現自我的自由。
如果說幫助學生實現自我是教育的應有之意,那現代教育在這一方面無疑是有所欠缺的。在現代教育的現實場域中,“教育為了讓學生在未來的競爭中獲得‘成功’,對學生的時間和空間都給予了嚴格的管控”[22]。具體而言,學生的全部時間幾乎都被分配給了學習,在校期間,課程表上名目繁多的課程使得學生在校期間始終處于忙碌和緊張的狀態,還需要面對各種測驗和考試,甚至于周末休息時間都被大量的家庭作業所占據。再者,由于學生始終處于不斷學習的繁忙狀態,因此,其自身也就被限制在教室和書房等封閉或者半封閉的空間之中。此外,“現代教育日益成為一種通過‘教育科學’精心設計的、教育的科層管理細致安排的特殊的塑造機制,強制性的教育操縱每個人,把他們造就成特定類型的人”[23]。成為“一種事先謀劃好的、科學或藝術地控制人們心智的技術,成為一種人們必須服從的機制”[24]。它并不關心學生自身的想法和人生規劃,只是盲目地將變動不居的教育目的施加于學生身上,“如為了你的未來你必須怎樣怎樣”,而這“似乎都是為了給被規訓者造福”。[25]也就是說,現代教育不但對學生個人的時間分配和活動空間即個人行為作出了明確的限制,而且還在不遺余力地為學生設定人生之目標,全然不顧學生的自由權利。
面對教育中的諸多束縛,處于不利地位的學生要么逆來順受而最終成為“被塑造者”,成為教育千篇一律的產品中的一個,要么采取措施主動為自己爭取自由。但由于學生自身思想的不成熟性,其對自由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差的,甚至是錯誤的,因而會采取十分過激的行為,學生的自殺行為就是其中之一。“就沒有人或人的群體干涉我的活動而言,我是自由的”[26]。所以,學生首先會追求一種“消極的自由”,亦即“個人在特定的領域內保有自己的空間,保有不受阻礙與干預的自由”[27]。因為,“在一個尋求幸福、公正或自由的人覺得無能為力的世界上,他發現太多的行動道路都被阻塞了,退回到自身便有著不可抵抗的誘惑”[28]。所以,學生會想盡各種方法割斷自己與外界的聯系,甚至沉浸于虛擬的網絡世界之中,因為對他們而言,網絡世界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同時這種逃避也使得個體之間的關系出現斷裂,造成師生、家長和學生之間人際關系的疏離。總之,他們“借逃避世界、孤立自己,來得到保護”[29]。但現代教育對個人的控制并不會因個人的逃避而有所收斂,教育中的控制會步步緊逼,逐漸將學生的自由空間壓縮至最小。例如,學生在校期間受到老師在學業方面的控制和管理,而當學生離開學校之后,這種控制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借助著大量的家庭作業將控制者由教師轉變為家長,將規訓的空間由學校轉移至家庭。而作為學生本身又并沒有能力來阻止外界的控制,當學生現實生活中的自由領地一步步被學業壓力所蠶食,相對于志向缺失、意志薄弱、耐挫力差的個別學生,留給他的自由就只剩下最后一種了,即去死的自由,而通過自殺他為自己贏得了最后的自由——“面對死亡的自由”[30]。
三、教育:面向志業與自由
(一)面向志業
古代學子雖然也面臨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學業壓力,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現實生存環境,但個人卻能夠找到得以依賴的精神支撐和靈魂關照。具體而言,個人內心對于志業的堅守使得志業成為一種關照個體精神世界并為之指引方向的精神理想和人生希望。就此而言,外在的讀書之苦也與人生理想達成了一致,共同成為了促進和鞭策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上升力量。而現代教育對于個人志業的忽視使得學生心中失去了可以統攝個體精神的人生理想和目標,使得讀書之苦成為了一種純粹的肉身之苦,而無法與個人理想達成一致。可以這樣說,志業使得學生將讀書之苦視為對個人秉性的磨煉,視為實現人生理想的必經之事,視為通向人生價值的階梯。
如此而言,現實教育自然要關注對學生志業的培養。正如前文所言,志業的本質就體現在“志”上,也就是個人的人生追求和價值理想,這種內在于個體的精神性存在使得個體將讀書之苦視為一種對身心的磨礪,而不是一種痛苦的肉體折磨。因此,教育就應當積極關注學生的精神成長和價值塑造,因為若個體失去了自身堅信的道德標準和價值理念,他將會失去面對各種艱難險阻的堅定力量,他的行為將會失去價值依據,他的人生將會失去方向感和使命感。進而言之,他將會成為一個沒有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的“空心人”,對于一個無理想和信仰追求的人而言,他自然不肯、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面對生活的種種磨礪。于他而言,自殺就成為了結束這種無意義的痛苦的路徑。所以,教育必定需要賦予學生以高尚的價值觀念,引導學生追求高貴的人生理想,因為“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31]。唯有如此,才會賦予讀書之苦以意義和價值,才會使學生內心深處擁有忍受磨礪的毅力。而在具體的教育實踐中,可以采取以下幾方面的措施來促進“學業”向“志業”的轉變。
其一,教育應該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引導學生去主動確立積極的人生價值和追求,而不是把教育當作機械的知識計算和羅列的過程。教師應在日常教學過程中貫徹教育性教學的思想,通過對課本知識的深度挖掘和拓展引導學生樹立高尚的人生追求,使得學生可以在學習過程中體會到對自身精神層面的人文關懷和價值引領,通過學習過程堅定自身的追求和信仰,將學習過程視為修正人生理想、塑造價值觀念、磨礪個人品質的途徑,以此來關懷個體的志向成長。
其二,教師應該成為學生的精神導師和靈魂伴侶,因為“教育不是一項靠孤軍奮戰就可以完成的任務”[32]。教師應該在教育活動中引領學生追求真善美,而對經典人文名著的閱讀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路徑。因為在閱讀名著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可以與眾多的思想家進行精神層面的溝通與交流,領略人性之善惡,品味世間之百態,可以一同體會人類對至善理念的贊美和憧憬。此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引導者身份要求教師應該在教學過程中逐漸引導學生認識和內化積極高尚的價值觀念,以此引導學生樹立符合社會價值取向,確立積極崇高的人生理想。
(二)面向自由
現代教育的規訓屬性不斷蠶食著學生的自由空間,使得學生成為了被規訓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生以自殺這一過激行為來反抗或者逃避現實。那么,為了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教育就應該給予學生以合理限度的自由,所以教育應該訴諸自由,而不是控制。
其一,學校制度應該賦予學生以自由。當下的學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學業而制定的,而不是為學生而制定的,更不是為了學生的自由而制定的。為了使學生將時間和精力全部集中于學習上,包括校規校紀等一系列校內規章制度都對學生的人身自由作出了極為明確的限制,什么時間做什么事情都被制度安排得一清二楚,學生幾乎沒有選擇的權利,這集中體現在學生在校期間的作息時間表上。因此,在學校各項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學生個體的人身自由權,給予其充分的自由時間和空間來發展個人興趣和旨趣。此外,學生作為校園中的小主人,應當有參與校規校紀制定過程的自由權利,而不能僅僅是單純的不能發聲的被管束者。即使學生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也應該允許學生參與制度的商議和討論,給予學生發表自身意見和觀點的合理自由,并對其合理意見予以考慮和采納。
其二,就教師而言,應該以合理的自由的教育方式來促成學生的個性發展。具體而言,教師應合理尊重學生基于個性而作出的價值判斷和選擇,但不能否認,學生囿于自身價值觀念和思想的不成熟性,難免會作出錯誤的選擇。但此時,教師不應以強硬的態度和獨斷的方式對學生的行為和價值判斷予以批評,甚至于完全地否定而不給學生以解釋和言說的機會。而是應該尊重學生的個性選擇和自由表達,在與學生的溝通中以討論和協商的方式在充滿溫情的談心過程中對學生的不合理價值觀予以不斷地修正和引導。[33]唯有如此,才能夠以充滿自由精神的教育實踐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個體。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做此總結:雖然導致學生自殺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復雜多變的,但過重的學業壓力始終是最為主要的因素之一。而這種學業壓力體現的是教育實踐中的偏頗:由志業轉變為學業,忽視了對學生精神和靈魂的關懷與教育,使得學生難以忍受學習之苦;由天性異化為規訓,忽視了學生個性發展的權利,使得學生難以忍受來自學業壓力的桎梏。那么,為了杜絕學生自殺行為的再次發生,在現實教育中應該注重學生積極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的塑造,并在學校制度制定和教學過程中充分尊重和賦予學生自由發展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