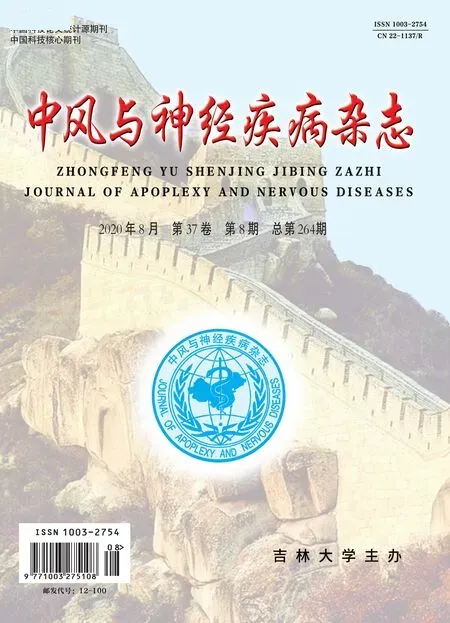三核苷酸重復序列的不穩定性在1型強直性肌營養不良中的作用
王子燚,孫 慧,李希希,霍龍文,王 猛綜述,于雪凡審校
強直性肌營養不良1型(Myotonic dystrophy type 1,DM1)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神經肌肉疾病。其發病的核心機制是由于DM1蛋白激酶(DMPK)基因3’未翻譯區域的胞嘧啶-胸腺嘧啶-鳥嘌呤(CTG)擴增所引起的轉錄RNA功能的改變,由此引起的下游事件導致一系列臨床癥狀。該病由于具有極大的遺傳變異性及臨床異質性,因此給臨床診斷與鑒別帶來極大的困難。近年來,由于DM1患者具有遺傳早現現象,CTG的重復次數不斷擴大,在理解病理生理機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DNA水平上三核苷酸重復序列的異常擴增成為DM1的導火索,本文綜述了CTG重復序列的不穩定性以及CTG擴增與臨床癥狀的關系,旨在闡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1 CTG重復序列的不穩定性及相關機制
DMPK基因CTG重復擴增是導致DM1的致病突變,擴增的CTG重復序列的轉錄產生有毒的功能效應的CUG-RNA,從而導致疾病癥狀[1]。但驅動這種擴增的潛在突變尚未確定,有人推測DNA錯配修復機制以及參與二級DNA結構的機制,如發夾結構或R-環,可能以某種形式參與其中[2]。DM1患者發病年齡從胎兒到中老年不等,并影響多組織系統。由于在DM1患者的精子和未成熟卵母細胞中已經存在CTG重復長度的變化,這表明CTG不穩定性主要發生在生殖細胞胚胎早期的有絲分裂期間[3]。DM1小鼠模型顯示CTG擴張已經存在于精原細胞中,在7周齡的精子中就已經出現了對擴張的生發嵌合現象,此外CTG重復數目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繼續增加且獨立于減數分裂過程[4]。在妊娠第13~16 w,胚胎在組織中CTG數目變得不穩定且并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擴增,其中心臟、皮膚最為明顯[5]。上世紀末,Southern blotting結果顯示在不同組織中的CTG重復擴增高度不同,肌肉、心臟和睪丸中的CTG重復長度比血液、小腦和胸腺中的CTG重復長度更大[6]。由于DM1患者存在這種體細胞嵌合現象,因此很難通過患者體細胞的CTG重復數目來預測下一代。但是在DM1血液樣本中,CTG重復長度的平均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并且取決于重復序列的初始大小[6]。這表明重復的有絲分裂不穩定在整個生命中持續存在。擴張的程度與最初的重復大小相關。
2 錯配修復途徑在DM1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三核苷酸重復擴增不僅降低了DMPK基因所表達的蛋白或mRNA水平,還改變了相鄰的染色質結構,減少了相鄰基因的表達,如下游的SIX5基因和上游的DMWD基因[7]。最近假說提出,CTG重復序列周圍的甲基化導致SIX5基因表達降低的原因,可能對精原細胞有害,從而阻止父系遺傳后大量重復序列擴張的傳播[8]。相反,當受影響的母親攜帶從80到250個CTG重復序列的突變等位基因時,CTG數目不會受到甲基化的影響,從而在下一代會更大,因此先天性強直性肌營養不良往往來源于母系遺傳[9]。由此可以發現DNA修復、復制、轉錄和表觀遺傳變化都會影響CTG重復不穩定的動態。每個過程可能以多種組合的方式參與,其有效性在不同的組織中可能有所不同,并可能導致的DM1患者之間的差異。
表觀遺傳學的改變被認為是DM1患者三聯體重復不穩定和表型變異的修飾因素,其中甲基化修飾在DNA水平上起到了巨大作用,焦磷酸測序數據顯示,DMPK基因內的DNA甲基化可以改善呼吸參數和肌肉力量,而與CTG重復長度無關[10]。幾個DM1小鼠模型已證明錯配修復途徑在CTG重復不穩定動力學中的作用,其中MutSβ復合體(MSH2-MSH3)在CTG重復擴張的形成中至關重要[11]。MSH3作為錯配修復基因,其表達是衡量三聯體不穩定程度的一個重要參數,并被認為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限制因素。在DM1轉基因小鼠中,MSH3是形成代際CTG擴增的限制因子[12]。此外,遺傳關聯分析表明,MSH3/DHFR3個串聯重復等位基因,稱為3a等位基因,可能會降低DM1患者的體細胞率,以及延遲發病[13]。不穩定性的水平是高度遺傳的,這意味著不同的DM1個體存在特異性的反式遺傳修飾的作用。識別這些反式作用的基因修飾物將有助于制定新的治療方法,從而減少體細胞擴展的積累,并可能為這些因素在普通人群中癌癥、衰老和遺傳性疾病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提供線索。
3 CTG重復擴增數目的多少與臨床異質性之間關聯緊密
DMPK基因內擴展的CTG重復序列被轉錄成RNA但不被翻譯,這些RNA與各種剪接調節因子形成聚集體,這反過來會損害多個基因在各種組織中的轉錄,從而影響下游各器官功能基因的表達[14]。一般說來CTG重復擴增較大的患者發病年齡較早,癥狀較重。國內外多家研究中心試圖將CTG重復長度與癥狀嚴重程度、臨床特征以及該病相關并發癥聯系起來。由于DM1患者的體細胞嵌合性,因此CTG與臨床異質性之間關系大多以血清白細胞或研究的目的細胞中CTG數量含量為評價標準。重復次數較多的患者如果在最初檢查時已經有癥狀,隨著血液中的重復次數增加,在5 y內臨床癥狀進展的可能性極大,也有部分DM1基因攜帶者可能會一直無癥狀,直到高齡。先前通過肌肉損傷評定量已驗證對于DM1患者的核心癥狀(肌無力、肌強直以及活動耐力下降)與CTG重復擴增存在明顯的正相關[15]。同樣,CTG大小對于DM1患者多系統并發癥亦存在極強的關聯性。
3.1 CTG大小與中樞神經系統相關并發癥 通過彌散加權呈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可以發現CTG擴增明顯的患者腦組織多部位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明顯下降,提示CTG擴增程度越高,FA所呈現的纖維組織受損越重[16]。DM1患者包括雙側眶額葉、額葉前部、島葉、外囊和枕葉皮質在內的廣泛區域內的彌散度指標下降。此外,厚度與這些區域的CTG重復數呈負相關。DM1患者的皮質脊髓束(CST)中的DTI參數與遺傳因素和運動性能之間存在顯著的關系。這些發現提示CST的介入反映了運動束的惡化,可能在臨床肌強直中起重要作用。此外,皮質灰質體積與CST中DTI測量值之間的直接關系表明,CST中白質異常與DM1患者感覺運動皮質的體積減少密切相關[17]。同時,灰質和白質的完整性與CTG重復序列相關,但CTG重復序列大小與腦結構改變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證實,亦有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DM1患者在社會認知及情緒調節方面存在明顯障礙,已經證明這些高級功能障礙與大腦結構和功能障礙密不可分。部分患者對自己的癥狀漠不關心,這也是由于DM1導致的認知能力下降所致。在IQ分數和CTG重復的大小之間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相關性。DM1與廣泛分布的灰質和白質網絡變化有關。一些與認知相關的區域與CTG重復顯著相關[18],由于大腦由高度專業化的功能區組成,因此與CTG重復大小有關的區域信息將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3.2 CTG大小與心血管系統相關并發癥 雖然CTG重復擴增引起多系統受累,但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肌肉萎縮和心臟性猝死。過三分之二的DM1患者經歷嚴重的心臟功能障礙,包括心臟傳導延遲、致命的竇房和房室傳導阻滯、心房顫動和室性心律失常[19]。對于CTG重復大小作為傳導障礙或心臟事件的預測指標是否有價值,目前文獻存在較多分歧,尚無法達到統一共識。CTG 數量大小是否可以循環系統障礙的并發癥的預測因素仍然需要大樣本進行統計。近日相關研究發現,在DM1心臟組織中,CTG擴增引起的RNA結合蛋白RBFOX2的非肌肉剪接異構體上調是導致了DM1個體的心臟傳導缺陷的重要因素。RBFOX240上調的程度與CTG重復擴增的大小亦是當下重點研究方向[20]。這就意味著修飾基因以及錯配修復機制在DNA水平上對CTG的影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3.3 CTG大小與呼吸系統相關并發癥 DM1患者較其他患者更早出現呼吸功能不全。Salvatore等人通過對268名DM1患者進行多中心橫斷面研究發現白細胞CTG擴張大小與呼吸肌受累的大部分功能參數、勞力性呼吸困難顯著相關,且證實CTG是DM1患者呼吸受限的獨立預測因子[21]。對于DM1患者,睡眠中的呼吸障礙更為常見,日間睡眠亢進,伴有睡眠潛伏期短,入睡時眼球運動迅速,下丘腦下泌乳素系統異常這些均可能歸因于睡眠呼吸暫停[22]。在慢性呼吸功能不全的主觀癥狀中,只有疲勞性呼吸困難與限制性模式顯著相關,這是由于呼吸困難不僅僅是由于肺部功能損害,骨骼肌無力也是其主要原因,這與DM1中的特征密切相關,而CTG作為二者共同的預測因素,其在臨床工作中具有評價預后的價值。
3.4 CTG大小與眼部相關并發癥 白內障、上瞼下垂、眼動異常和低眼壓是DM1中最公認的眼部問題,其中前三者與運動功能障礙有關。眼壓降低也很常見,但似乎與運動障礙無關[23]。與DM1相關的晶狀體混濁似乎具有完全的遺傳性,也就是說,近100%的DM1患者存在白內障[24]。即使特別小的CTG重復序列也會引起眼部癥狀的發生,而且其嚴重程度會隨著病程的進展而加重,因此兩者之間的關系則顯得撲朔迷離。一項對于韓國DM1患者眼部研究結果表明CTG>700的DM1患者行白內障摘除的幾率遠高于<700的患者,即兩者呈正相關[25],但這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來證實。
除了上述并發癥以外,DM1患者惡性腫瘤的風險也有所增加,患癌癥的風險增加了約一倍,最常見的有皮膚癌、甲狀腺癌和乳房癌等[26]。消化功能障礙、內分泌紊亂、周圍神經病和其他發育和退化表現也是DM1患者的常見表現,其與CTG的重復數目之間的關系由于原始研究的不足,因此尚無定論。
4 總結與展望
自從發現DM1的CTG重復序列的不穩定性以來,CTG重復序列擴張的動力學及其與疾病的各個方面的關系方面均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統計學的發展使人們有可能改進重復序列的大小和臨床癥狀之間的相關性,并揭示了DM1中明顯的一些變異性。RNA的毒性作用起源于DM患者DMPK基因的非編碼區的CTG重復擴增,導致在S期復制叉停滯,以及細胞應激反應[27]。因此致病過程在DNA重復擴增階段最為簡單也最好把控,無需針對下游再行過多干預。對于DM1患者,藥物作用的等位基因只有一個,所以理論上用藥的種類以及濃度都應少于作用于特定的下游途徑。因此在DNA水平上的如果能夠減少GTC擴增數量則可獲得最有效的治療效果,但在技術上存在相當大的難度。隨著CRISPR/Cas9基因編輯平臺的廣泛應用[28],DM1的基因治療手段也逐漸被完善,從而使得遺傳學和修飾物的鑒定取得進展,這將有助于在未來的臨床試驗中對患者進行分層與治療。因此對于DM1患者的三核苷酸重復序列的不穩定性來說,更好地了解這種變異性的來源對于開發新的具有挑戰性的療法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于在個性化治療的道路上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