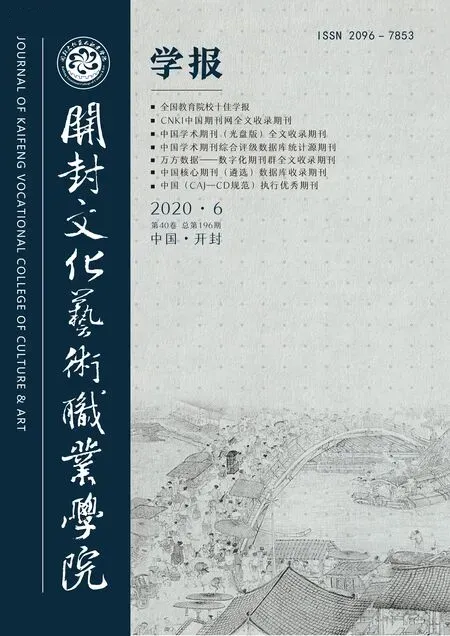明清男女戲曲作家作品中的夢境創作研究
趙 強
(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湯顯祖是明清時期善用夢境方式創作的戲曲大家,創作了譽滿世界的戲劇藝術珍品——“臨川四夢”。四部作品都有“夢境”情節,從題材上可以分為兩類,《牡丹亭》《紫釵記》屬于愛情題材戲,《邯鄲記》《南柯記》是度脫世人題材戲。學界認為《南柯記》《邯鄲記》是符合作者主觀意識、觀照內心的巨作。《邯鄲記》作品中充斥著隱退出世的仙佛道思想,告誡人們宗教可以帶給塵世中螻蟻般的人以通悟、智慧、豁達;《南柯記》告誡人們只有通過宗教才可以找到救贖自己的良方,把證道飛仙當作人生價值的最好體現。
在明清女性劇作中,女性形象除了通過喬裝的方式,以男性身份表達自身愿望以及對理想的追求之外,也通過夢境的方式轉換性別,以男性身份表達自我,展現精神困境和封建專制時代自身對性別的反思。此類劇作,明末清初葉小紈《鴛鴦夢》開了先河,清中期王筠《繁華夢》繼之,清后期有何佩珠《梨花夢》,三部劇作創作時間跨度近150年。葉小紈在《鴛鴦夢》中,借男子之口抒發對姊妹的思念;王筠在《繁華夢》中,借男兒之身求得功名,展現了她對封建時代性別的反省;何佩珠在《梨花夢》中,借男性身份追求女性,反映她對精神知己的渴求。
一、鴻鵠志躊躇,一朝嘆蹉跎——精神危機之夢
湯顯祖一生坎坷,戲曲創作是其逃避殘酷現實、疏解精神的方式。如果說湯顯祖的《南柯記》對現實社會政治的批判還留有余地,那么他晚年最后的作品《邯鄲記》,則是其官場失意、痛失愛子、徹悟之下對顛倒“情理法”的黑暗現實更為理性的表達,諷刺也更為尖銳。
首先是批判晚明時期金錢至上的觀念。《邯鄲記》中,盧生依靠崔氏一步登天,靠金錢顛倒人生,“文章敕動君王在落卷中翻出做個第一”[1]255。金錢通天本領的背后是科舉制度的黑暗。盧生高中后,開始用自己的才智“建功立業”,開河鑿石、鹽蒸醋煮耗盡百姓血汗;為迎皇帝巡幸新河,又精心挑選彩女千名搖櫓,以悅龍顏。種種“功績”不利人民,反苦百姓,然而盧生卻憑著“河功”、帝王寵信,在官場上平步青云。奸臣宇文融嫉妒盧生,生出一條條奸計使得皇帝對盧生的態度一變再變,盧生的官宦生涯因此一波三折。官場上黑暗的權勢斗爭、勾心斗角以及皇帝任人左右的昏庸躍然紙上。晚年盧生權勢達到頂峰,誠如盧生所言:“大丈夫當建樹功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饒,然后可以言得意也。”[1]346然而,得意至極的盧生終究還是夢醒了。從入夢到夢醒,不變的是殘酷、荒唐的黑暗現實,變的是心隨境轉、迷失自我、腐朽荒淫的盧生。無獨有偶,《南柯記》中,淳于棼初任南柯太守時,戒除酒癮,造福一方,備受南柯百姓愛戴。后官拜左丞相,于朝堂之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滔天的權勢最終讓淳于棼迷失自我,嗜酒縱情,甚至于淫亂宮廷。“淳于棼的善始而繼之以惡終,表現了在渾濁的官場中人格的扭曲、人性的墮落和靈魂的污染。”[2]172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說,渾濁的官場猶如一個大染缸,任憑自身清正廉潔、清心寡欲,一旦到了權力的核心位置便身不由己,喪失主觀能動性,最終人性墮落、人格扭曲。淳于棼和盧生是湯顯祖筆下的玩偶,提線的卻是明中后期黑暗骯臟的官場,湯顯祖否定的不僅是淳于棼與盧生,還有對封建黑暗政治現實的強烈抨擊與揭露。
其次,對封建禮教偽道學的諷刺也極為深刻。如《邯鄲記》中《極欲》一出,盧生建功歸來,皇帝以24名女樂為賞,盧生內心狂喜,表面卻大肆批判女色:“小人戒色,須戒其足。君子戒色,須戒其眼。相似這等女樂,咱人再也不可近他。”冠冕堂皇的道學言論,其妻聽罷便道:“這等,公相可謂道學之士,何不寫一奏本,送還朝廷便了。”盧生則道:“這卻有所不可,禮云不敢虛君之賜。所謂卻之不恭,受之惶愧了。”盧生既要縱欲淫樂,又標以禮法君子。他命女樂:“每房門上掛一盞絳紗燈為號,待我游歇一處,本房收了紗燈,余房以次收燈就寢。倘有高興,兩人三人臨期聽用”[1]427。
盧生、淳于棼的夢醒是湯顯祖對官場幻想的破滅,夢醒時刻面對現實之痛楚,只有通過求仙證道來應對精神困境。湯顯祖以夢托情,以夢喻志,以夢寫實,以夢刺實,完全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手法。這種手法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作者用以反抗黑暗勢力的巧妙武器。“它并不違背全劇的主題,相反,給全劇增添了一層保護色,更有利于作者進步的政治思想傳播。”[3]兩部作品結尾之處看似“播道”的背后,實則是對封建社會的尖銳諷刺。
二、不能身貴不能仙——現實困境之夢
明清女性作家的“夢幻”戲劇作品大多以自身生活經歷為藍本。封建時代,女作家因為女子之身,無法在現實中表達自我,只能在文學營造的一方空間內,吐其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在劇中“夢幻”形式下、“女扮男裝”之性別錯位的敘事中,女性作家得以抒寫情志。《鴛鴦夢》《梨花夢》《繁華夢》等幾部女性劇作在夢醒時分的感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時期知識女性的精神困境。
《鴛鴦夢》:
【煞】(末)為嗔癡久戀身……今已后同登碧落,共渡悲航。
【尾】端的是千里故人逢……一任俺大地翱游也只半晌。[4]26
《鴛鴦夢》中蕙百芳、昭綦成、瓊龍雕三人與葉氏三姐妹(葉小鸞、葉小紈、葉紈紈)不但表字一致,而且年齡一致,另有昭綦成、瓊龍雕相繼而逝的情節與現實中葉小紈姊妹相繼而逝的現實呼應,足見這部劇是葉小紈悼念姊妹情深的抒情劇。蕙百芳角色在劇中的悲嘆、傷情,正是葉小紈精神情感的外化。“今已后同登碧落,共渡悲航”亦能看到葉小紈在現實中求而不得,遂于亦真亦幻的仙佛宗教中找尋其姊妹的身影,并妄想同登碧落,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釋懷內心的苦楚。
《梨花夢》: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黯離情若個憐……倍覺凄涼!
【清江引】浮生幻影原如電……分不出女和男同一現。[4]290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講述杜蘭仙被二位姐姐送上紅塵道中,黯然神傷魂欲斷,相思淚虛空成串,夢醒后,倍覺凄涼。【清江引】“浮生幻影”感嘆人生無常,夢中稍縱即逝的美好時光如曇花一現。杜蘭仙對梨花仙子的相思之情來源于新婚不久的少婦杜蘭仙對東鄰女伴的懷念,由于身份、地位的一致性,她們容易成為知己,產生精神共鳴。劇中,閨閣密友間的游玩、夢醒后的思念都有著深層的社會根源和情感指向,一定程度上傳達出封建才女對心靈知己的渴求。
《繁華夢》:
【沽美酒帶太平令】見雙鬢云路迎……俺引恁朝元果證。
【清江引】無端一覺消春夢……方曉得女和男一樣須回省。[4]141
王筠作為一名才女,美好的青春不得不沉埋閨閣。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然囿于女子之身,自己的才華無處施展。因而她討厭自己的女兒身,唯有借劇中胸懷壯氣的王夢麟,一飛沖天,實現自己對男權的幻想。夢醒后的王夢麟仍處在閨閣之中,宛如現實中依舊處于“樊籠”之中的王筠。【沽美酒帶太平令】中麻姑允諾她洗盡塵心后,引她超脫凡世;【清江引】中王夢麟感嘆:“三生情枉癡,一笑今何用?方曉得女和男一樣須回省。”全劇以王夢麟悟道作為結尾,同時也表達了王筠對封建時代兩性地位的反思。在王筠看來,唯有證道才能擺脫如夢幻泡影般的人生。
結語
封建時代,男尊女卑的等級意識使女性的一生大多是從自家的“閨閣”進入夫家的“閨閣”。游玩交友、考取功名、建功立業等往往是男性權力的專屬。女性作家無法走出閨閣,她們的創作多是從自我角度出發,向閨閣生活取材。她們的戲曲作品在情節上雖不如男性作家曲折婉轉、豐富多姿,但不能因為歷史局限性而否定其中蘊含的知識女性的豐富內心世界,從而忽視女性作品的潛在價值。
“夢最顯著的作用便是讓人看清自己心底的欲望,以及其不可能實現的悲哀。”[5]男女作家劇終夢醒時分的感慨絕不是空穴來風,現實中所缺少的正是夢中苦苦所追求的。他們都在劇終夢滅之際感慨人生如夢,并在夢醒時分醉心于宗教以實現人生“超脫”。湯顯祖的人生如夢,實則是對封建黑暗官場社會的控訴、嘲諷封建禮法后的超脫精神的外化;而女性作家的人生如夢,則更生動地展示了明清時期女作家的精神寄托和內心世界的壓抑與焦慮。與湯顯祖看破紅塵的升仙之夢不同,女性作家無法掙脫黑暗封建綱常之鎖,夢醒后仍將自己禁錮于“樊籠”之中,選擇回歸悲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