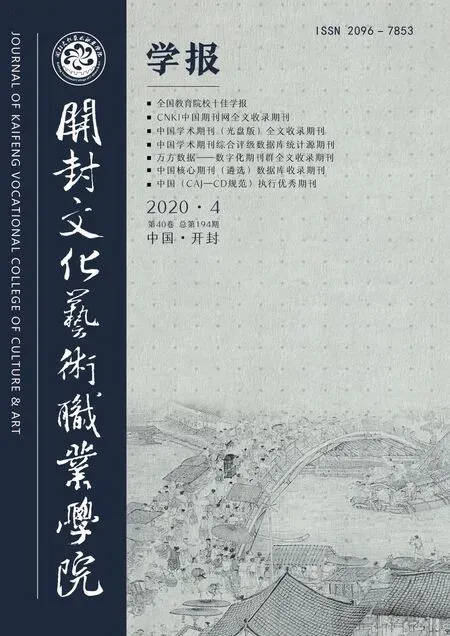從《亡人逸事》看中國傳統女性的幸福與悲哀
劉寧寧
(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亡人逸事》是孫犁創作的一篇散文,內容主要描寫亡妻。孫犁主要描寫與妻子如何認識和婚后的點點滴滴,如小橋流水,娓娓道來,但在平淡的敘述中,給人以無限的最柔軟的心靈觸動。
一、作為傳統女性的妻子形象
《亡人逸事》中的妻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首先,婚姻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文章開頭便交代了“我”與妻子的婚姻是舊式婚姻。舊式婚姻就是兩人的結合并不是建立在彼此了解、相愛的基礎之上,而是由于偶然原因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婚姻。其次,禮教觀念較重。例如,作者回憶與妻子在婚前唯一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我”的一位遠房姑姑特地叫“我”去妻子的村莊看戲,并把“我”領到一條長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著三個大姑娘,在聽到“我”的名字后,中間的一個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后,便從板凳上跳下來,鉆進了照棚外面的一輛轎車里,這個姑娘就是“我”的妻子。可見,妻子是一個深受封建禮教影響的傳統女性。在中國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個被嚴格限制的弱勢群體,她們深受封建禮教的束縛,缺乏自由。自學齡開始,男女兩性便隔離生活,“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1]。因此,在傳統觀念里,女子不能隨便見陌生男子,定了婚的男女更是禁止見面,從妻子見到“我”后近乎逃跑的反應可以看出,傳統禮教在她的思想觀念里已根深蒂固。再如,結婚多年后,“我”路過妻子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卻嚴肅地說:“你明天叫車來接我吧,我不能這樣跟著你走。”這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即使是結婚多年的夫妻一起走在路上也會被認為是輕浮、隨意的行為,因此妻子才會如此“不近人情”地不跟丈夫回家。
二、以妻子為代表的傳統女性的幸福
在《亡人逸事》中,妻子的幸福首先體現為婚姻的甜蜜。文中第一節,作者將與妻子的婚姻稱為“天作之合”,足以見作者對自己婚姻的滿意。而妻子在懂得“天作之合”的含義后更是表示:“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來!”從這簡單的一句話便可以看出妻子對“上天安排的姻緣”非常滿意,言語中透露著嫁給丈夫的喜悅[2]。傳統的封建婚姻都是由父母包辦的,婚前男女雙方基本都未曾見過面,更不要說互相了解了。對于舊時的女子而言,既嫁從夫,結了婚以后丈夫就是自己最大的依仗,所以能嫁給一位自己滿意的丈夫可以說是自己一生幸福的基礎。此外,對于夫妻新婚時的相處,作者并沒有過多描述,但從他教妻子學認字也可以窺探出夫妻新婚時的甜蜜。
其次,妻子的幸福體現為家庭的和睦。對妻子這樣的傳統女性而言,婚后的家庭就是其全部,而婚姻家庭生活中,除了丈夫,還有公婆和孩子。從文中可以看出,婆婆雖然勤勞嚴厲,但對妻子并不刻薄,婆婆叫妻子早起勞作,但自己起得更早;讓妻子背北瓜,妻子背不動,母親也沒有責備她,而是笑著自己把北瓜背回去。從婆媳相處的場景中可以感受到長輩對晚輩的慈愛。另外,作為一個女人,她與丈夫有兒有女,家庭圓滿,這是像妻子這樣的傳統女性最大的幸福。
妻子的幸福與其容易滿足的性格密切相關。例如,在最后一節,妻子臨終前回憶丈夫給自己買花布,丈夫為了讓她方便做衣服,貼心地將花布寄到了娘家,這對妻子而言,是丈夫對自己關心體貼的表現,想到這點,妻子是滿足的。但實際上,丈夫對妻子的關心較少,“我們結婚四十年,我有許多事情,對不起她,可以說她沒有一件事情是對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一件寄花布的小事都能讓妻子記憶多年,可見妻子對丈夫的要求并不高,在妻子看來,丈夫對自己有過關愛,這就足夠了。作為傳統女性的妻子,在夫妻情分上是比較容易滿足的,這與傳統女性一直被要求“以夫為綱”有關,對她們而言,丈夫對自己尊重,不離不棄,白頭終老,這樣就很滿足了,如果丈夫再有些許關愛體貼,這就足以讓她們感覺到幸福了。
三、以妻子為代表的傳統女性的悲哀
初讀《亡人逸事》,是在高中課本上,當時關注更多的是作者對亡妻真摯的情感。現在再讀,能進一步體會到以妻子為代表的傳統女性的悲哀。首先,關于婚后生活的描寫,讀者看到了妻子賢妻良母的形象,但卻看不到多少夫妻之間相處的情景。作者在最后一節中也交代了與妻子是“相聚之日少,分離之日多;歡樂之時少,相對愁嘆之時多。我們的青春,在戰爭年代中拋擲了”。夫妻之間相處時日少,與當時的現實環境有很大關系。在之前動亂的年代,乃至后來雖然和平但物質匱乏的年代,養家糊口都存在較大困難,夫妻之間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恩愛相處,這是整個時代與社會環境所致。身為丈夫的“我”常年在外為生計奔波,而妻子在家獨自承擔贍養老人、養育孩子的重任,“所有這一切,都得自己一個人默默承擔,作者常年不在家,不能分擔這一切辛苦,也不能給妻子一個傾訴的依靠”[3]。文中的作者與妻子相處甚少,除了客觀原因,還與兩人之間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差異有很大關系。妻子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傳統女性,而作者卻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著名作家,兩人在思想觀念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很難有思想上的溝通和深層次的情感交流。作為傳統女性的妻子,也許從未與丈夫有過深層次的思想交流,靈魂上的溝通,也許從未真正地懂過自己的丈夫,這是作為妻子的一種悲哀。
其次,妻子婚后對家庭幾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但在養家育兒、共同生活中,夫妻雙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平等。眾所周知,在中國封建傳統中,父權制是社會的基礎,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三綱五常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在作者描述的家庭生活中,身為丈夫的“我”外出謀生,而妻子在家照顧家庭,妻子的全部生活可以說都是圍繞著丈夫及家庭進行的。作為中國傳統女性的妻子,禮教觀念根深蒂固,自覺遵守傳統社會中男主女從、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觀念。“作為女性,她們最高的人生價值、美德規范就是做一個孝婦、賢妻與良母。”[4]與此相應,在社會角色定位上,作為男性的“我”處于支配者的角色,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而身為女性的妻子處于從屬性角色,她被期待為賢惠的妻子、盡職的母親、孝順的兒媳,沒有主體性,沒有獨立的人格,她是男性的附屬物,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只有在與男性發生聯系時才能夠被展現出來。從作者的描寫中可以看到,妻子為家庭付出了一切,從未出嫁前嬌慣的小女兒,到婚后早起、下地勞動、紡線織布、遠路糶米的辛勤持家,再到丈夫常年不在家,獨自養育幾個孩子。作者回憶妻子養育孩子的場景,“每逢孩子發燒,她總是整夜抱著,來回在炕上走”。妻子獨自照顧孩子的場景讓人讀來心酸,甚至連作者回憶起來也對妻子充滿愧疚,但也無力改變。在當時的家庭生活中,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是妻子的悲哀,是中國傳統女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