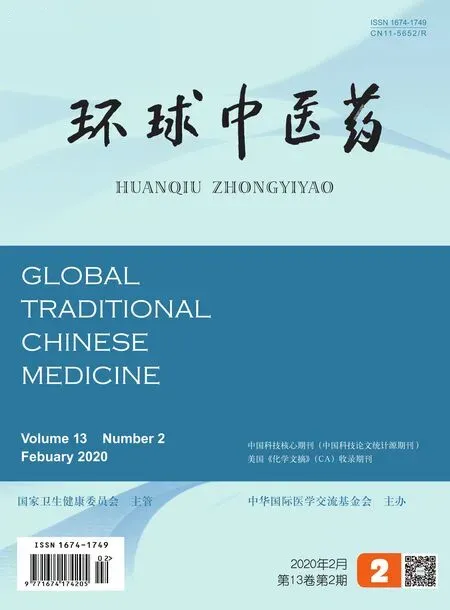中西醫結合治療腎移植術后糖尿病一例
李麗娟 潘滿立 王靜飛
隨著手術技術的發展和各種免疫抑制劑的應用,實體器官移植的數量和存活受者數量得到了明顯增加。器官移植受者的生存時間延長,代謝性疾病的發生率也隨之升高[1],移植后糖尿病(post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mellitus,PTDM)就是腎移植術后常見的并發癥。如果PTDM控制不佳,不僅影響移植腎功能,還影響腎移植患者的遠期生存率。筆者通過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1例腎移植術后糖尿病患者,療效滿意,現介紹如下。
1 病例摘要
患者,女性,56歲,主因“同種異體腎移植術后1年余,血糖升高10個月”于2018年9月12日來本院內分泌科住院治療。患者2017年2月因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癥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九醫院行同種異體腎移植術,術后腎功能恢復正常,采用口服他克莫司+嗎替麥考酚酯+醋酸潑尼松三聯免疫抑制劑方案維持治療。10個月前常規復查時發現血糖明顯高于正常,診斷為“繼發性糖尿病”。經胰島素四針強化治療2周后改為口服降糖藥至今,具體方案為瑞格列奈片口服2 mg(3次/日) ,阿卡波糖片100 mg(3次/日),隨餐嚼服,隨機指血血糖:6.5~11.4 mmol/L。9天前感冒后出現口干、周身乏力,自測血糖較前明顯升高,隨機指血血糖:12.6~21.2 mmol/L。既往原發性高血壓病史20年,口服纈沙坦膠囊80 mg(1次/日)、非洛地平緩釋片5 mg(1次/日),血壓波動在110~125/60~80 mmHg。否認糖尿病家族史。入院后查三大常規、肝功能、離子、凝血功能、紅細胞沉降率、血脂、甲狀腺功能、女性激素、骨代謝均未見明顯異常;腎功能:肌酐71 μmol/L,尿素氮6.1 mmol/L,尿酸286 μmol/L;糖化血紅蛋白 7.9%;糖尿病抗體陰性,血清C肽:空腹1.7 ng/mL、餐后1小時 4.6 ng/mL、餐后2小時 5.4 ng/mL、餐后3小時 2.9 ng/mL;下肢動脈超聲:下肢動脈粥樣硬化伴斑塊形成;眼底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肌電圖:雙下肢感覺神經輕度受損。入院后予以二甲雙胍緩釋片1 g(1次/日)、沙格列汀片5 mg (1次/日)口服,甘精胰島素8~14 iu睡前皮下注射,血糖逐漸控制理想。
入院癥見:口干多飲,乏力,時有胸悶氣短,納差,失眠,眠淺夢多易醒,二便調。舌質黯紅,苔薄黃不潤,脈弦細。西醫診斷:(1)繼發性糖尿病;(2)同種異體腎移植術后 ;(3)原發性高血壓病。中醫診斷:消渴病之肝郁化熱證。治法:疏肝清熱。方用化肝煎加減,處方:牡丹皮10 g、梔子10 g、赤芍10 g、青皮10 g、陳皮10 g、柴胡 10 g、薄荷10 g、澤瀉10 g、浙貝母10 g、珍珠母30 g、丹參10 g、砂仁6 g,5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囑其忌食辛辣,避免勞累。
2018年9月17日二診:患者訴口干、乏力、胸悶氣短較前改善,夜眠略有好轉,仍納食不佳。舌質黯紅,苔薄黃轉潤,脈弦細。上方加焦三仙各15 g,7劑,服用方法同前。
2018年9月24日三診:患者口干渴、胸悶氣短消失,納食改善,睡眠仍較淺多夢。舌質黯紅,苔薄黃,脈弦細弱。上方去砂仁、薄荷、浙貝,改梔子6 g,加白芍10 g、當歸10 g、生地黃15 g、山茱萸15 g,7劑,出院帶藥。
2018年10月9日四診:患者已將睡前甘精胰島素減量至6 iu皮下注射,測空腹指血糖波動在4.6~6.3 mmol/L水平,囑停用甘精胰島素,繼續原劑量口服二甲雙胍緩釋片、沙格列汀片。自訴體力增加,情緒平穩,偶感乏力,納眠可,大小便正常。舌質黯淡,邊有齒痕,苔薄白,脈細弱。現諸癥平穩,前方去珍珠母、赤芍,易生地為熟地15 g,加山藥20 g、茯苓15 g、懷牛膝15 g,14劑。其后,患者多次復診,隨癥調方,未再出現口干、納差、失眠等癥,乏力感減輕。12月23日復查糖化血紅蛋白6.7%,肝腎功能均正常。
2 討論
血糖異常是實體器官移植后的常見并發癥,增加移植物丟失、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和死亡率。2013年美國腎臟數據系統報告顯示,成人腎移植后3年內糖尿病的發生率為 41%[2]。術后1 年內是發病高峰期,1 年后發生率顯著下降,該患者即為手術9個月后發生PTDM。年齡、肥胖、基因背景、代謝綜合征、HCV感染和某些免疫抑制劑等多種因素共同參與了腎移植術后糖尿病的發生,尤其以糖皮質激素等免疫抑制劑的應用為重要的致病因素[3]。腎移植術后糖尿病的發病機制與2型糖尿病相似,主要包括胰島素敏感性降低和β細胞功能衰竭兩個方面。根據 ADA指南,PTDM的治療和管理也主要參考2型糖尿病,保護胰腺分泌功能是治療的重要策略[4]。需要指出的是,在選擇降糖藥物時,要充分考慮移植器官的功能和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
2.1 中醫辨治思路
本案患者為本科室遇到的第1例PTDM患者,對于此類繼發性糖尿病的中醫認識,可參考的相關文獻論述較少。糖皮質激素的應用是其發病的重要因素,因此筆者從激素角度對其病因病機進行分析。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外源性激素為純陽燥烈之品,類似于溫陽藥,其作用多與腎相關[5]。從激素的早期使用,到長期維持階段,再到逐步撤減,直至停藥,從中醫證候學角度來講,機體大致呈現“陰虛火旺→氣陰兩虛→陽虛→陰陽兩虛”的變化過程[6]。如仝小林教授認為,激素原因導致的類固醇性糖尿病多有明顯的火熱內熾,陰液虧損之象,當以滋陰降火為主,可以知柏地黃丸為基礎方加減治之[7]。該患者入院時口干多飲、乏力癥狀明顯,苔薄黃不潤,似與陰虛內熱征象吻合,但在詳細交談過程中得知患者移植的腎來源于胞妹,莫大恩情無以回報,感冒后更是擔心身體每況愈下,心境愁郁,時有嘆息。中醫學中,肝屬“厥陰風木”,主疏泄,喜條達而惡抑郁,調暢情志,調節氣血運行,協調五臟氣機升降出入,調控整個機體新陳代謝的動態變化。筆者認為,激素在發揮抑制免疫、抗排斥、抗變態反應等作用時,機體是處于低反應、低水平的抑制狀態。在此狀態下,肝臟的疏泄調節功能勢必先受影響,疏泄失司,肝氣郁滯。通過檢索文獻發現,現代醫家亦有從肝認識激素不良反應的見解,大多散在于對某個具體疾病的認識當中。如傅文錄[8]指出腎病綜合征發病初期大多屬命門火衰、水濕泛溢之證。命門火衰者,運用激素來溫補命門之火是為第一要法。但是,當遇溫補命火不應,或者純陽體質的患兒,或時值陽盛之夏季,不恰當的使用激素,不僅陽氣不易升發,往往還使少陽樞機不利,氣機郁滯。糖皮質激素為治療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的首選用藥,而長期使用激素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王瓔等[9]采用疏肝解郁為法的加味小柴胡湯聯合強的松治療ITP,并與單用強的松治療對照觀察,結果顯示聯合應用既能明顯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又能增強止血療效、延長有效期,減輕激素的不良反應。
對于本患者而言,外源性糖皮質激素的補給,導致了肝失疏泄,肝氣郁結,不得宣泄。一旦再遇精神刺激,則生陽火而爍陰津,津虛火實,臟燥無液,求救于水,代謝失控,發為消渴。肝郁化火,火邪肆虐,犯肺、乘胃、擾心,故表現為口干、乏力、納差、失眠等癥狀。正如《醫學真傳·三消癥起于何因》說:“消癥生于厥陰風主氣,蓋以厥陰下水而上火,風火相煽,故發生消渴諸癥。”
2.2 選方用藥
本患者PTDM病機責之于肝失疏泄,郁久化火,故首診以疏肝清熱為法,方用化肝煎加減,“清化肝經之郁火”。方中丹皮微涼而辛,善行血滯,滯去而郁熱自解;梔子味苦氣寒,陰中有陽,“解郁熱,行結氣,其性屈曲下行,大能降火,從小便泄去”;赤芍養陰涼血,助丹皮、梔子清瀉肝火之功;青皮、陳皮、柴胡、薄荷疏肝氣之郁滯;澤瀉滲水去濕,利小便以瀉伏火,使熱有出路;浙貝母善開散結,佐金制木;珍珠母平肝潛陽;丹參涼血柔肝;配砂仁調胃和中。諸藥合用,共奏疏肝清熱,調達氣機之功。二診時患者口干、乏力、胸悶氣短、失眠均有好轉,仍納食差,考慮為肝木橫犯脾土,脾失健運之功,故加入焦山楂、焦神曲、焦麥芽以健脾助運。三診時患者諸癥減輕,唯眠淺多夢較為突出,考慮與肝火日久,劫灼肝陰,陰不制陽有關,正如《丁甘仁醫案》中云“郁火宜清,清火必佐養營”。因郁熱已減,故去砂仁、薄荷、浙貝,減梔子用量,加白芍、當歸、生地等以滋陰養血柔肝。四診時患者病情平穩,偶有乏力,此為邪氣漸去,故去珍珠母、赤芍、生地,酌加熟地、山藥、茯苓等藥物,取六味地黃丸之意以補益肝腎,扶助正氣。
2.3 臨床啟示
腎移植術有效提高了終末期腎病患者的生活質量,但PTDM的發生削弱了腎移植的優勢。早期診斷、合理管理是治療PTDM的重要策略。PTDM屬繼發性糖尿病,激素的應用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大部分學者從激素“其性為陽,主入腎經”的角度入手來闡釋類固醇性糖尿病的中醫病機和治則治法。筆者根據本案患者舌脈征象,判斷其主要病機為肝失疏泄,肝氣郁滯,久而化火,治以疏肝清熱,養血柔肝為法,減輕了激素的不良反應,并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疾病的發生、發展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因此在臨床實踐中,除了把握疾病本身發展變化特點,也要根據個體的具體情況不同,分析疾病證候規律的常與變,抓住關鍵病機,才能給予針對性的有效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