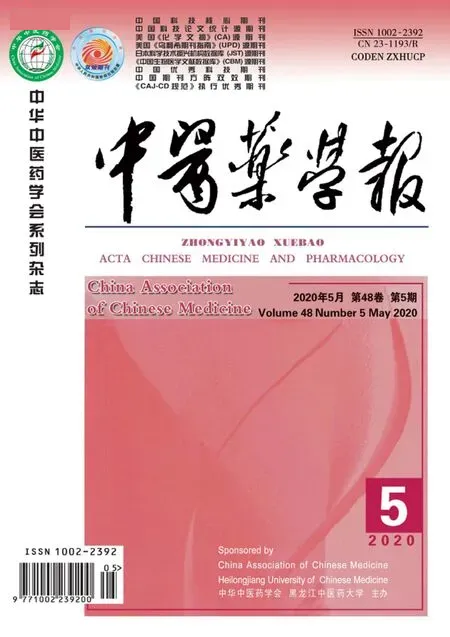林慧娟治療慢性心衰中寒涼藥的理論探討及應用
呂佳譽,林慧娟,蘇文革,崔向寧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014;2.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東 濟南 250014;3.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林慧娟,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教授,碩士博士生導師,山東省名老中醫,全國第三、第四批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曾任中國中醫藥學會內科專業委員、中國中醫藥臨床藥理專業委員會委員等,從事心血管研究50余載,勤于臨床,精于鉆研,提倡中西結合,善于用中醫的理法方藥治療心力衰竭、復雜性心律失常、頑固性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
近年來,隨人口老齡化及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中國心血管疾病呈明顯上升趨勢,據2014年中國心血管病報告[1]指出,目前我國心血管疾病死亡原因占城鄉居民總死亡原因的首位。且心力衰竭作為各種心血管疾病發展而致的終末階段,具有發病率高、預后差、年病死率高的特點,已然成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2]。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GHF)主要表現為呼吸困難、疲乏無力和體液潴留(肺淤血、體循環淤血及外周水腫)等,在中國古代文獻根據其癥狀和體征可歸于“心痹”“心水”“心咳”“水腫”“咳喘”“心臟麻痹”[3]等門中,最早《靈樞·水脹》中“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咳……如裹水之狀”的描述與心衰腹水頗有相似之處。大數據統計顯示,中醫治療在改善心衰患者心功能、提高其生活質量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4],也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心力衰竭的重要意義。
1 慢性心衰的病因病機認識
1.1 西醫對慢性心衰的生理病理機制認識與治療
現代醫學對心衰的認識從最初的鈉、水潴留模式給予利尿劑治療,到后來的血液動力學異常模式給予強心和擴血管治療[5],近50年來,由于1987年ACE抑制劑治療心力衰竭成功降低心衰死亡率27%的驚人成果取得,對其生理病理機制認識逐漸轉變為神經體液機制并延續至今,目前認為神經內分泌系統在心力衰竭的自發進展中主要通過以下方式:①為了保持重要器官的充分灌注,交感神經系統被激活,導致心肌收縮力增強、耗氧量增加;②腎上腺素能系統和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RAA)系統的激活也會導致心肌纖維化,從而增加心肌的硬度,破壞舒張期的左心室舒張功能;③RAA系統的長期激活破壞心室重構,導致心肌組織凋亡破壞[6],此外精氨酸加壓素、利鈉肽類、內皮素、一氧化氮、緩激肽等體液因子也參與心肌和血管重構[7]。因而,相應采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ACEI、ARB或ARNI)、β受體阻滯劑、利尿劑等聯合治療[8]。
1.2 近現代中醫對慢性心衰的病機認識與治療
上世紀,大多數中醫學者認為慢性心衰的基本病機以氣虛陽虛為本,瘀血水飲為標,治療以益氣溫陽、活血利水為基本治法[9]。然而基于近年來多項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結果來看[10-11],陰虛及合并其他證型的比例(如兼見氣虛、痰濁、瘀血等)整體上不低于陽虛及其合并證型的比例,甚至在心衰早期心功能Ⅱ級的中老年患者中高于陽虛及其合并證型比例。2014年發布的《慢性心衰中醫診療專家共識》認為,慢性心衰本虛以氣虛為主,常兼陽虛、陰虛;標實以血瘀為主,常兼水飲、痰濁[12]。且此六種癥候要素流行病學調查所占比例較高者為氣虛、血瘀、其次為陽虛、陰虛、水飲、痰濁[13]。在治療上則相應予以益氣、活血、溫陽、養陰、利水、化濁等方法。
2 寒涼藥物在慢性心衰應用中的理論探討及臨床總結
2.1 陽虛及其合并證型,益氣溫陽,佐以寒涼
陽虛及其合并證型主要包括陽氣虧虛、陽氣虧虛血瘀、陽虛水泛、陽虛血瘀兼痰飲、陰陽兩虛等。陽虛患者常在心衰癥狀上并見畏寒肢冷、神疲乏力、精神不振、脈沉遲或弦緊或無力、舌淡或胖有齒痕等陰性癥狀或體征,伴脾陽虛者多見納少腹脹、腹痛便溏、喜溫喜按、肢體困重,或周身浮腫等,伴腎陽虛者多見腰膝酸軟、下肢無力、大便久泄、或水腫、小便不利或清長、夜尿頻繁等。
慢性心力衰竭陽虛證型的治療常以益氣溫陽為基本原則,根據其合并證型予以相應的活血、利水、化濁等,常用方劑為真武湯、補陽還五湯、苓桂術甘湯、保元湯等,林教授在臨床治療此類證型常佐以寒涼之品,如酌情配伍苦寒之丹參、玄參、苦參、黃連,甘寒之麥冬、西洋參、玉竹,咸寒之地龍、牡蠣等,對心衰患者癥狀改善及預后往往有益。其中理論依據可從以下幾處考慮:
一者,林教授認為,溫熱藥物長期使用導致兒茶酚胺蓄積對于心衰患者預后不利,寒涼藥物的使用可改善或抵消這一不良影響。心衰患者本身存在交感神經過度激活、血漿NE水平升高的機體環境,且對NE再攝取減少[14],而NE水平的持續升高會加重心臟負荷和能量消耗,進一步使細胞凋亡、心肌壞死[15]。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溫陽藥物如附子、桂枝等具有擬交感作用,使催化兒茶酚胺生物合成的重要酶—多巴胺β羥化酶(DβH)的活性增加,促進體內兒茶酚胺的生物合成從而具有強心(表現為正性肌力和正性頻率作用)收縮血管、升高血壓、提高基礎代謝率等作用[16],而寒涼藥物可使亢進的交感—腎上腺系統的功能減弱,降低血清、腎上腺中的DβH活性,提高細胞中cGMP 水平,且能夠降低植物神經平衡指數、抑制腎上腺皮質及性腺的作用、降低基礎代謝水平、抑制Na+,K+-ATP 酶活性[17],因而兩者配合使用一定程度上或對心衰患者的預后有長遠意義。
二者,寒熱并用體現中醫上“陰陽相須”的組方思路,也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尚中尚和”思想在中醫方劑學中的運用[18]。中醫自古認為,藥物具有四氣五味,如《景岳全書·氣味篇》中云:“氣本乎天,氣有四,曰寒熱溫涼是也……溫熱者,天之陽;寒涼者,天之陰也。”溫熱者屬陽,主升散、主動而走,能溫能通;寒涼者屬陰,主斂降、主靜而守,能清能定。溫熱與寒涼藥升降相因,陰陽相須,正如《醫原》所云:“用藥治病,開必少佐以合,合必少佐以開,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輔助之功,或反佐以做向導之用。陰陽相須之道,有如此者。”兩者并用以成“相制相佐,相輔相成”之功,作為中醫方書之祖的《傷寒雜病論》多行此法如柴胡劑、瀉心湯劑、梔子劑等。此外,慢性心力衰竭屬于本虛標實的復雜內傷雜病范疇,林教授治療多補虛瀉實、攻補兼施,而現代認為同一方劑之中寒性藥物與熱性藥物同時并用、祛邪與扶正同時并舉[19]的方式對于病機復雜的病癥治療有積極意義。
三者,“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長期使用溫熱藥物可能導致氣耗陰傷,陰陽失衡。“無陽則陰無以化”,陽虛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長期陽虛亦導致陰氣無以生化,從而陰氣不足,單純溫陽、補陽、扶陽更傷伐陰液,故當于陰中求陽,正如張景岳所云:“善補陽者當于陰中求陽, 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因而林教授在臨床對于腎陽虛及心衰后期心腎陰陽兩虛患者多采用右歸丸、地黃飲子等加減,陰陽并補。
2.2 陰虛及其合并證型,益氣養陰,主以甘寒
陰虛及其合并證型主要包括氣陰兩虛、氣陰兩虛血瘀、氣陰兩虛血瘀兼痰飲等。陰虛患者常在心衰基礎癥狀上見畏熱汗出、五心煩熱、咽干口燥、脈細數或洪緩或燥動、舌紅等,伴胃陰虛者常見饑不欲食、口燥欲飲、胃脘嘈雜、大便干結、舌面光鏡等,伴肝腎陰虛者常見腰膝酸痛、眩暈耳鳴、失眠多夢、潮熱盜汗等,治療上益氣養陰,以生脈飲加減補益上焦心肺之陰的基礎上,胃陰虛者合用益胃湯,肝腎陰虛者選用六味地黃湯、左歸飲等,肝郁化火者加入牡丹皮、梔子、郁金、合歡皮等疏肝解郁,合并其他痰、瘀者,相應的予以化痰祛瘀。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寒涼性藥物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林教授認為寒涼藥物的免疫作用或可對逆傳心室重構有益,因為近年來實驗研究反復表明,心臟“無菌炎癥”與左室重構和左室功能障礙密切相關。由于意外壞死、調控壞死(壞死)和/或繼發性凋亡而死亡的細胞將其胞質內容物釋放到細胞外空間,從而通過細胞外或細胞內的PRRs合組激活炎癥反應。因這種炎癥反應發生在沒有已知致病性感染的情況下被稱為“無菌炎癥”[20],而現代藥理學動物實驗表示,寒涼藥通過調節大鼠細胞色素(可引起細胞凋亡)相關同工酶等涉及炎癥反應、應答刺激相關基因及超基因家族的表達而發揮一定的抗炎、解毒作用[21],對心室重構的延緩或逆轉可能有積極意義,具體內容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臨床實踐。
同樣,滋陰藥生地黃、知母等,均可使升高的β受體(AR)減少, cAM P系統反應性降低, cGMP系統反應性增強[22]。臨床上,心衰后期,由于長期利尿劑的使用而常出現陰傷癥狀,但往往病機復雜,多表現為畏寒怕熱、或伴水腫便黏、口干舌燥、舌紅伴胖大或伴舌苔厚膩等陰陽兩虛、痰瘀互結之證,辨證用藥須謹慎斟酌。
2.3 慢性心衰并發癥中寒涼藥物的運用
2.3.1 慢性心衰合并快速型心律失常,重鎮定悸,介以潛之
慢性心衰合并快速型心律失常如房顫、早搏、心動過速等在心衰癥狀上出現心悸、心慌、頭暈等,林教授常選用礦石之類如磁石、龍骨、紫石英等重鎮安神,或介甲之屬如龜甲、鱉甲、牡蠣等潛陽復脈。《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本草論》中論曰:“重,怯則氣浮,欲其鎮也。如喪神守而驚悸,氣上厥以癲疾,必重劑以鎮之”,《本草》曰:“重可去怯……故驚乃平之”,認為重鎮之能夠鎮靜定悸,現代藥理也證實了礦物藥物具有鎮靜催眠、抗抑郁、抗焦慮、抗精神分裂[23]等作用;再者,《臨證指南醫案》中曰:“夫陽動莫制……法當介以潛之,酸以收之,味厚以填之”,認為介類能夠潛陽斂陰熄風,與快速性心律失常突發突止、有如風動之特性相符。
2.3.2 慢性心衰伴胃腸道瘀血,寒溫并用,辛開苦降
在慢性心衰伴胃腸道瘀血時常見納呆腹脹、食欲不振、嗝氣嘔惡、大便黏濁、舌苔黃厚膩、脈濡滑等濕熱中阻證,林教授常以半夏瀉心湯或小陷胸湯加減治療,運用辛開苦降法,即辛溫之半夏、干姜與苦寒之黃連、黃芩配合使用共奏降逆消痞、散結化濁之效;肝脾氣滯者合用四逆散,胃氣上逆者多連用丹參飲,水腫者兼行溫陽利水,苓桂術甘湯、茯苓澤瀉湯等均可辨證選用,長期胃腸道瘀血常導致胃氣虛弱,五臟化源不足而血虧氣弱,治療上在健胃運脾基礎上,注意調補氣血。
對于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肺部感染、肺瘀血等痰熱表現時,則加用魚腥草、黃芩、金銀花、前胡、連翹等清肺祛痰,或地龍、葶藶子瀉肺平喘。此外,這些并發癥的病機仍屬于本虛標實,注意在益氣溫陽或養陰基礎上行瀉實治標之法。
清代醫家徐靈胎在《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中指出:“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時,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其他寒涼藥物的如活血之丹參、赤芍、牡丹皮,蟲類通絡之水蛭、土鱉蟲等運用時常不(光)取其寒涼之性,則歸在其相應的活血、通絡治療應用中,不作贅述。
3 典型醫案舉隅
患者錢氏,男,54歲,2019年1月5日初診,主訴:陣發性胸悶心慌3余年,加重伴憋喘、頭暈一月余。現病史:3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胸悶、胸部隱痛、心慌,伴短氣乏力,勞累后加重,休息后緩解,夜間難以平臥,于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診斷為“慢性心力衰竭”,抗心衰治療后癥狀有所緩解。一個月前上述癥狀無因旅游后勞累加重,伴頭暈目眩,四肢乏力,為求進一步系統治療于我門診就診,現癥見:陣發性胸悶、心慌、短氣,偶有前胸部隱痛,夜間難以平臥,時有憋喘,活動后加重,休息后好轉,頭暈、偶有兩側太陽穴處疼痛,平素怕熱,出汗較多,時有盜汗,易緊張焦慮,全身無力,無雙下肢水腫,無咳嗽咳痰,納可,偶有嗝氣、反酸,口干口苦,眠差,多夢易醒,小便可,大便稍稀,1日1~2行,舌紅、苔白稍膩,脈弦滑數而代。既往史:冠心病5年余,陳舊性心肌梗死(下壁)3年余,2型糖尿病2年余,平素空腹血糖在6.5~7.0 mmol/L左右,目前飲食調養,未行規律藥物治療;房性早搏5年余,高膽固醇血癥5年余,否認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病史,否認肝炎、結核等傳染病病史及其密切接觸史,否認手術史,否認食物及藥物過敏史。查體:血壓117/69 mmHg,脈搏74次/min,雙側胸廓對稱,雙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律欠規整,可聞及早搏,心音低鈍。血清NT-proBNP 3 501 pg/mL;心臟彩超:左房前后徑39 mm,左室前后徑57 mm,射血分數40%(辛普森法),提示:左心擴大;節段性室壁運動異常(左室下壁基底段);二尖瓣中度反流;左室收縮功能減退;心包積液(微量)。心電圖示:竇性心律;房性早搏;ST-T改變。西醫診斷:慢性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肌病,心功能Ⅱ級(NYHA分級);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型心臟病,陳舊性心肌梗死(下壁);心律失常,房性早搏;2型糖尿病。中醫診斷:心衰病、氣陰兩虛,痰瘀互結證,治則:益氣養陰,活血化痰。處方:黃芪50 g,麥冬30 g,清半夏12 g,西洋參10 g,酒五味子9 g,葛根30 g,甘松30 g,丹參30 g,槲寄生30 g,桂枝30 g,生龍骨15 g,生牡蠣15 g,地龍10 g,赤芍15 g,苦參12 g,川芎15 g,膽南星12 g,土鱉蟲10 g,燙水蛭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兩次溫服。諾欣妥、倍他樂克等繼用。注意事項: 調情志,勿勞累,節飲食,忌食辛辣油膩及過咸之品。
2019年1月15日二診,胸悶心慌、乏力怕熱癥狀減輕,睡眠好轉,仍有焦慮心煩,舌苔由膩轉薄白,脈弦滑,處方:上方去膽南星、槲寄生,加郁金12 g,合歡花30 g,14劑,煎服同上,并予以情志開導。
2019年2月3日三診,自述諸癥好轉,無心慌胸痛,勞累后時有胸悶,復查血清NT-proBNP 235 pg/mL;心臟彩超:射血分數62%,左房37 mm,左室56 mm(左室收縮功能有所提高);處方:上方改地龍6 g,加炒白術12 g,10劑,煎服同上。
半月后電話隨訪患者家屬述患者覺諸癥好轉,可日常工作、家務。
按語:患者中年男性,平素焦慮、思慮較多,常有抑郁、悲傷之意,《靈樞·本神》有:“心怵惕思慮則傷神……脾愁憂不解則傷意……肝悲哀動中則傷魂”,且長年眠差、時常操勞,飲食不當,從而肝脾不調,心氣耗傷,而致氣陰兩虛、痰瘀互結,而見上述諸癥,方選生脈飲加減以益氣養陰,活血化痰,其中黃芪、西洋參益氣,麥冬、五味子斂陰生津,清半夏、膽南星化痰,丹參、赤芍、川芎行氣活血,土鱉蟲、水蛭通絡止痛,生龍骨、生牡蠣重鎮潛陽、安神定悸,理法并全,攻補兼施,藥到而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