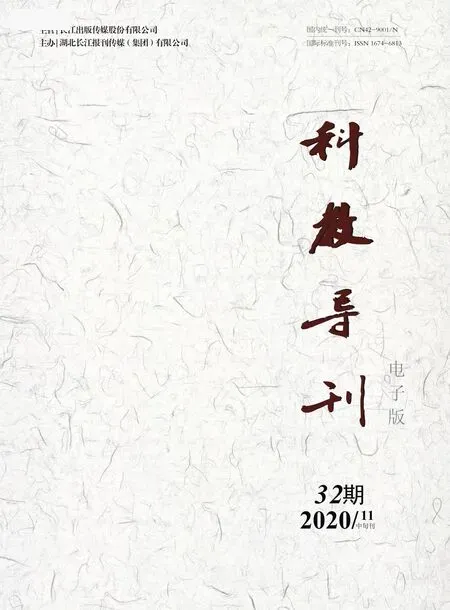我們如何以言行事
——俄語施為動詞研究概覽
馮棟麗
(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 北京 100089)
1 施為動詞與言語行為理論
言語行為理論由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奧斯汀(J.Austin)提出,其代表作《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 things with words)(1962)標志著該理論的誕生。此前對語言的分析主要集中于邏輯方面,研究句子的真值。而奧斯汀認為人們在言說時并不總是在陳述事實或報導信息,因而并不是所有句子都有真假。有些句子是在“以言行事”,奧斯汀將此類句子稱為施為句(performative sentence),并分析了1000多個英語詞典中可構成施為句的施為動詞,據此分出5類言語行為。但正如其學生塞爾(J.Searle)所言,奧斯汀其實是在劃分施為動詞類型,而不是言語行為類型(Searle 1979:9)。這是因為,施為動詞是言語行為類型最明顯的語力顯示手段,而言語行為的基礎是意向性,即說話人想說什么,這也是話語的語力或意向功能核心,施為動詞是說話人意向的載體,可以直接確定言語行為類型,是最強的語力顯示手段。在實際交際中,說話人還可以通過以下手段來明示說話意向:(1)詞形手段;例如用動詞命令式或動詞不定式表指令意向:“”(請坐),或者“”(列隊!);(2)情態詞、語氣詞、感嘆詞;(3)語音手段,包含語調、停頓、語速、重音等。而這些語力顯示手段都較弱,在交際中往往只能作為語力顯示的輔助手段。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言語意向或語力都由施為動詞表達。有的言語意向在語言系統中缺乏相應的施為動詞,只能借由其他的語言手段表達,例如人們常用陳述來實施恭維這一言語行為:(.你看起來氣色真不錯)。有的意向動詞本身沒有施為用法,例如含正面評價意義的動詞等,含負面評價意義的動詞等。還有的動詞雖然含有言說的義素,但不是施為動詞,只能算作言語動詞,例如阿普列相(1986:212)提到的只表示說話方式不含言說內容的動詞:等。由此可見,意向動詞的范圍比施為動詞廣,有施為性的意向動詞可用作施為動詞,有施為性的言說動詞可用作施為動詞。本文只分析施為動詞,也就是在施為句中作謂語的意向動詞,不涉及其他兩類動詞范疇。
2 施為動詞及其用法
雖然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為學界共知,但阿普列相(1986)提出,這一認識早在康什米杰爾及本維尼斯特的著作中就有所論及,只是不為人所共知。康什米杰爾(1969:162)寫道,“我所理解的施為性,就是言說即行事......‘我在寫’只是陳述我在寫這個行為,不是言語行為,而‘我請求你’即是指請求你這件事而不是別的行為,說出‘我請求你’的時刻就是由‘請求你’這個動詞指代的請求你這個行為發生的時刻”。需要注意的是,一詞本身不能算作施為動詞,因為施為的基礎是說者的意向性,而往往是對客觀世界的陳述或報道,因而不能算作施為動詞。阿普列相(1986:210)劃分出了15類純施為動詞:(1)專門的報道和陳述(相當于奧斯汀的陳述類);(2)承認;(3)承諾(相當于奧斯汀的承諾類);(4)請求;(5)提議和勸告類(部分和奧斯汀的裁決類一致);(6)警告和預告;(7)要求和命令;(8)禁止和允許;(9)同意和反對;(10)贊許;(11)評論;(12)原諒;(13)言語儀式;(14)移交、廢除、取消、廢除等社會化行為;(15)命名和任命。
此外,阿普列相對施為動詞的具體用法從詞形、語義、語用三個角度進行了分析。詞形方面,施為動詞的詞形聚合體是不完整的。施為動詞的基礎形式為第一人稱單數現在時主動態陳述式,但在俄語中,施為動詞有多種表現形式:(1)動詞將來時:(我承認,這件事是我做的);(2)不定人稱句中的第三人稱:(請各位旅客按時登機);(3)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被動態:(請各位旅客按時登機);(4)第三人稱,這種情形下說話人一般是某個機構的負責人或發言人:(黨委建議解除鮑里索夫的廠長職務);(5)(請求)(推薦)、(勸告)等詞的假定式形式;(6)表禮貌的話語中動詞不定式形式,例如:(冒昧提醒您)。此外,其他動詞形式和名詞短語等也有施為用法,例如動詞命令式(請原諒)表示道歉,名詞固定短語(說實話)表示承認,語氣詞(謝謝)表示感謝,(行)和(好的)表示同意等等,由此看出,言語行為不一定要有施為動詞參與。
句法上,部分施為動詞用于施為句時支配關系會發生變化:(1)施為動詞的客體可以不出現,因為客體即受話人是在場且確定的,有時沒必要出現。例如:(請你離開這房間),句中省去了客體或;(2)若動詞既可以接從句,也可以接,則前者是動詞的施為用法,因為接時句子往往就會變成陳述句。語義上,由于言語行為的發生具有即時性,施為動詞沒有未完成體的現實延續意義,因而在與很多狀語的搭配上都受到一系列限制,不與等表時間長短的詞連用,不與程度狀語連用,不與表時間同步關系的連用。施為動詞雖然有完成體的完成意義,但不與表時間意義的前置詞連用,如(三分鐘內);由于施為動詞本身就表示行為的發生,因而不與描述行為的詞連用,例如等;不與表評價的連用。由于施為動詞內涵謂詞,因而不與外延謂詞連用,包括等。因而不能說.(我哭著保證不會再犯),但可以說.(她哭著保證不會再犯)。
施為動詞的施為性主要取決于動詞的詞匯意義及其語法意義。雖然很多施為動詞都有(言說)這一義素,但這并不是判定動詞是否是施為動詞的標準。首先,本身就不能算作純施為動詞,其半施為用法往往帶有一定的修辭意義,常見于重復性話語中:(都跟你說了,他已經原諒你了)。不是所有的施為動詞都有這一義素,而有這一義素也不一定是施為動詞。關鍵在于,這一義素構成詞義的陳述部分,而不是預設部分,并且陳述部分的義素不能表示行為方式、目的、評價、多次行為等等。但這也不是判定施為動詞施為性的充分必要條件,例如動詞均表示禁止,均滿足上述條件,但只有前者有施為用法。
3 施為動詞與俄語動詞的時體意義
此外,俄語中動詞的未完成體形式和完成體形式可能分屬不同的言語行為。例如:(請您幫幫我兒子)是請求言語行為,而(請您出示證件)則是要求言語行為,原因不在于說話人的意向強弱,而在于受話人是否有義務完成這一行為。
施為動詞的時體意義還取決于人稱。施為動詞只有用于第一人稱時才有施為性,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第一人稱并非語法形式上的第一人稱,而是指物意義上的第一人稱。此外施為動詞表達持續性動作時會轉化為非施為動詞,例如:.(我求他求了兩個小時,就為了騎個車),這里的為非施為動詞。此外,施為動詞時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與英語中的即刻意義相契合(Simple Present)。利奇(G.Leech)(1971)將英語中的即刻意義分為三種:(1)現場直播式的報導具有的即刻意義;(2)解釋性的報道話語具有的即刻意義;(3)施為動詞的即刻意義。認為,前兩種即刻意義和第三種即刻意義是有區別的,前兩種即刻意義是主觀即刻意義,而施為動詞的即刻意義是一種客觀即刻意義,主觀即刻意義是以說話人的意向為時間基準點,行為可能發生在話語發出時,也可能發生在話語發出前或后。而客觀即刻意義是話語與行為絕對同時發生。
施為動詞的特殊之處在于其未完成體形式可以表示動作結束或完成,而施為動詞一般而言都成對出現,這樣一來,施為動詞未完成體就可以表示與其成對的完成體的意義。原因在于,雖然施為動詞現在時即可表示言語與行為的發生是共時的,但語言系統中有兩種共時關系:時間狀語的所指時刻可歸入動詞所指時刻內,成為后者的一部分,叫做插入共時;時間狀語所指的時刻可包容動詞所指時刻,后者成為前者的一部分,叫做包容共時(武璦華2001:189)。不同的共時關系會影響句子的時間前指,例如插入共時關系(昨天10點時候我正躺沙發上,突然鈴響了),句中鈴響的時間前指是由時間狀語引發的,而包容共時關系(去年我因肺炎生病住院,期間我中學時期的朋友來看我),句中朋友來看我的時間前指不是去年這一時間狀語,而是我生病這一事件持續期間。動詞未完成體表示現實延續意義時,言說時刻與行為之間是插入共時關系,而施為句中言說時刻與言語行為是包容共時,也就是說,言語行為在言說時間內開始并結束,也正因此,施為動詞獲得了完成意義。
4 施為動詞與元話語、插入動詞
其次,施為動詞失去施為性的另一種情形,就是溫德爾(1985)所說的言語行為自毀(。根據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標準的施為動詞是第一人稱現在時主動態,但有些動詞在這樣用時會使得話語的命題內容與動詞本身沖突,造成言語行為自毀,因而這樣的動詞一般只用于描述句,不用于施為句中。例如人們撒謊時不能說來實施撒謊這一行為。此外,部分言語行為動詞的言后取效不可預知,也就是說完一句話并不能確定實施一個行為,因而也沒有施為用法,例如等不能用于施為句。溫德爾認為,言語行為動詞的基本意義在于指示言語目的,因而言說動詞在指示言語行為目的時,如果不是造成言語自毀的破壞因子,就可以充當施為動詞。而言語行為自毀和施為句的區別在于,言語自毀時,主要言說內容與動詞語義相斥,根據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兩者出現在同一句話中,會使得話語因此而分裂成兩個無對話性的話輪。
此外,施為動詞所指的行為必須具有實際的社會規約意義,否則只能算作元話語。例如:.(跟您說個秘密,不是所有人都會死,只是在最后一口氣盡的時候,眨眼之間,突然轉化),說話人在說出這句話時,只是在陳述內容或信息,實際上并未實施言語行為,因而只能算作敘述。另外,在某些情境下,施為動詞的出現會使得句子顯得冗余,例如:(我向您提問,幾點了),因本身就是提問言語行為,因而施為動詞不需要出現。
5 施為動詞和施為假設
言語行為理論也對句法研究產生了影響。隨著對言語行為理論中施為動詞和施為句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有學者提出了施為假設和語用假設,持施為假設的學者認為,每個句子,不管其表層結構是否為顯性施為句,都有一個與顯性施為句的施為前綴對應的結構。即不管話語中的施為用意是顯性的或隱性的,凡是認為施為用意總可以通過施為句表現的觀點,就是施為假設(Sadock,1988)。持語用假設的學者認為,這一表達施為意圖的施為前綴可以由顯性施為句中的施為動詞表達,也可以隱含在語境中,不總是隱含在話語中。試比較:
持施為假設的學者認為,這兩句話有相同的語力,第一句話隱去了施為前綴。而持語用假設的學者認為,第二句話的語力是明確的命令,而第一句話的語力則不確定,可能是勸告、提示或者命令。此外,某些施為動詞只用在特殊語境下,構成顯性施為句,例如在法庭上目擊證人對法官說“”(本人在此聲明,從未見過被告),而實際上,施為句的使用頻率要比非施為句的使用頻率低。
施為假設使話語的邏輯分析陷入了困境,如果任何話語都可以通過施為前綴變成施為句,施為句沒有真假一說,那么所有的話語都無真值可言。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我說的是真的)是施為句,那么根據言語行為的定義,說話人永遠不會說假話,這顯然與實際生活相悖。阿普列相(1986)認為不具有施為性,這樣一來以上問題便迎刃而解。
博格達諾夫(1983)認為,這兩派學者的觀點并非完全沖突,因為沒有施為動詞,同樣可以以言行事,同一語力可用不同的手段來表達,只是語力強弱不同,施為動詞可直接明確話語的語力,而同樣的語力也可以由說話人的語調、重音來表達,只是語力會因此而變弱。施為假設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反對,僅靠施為動詞才可以言行事這一觀點有一定的局限,此后學者們對話語施為性的隱性表達手段進行了研究,施為假設也為塞爾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奠定了基礎。
6 結語
本文從言語行為理論出發,從多個維度展現了俄羅斯學者對施為動詞的研究。從語法角度看,施為概念對俄語學的最大貢獻是豐富了俄語動詞的時體意義(武璦華2001:189)。雖然言語行為理論源自奧斯汀,但由于俄語與英語在語法、語義、語用等方面的不同,言語行為理論及施為動詞在俄語的研究中汲取了新的內涵,煥發了新的生機。俄羅斯學者對言語行為理論及施為動詞的研究不僅豐富了語用學理論,也促進了本土其他的理論創新與研究,例如話語儀式、言語活動論等。筆者水平有限,難免掛一漏萬,尚不足以反應其全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