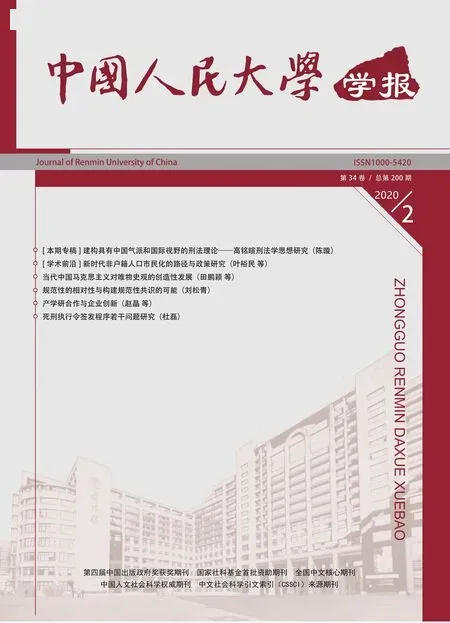規范性的相對性與構建規范性共識的可能
劉松青
從運思到日常的交往,從認知到行動,從制度性構建到群體性合作,規范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它的形式和種類多種多樣,作用的領域也殊為不同。比如,不同的民族、國家或群體,其各個領域的規范常常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民族、國家或群體內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規范也會與時更變。可以說,規范因時因地以及具體的實踐環境而不同。尤其是生活在不同群體、不同文化與文明,甚至不同歷史背景下的人們,在思維、認知及行動方面都會存在差異,在規范層面也會表現出不同的訴求和不同的價值取向。如果規范的多樣性與相對性是基本的事實,那么規范性的統一性或規范性共識就是一個有待辯護和澄清的問題。正如特納(Stephen P.Turner)所言:“規范的多樣性或局部規范性(local normativity)可能會給規范性的統一性帶來嚴重的挑戰,規范主義者需要提供一種有力的解釋,來調和規范的多樣性,以及說明規范的客觀性。”(1)Stephen P.Turner.Explaining the Normativ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p.26.
如果規范性是相對而言的,那么,在各個群體、各個國家交往日益頻繁和深化的趨勢下,我們如何看待不同文化與文明、不同群體或者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在具體規范上的差異以及在規范性建構方面的不同傾向,如何處理現實中的規范分歧及其背后的價值張力,如何避免一種規范凌駕于另一種規范之上,或者如何化解實踐中的規范沖突,就是一個十分重要且緊迫的課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尋求一種更廣闊、更復雜的規范與秩序,向著一種“世界公民”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來運思的話,就必須回答這樣一些問題:(1)規范之不同是否因其背后具有不同的理性訴求或規范性結構?其合理性的依據是什么?(2)不同民族、國家或群體之間的規范存在諸多不同,在這些不同的規范之間是不可逾越的鴻溝還是表面的分歧?(3)構建一種超越局部規范性的規范性共識是否可能?換言之,規范性能否超越特定的利益訴求和特殊的文化身份或群體身份而走向統一或共識?
一、規范性的相對性?
我們為什么會遵從規范?規范性的有效性與約束力因何而來?按照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以及布蘭頓(Robert B.Brandom)等人的理解,規范性的合理性與有效性是“共同體”或“集體意向性”的實踐推理結果,因而“共同體”或者“集體意向性”是理解或解釋規范的約束力或規范性來源的基礎。換句話說,規范性既不是某個個體的獨特創造,也不是先于個體而存在的某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是我們在參與共同體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有效共識。規范性蘊含在主體的實踐之中,它通過作為行動主體的人的規范思考、規范言談、規范推理與規范判斷,編織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理由的規范空間”(normative space of reasons),受“予求理由”(giving and asking for reasons)游戲的指引和支配。
可問題就在于,如果規范性的約束力或它的合理性與有效性是“共同體”或“集體意向性”的實踐推理結果,那么,由于“共同體”在歷史、文化及價值等方面的差異,我們在進行實踐推理的時候難免“是己非人”。至少,在相對主義者看來,不同共同體在文化、禮儀、風俗、政治、法律、道德上總是存在差異或分歧,因而存在一個統一的關于規范的標準或存在一個普遍有效的推理實踐的觀點十分可疑。按照這種思路,如果“理由”是規范性的媒介,那么,我們關于世界的談論就成了相對于“理由的規范空間”或者語言框架內的不同表征系統。這也恰好說明,為什么基于規范言談和規范思想的實踐并沒有將我們領進和平、幸福與真理的烏托邦,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與文明形態之間的沖突以及不同共同體之間的隔閡。如果不存在同質化的“理由的規范空間”或單一的推理模式,那么,以推理實踐為基礎的規范性如何保證其有效性、客觀性和一致性,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特納將規范的多樣性或者局部規范性視為規范性面臨嚴重的挑戰。比如,對于曼哈頓的單身漢而言是規范的,對于安達曼群島的島民來說則不是規范的。因此,規范主義者需要一種規范性的統一解釋,這種解釋可以調和規范性的多樣性,也可以解釋規范性的客觀性。特納認為,如果規范主義者要拒絕或者反對規范的多樣性這一明顯的現實,并且堅持這些表面的多樣性或相對性是純粹誤導,那么,他們就必須發明一種方式來避免將某種規范凌駕于另一種之上的指控,并且找到一種方法來調解現實實踐中的不同。(2)Stephen P.Turner.Explaining the Normativ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p.26.
特納認為,從柏拉圖的“形式理論”到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從弗雷格的“概念”到劉易斯—塞拉斯—布蘭頓的“推理主義”,我們所知的哲學史就是散布在理解世界的嘗試之中。然而,存在一個融貫領域或者理由空間的觀點,必然要受到理解世界的不同嘗試的多樣事實的挑戰。盡管這些多樣性的解釋方案都試圖找出世界的某些共同特征,然而,它們卻將我們帶向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理解,它們試圖找到一個最終的辯護,一個事實開始的源頭,一個邏輯的基本法則,一個推理性的概念,一個基本的標準,或者一個彼此承認的道義計分系統,等等。然而,答案的多樣性制造了更多的麻煩和問題。因為在每一種解釋背后都預設著這樣一種想法:在我們的思維背后存在一個認可它或為它辯護的隱藏的有序結構,但辯護目的的巨大多樣性,以及在它們之間進行抉擇或從一個目的導出另一個目的的困難,常使人覺得,與其說隱藏的是秩序或結構,不如說是混亂,并且要達成大批隱藏結構(所有推理和術語都有一個隱藏的結構這個程度)已經擊敗了結構本身這一想法。除非存在真正有待發現的深層結構,否則我們就必然陷入無數的死胡同。(3)因而,在特納看來,“規范性”這個詞的意義是含糊不清且十分負面的,根據它的語言學功能勉強建立起來的“概念內容”也是有限的,即使它可以被視為人類交互行為的一部分,也是多余的甚至無法解釋的一部分。
比方說,人類推理需要依據某些一般性的原則,諸如演繹論證的原則來進行推理,然而,特納認為,有時候這樣的推理原則并非總是有效的,似乎并不存在一種人們普遍接受的理性推理方式,因為即使某些被公認為有效的推理方式也可能在某些群體中不被使用和理解。特納引述了盧里亞(Alexander Luria)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研究者問一個未受教育的蘇聯農民:“德國沒有駱駝,B是德國的一座城市,城市B有駱駝嗎?”蘇聯農民回答:“我不知道,我沒去過德國農村。”研究者又重復了一遍問題:“德國沒有駱駝,德國的城市B有沒有駱駝?”蘇聯農民回答說:“如果那是大城市,可能會有駱駝。”研究者又問:“如果整個德國都沒有駱駝呢?”蘇聯農民答:“如果B是一個大的城市,那里會有駱駝。”(4)Stephen P.Turner.Explaining the Normativ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p.192,p.35.特納認為蘇聯農民的推理顯然和三段論是相分離的。三段論在此坍塌了,因為蘇聯農民的推理并不是從詢問者的前提中得出來的,其結論和三段論無關。特納認為,這個例子表明人們的實際理性是和規范理性不同的,在解釋人們實際所做與他們實際所思之間有很大不同。因此,與存在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遍理性這種觀點相反,推理只不過是人類理性的一個模型。就像這個例子所表明的那樣,蘇聯農民的推理方式是大多數人不會使用或不能理解的一種模型,然而卻是實際存在的一種“理性”模型,這無疑對理性的普遍性及規范性的客觀性提出了挑戰。
雷爾頓(Peter Railton)對于存在一個普遍有效的推理形式的觀點也表示懷疑,他從邏輯的有效性方面指出了演繹推理存在的困難。在他看來,演繹邏輯實際上并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是合理的、可以相信的,它只告訴我們命題接著另一個命題(或者說,在邏輯真理中,完全不是從命題得出來的)。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如果“我相信p”,并且“p蘊含q”,那么,“我應該合理地相信q”。雷爾頓認為,這樣的推理顯然是邏輯上無效的,因為這個前提可能是從一個附加的前提得出來的:“人們總是應該合理地相信他當前信念中的邏輯蘊含。”但是,這個附加的前提完全不是一個邏輯原則。此外,它也不是一個非常可信的原則,因為這個前提還會要求我們相信無限多的事情;并且,如果剛好有任何和我們信念相反的情形,它可能要求我們去相信所有命題以及它的否命題。演繹邏輯原則毫無疑問是與“人們應該合理地相信什么”這個問題相關的,因為遵循這些原則,或者知道它們的含義,有時服務于實踐推理的目的。因此,雷爾頓認為,人們應該合理地相信什么,這個問題總是屬于實踐理性而非理論理性。(5)Peter Railton.Facts,Values,and Norms:Essays toward a Morality of Consequ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4-45.換句話說,人們可以合理地相信的東西總是處于我們的實踐推理或者說理由空間之中,我們的規范言談、規范思想和規范判斷的合理性,總是我們所在的理由空間之內的合理性。但是,將實踐推理的合理性訴諸共同體,顯然回避不了實踐的相對性問題,因為“理由空間”是有邊界的,不同共同體構筑的“理由空間”也總是存在差異。正如芬利(Stephen Finlay)所言,規范言談和規范思想有時候并沒有將我們帶向共識和理解,反而在丑惡的沖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關系到什么是正義與不正義、什么是善良與邪惡的問題上,不同共同體之間存在著廣泛分歧和敵意。我們似乎缺乏建立關于規范事實的客觀真理的有效方法,因為不能簡單地將那些與我們相沖突的觀點視為不正確的,而將我們自己的觀點視為正確的。在芬利看來,規范分歧,尤其是道德和元倫理學分歧(比如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應該的)在不同方式下包含了一種語言混亂(confusion of tongues),它重建了巴別塔的神話。(6)Stephen Finlay.Confusion of Tongues:A Theory of Normative 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
可見,如果理性的推理模式總是存在差異,那么不同推理模式之下以規范、規則形式呈現出來的事實顯然也具有相對性,包括我們的道德評價與價值評價,都可以看作相對于不同共同體的某種承諾,或者相對于群體的選擇與偏好。這樣一來,從現有的規范事實來看,它們似乎不可能對應一個完全相同的規范真理體系,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意義的客觀性與普遍性,或者說形成一種元規范意義上的規范性共識或重疊共識。如果規范性的效力是基于人們所在的共同體,是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推理結構,那么,這種推理實踐如何保證同一共同體之中的人們不犯錯誤,又如何保證不同共同體之間規范性的統一性,即不發生規范分歧與沖突?畢竟,無論人多么理性,“在推理實踐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7)Robert B.Brandom.“Review:Precis of Making It Explicit”.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7,57(4):153-156.。那么,我們如何才能在推理的維度中理解推理實踐基礎上的規范性?我們如何才能跨越不同共同體或不同“理由的規范空間”來構建規范性的共識?
二、構建規范性共識的基礎
“規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法律的、政治的、道德與倫理的、宗教的、禮儀的、科學的以及日常實踐中的其他規范,都構成規范的不同形態。事實上,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在法律、政治、道德、禮儀、價值等方面的規范也存在差異,他們關于“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正義的”“什么是應該的”等基本問題的理解也確實存在不同,那么,這是否可以說明我們推理理性的失效,或者意味著“怎么都行”?實際上,相對主義者混淆了不同層次的問題,比如,將規范分歧看作某種不可調和的對立,因而混淆了實質性分歧(規范沖突)和可以相容的分歧,將規范性等同于規則意義上的規范,將規范性事實等同于規范性事實的合理性、客觀性或者等同于規范性事實的辯護,等等。然而,有些規范分歧并非真正的分歧,而承認局部規范性或者接受某些規范的相對性,并不意味著某些規范就在同等條件下都是客觀有效的,也并不意味著規范性不具有真理的客觀形式;相反,我們既可以承認局部規范性的事實,承認不同群體、不同文化之間具體規范的差異,同時又保持對規范推理的有效性和客觀性的信念。這就要求我們對規范性的有效性和客觀性做出層次上的區分,并且提出一種元規范敘事的可能方案。
(一)明確何謂真正的規范分歧
局部規范性的存在是否一定會導致規范性沖突,是否意味著推理實踐的客觀性和有效性的喪失?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規范分歧,什么是可以相容的分歧。按照特納的說法,規范隨著具體時空的變化而改變,對于曼哈頓的單身漢而言是規范的,對于安達曼群島的島民來說則不是規范的。這樣的例子顯然過于籠統,如果這些規范只涉及具體生活方面的規范,比如著裝禮儀、風俗習慣,那顯然不能算真正的分歧。同樣,如果是規范推理方式,比如推理有效性的分歧,就特納所舉的例子而言,也不能視為真正的分歧。表面上看來,蘇聯農民的推理形式可以表明規范推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是無效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的人在推理能力上和受過教育人是有差異的,如果這個蘇聯農民的智商沒有問題,那么經過適當的教育和學習,他就可以理解這種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他之所以無法做出有效的推理,很可能是缺乏相關知識和概念,比如,對于一個不知道植物、花與玫瑰之間的蘊含關系的人,要推出玫瑰是植物就是不可能的。同樣,對于一個不知道“歐洲”“德國”“城市”“駱駝”等概念之間的關聯的人而言,這種推理并非易事。然而,這恰恰說明我們的推理是處在我們的概念網絡之中,處于我們的推理系統之內。顯然,我們不能說蘇聯農民的推理是“正確的”而三段論的推理是“錯誤的”。同理,雷爾頓對先于邏輯推理所預設的前提的批評,也不能從根本上瓦解演繹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如果要做出恰當的推理,的確需要依賴很多東西,借助很多概念。我們所依賴的概念之間的關聯(比如“玫瑰”與“植物”之間的蘊含關系)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由于我們是在實踐的意義上而不是在理論或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建立起概念之間的關聯,因而任何推理的首要目標總是實踐的。正如雷爾頓自己所表明的那樣,我們有理由相信什么問題是一個實踐理性而非理論理性的問題。對規范推理的普遍有效性的質疑并不必然導致規范的分歧,因為在推理實踐中,我們總是可以通過比較并發現,有一些規范推理比另一些更合理,因而有一些規范事實總是比另一些更客觀,但這種正確客觀絕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客觀必然性。
真正的規范分歧是什么呢?按照司徒莫(Bart Streumer)的說法,真正的規范分歧不是出于我們的態度和偏好或者行為習慣,而是在根本上涉及我們對于某事的正確性認知,也就是說,當兩個人做出沖突的規范判斷時,最多只有一個判斷是對的。換句話說,當兩個人或兩個群體做出的規范判斷相互沖突時,不是由于情感或態度上的不同,也不是某種選擇上的兩難,而是至多只有一個判斷是正確的,那么這種情況才是真正的規范分歧,因為世界不可能同時處在兩種不同的方式之下。比如,假如認知主義是正確的,“任何情況下虐待兒童都是允許的”與“任何情況下虐待兒童都是不允許的”這兩個判斷就不可能都正確。(8)Bart Streumer.“Are There Irreducibly Normative Properties”.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8,86,(4):537-561.
(二)區分規范與元規范
我們需要區分元層次意義上的規范性和規則意義上的規范性。元層次上的規范性是規范真理的制造者,是真或假、正確或錯誤的頒布者和裁定者,因而它們自身作為元規范語言沒有對與錯、正確與不正確的區分,它們是超越個體的,不受個體的限制和修正。只有處在共享的理由空間中,在集體意向的反思均衡下,規則、習俗、倫理等事物才可能通過集體或共同體關聯到個體;而作為元層次上的規范性,它隱含在人們的實踐和行動背后,是被假定或預設為前提的東西,它具有一種特殊的規范地位,并且顯然不是作為已經呈現為規則、習俗、制度、知識之類的東西,它們不能被觀察,也不能被評價,甚至不可能做出修正。元層次意義上的規范性是人所具有的一種理性能力,這種能力是進化的產物,即為規范思想、規范言談和規范行動提供基礎或充當條件的某種東西是人與生俱來的,它以某種方式先天地存在著。只有當這種元層次的規范性轉換為基本的可以遵循的法則——不管是自然法則,還是社會法則——我們才可能對它們進行斷言、評價和修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有可能面對規范的不對稱性或者規范的分歧。因此,所謂局部規范性或規范的相對性,并不是元層次意義上的規范性分歧,而是規范性呈現方式之間的分歧。比如,出于理由或者既有的交通規則,某些地方的司機會說“我們應該向左行”,有些地方的汽車司機則會說“我們應該向右行”。從某種程度上講,向右行駛或向左行駛是規范分歧,即具體的交通規則的沖突,然而并不是規范性本身的沖突。
規范性與實踐密切相關,其客觀有效性也蘊含在實踐中。如果我們知道不同文化中存在不同的規范,那么就能夠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遵循不同的規范,而不會將其視為是沖突的。因為將規范性的客觀性或真理條件訴諸超出“我們”所在的語言實踐共同體之外的基于先驗自我基礎上的絕對客觀性的想法,也許只是某種形而上學的烏托邦。換句話說,實踐作為一種隱含的規范結構,其自身既是規范事實的目標,也是規范真理的評判標準,既是理論解釋的有效手段,也是日常解釋的有力武器。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將“實踐”視作規范性的基礎,就可以理解為是去除其神秘性的一種嘗試。
正如布蘭頓所指出的,我們不能將規范性等同于既有的規范或規則,而應當根據規范的起源來尋求規范性的解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回到生活世界,在實踐中揭示規范的來源。(9)Robert B.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43-44.同時也在實踐中尋求規范性共識的可能。也就是說,規范的形成有賴于推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實踐機制,這一套實踐機制會根據具體的情景對不同規范進行平衡、選擇或轉換,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更高的規范的統一或規范性共識,因而將更多的人整合到一個“大共同體”(great community)(10)布蘭頓提出了“大共同體”(great community)的概念。參見Robert B.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之中。這也正是從人類整體的視角與人類理性推理之結構來尋求規范性的理解以及重疊共識之可能的關鍵。
(三)區分規范性的現實性與合理性
要尋求更高層面的規范性共識或重疊共識,除了要重視局部規范性問題的存在外,我們還要區分規范性的現實性與合理性。規范性能夠對我們起到約束作用,能夠給行動提供理由,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這種形式的客觀性并非絕對的,它是相對于其實踐共同體而言的,正因為其具有這種局部性特征,如果要在更廣闊的“理由的規范空間”之中發生效力,就要為其更廣泛的客觀性和合理性提供辯護。正如奧尼爾所言,從一些可以觀察到的經驗來看,即使許多廣泛接受的規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存在爭議,甚至非常極端。比如,那些被政治極端分子和其他恐怖團體接受的規范,他們同樣宣稱自己在堅守“正義”,在推動世界“和平”。此外,除了群體之外的沖突與差別,同一文化共同體內的人也會采用不同的規范。因而,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關于規范性事實的經驗要求,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變成各種各樣的相對主義者。但是,如果將規范性看作是特定的群體實際接受和試圖以之指導生活的標準、規則和規范,而拋開這些被接受的規范所需要的合理性辯護,那么,要擔保任何深層的規范要求似乎都是不可能的。(11)Onora O’Neill.“Science,Reasons and Normativity”.European Review,2013,21(1):94-99.
顯然,規范性的現實性與合理性是不同的。圣經對于信徒而言具有約束力,可以為其推理和行動提供理由,但這并不表明圣經中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極端分子雖然舉著“正義”的旗幟,但并不表明他們理解和辯護的“正義”就是客觀正確的,雖然它同樣能夠被辯護以及被堅持;某些錯誤的政策和法令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被推行,也并不說明這些政策和法令就是經過合理辯護的,就是經得起檢驗和拷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規范思想、規范言談以及規范判斷的確是“相對的”,或者如芬利所說:“規范思想并不尋求一種共同的客觀真理。”(12)Stephen Finlay.Confusion of Tongues:A Theory of Normative 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5.而帕菲特(Derek Parfit)認為,有些問題可能是不確定的,因為他們沒有答案。比如,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禿子,我們可以說,如果這個人沒有頭發,他就是禿頭,如果這個人滿頭秀發,他就不是禿頭。但我們不能認為,在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的所有情況中,任何人必須是或不是禿子。很多描述概念(比如高、大陸架)和規范概念(比如善)像“禿子”一樣,也是含糊不清的,很難給出一個精準定義。(13)Matti Eklund.“Recent Work on Vagueness”.Analysis Reviews,2011(1):1-12.這樣的情況在局部規范性問題中確實常見,也就是說,一些規范性問題可能是不確定的、沒有答案的,這就為規范性的現實分歧或規范相對性提供了另一種解釋。然而,我們已經指出,真正的規范分歧是有對錯的,比如,即使希特勒及其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種族滅絕是對的,我們肯定不會同意希特勒對于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是正義的或者正確的。同理,我們也肯定不能接受恐怖分子無端地襲擊或屠殺平民是在維護世界正義與和平,我們肯定也不會同意虐待兒童來獲得心理上的快樂是可允許的,等等。如果規范性的分歧只是“何謂禿子”這種問題的分歧,那么,我們的確很難給出一個精準的定義,然而,我們肯定知道沒有頭發的人必定是禿子。同樣,也許何謂“正義”“善良”“美德”以及“真理”的問題同樣很難精確定義,但我們可以確定何種情況下的行為是非正義的、邪惡的或錯誤的。作為有限的存在者,我們無法確證每一個規范事實,也無法確知關于世界的所有知識,然而,在我們的有限理性中,我們能夠通過不斷反思和求證,通過我們的推理和實踐,在最廣泛的對話和溝通中,尋找到一種合理的可接受的重疊共識,或者為更高的規范性提供一種合理性辯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而說不清楚的也未必就缺少合理性。換句話說,我們既要在實然層面檢視我們的現實,又要在應然層面測度人類之可能;我們既不能倒向相對主義,也不能默許某種非認知主義,而有必要走出一種以局部理性為特征的保守主義和相對主義以及以“認知”為中心的哲學范式,轉向一種以“實踐”“交往”為核心的哲學范式,從而為更廣泛的規范性共識奠定基礎。
三、構建規范性共識的可能
規范性的理解及其廣泛共識的構建是可能的,它需要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相結合,而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就需要更廣泛的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正如布蘭頓曾指出的那樣,“我們”的社會實踐是具有不同社會視角的人們共同參與的實踐,人們介入到共同體的溝通交流之中,首先必須具有一種實質推理的能力,能夠基于理由的邏輯空間或者交往雙方的彼此理解,從他人的前提正確地推導出結論。在實際交往活動中,聽話者通過將說話者的承諾當做理由來構筑自己的信念,以此達到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真正的理性交往活動。按照這種觀點,局部規范性問題即使存在也是可以化解的,因為當我們站在一種更高、更廣泛的理由空間展開思想與行動的時候,制約我們的將不再是我們的某種特殊身份,而是一種基于“大共同體”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信念和承諾。因而,即便這種規范性共識需要涵蓋整個人類,一種規范性共識的確立也是可能的。
另外,哈貝馬斯以溝通為取向的交往哲學范式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迪。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如果“我們”要走出規范分歧的誤區,并且在某些問題上達到原則上的共識或者確立某種元規范性話語,“我們”就需要走出主體(個體、自我或小我)哲學的誤區,不再將世界所具有的創造性意義置于主體的自我關涉或籌劃之中,而是要歸入具有交往結構的生活世界,以規范的正確性和主觀的真誠性來支配我們的認識和行動。他認為:“如果我們暫時可以肯定這種行為模式是成立的,那么,認知主體針對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實體所采取的客觀立場就不再擁有特權。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動參與者的完成行為式立場,互動參與者通過就世界中的事物達成溝通而把他們的行為協調起來。”(14)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347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哈貝馬斯提出了一種基于話語的程序主義的推理構想。它是一種類似于古希臘邏各斯意義上的想法,因為它包含著一種話語所具有的非強制性的統一性力量和共識性力量,在這種程序主義的推理構想中,所有參與對話的人都力求克服其最初的有限的主觀觀念,投入到一種具有合理動機的交往對話之中,這種交往理性因而就構成一種去中心化的世界觀。(15)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366-367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因而,也為一種更大范圍內的規范性共識和統一提供了可能和條件,這也可以視為規范性共識或規范性的統一性之可能的內在依據。
布蘭頓和哈貝馬斯的觀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布蘭頓試圖將規范性的解釋與我們的社會實踐相結合,將“我們”的社會實踐視為具有不同社會視角的人們共同參與的實踐,在實際交往活動中,人們通過予求理由來構筑自己的信念,以此實現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真正的理性交往活動,從而向著一個“大共同體”邁進。哈貝馬斯訴諸“交往共同體”的概念,提出一種以對話和交往為核心的哲學范式,將世界理解為具有交往結構的生活世界,并將世界所具有的創造性意義置于互動參與者的交往理性之下,把主體間相互承認的有效性視為我們認識和行動的準則。實質上,他們的觀點可謂殊途同歸,都主張一種以“實踐”“推理”為基礎的哲學觀,一種以“交往”為核心的哲學范式。在這樣的世界觀或哲學方式之下,“規范性”首先意味著一種創造、遵循和改變規范的實踐性能力,同時也意味著對“局部規范性”的克服,雖然它們無論如何都無法超越“我們”的邊界,但如果一種更廣泛的“理由的規范空間”是可能的,那么,不管是康德意義上的“世界公民”(16)康德:《實用人類學》,27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的構想,還是我們今日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都將從可能走向現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管是實質性的規范分歧,還是非實質性的規范分歧,只要“我們”的尺度與邊界調節適當,理性的共識或普遍規范的達成就是可能的。換句話說,規范性是人所具有的創生、改造和運用規范的能力,它蘊含在人所特有的理性或推理實踐之中,它可以根據不同情境及“我們”的需要在具體的歷史與時空中做出順應、平衡,并最終系統化為一種穩固和恒定的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分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文化群體的時候,“我們”是有差別的,因而局部規范性問題或規范分歧也在所難免;然而,當“我們”以“人類”之名尋求更廣泛的群體性合作并講述“我們人類”自身的故事的時候,“我們”又是沒有差別的。
當然,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規范性共識并不依賴于規范的一致性,更不是一種規范對另一種規范的壓制、消除或勝利,一種普遍性話語對個體性話語的控制;規范性共識取決于共同體成員對于規范的需要,取決于共同體的大小,取決于亞共同體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實踐情景的轉換。我們還需要強調,規范性共識所能達到的程度是與共同體的尺度即“理由的規范空間”相關的,它有一個動態的運行和轉換規律,表現為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理性推理,以及一種類似于羅爾斯意義上的“反思平衡”,這種平衡可能不會越出共同體的邊界,而是順應這個共同體的既有共識和需要,以此來調整自身,以期達到一種元規范層面上的有效性與合理性。
總之,規范性是人創造自身的一種特性。要理解規范性,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理解人及其實踐活動本身。“我們”或者社會的構成不僅需要規范,還需要不同類型的規范。“我們”不僅需要具體的規范,還需要回答為什么需要規范,需要什么樣的規范,需要多大范圍內的規范。“我們”不僅要看到不同規范之間的差別,還要在不同規范之間做出調整和選擇,即使具體規范或一階規范之間存在沖突,“我們”還可以訴諸二階或者高階規范,因為更高的規范意味著對具體的一階規范的整合,是一種更高的理性推理,或者說是反思平衡的更高水平,它可以重新確立“我們”的范疇和推理游戲的目標。從無序到規范,從規范分歧到更高的規范,這也正好說明,作為推理實踐而存在的規范性,其結構本身并非靜態不變的,而是動態平衡的,因為規范或理由空間確實存在適用范圍的問題,它可以適用于較小的群體,比如家庭,也可以適用于較大的群體,比如民族或國家。在具體層面,不同共同體的規范確實會呈現出差異與不同甚至相悖。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們在實踐推理層面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正如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是誰,這依賴于每一具體情境下共同體的尺度有多大,依賴于一組特定對照的邊界在哪里。(17)伯納德·威廉斯:《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2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共同體尺度足以容納所有人類,即它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一種更高的規范性的統一或共識就是可能的。這種統一或共識可能是更高層次上對于差異的否定之否定,也可能是尊重差異基礎上的“和而不同”,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從實踐出發,引入一種元規范或元語言的敘事及推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