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脫鉤迷思

當今全球貿易的高融合度,意味著全球脫鉤的低可能性。如果不解決美國的儲蓄不足,而靠提高關稅和增加其他對華貿易壁壘,無非是將貿易從中國轉向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這種雙邊脫鉤,僅僅是一種貿易轉移,而非全球脫鉤。
用來形容世界秩序深遠而持續的分裂的“脫鉤論”,在2019年成為爭論焦點。這也是中美不斷上升的摩擦所釋放的一個警告信號,以牙還牙的關稅之爭只是冰山一角。
歷史學家很快就指出,中美關系的緊張并不具備被許多人認為是“冷戰”決定性作用的意識形態因素。也許如此,但那又如何呢?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發生持久沖突的可能性決不能掉以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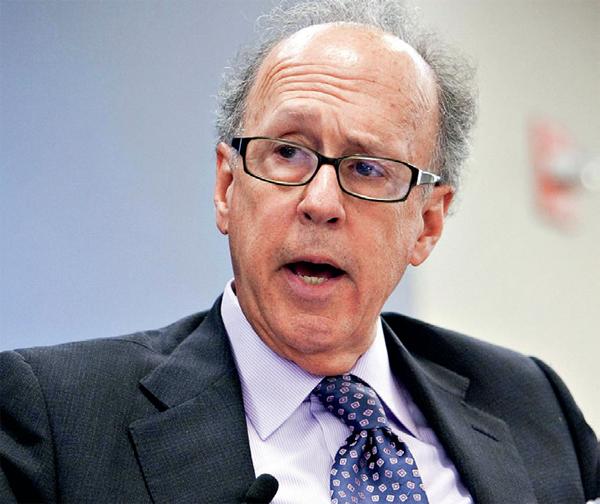
史蒂芬·羅奇
盡管如此,哪怕中美之間存在永久性裂痕,87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也不可能在2020年或以后分裂為兩個陣營。原因很簡單:僅靠雙邊行為,還不能割裂緊密相連的多邊貿易體系。
今天全球體系的融合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貿易增長確實進入了漫長的減速期,但貿易在GDP中的占比仍保持著28%左右的水平。這大約是冷戰時期的兩倍,在1947年至1991年間,這個數據為13.5%。貿易和全球商業的聯系越緊密,打破這些聯系的難度就越大,要形成普遍的破壞力強的脫鉤,可能性也越小。
此外,當今貿易聯系的性質意味著全球脫鉤更加不可能。完全由個別國家負責生產的傳統成品進出口日益被零部件分散貿易所取代,其生產和組裝都是在一個龐大的全球多國價值鏈網絡中完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的一項研究,1993至2013年間全球貿易額暴漲五倍,其中整整73%的漲幅由全球價值鏈貢獻。雙邊貿易向多國供應鏈的擴散,對雙邊脫鉤起到了抑制效用,不論兩個經濟體規模多么巨大。
這些考量在推斷中美貿易摩擦的潛在影響時非常重要。美國政客常說,美國的貿易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畢竟,從2013年至2018年這六年中,對華貿易占了美國商品貿易赤字缺口的47%。美國政客沒有承認或理解的是,總體貿易赤字是美國長期以來凈國內儲蓄率低迷的副作用:2018年,美國凈國內儲蓄只占GDP的2.4%,遠低于20世紀后30年6.3%的平均水平。
通過雙邊脫鉤來封鎖中國無益于美國消除貿易赤字的總規模,而只能迫使美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多邊貿易赤字結構發生改變。
缺少儲蓄但又想擴大投資和刺激增長,使得美國必須從國外引進盈余儲蓄,保持長期經常項目赤字以吸引外國資本。這一宏觀經濟失衡讓中國成為好伙伴,成為美國對102個國家商品貿易的多邊赤字的一部分,只不過占比比較大。
當然,政客總是最后承認他們是問題的根源,他們應該為造成美國國內儲蓄長期不足的巨額預算赤字負責。不幸的是,這一美國貿易地位的關鍵特征,可能因為雪上加霜的美國聯邦赤字預算而進一步惡化。
儲蓄不足是美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源,這意味著必須從不同角度看待同中國的貿易摩擦,脫鉤論也應該據此重新定義。如果不解決美國的儲蓄不足,而靠提高關稅和增加其他對華貿易壁壘,無非是將貿易從中國轉向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雙邊脫鉤,并不意味著全球脫鉤,只意味著貿易轉移。
這一轉移將因為全球價值鏈而變得復雜。基于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的貿易增加值數據,龐大的美國對華商品貿易赤字中,有大約20%并非中國制造,相反,它們反映了其他國家的零部件和配套產品是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價值鏈的。這表明,美國對華雙邊貿易赤字的官方數據被夸大了,美國多邊貿易赤字需由中國來“解鈴”的說法就更值得懷疑。
貿易結構已經由單個國家生產制成品的傳統交易向全球價值鏈驅動的多邊生產平臺貿易轉變,這反映出日益一體化的泛亞洲工廠從根本性上進行了結構重組。《2019年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的研究發現,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對華商品貿易赤字的猛增原因,主要是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向中國大陸的離岸轉包,特別是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等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這與美國大部分政客所鼓吹的“中國責任論”大相徑庭。
因此,全球價值鏈聯動程度的強化意味著中國對美輸出制成品關稅不但將由美國出口商承擔,也會由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有關聯的第三方國家承擔。因此,美國加征關稅已經產生了廣泛影響毫不奇怪,不僅對中國如此,對于其他東亞貿易敏感型經濟體也是如此。
所有這些都不意味著中美關系無法脫鉤,不管是實際意義上的貿易流,還是金融意義上的資本流。事實上,筆者在幾年前出版的一本關于中美相互依存風險的書中已然強調指出了這一擔憂。中國依賴美國消費者作為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的主要外部支持來源,而美國依賴中國作為其第三大和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以及其國債的最大外部買家,兩國都需要并歡迎對方的支持。但是,作為人類,當相互依存的一方改變了保持關系的要素時——就像中國從出口拉動型增長轉向了消費拉動型增長——沖突就會產生。當前的貿易摩擦,便是相互依存進入沖突階段的典型例子。
貿易戰由全世界最大的儲蓄赤字國美國發起,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美國的財政軌跡已經出現了不好的兆頭,貿易赤字在未來幾年還會進一步加劇。通過雙邊脫鉤來封鎖中國無益于美國消除貿易赤字的總規模,而只能迫使美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多邊貿易赤字結構發生改變。
這就造成了一個更加棘手的政治問題。雙邊脫鉤所造成的貿易轉移意味著美國的外包將從低成本的中國生產平臺轉向水平參差不齊的其他國家。這是否會將貿易推向其他亞洲平臺,甚至是回到美國,就像特朗普總統一直堅持會發生的那樣。但總歸,這都是轉向成本更高的生產平臺。諷刺的是,這在功能上等價于對美國公司、工人和家庭增稅。最終的結果會是,接下來的很多年里,美國政客同長期陷入困境的中產階層間的最具爭議的脫鉤,可能就此奠定基礎。
當今全球貿易的高融合度,意味著全球脫鉤的低可能性。如果不解決美國的儲蓄不足,而靠提高關稅和增加其他對華貿易壁壘,無非是將貿易從中國轉向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這種雙邊脫鉤,僅僅是一種貿易轉移,而非全球脫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