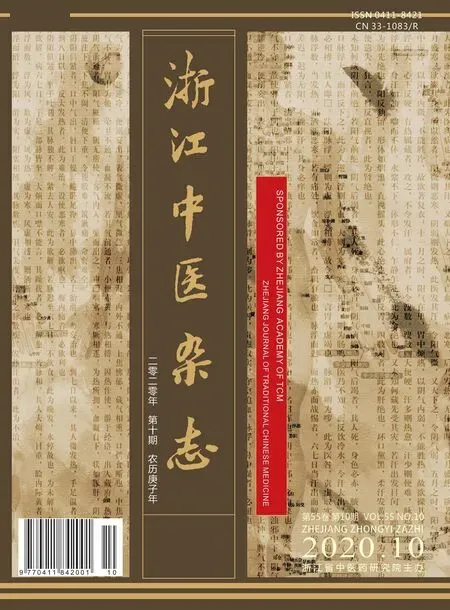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
李佳嘉 夏鰲安 余 謙 汪紫虹 李如輝
浙江中醫藥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53
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的關系是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長期以來探討者甚眾,本文嘗試從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這一嶄新的角度,力圖將有關認識在現有水平基礎上推向新臺階,以冀為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的離、合等問題的解決提供理性依據。
1 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存在著特殊性
關于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迄今最為經典且最具權威的論述當推恩格斯,“不管自然科學家們高興采取怎樣的態度,他們總還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1]。就原子論哲學與西方自然科學而言,正如童鷹所說:“由于原子學說的復興,原子學說中所包含的微粒思想和其他思想,在當時以及后來的整個近代科學發展時期,便成為孕育出近代各種科學理論的思想土壤。”[2]在這里,哲學是作為一種思想背景因素通過為自然科學研究提供自然觀、方法論、認識論的指導而發揮其支配作用的,是“隱藏”在特定自然科學理論形態背后的強大的思想力量,其作用形式是深藏不露的,甚至于是潛意識的,因而,其影響只有透過自然科學理論的具體表述本身進而把握其理論實質的層面上才能得到體認與窺視。鑒于這一觀點的普遍意義并廣為接受,筆者稱其為“哲學對自然科學影響的共性原則”(以下簡稱“共性原則”)。
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學科主體屬性為自然科學)的關系,毫無疑問地遵循并體現著“共性原則”,透過中醫理論具體表述層面,人們無不為其背后濃重的中國古代哲學精神而感嘆,中國古代哲學同樣也曾作為一種思想背景因素通過為中醫學研究提供自然觀、方法論、認識論的指導而發揮其支配作用,是“隱藏”在中醫學理論形態背后的強大的思想力量。正如印會河所說:中醫學“用當代的先進哲學思想為指導,從而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3]。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又絕不局限于“共性原則”,因為,人所共知的中醫學理論濃重的中國古代哲學文化色彩又是顯在的,普遍見諸于理論表述層面。中國古代哲學既是“隱藏”于中醫學理論形態背后的決定醫學精神實質與方向的“無形觀念”,又是顯在地將其自身的概念、原理、結論等直接地編織于中醫學理論具體表述的網絡中,并最終固化成為中醫學“理論之網”上的“繩線”與“紐結”,“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這一鐵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存在著特殊性。
2 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特殊性的具體體現
以原子論哲學及其對西方科學包括西醫學的影響作為參照系,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哲學概念成為中醫學“理論之網”上的“紐結”:中醫學概念賴以發生的途徑是復雜的,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來自于哲學概念的移植、嫁接與改造,就《黃帝內經》一書所見,如精、氣、形、神、陰陽、五行等與中醫學自身實踐而發生的概念相嫁接便產生了大量新的醫學概念,于此,李如輝等[4]已有詳論,恕不贅述。而后隨著宋代理學的興起,哲學概念繼春秋戰國秦漢之后,又一次大規模地滲入醫學領域,體用、升降、氣機、氣化等在宋明醫籍中更是屢見不鮮。
盡管道爾頓也曾經直接將哲學的原子概念遷移到化學領域,創立舉世聞名的化學原子論,“如果說,古希臘原子論還是一種哲學理論的話,那么道爾頓的化學原子論則完全是一種科學理論了”[5]。但這在西方科學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的事例了。
由此,“大量的哲學概念涌入醫學理論中”[6]不得不說是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之一。
2.2 哲學理論成為中醫學的說理工具:除了中國古代的多學科知識外,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精氣學說、陰陽五行學說乃中醫學進行說理的無法取代的工具,“運用哲學原理對醫學問題進行廣泛的說明”“把哲學觀念作為醫學理論的體系構架”[6]。
反觀西方科學史,盡管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嘗試,如波義耳就曾“試圖以原子學說來解釋化學反應”[2],但并沒有獲得成功,更不用說理論體系的構建。可見,作為中醫學說理工具的中國古代哲學則是其對中醫學影響特殊性又一內容。
2.3 哲學理論成為中醫學理論發生的推理前提:在中國古代哲學天人一氣、天人一體、天人一理等命題下,執哲學命題推導出中醫學的某些具體的理論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于是,“援物比類”在中醫學理論構建過程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如“人右眼不如左眼明”、心化赤為血、心包絡“代心受邪”、肺氣“肅降”、脾主升清、脾為后天之本等理論無不藉此途徑而發生。于此,李如輝等[4]曾有一文專論,故從略。
西方科學史上雖然也能看到諸如此類的運用,如布魯諾在1584年以后發表的基本著作中,也曾從天體與人體的類比中,以行星繞日的循環運動提出過人體中的血液循環的猜想[7]。但由于在原子論哲學內部找不到邏輯支撐,這種運用從來不曾被看作是順理成章的,受制于此,故難以得到發展。
眾所周知,中醫學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便形成了理、法、方、藥為構成要素的完整的理論體系,較之西醫學明顯是“早熟”了。無獨有偶,在梁漱溟[7]先生看來,中國古代哲學同樣有著“早熟”的特征,史實也確實如此。中醫學的“早熟”現象堪稱世界科學技術史之奇跡,而造就這一奇跡的,除了先賢們在醫學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材料之外,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早熟”的中國古代哲學,其中,尤以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為代表。綜合前文三點不難看出,倘若沒有“個性殊強”[7]與西方哲學“適成一種對照”[8]的中國古代哲學,倘若沒有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的這種特殊的影響形式,編織中醫學“理論之網”的努力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概念(“紐結”)不足與敘述工具(“繩線”)缺乏的困境而落空。如果說哲學概念成為中醫學“理論之網”上顯在的“紐結”,有效地克服了由于醫學實踐的有限所衍生的概念數量不足的問題,如果說哲學理論成為中醫學的說理工具成功解決了編織中醫學“理論之網”的“繩線”問題,那么,哲學理論成為中醫學理論發生的推理前提便是既提供“紐結”又提供“繩線”。于此可知,正是中國古代哲學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的“早熟”及其對中醫學影響的獨特形式,為兩千多年前編織中醫學“理論之網”的努力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條件并獲得了巨大成功。
2.4 數量可觀的醫哲“兩棲”性質的研究群體:以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深刻性論,當首推道、儒二家,既為道家又為醫家、既為儒家又為醫家的情形,即道醫、儒醫“兩棲”性質且數量可觀的研究群體,又是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特殊性的另一個極為突出的標志。茲分述如下。
2.4.1 道、醫兼修:習道者大凡兼能明醫,《抱樸子·雜應篇》曾說:“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據有關統計,六朝道醫占當時全部醫生總人數的28.7%[9]。《漢書·藝文志》的“七略”,其中“方技略”又分為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而房中、神仙都與道術密切相關,占據了中醫藥文獻的半壁江山。而《道藏》收錄的醫藥書籍,占《道藏》內容的70%以上[10]。故自古就有“醫道通仙道”“十道九醫”之說,它充分反映了道教“尚醫”的歷史傳統。
2.4.2 亦儒亦醫:《圖注八十一難經·序》言:“未有通乎醫而不通乎儒者也。”縱觀中醫學的發展,一方面,大儒也多能兼醫甚至于通醫。《醫說·醫功報應》云:“季明其儒醫之良者也。”《續醫說·醫書》云:“余近見趙繼宗《儒醫精要》一書,駁丹溪專欲補陰以并陽,是謂逆陰陽之常經,決無補陰之理。”中醫學術群體——儒醫,便指有著一定文化素養的醫者,或宗儒、習儒的醫生和習醫業醫的儒者。
一方面,如皇甫謐、張潔古、朱丹溪、滑壽、高武、李中梓、汪昂、薛雪、劉完素、李時珍、喻嘉言、吳鞠通等均為棄儒從醫而在中醫發展史上作出杰出貢獻的名家。《格致余論·序》云:“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論》。”另一方面,歷代大醫也不乏大儒,“醫圣”張仲景曾為長沙太守;皇甫謐曾多次受到晉武帝召見授官,然其辭請不就而執意從醫;孫思邈,《舊唐書》稱其“善談老莊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在當時即享有盛名。
西方醫藥學盡管也存在有醫哲“兩棲”性質的學者,如阿拉伯煉金術的主要代表人物賈比爾·伊本·海揚是一個與陶弘景一樣的藥學家和醫學家。賈比爾的繼承人、另一個著名的煉金術士士拉澤同樣也與中國煉丹家一樣兼通藥學與醫學。而阿拉伯煉金術、醫學與哲學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阿維森納同樣也具有中國煉丹家的特色。[2]但該性質的群體在西方醫學史上較之中醫學在數量上、影響上確實存在著天壤之別。
3 結論
綜上,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①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是一個真實命題,這對于掙脫以“共性原則”論哲學對自然科學影響的單一、狹隘的思維陷阱,克服以“共性原則”抹殺“特殊性”的弊端,對于理解并認同文化哲學、科學、醫學的多樣性、多元性、多形態性等具有普遍價值。②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其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使得早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構建完整的醫學理論體系的努力獲得了成功。③獨特形態的中國古代哲學及其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賦予中醫學區別于西方醫學的獨特的理論形態。④中醫學理論的臨床實效,為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學影響的特殊性的價值提供了終極依據,這將強有力地引導對中醫學的“哲學醫”特征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積極的評價,而不是相反。主張將哲學與中醫學進行剝離等觀點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