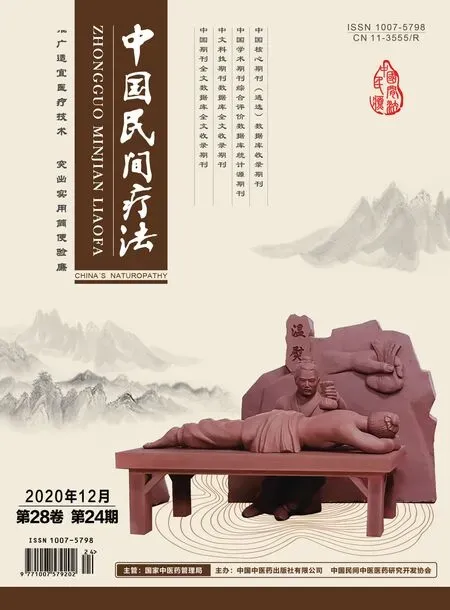周煒從“風”論治支氣管哮喘經驗
李 燦,石煥玉,周 煒,毛婭男
(1.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0;2.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
支氣管哮喘是一種以慢性氣道炎癥和氣道高反應性為特征的異質性疾病,以反復發作的喘息、咳嗽、氣促和胸悶為主要臨床表現,常在夜間和/或清晨發作或加劇,呼吸道癥狀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隨時間變化而改變,并常伴有可逆性呼氣氣流受限[1]。根據哮喘的臨床表現,其歸屬于中醫“哮病”“喘證”范疇[2]。
周煒教授,江蘇省名中醫,江蘇中醫兒科學會主任委員,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兼職教授,善從“風”論治支氣管哮喘、過敏性鼻炎、急慢性咳嗽、兒童抽動癥等,認為風邪侵襲是支氣管哮喘發病的重要機制之一。周煒教授運用中醫藥治療哮喘,療效顯著。筆者師從周煒教授3年,對其從“風”論治支氣管哮喘略有體會,現分享如下。
1 病因病機
周煒教授認為,哮喘病多與“風咳”相關。哮喘病以長期反復發作的慢性干咳為主,氣道敏感性反應增加,咳嗽特點為易突發突止,咽喉、氣道一旦有癢感,即出現劇烈咳嗽,氣道痙攣,難以克制[3],符合中醫風邪“善行而數變”“風勝則攣急”的致病特點[4-6]。中醫認為,癢感屬風,《醫學入門·咳嗽總論》中提出:“風乘肺咳,則鼻塞聲重,口干喉癢,語未竟而咳。”《證治匯補·哮病》載:“哮即痰喘之久而常發者,因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膈有膠固之痰,三者相合,閉拒氣道,搏擊有聲,發為哮病。”周煒教授認為,人體對冷空氣、刺激氣味及多種外源性物質相對敏感,氣道的慢性炎癥、高反應性與“氣道壅塞”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可歸為“外風”,“伏痰”是哮喘病的夙根,為“內風”,外風引動內風,致氣道痙攣狹窄,肺氣升降受阻,痰鳴如吼,氣息喘促,是哮喘病的病理機制。
2 治則治法選方
《臨證指南醫案》載:“若因風者,辛平解之。”《沈氏尊生書》載:“哮癥,古人專主痰,后人謂寒包熱,治須表散。竊思之,大都幼稚多吃咸酸,滲透氣脘。一遇風寒,便窒塞道路,氣息喘促,故多發于冬初。”因此,周煒教授治療哮喘以疏風宣肺、宣壅通塞為總原則,配以散寒、清熱、化痰、利咽等治法。
基于以上治則治法,周煒教授自擬的息喘湯在臨床應用中收效頗佳。息喘湯由射干、蜜麻黃、苦杏仁、生石膏、鉤藤、紫菀、黃芩、浙貝母、僵蠶、蜈蚣、法半夏、赭石、魚腥草、細辛組成。方中射干苦寒,入肺經,長于化痰,《神農本草經》記載其“治咳逆上氣,喉痹咽痛不得消息”,與黃芩、法半夏、細辛合用,祛痰化飲。蜜麻黃辛溫,祛風緩急,宣肺平喘,配以苦杏仁一宣一降,正和肺之特性,助其宣肅,故而定喘。生石膏甘寒,使麻黃宣肺而不助熱,二藥相配,清肺而不留邪,相制為用。鉤藤甘寒,蜈蚣辛溫,僵蠶咸平,三藥合用,共奏祛風解痙平喘之功。配以紫菀、浙貝母、赭石降逆止咳。黃芩苦寒,善泄肺熱;魚腥草辛寒,《本草經疏》言其“治痰熱壅肺,發為肺癰,咳吐膿血之要藥”。黃芩、魚腥草二藥助射干化痰,助石膏清泄肺熱。石膏寒涼清熱,細辛溫化寒飲,一寒一溫,防寒涼太過滋生痰飲、溫化太過灼劫肺陰。此方寒溫并用,故寒哮或熱哮均可加減使用。若外感風寒、內伏痰飲,治當祛風散寒、化痰平喘,可去鉤藤、魚腥草,加紫蘇子、芥子、葶藶子、橘紅,降氣快膈,溫化寒痰;寒甚者可加桂枝、干姜助陽化氣。若患者咳黃白痰,舌尖略紅,為寒飲化熱之象,則加大石膏用量。若患者素體痰多,復感風寒,肺氣壅閉,郁而化熱,則去細辛,加紫蘇子、款冬花、桑白皮清熱化痰,祛風解痙,降氣平喘。若兼外感風熱,則去細辛、鉤藤,加桑葉、連翹、梔子、荊芥、防風之品宣肺疏風。若哮喘劇烈,則加全蝎增強祛風解痙之功。若咳逆上氣明顯,可去魚腥草、細辛、鉤藤,加旋覆花,加大赭石用量,以達降逆平喘、祛風化痰之功。若氣虛易感者,可加黃芪、防風益氣固表。
總而言之,周煒教授認為,疏風通塞解痙是治療哮喘的重要方法。臨證時應根據患者疾病發作之輕重、表里寒熱虛實選方配藥。可萬變不離其宗,治療不離祛風通塞。
3 用藥特點
周煒教授不拘泥于古方,在臨床遣方用藥時擅用祛風解痙之品,如蜈蚣、僵蠶、細辛等,加強祛風抗敏、解痙平喘之力,臨床應用每獲良效。蟲類藥物為血肉有情之品,能走竄入絡,搜風止痙化痰,其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著,氣可宣通,剔除滯痰凝瘀,通達絡脈,降氣平喘,息風解痙,活血化痰,有些還有補益培本的功效,正合哮喘病機。僵蠶味咸、辛,性平,能息風止痙、袪風熱、化痰散結。《本草思辨錄》言僵蠶“劫痰濕而散肝風”,指出僵蠶的功效特點是“散風”和“祛痰”。研究證實,僵蠶水提液可能通過調節機體白細胞介素-4(IL-4)和γ干擾素(IFN-γ)的水平,達到調節Th1/Th2平衡、有效控制哮喘發作的目的[7]。蜈蚣味辛、咸,性溫,有毒,入肝經,辛散走竄、息風止痙、通絡解毒散結力強。張錫純言蜈蚣“走竄之力最速,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氣血凝聚之處皆能開之”。細辛味辛,性溫,有小毒,入心、肺、腎經,具有祛風、散寒止痛、溫肺化飲、宣通鼻竅功效。《神農本草經》云:“細辛,味辛、溫。主咳逆,頭痛腦動,百節拘攣,風濕痹痛死肌。”《本經疏證》載:“細辛,凡風氣寒氣,依于精血、津液、便溺、涕唾以為患者,并能曳而出之。”《本草通玄》載:“主風寒濕頭疼,痰歇氣壅。”結合《傷寒論》《金匱要略》中使用細辛的方藥,可知細辛對咳逆、厥冷、疼痛有良好的治療效果。陳慧等[8]探索細辛對哮喘豚鼠的干預作用,發現其可通過調節炎癥因子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及金屬蛋白酶抑制劑1(TIMP-1)的失衡,起到緩解豚鼠小氣道重塑的作用。
4 小結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靈魂。只有充分認識哮喘發生發展過程中“證”的變化,才能準確辨證,有的放矢。哮喘的直接病因復雜,風、寒、熱、痰、飲常相兼致病,病機有表里、內外、虛實之差異,所以治療當分清寒熱虛實,對癥下藥,但均不離祛風解痙之法。周煒教授從“風”論治哮喘,臨床療效顯著,可減少患者對激素的應用及不良反應,同時中藥價格較低,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
周煒教授運用蜈蚣、細辛治療哮喘,輕微不良反應發生率極低,據統計不足千分之一,且停藥數天即可自行緩解,尚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可能原因為,用量均在常規用量范圍內,蜈蚣1條,細辛2 g;藥物經過炮制或久煎后,毒性降低[9-10];以中醫理論指導為背景,合理配伍可以減毒增效[11]。《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中言“有故無殞,亦無殞”,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治病關鍵是藥物的運用與病證是否相符。因此,吾當勤思敏學,細細體會吾師辨證論治、選方用藥之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