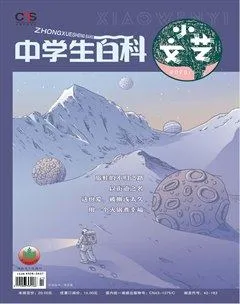梧桐路
顧一燈

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唯獨這一條路叫作梧桐路。
北城遍地都是梧桐。冬天它們褪去所有的葉子,變成光禿禿的看不出品種的樹。春天,葉子又陸續萌生起來,從讓人不忍心掐去的嫩綠變成更深沉的顏色,然后黃色慢慢泛上來,帶著斜陽將晚的紅,一陣北風吹過來就落了個干凈。
我能數出許多這樣的街道,兩邊栽滿了這種樹,可是只有這條路鄭重其事地把它當作自己的名字,似乎在彰顯著某種我看不透徹的不同。
梧桐路坐落在北城一中旁邊。打正門出來走上坡,再向右轉,就能看到寫著路名的標牌。標牌本是磚紅色,后來經風吹雨打剝落了不少漆,露出鐵的原色,慢慢覆蓋上一層斑駁的銹跡。這片一直被劃為有待拆遷的部分,包括我們學校。但說是這樣說,一直也不見有實際的動作,我們也就不把這當回事。
我們常在這里躲捉人的政教處老師。我們學校有許多奇怪的規定,比如不能早到,政教處的幾位巨頭會在七點半前竄出校園,抓獲無故早來的同學。于是我們躲在梧桐路上,有時候就著花壇臺子邊緣補昨晚的作業,有時候無所事事地坐在臺階上聊天。偶爾前面有人大喊一聲“大曾來了!”(大曾是學校政教處的主任),一群人便慌慌張張地跑。聲勢浩蕩仿佛逃難,場面頗為壯觀。
后來有頭腦活絡的人發現了商機,開始在路兩邊擺攤賣早點。最早是一位賣油條、豆腐腦的,顧客不少。陸續多了售賣煎餅和雞蛋灌餅的小攤。這些東西更有滋味,還能加培根、牛肉或火腿,深受肉食愛好者的歡迎。第一家攤位也就漸漸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學校反復在國旗下講話時聲明,不能吃街邊沒有營業執照的不衛生食品,可沒什么人聽。我懶得排隊,于是常常還是去投奔油條和豆腐腦。
攤主是一對中年夫妻,他們駐扎在梧桐路盡頭的那棵梧桐樹下。男人默不作聲地在滾燙的油鍋里炸油條,重復著翻動和打撈的動作;女人被油煙氣熏染著,收錢、裝食物,動作不快,也從不和顧客講家長里短。這讓有社交恐懼癥的我感到心安。厭倦了和政教處老師的追逐戰,常常早到很久的我不愿靠近學校,索性站在攤位旁邊吸豆腐腦。時間久了,大概他們也對我熟悉起來,一回我忘了帶錢,女人告訴我先拿著吃,明天再給錢就好。
但這只是我的猜測,事實上,直到這家攤位消失,我們仍沒有過多的交流。即便是前一日我來買豆腐腦、油條,他們也不曾給我打過招呼,說以后就吃不到了。我在攤位原先的地方停了一會兒,看到紅磚地上留下的黑色印記,轉身去買雞蛋灌餅。它著實更好吃一些。直到高中畢業,梧桐呈現出一片茂盛的翠綠,梧桐路也沒有替代賣油條豆腐腦的商家出現。也許是因為這種食物太過平常了吧。
去年冬天我回到北城,才得知梧桐路附近要拆掉許多房子,包括北城一中。一中會搬到城市的東邊,新校區已經修建完畢。我冒著雪去看了一次,趕上寒假,只有傳達室值班的爺爺在。教學樓嶄新,操場是原先的兩倍,附近有兩家正規的連鎖餐廳,不再給小商小販生存的機會。
我是一個不把戀舊掛在嘴邊,但行動上十分誠懇的人,連丟掉一個用完了的筆記本都要猶豫許久,最后還是把它塞到柜子里保存。所以當得知我記憶里的梧桐路不再時,某種情緒輕而易舉地涌到了我的心頭,是感傷,是無奈……
把梧桐路藏進心里,我還是要堅定地往前走,經歷許多遺棄、失去和淡忘的過程。它們讓我哀傷,我珍視這種哀傷,甚至覺出一絲欣慰來。至少在這個太過于浮躁繁雜的俗世里,我還沒完全失去對一棵樹、一條街、一段過往的情感。我仍能觸摸到生活的脈搏,就像感知梧桐葉脈粗糙的紋理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