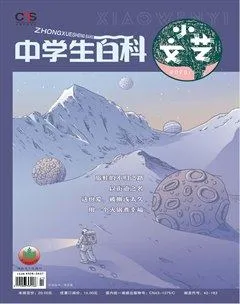火 車
伍若虛
我小時候愛看火車。但是我家和能看見火車的地方隔著一段很遠(yuǎn)的距離,所以每一次看到火車從我面前呼嘯而過時,我都會緊緊地盯著它,生怕慢了一秒它就會從我眼前消失。
幸運(yùn)的是,一位姑奶奶住在鐵軌附近。從她家的窗子望出去,能看到那一眼望不到頭的鐵軌,以及鐵軌旁冰冷且不近人情的鐵網(wǎng)。鐵軌上搭了幾塊鐵板,火車沒來的時候便于汽車過往。鐵軌附近有一個小屋,是專門監(jiān)視火車是否靠近的。如果火車將要過站,就會提前響起鈴聲作警示,然后放下鐵軌兩旁的長桿,將汽車擋在鐵軌外,等待火車通過。
每次去拜訪姑奶奶的時候,我都很興奮,總會迫不及待地爬上她家二樓,倚著陽臺,翹首以盼那在我聽來無比悅耳的鈴聲,等待著兩束長長的車燈穿破黑暗,向我所在的方向飛奔而來。它飛快的速度會在我身邊刮起一股強(qiáng)力的風(fēng),帶起一眾沙石上天,迷住我的眼,使我流下眼淚。
即便如此,每到此時我都很興奮,幻想著它能載著我離開這個小小的縣城,背上我沉甸甸的夢想,去到那未知遠(yuǎn)方,去看人們歌頌了千遍萬遍的長江黃河,去看畫冊上南方在陽光下燦若金子的成片成片的稻田,北方白雪皚皚、肅穆莊嚴(yán)的大地,去看那電視里高樓鱗次櫛比、繁華美麗的大都市。可我不能,我只是一個蹲在鐵軌旁做著大夢嘿嘿傻笑的農(nóng)村孩子。
每當(dāng)有火車經(jīng)過時,我都會和弟弟打賭,看誰能先看清楚火車車廂上掛著的起始地點(diǎn)的牌子。“火車來了!”弟弟指著遠(yuǎn)處的火車大喊一聲,隨即我們倆立刻進(jìn)入“警戒”狀態(tài),繃緊神經(jīng),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火車。然而,大部分時候的結(jié)果是我們倆都沒有看清,雖然頭都暈了,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車無情地離去。但是一旦我能夠捕捉到部分偏旁和筆畫,我的腦子就會飛快運(yùn)轉(zhuǎn),排除一個又一個可能后猜出火車的起始地。向大人確認(rèn)時,沒想到,竟準(zhǔn)確無誤。我和弟弟拍著手歡呼,我更是肆意大笑,蹦蹦跳跳地轉(zhuǎn)來轉(zhuǎn)去,雙手叉腰看向爸爸媽媽,用無比自豪的語氣說:“你們看,我多厲害啊!”
時過境遷,我回憶起小時候的傻事,不禁搖頭輕笑自己曾經(jīng)的天真。可是,童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不都是由那些簡單的小事組成的單純的快樂嗎?
還記得第一次乘火車去上海看世博會,我心中激動得不能自已,但又對陌生的環(huán)境感到害怕,于是緊緊地抓著媽媽的衣角,生怕走丟了。我左顧右盼,觀察著火車上的環(huán)境和站臺上、火車上來往匆匆的乘客。當(dāng)時的我不懂心中為何如此激動,只當(dāng)作好奇感。時隔很久,我才明白——這意味著我第一次能夠跳出一個狹小的空間,奔向更廣闊的天地。我正發(fā)著呆,忽然看見站臺正在往前“走”——火車啟動了!我睜大了眼睛,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遠(yuǎn)方的風(fēng)景。我期待著,接下來出現(xiàn)在我眼前的會是怎樣一番天地。
隨著時代的進(jìn)步,科學(xué)技術(shù)也在突飛猛進(jìn)。后來,我坐上了高鐵。高鐵整潔舒適的環(huán)境實(shí)在是讓人滿意,然而我卻再也沒有當(dāng)初第一次坐火車時的激動了。我靠在柔軟的座椅上,閉上眼,一片黑暗中卻記起我當(dāng)初在火車上拍的照片。一個扎著雙馬尾的女孩兒對著鏡頭靦腆一笑,手中比著“V”字,眼中流露著掩飾不住的興奮。“看吶,好漂亮!”后座有一個稚嫩的童聲驚呼道。我睜開眼,往窗外望去。正是春天,萬物復(fù)蘇,春暖花開,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開在田野之間,生機(jī)勃勃的綠色和清新的黃色交織在一起,向東西方向蔓延開來,在天地之間織成了一幅清新美麗的畫卷,在人們的心湖中蕩起陣陣漣漪。遠(yuǎn)方大大小小的丘陵綿延起伏,肅穆地注視著我們遠(yuǎn)去。我還沒欣賞夠這美麗的景色,眼前突然一黑——進(jìn)隧道了。
每當(dāng)我夢回童年,我仿佛又變回了當(dāng)初那個蹲在鐵路旁,癡癡觀察火車的五六歲孩子,聆聽著警示鈴聲,感受著火車經(jīng)過時刮起的大風(fēng),任它吹亂我的頭發(fā)。回憶瞬息變化,綠皮的、紅皮的火車像幻燈片一般從我眼前閃過,最后定格在樣式先進(jìn)、氣勢宏大的高鐵。我站在列車前,拉著滿載回憶的行李箱,在踏上高鐵的臺階之時,我回過頭,向那個小小的自己揮了揮手告別,隨后乘著高鐵,繼續(xù)行駛在歲月的旅途中。
編輯/胡雅琳
- 中學(xué)生百科·小文藝的其它文章
- 我以為自己在寫作
- 野生的脈搏
- 不過是不喜歡失望
- 人間白雪落,星河間有你
- 追星應(yīng)該是件快樂的事
- 選 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