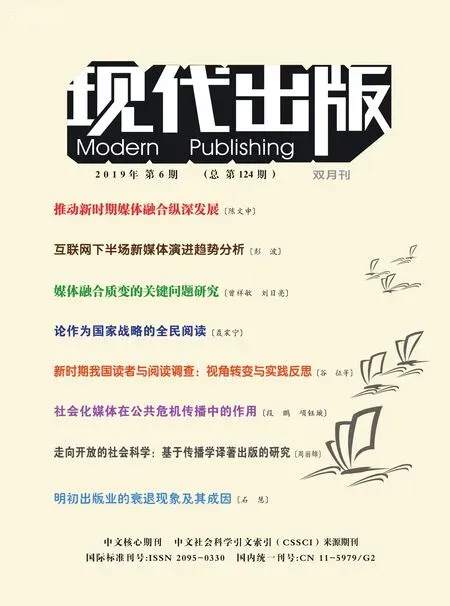轉型和轉場:范式轉換視角下傳統出版社數字化發展策略*
◎ 劉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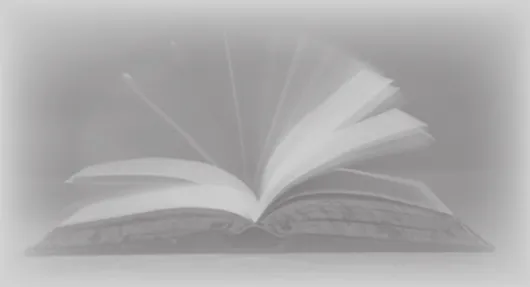
經歷互聯網和數字技術這些年對傳統出版業的沖擊,“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轉型”“融合出版”“內容付費”“大出版產業”這些依次出現的關鍵術語,表明出版業在擁抱新技術和堅守印刷出版的猶疑兩決間,無論是否高調提“轉型”二字,終究是走上了轉型之路,即不再抱持印刷書是知識文明的唯一載體的認知。
傳統出版人以書籍承載人類所有智慧和文明為由來為自己的事業背書,他們把印刷文化置于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可能像麥克盧漢在給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作序時說的:“我們這種文明追隨印刷工業的發展。也許,我們和它的關系實際是太密切了,所以我們探察不到它的特征。”伊尼斯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有它的傳播偏向,“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印刷文字是視覺型的,消滅了口語和聲音,促進了線性的因果思維和個體閱讀,消滅了對話交流而且把讀者參與完全排除在外……我們今天從音頻產品的爆發、數字閱讀的社交化等新需求似乎看到在互聯網語境下口傳文化的一些優勢被“復活”,麥克盧漢形容為我們正在“將磁帶倒過來放送”。從歷史主義的視角,印刷文明既沒有同人類命運同始,自然也不會共終。
很多出版人看到技術的重要性,但仍然堅持圖書是系統的優質的閱讀,視互聯網數字化內容為碎片化的淺薄閱讀;或者在融合出版實踐中把新技術當作花蝴蝶般的點綴,認為其對紙質書出版只有助益,而不會對印刷出版范式產生任何影響。“把媒介融合看成是先前諸種不同技術正經歷著的無縫整合……此種腔調目前在研究、政策或是公共討論中均十分流行。”正如馬克·波斯特批評的:“探討新傳播技術的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代性視野的限制,即因特網是一個透明的工具,只會產生種種新的效率,就其本身而言卻不會改變什么。”
傳統出版業正在走上的轉型之路,準確地描述是一種“現代性語境的轉型”,即現代工業社會培育了印刷出版以出版機構為主體的、以圖書為主要產品形態的強大認知,“來自優勢地位的束縛”和麻木,使出版社把轉型面對的新出版領域想象成自己居于絕對支配地位、新技術逆來順受任我統治的靜止的王國。本文欲借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論證互聯網媒介技術特征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知識生產新場域,新場域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依靠各自擁有的資本進行激烈斗爭的結構空間”。從印刷書出版到互聯網媒介環境下的知識生產(內容出版)是一場范式轉換。如果出版社不能認清這一態勢進行“轉場”,還談不上真正的轉型。
一、“現代性語境的轉型”:以出版機構為主體
馬克斯·韋伯關于社會學類型的建立和研究,使“轉型”被用于結構性的比較分析;國內熱度最集中的研討也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的時代課題。社會轉型主要指“現代性轉型”,這使“轉型”一詞一開始就帶有“現代性”限定;后來泛化于社會生活和行業的各個層面(組織、制度、行動等)的“轉型”,逐漸變成中性詞,核心問題指某一領域的基本結構模式改變,即庫恩提出的“范式”的轉換。但出版業的轉型一直是在“現代性語境”下展開的。
中國歷史上出版能稱為轉型的有兩次:一次是宋代的轉型,“是指出版由‘寫在紙上的抄本出版’轉向‘雕版出版’”,使中國古代社會總體上進入了“印本時代”;另一次是以近代上海出版為代表的現代性出版,西方機械印刷技術傳入取代傳統雕版印刷術,以及形成與工業技術相匹配的專業分工合作的現代出版產業形態。
兩次以技術為起點的出版轉型,帶來的是知識傳播機制的相應變化。從抄本到印本、從雕版印刷到機械印刷,出版物的復制速率成倍提升,對資金、市場以及智力活動的保護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個體的出版行為發展為專門的印刷作坊;再到近代轉型中,出版商作為專業化的“不確定性承擔者”,把印刷商和銷售商降到次要位置,進而發展成為主導書業的出版企業,形成“出版大于印刷”的局面。這種出版機構主導的產業模式成為19世紀和20世紀至今全世界的普遍樣式。
印刷文明形成以出版機構為知識生產中樞、以圖書為產品形態、作者向出版社投稿、讀者通過固定營銷渠道買書的線性出版流程和產業鏈形態。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出現以前,歷史上的出版轉型都是不斷強化出版機構的主體地位的。所以我們面對數字出版轉型,很自然形成以現代出版機構為主體的歷史性路徑依賴。不管是產品形態、生產流程還是組織架構的改造,都是圍繞著出版機構這一主體展開的,差異只是轉型程度的深淺不同而已。這種毋庸置疑的轉型思路來自印刷文明的歷史慣習。
二、轉場: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的范式轉移
傳統出版業現在不認可向數字出版全面轉型,是因為“數字出版”在過去的實踐中被定義為一個窄化的概念,即“紙質出版物向數字介質的轉移”,并不能涵括互聯網影響下的整個出版業的新生態。新事物的出現總是面臨“詞不及物”的尷尬。我們對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認識,經歷了互聯網是與現代三大傳播技術(報紙、電視、廣播)平列的“第四媒介”、“新媒介”到“互聯網思維”、“互聯網+”的變化。后面這些流行詞語的出現,隱喻互聯網可能像歷史上“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帶動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成為社會各行業的新的參照系,同樣在范式上對印刷出版提出了根本挑戰。
1. 范式不同:互聯網VS.工業化媒介
麥克盧漢提出著名的“媒介即訊息”觀點,他旨在闡明:任何技術都逐漸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人的環境,環境并非消極的包裝用品,而是積極的作用進程。他認為印刷術和電子媒介這兩套技術環境隱含著完全不同的意義體系。他的理論放到互聯網環境下似乎更有說服力。
工業革命機器化大生產和啟蒙運動對科學理性精神的推崇,在20世紀初形成了被葛蘭西稱為“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的現代工業社會,其整體特征是:以分工和專業化為基礎的標準化產品的大批量生產、相應的垂直一體化的組織結構和科學管理。工業化媒介報紙、圖書、電視都附著生長于這套政治經濟體制;而印刷媒介和書寫文字的線性排列、封閉、穩定的特性,特別支撐了理性自律的獨立個體的構建、現代“科層制”的組織管理和教育的分類資料系統學習模式。
“互聯網是一個不同于工業社會的人機關系的媒介的領域”。互聯網從分布式網絡、阿帕網到萬維網,根據TCP/IP協議奠定了“去中心”和“連接”的技術結構骨架。進入大眾社會商業化應用后,新技術迭代速度令人眼花繚亂,然而互聯網這兩個基本結構特征是不斷被強化的:其一是自web2.0自媒體出現以來“信息中心”讓位給“用戶中心”模式,個人和機構均作為“節點”,建立了點對點之間自由平等的直接交流,徹底顛覆工業化機構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秩序等級;其二是基于社會化媒體、移動互聯、傳感器、大數據、智能化越來越強的“萬物互聯”模式,打破專業化的社會分工壁壘,使基于用戶需求的信息知識和物質消費一體化成為可能。工業社會“機構+產品”的專業封閉的范式,從底層邏輯上被“用戶+需求”的連接的互聯網范式改變。零售、餐飲、銀行等所有傳統產業都要接入網絡新范式,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出版業概莫能外。
2.策略改變:“場域”形成與出版機構“轉場”
“現代性語境的轉型”造成的結果,就是傳統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是禁錮在印刷出版范式里的,很自然地會以出版機構為主體、以圖書作為核心產品,僅僅把互聯網和數字化視作紙質書出版的“延長線”,即只會提高印刷出版的效率,卻不會動搖印刷出版的范式。
目前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兩大成就,都基于“延長線”思維:第一,電子書作為圖書的新載體;第二,電商作為圖書的網絡銷售新渠道。新媒介固然擴大了圖書傳播范圍、提高了傳播效率和延長了圖書使用壽命,也有效粘住年輕消費者,但還遠不是能讓傳統出版產業煥發新生命力的轉型,甚至暴露出來的矛盾、不協調,都直擊傳統出版業的痛點。封裝加密的電子書仍然固守紙質書的結構,困擾出版業的問題都來自傳統出版圖書生產的視角,閱讀體驗差、制式不統一、盜版等,數字技術的長處毫無用武之地。直到最近才有人疾呼:電子書像書,一開始就錯了!京東、當當、天貓也不是原來附著于出版社處于傳統出版產業鏈下游的發行商,傳統出版社對于電商利用圖書大打折扣吸引用戶流量的做法束手無策。
相反,我們越來越看到,互聯網在吸引用戶流量、釋放作者讀者的能量以及改變知識的流動重組方式方面,顯示了巨大的變革力量,這些無不是印刷出版的短板。因為基本范式不同,印刷出版作為獨立產業和以出版機構為出版主體的“寫作者—出版者—銷售者—閱讀者”的線性產業鏈,到互聯網環境下變成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形容的“場域”—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依靠各自擁有的資本進行激烈斗爭的關系型結構空間。印刷范式下唯我獨大的出版社將之稱為“外行攪局”,其實是出版新場域新范式的出現。出版機構需要來一次“轉場”—離開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以出版機構為中心組織圖書生產的現代性出版模式,把自己的專業生產能力融入到互聯網“用戶+需求”的連接新范式中,積極尋求與互聯網平臺運營商、數字技術服務商、自媒體個人或組織等的合作,因應讀者(用戶)基于新媒介環境的知識新需求。
三、互聯網影響下的出版場域:行動者位置、資本、慣習
最先系統運用“場域”理論分析出版業的,是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家、學術出版社Polity的社長約翰·B.湯普森。他認為布爾迪厄場域理論適用于出版界,主要是同樣可以把出版領域概念化為一個由不同出版組織構成的社會位置的結構化空間,每個出版商的位置依賴于他們占有的經濟、人力、智力和象征資本資源的數量。遺憾的是,國內“鳳凰出版研究譯叢”翻譯引進他的兩部相關著作時,將通譯的“場域”改為“領域”一詞,“領域”一詞抹殺了布爾迪厄場域原生理論的張力。與領域作為一個平面靜態的術語不同,“場域是力量關系和旨在改變場域的斗爭關系的地方,因此也是無休止的變革的地方”,這恰恰準確描述了互聯網影響下多頭行動者激烈爭奪利益的出版新現狀(更準確地說,這里“出版”可能指超越圖書生產的“知識生產”)。而約翰·B.湯普森代表了多數傳統出版人對數字化偏保守的立場—他理解的數字化革命也就是前面所言的“現代性語境的轉型”,改造的只是傳統出版的流程,提高了傳統出版的效率。
1. 場域的形成首先是由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的不同位置所決定的
布爾迪厄指出:場域的結構,是參與到專門資本的分配斗爭中去的那些行動者同行動者,或者機構同機構之間的力的關系的狀況。現代圖書出版造就了出版社的主體地位(基于歷史成就和合法授權)和線性生產模式,而互聯網推動形成的新的內容出版場域,更符合不同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結構性空間,充滿斗爭的關系。
少兒出版是現在此種表現最鮮明的一個領域。單從圖書生產角度,以“華東六少”為代表的傳統少兒出版社沒有受到任何數字化威脅,童書是近年圖書市場份額增長最快的一大品類。但我們也看到,以親子公眾號為代表的“凱叔講故事”“小小包麻麻”“大手牽小手”等,以嬰童、學齡兒童及其家長為對象,進行免費育兒知識傳播,先吸納用戶,再全方位包攬兒童成長的需求,賣書賣玩具賣童車、開發微課音頻產品、組織冬夏令營游學營等,已經建立起符合互聯網“用戶+需求”范式的全新的場域。自媒體人、兒童家長(生產消費者)、教學名師、出版社、兒童用品供貨商等行動者在這個場域占據不同位置,憑借不同資本和資源爭奪利潤。但出版社現在出于印刷范式思維慣性把新場域簡單視作圖書銷售的又一新渠道—社群營銷,并未意識到自媒體大V借助社會化媒體已經組織起來一種新生態,建立兒童知識服務場域的新邏輯。甚至在這個場域,我們發現知識生產、知識服務的稱呼都是不恰當不全面的,讀者“用戶化”“消費者化”,互聯網建立起圍繞兒童及其家長(用戶)需求的一切連接。
2. 資本決定行動者在場域內的位置和他們在場域關系中的力量
布爾迪厄認為,場域的斗爭緊張結構是場域內握有各種資本的行動者運用游戲規則的結果,反過來場域為各種資本提供了相互競爭、比較和轉換的場所。他提出四種根本的資本類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征(符號)資本。約翰·B.湯普森結合出版業發展實踐,把文化資本具化為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出版是內容產業,傳統出版社的資本優勢在于長期積累的智力資本(內容資源)和象征資本(品牌效應),在印刷出版占主導范式時使它們居于支配地位。
但布爾迪厄指出,各種資本類型隨著場域內游戲規則的變化都是可以轉換的。學術出版場域的分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約翰·B.湯普森注意到學術著作和期刊論文受數字化影響程度不同,但他沒有沿著布爾迪厄的理論進一步分析。學術著作出版受閱讀系統性習慣和科研評價機制的影響仍然以紙質書出版為主,傳統出版社握有內容智力資本和品牌象征資本,在場域內處于支配地位;但學術期刊論文出版完全向集成的在線數據庫轉化,檢索的豐富全面和即時動態上升為學者的剛需,使愛思唯爾、知網這些平臺型公司轉而在該場域內處于支配地位,品牌象征資本轉移到它們手中。愛思唯爾、知網能強硬地持續漲價,是因為場域內行動者的權力(或資本)對比關系改變了場域結構,“占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傳統出版人有時過于自信“內容為王”,其實是相信自己擁有的資本恒定不變,忽視了互聯網技術改變了內容和知識的利用方式,技術本身成為內容的一部分。所以相比“結構空間”,布爾迪厄更愿意把場域比作“游戲”,“游戲者之間力量關系的狀況在決定某個場域的結構”,不同種類的資本是游戲者手中握有的“牌”。
3. 行動者的慣習影響他們在場域中采取的策略,慣習只能適度改造
布爾迪厄把擁有一定數量資本的行動者在場域中采取的策略(顛覆、維持或遠離游戲)帶有性情傾向,稱作慣習(或習性,habitus);他認為內化于行動者的這種性情傾向系統,使他們的行動和行為模式總帶有歷史的痕跡。慣習不是習慣的重復性和惰性,仍然有創造性和再生性,又會對歷史原有的痕跡進行適當的改造,以便適用于當下的遭遇。但慣習只能適度改造,無法顛覆。
如果我們引入慣習理論工具分析傳統出版機構數字化轉型,就知道其有所為有所不能為。出版機構在歷史發展中獲得了它的主體地位,也形成了適應圖書生產的線性生產模式和科層制組織架構。印刷范式就是內化于它的行動策略的歷史慣習。首先,它最容易做到的轉型就是不影響傳統出版的“機構+圖書”范式,做印刷出版的“延長線”,如前所述的電子書和網絡營銷。難度上升一層,如果轉型做IP和社群運營,就對傳統出版只擅長封閉的圖書生產不善于讀者經營、內容開發提出了挑戰,但我們會發現少兒出版機構運營IP、專業出版社做數據庫開發和知識社區,比一些綜合性出版社效果顯著,因為它們的傳統讀者群和圖書口味都相對窄化一致,歷史慣習只要稍加改造,容易向“用戶+需求”的互聯網范式靠攏。如果難度再上升一層,新場域游戲規則完全基于互聯網互動、連接的范式邏輯,像網絡文學場域的新文創模式是基于“作者—讀者”互動機制,“得到”提出改變電子書過去的貨架陳列模式要做電子書內容策展,這些對印刷出版的慣習提出根本挑戰,場域內處于支配地位的不可能是傳統出版機構,只能是互聯網基因的平臺型公司。向互聯網范式轉移的難度越大,傳統出版社越難以轉型,在場域游戲規則中可能退居配合的一方或被邊緣化。但是現在有些研究者出于想象認為傳統出版社作為轉型主體可以通吃數字出版產業鏈,通俗地說,“簡直要了他們的老命”。不考慮歷史慣習的轉型,實踐中必然碰壁,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學界樂于趨新而傳統出版社面對數字化轉型多數趨于保守姿態。
四、結論:超越二元對立的數字出版結構性策略和研究
歷史上“現代性語境”的出版轉型捍衛了出版機構的主體性。在出版機構這個強大主體的組織下,借助印刷術和機器化大生產,人類知識生產和文明積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印刷書成為精通寰宇知識的最有效途徑。傳統出版面臨數字化轉型仍然沿襲了“現代性語境的轉型”的歷史慣習,把互聯網當作印刷出版的“延長線”。
但是不同于印刷文化取代手抄文化時,“印刷文化強化了舊有書寫技術的作用”,互聯網媒介技術特征攪亂了印刷媒介塑造的有界的、線性的、貫序的、理性的社會空間,“原來互相分割的社會交往語境和形態模糊乃至坍塌,媒介產業的霸權地位已經不在,而另外一種形式的融合—社會融合悄然崛起”。“用戶+需求”的互聯網新范式影響下,出版機構主導的傳統出版產業逐漸演化成為多元行動者依靠各自擁有的資本出于慣習進行激烈斗爭的知識生產新場域。出版社只有認清這一態勢并轉移到新的場域,才能實現真正的轉型(中性詞)。
復旦學者張大偉指出:“我國出版業數字轉型研究,缺乏對新技術的深刻認知和對出版實踐的深入調研,也缺乏建立數字知識生態的理論框架。”國內學者已有一些運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具體分析新出版場域的成果,但多是割裂式的碎片化套用,缺乏對該理論的系統論述和總體把握。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總體特征是超越二元對立性,諸如導致社會科學長期分裂的宏觀和微觀、主體和客體等,正好可以治傳統出版“現代性語境的轉型”的二元分裂癥。“現代性語境的轉型”的癥結恰恰在于,作為主體的出版機構把作者、書稿、讀者都視為它發生作用的客體,作者、讀者長期淪為被媒介組織規訓的對象;面對新技術的沖擊,照樣想把互聯網作為改造征服的客體,為我所用。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不跳出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就不可能意識到互聯網的結構性范式變革。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具體特征,一個是關系主義的結構空間,另一個是生成性、實踐性、反思性。如果我們認識到互聯網是重新結構社會的方式,而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會發現布爾迪厄理論運用于互聯網影響下的出版新場域的分析更加精妙適當。場域理論的基礎是關系性思維,布爾迪厄反復強調“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web2.0自媒體出現后的互聯網正是關系媒介。場域理論的特征是高度復雜精細的“生成的結構主義”,超越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而區別于線性、封閉的印刷媒介,互聯網的基本特征正是不斷演化的動態結構化網絡。“場域”理論的主要分析工具和單元是資本、慣習等,這有助于我們理解傳統出版社的數字化轉型有所為有所不能為,無法“一刀切”。場域理論以其“生成結構主義”的高度精細的分析模式能夠克服以往出版研究的主觀粗率和缺乏理論框架;而且布爾迪厄認為“真正的理論是在它推動產生的科學工作中不斷磨礪,才最終完成的”,場域理論以其實踐反思特征,為出版業的實踐性、新舊媒介趨于錯綜復雜的互動效果以及互聯網數字技術的發展和不可預估留下了空間,或可撐開一片研究新天地。
“轉場”也許更像一個口號、一種號召,但是運用場域理論仔細深入分析互聯網影響下知識生產場域以及每個出版子場域的結構和影響變量,出版社可能更清楚自己在“轉場”后的場域內的位置、相對力量、策略性取向,轉型之路會走得更踏實可靠。
注釋:
① 伊尼斯.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8.
② 伊尼斯.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2.
③ 黃旦.從業態轉向社會形態:媒介融合再理解[J].現代傳播,2016(1):13.
④ 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28.
⑤ 伊尼斯.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8.
⑥ 宮留記.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48.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30.布爾迪厄本人說“我并不太喜歡專業定義”,因此根據他本人的論述和研究者的闡釋作如上簡要概括。
⑦ 鄭杭生,朱曉權.論韋伯的“理想類型”及其晚期運用—社會結構分析和它對認識“轉型社會”的一點啟示[J].天津社會科學,1991(4):62-67.
⑧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71-78.庫恩通過科學革命論證,宣布舊范式的無效,必須有一個合適的新范式取代它的地位,遠不是對舊范式修改和擴展所能達到的過程;但新舊范式轉變期間,有一個很大的交集,并不是立馬否定。國內有關“Paradigm shift”的兩種譯法—“范式轉換”“范式轉移”皆有合理處,本文根據論述重點取其性質上的“范式轉換”。
⑨ 周寶榮.走向大眾:宋代的出版轉型[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197.周著的研究反駁了過去主流的“唐末五代雕版印刷出版占據主導地位”的說法。
⑩ 芮哲非.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M].張志強,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3-17.魏玉山把商務印書館的建立作為現代出版和傳統出版區分的標志,因為“商務建立之后, 才把現代的印刷技術、現代的出版管理、現代的形態與內容、現代的圖書發行等結合在一起”(魏玉山.關于中國現代出版業誕生的幾個問題[J].出版發行研究,1999(5):14.
? 于文.出版商的誕生:不確定性與18世紀英國圖書生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78.
? 芬克爾斯坦,麥克利里.書史導論[M].何朝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34.
? 愛森斯坦.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M].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5.
? 葛蘭西.獄中札記[M].葆煦,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83-417.
? 夏蒂埃.書籍的秩序[M]吳泓渺,張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3,24.
? 波斯特.互聯網怎么了[M].易容,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13.
? 段永朝.互聯網思想十講[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楊吉.互聯網:一部概念史[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 MATTERS,黃一琨“.電子書”,從概念上就錯了[OL].在下版君(公眾號),2019-04-24.
? 湯普森.數字時代的圖書[M].張志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湯普森.文化商人:21世紀的出版業[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
?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30.該書是布爾迪厄在芝加哥大學與一群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博士生在研討班上的交流,由華德康(Wacquant)整理組織,以訪談和對話的形式既系統全面又深入淺出地總結了布爾迪厄研究的核心意圖和研究成果,又回應了美國和歐洲大陸學者對其理論的批評詰難,是研究布爾迪厄著作的“一個跳板”“一個指南”。可以涵蓋此前國內出版的《實踐與反思》《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的主要內容,又是《藝術的法則》《科學的社會用途》《區隔》等專著的理論基礎。以下對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基本理解引用主要來自該書。
?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22-128.
? 劉影,高焱.童書數字化出版:從印刷本位到互聯網邏輯[J].現代出版,2016(3):39.
?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48.
? 湯普森.文化商人:21世紀的出版業[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4-9.
?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23-124.
[27]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31.
[28] 宮留記.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147-148.
[29] 羅振宇“.得到”2019春季知識發布會演講全文[OL].得到APP,2019-04-23.
[30] 曼紐爾.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31] 張大偉.數字時代中國出版業“生存戰略”的雙重誤區[J].編輯學刊,2018(2):6-11.
[32]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21.
[33] 陳先紅.論新媒介即關系[J].現代傳播,2006(3):54-56;喻國明,馬慧.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范式“:關系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系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J].國際新聞界,2016(10):6-27.
[34] 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