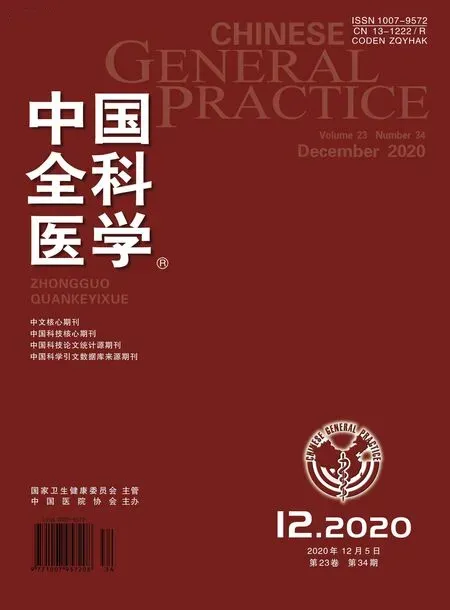我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背景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誘導需求的防范和規制研究
尹天露,高曉歡,韓建軍
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醫生可能對患者的健康服務需求進行誘導以獲得更多的利益,被稱為供給者誘導需求(supplier induced demand,SID)或醫生誘導需求(physician induced demand,PID)[1]。近年來我國對醫療衛生投入持續增加,隨著分級診療制度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持續推進,我國衛生費用“重醫輕防”和大醫院過于集中的配置格局在逐步改變,衛生費用分布調整的效果也逐漸顯現。但同時,由于家庭醫生服務體系尚不成熟,各層藥商、醫療器械供應者已有將營銷市場轉移到社區的趨勢。社區全科醫生在日常工作中擔任醫療“守門人”、顧問(adviser)、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等多種角色,且固定的合作關系更方便創造需求,其在提供簽約服務和具體醫療服務時,如果過于追求自身利益,則會目的性左右簽約者的衛生服務選擇,致使醫療衛生資源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利用甚至浪費。目前,我國關于醫生誘導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立醫院和對大型醫療機構誘導需求的規制研究,而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尤其是在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背景下社區醫生的誘導需求現象缺乏規制和規范指導研究。因此,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社區家庭醫生誘導需求情況,結合美國、澳大利亞及歐盟國家誘導需求現象和規制,為建立我國家庭醫生激勵和約束機制,尤其是簽約服務背景下社區全科醫生誘導需求防范和規制提供依據。
1 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誘導需求原因分析
1.1 社區居民的消費特征
1.1.1 醫療服務的選擇局限性 我國的社區衛生服務發展存在地域差異,社區居民因經濟水平和就醫觀念的局限,以及醫療服務的專業性,導致無法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何時何地進行消費。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醫療服務不同于其他商品,價格彈性相對較小,替代商品難以找到,也因此,醫療消費中存在的不可選擇性為醫生誘導需求提供了“先天條件”。患者在購買醫療服務時主動權相對較弱,而醫生在醫療服務中占據主導地位。
1.1.2 付費方式 目前,我國大多數社區衛生服務仍采用按項目付費的方式。2016年6月,國務院原醫改辦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印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指導意見的通知》(國醫改辦發〔2016〕1號),指出有條件的地區可探索將簽約居民的門診基金按人頭支付給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或家庭醫生團隊,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或家庭醫生團隊對經社區向醫院轉診的患者支付一定的轉診費用,并探索對縱向合作的醫療聯合體等以分工協作方式實行醫療保險總額付費[2-3]。按項目付費的方式使得醫生有動機通過誘導患者的醫療需求來彌補簽約患者數量不足的問題。
1.1.3 醫療服務的不確定性 通常醫生和患者都具有對醫療服務標準的不確定性。患者對于自身的病因、并發癥及發病時間等都依賴于醫生的專業診斷得以確認,對于醫療服務的選擇具有不可預測性。同時,醫生也可能在單項疾病的診斷過程中發現其他疾病或并發癥。因此,在患者就醫過程中,通常會接受更大范圍的檢查以降低潛在的治療風險,或被建議使用一些療效更好但價格更高的藥物等。此外,由于醫療衛生服務的高度專業性,服務中可能出現更多的不確定事件,使患者失去了對治療結果和醫療服務的評價標準,也增加了鑒定和監督機構對醫療行為的監管難度。因此,醫療服務的高度不確定性為醫生的誘導行為創造了條件。
1.2 我國的薪酬制度 在我國,社區家庭醫生的工資主要由基礎工資、績效工資、獎勵補助、簽約服務費等部分組成。其中,簽約服務費一般由醫療保險基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及簽約居民三方共同分擔。不同省份的簽約服務費籌資渠道、籌資標準、支付方式差距較大,且只有少數省份規定了簽約服務經費“不納入績效工資和其他應得的獎補經費總額”。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社區家庭醫生的月收入集中在2 000~5 000元,且東西部地區差距較大,家庭醫生對收入報酬、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滿意度較低[4]。在我國現行醫療體制下,政府的財政補貼較少,很多私營醫療機構通常會為了維持經營而增加服務量,體現在診療項目或藥品上,或選擇高價的診療項目或藥品,以及“開單提成”等激勵措施,以激發醫生工作的積極性,讓醫生的績效工資與其服務數量和藥單數量掛鉤[5]。績效考核的薪酬方式,在各行業都是激勵員工營銷、消費者多購買的強有力方式。而對醫生行業而言,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希望盡可能降低職業風險。所以,醫生想要增加收入需要多開檢查和藥品處方,同時為避免風險,更要盡可能讓患者進行更加全方位的檢查以消除隱患。因此,這種以診療數量和藥品量作為標準的薪資制度,是醫生誘導需求的“源動力”。
隨著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開展,社區家庭醫生數量逐漸增加,家庭醫生的收入因社區醫療市場競爭力增大而受到影響。因此,在日常的臨床診療中,額外的醫學檢查、更頻繁的患者隨訪、多余的藥品消費等都可能成為其彌補收入的方式。這種利用信息不對稱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的現象,在整個醫療市場的醫生誘導行為中表現得尤為突出[1,6]。
2 國外醫療誘導需求控制相關研究和經驗
國際上通過對醫療服務的供方和需方的不同群體研究,證實了誘導需求在初級衛生保健中的存在,且其與醫生密度具有一定關系。挪威學者GRYTTEN等[7]通過隊列研究得出了當家庭醫生密度增大,合同醫生相對于固定薪資的醫生更有動機通過誘導對服務的需求來彌補患者數量的缺乏。日本學者SEKIMOTO等[8]的研究結果顯示,治療慢性生活方式相關疾病的醫患接觸頻率與臨床醫生密度明顯相關,當診所醫生密度增加,醫患接觸頻率增大,醫療費用也明顯增加,證實了初級衛生保健醫生誘導需求在日本的存在。
2.1 對醫生的規制 在擁有大部分私營醫療機構的背景下,目前美國已有16個州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和實行了《患者權利憲章》,2002年頒布的《新千年醫師職業精神:醫師憲章》明確規定了醫師職業精神的三條基本原則和一系列專業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程度[9]。
2.2 付費制度改革 美國、澳大利亞、法國、巴西等多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開始實行醫療保障按績效付費(PFP)方式,其中多數國家把疾病預防和控制、醫療服務質量與效果、患者滿意度納入按績效付費的績效考核標準當中。另外,在英國的績效考核標準中包含了對電子病歷質量的評價[10]。美國的聯合職業醫生項目(Physician Group Practice,PGP)規定,醫生如果主動上報醫療質量信息可在醫護人員原本收入上增加2%[11]。2011年起,坦桑尼亞政府衛生和社會福利部對濱海7個地區實施醫務人員付費項目的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的內容中同樣納入了健康管理信息系統的使用情況[12]。法國通過將付費項目使用率與醫務人員的績效掛鉤,控制醫生使用昂貴檢查項目和藥品[13]。
2.3 醫療保險模式改革 STRIK[14]分析了荷蘭醫療保險變革可能對全科醫生及患者產生的影響,總結了由于道德風險產生誘導需求的情況。通過分析2005—2007年電子病歷結果,發現在預付費保險模式(PPS)下,醫生的診療行為明顯被激發,這表明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對醫生誘導需求具有影響。德國和荷蘭的社會醫療保險模式類似,商業保險銜接基本醫療保險正成為趨勢。在老齡化與醫療保險費用支出持續增長的壓力下,采用商業保險在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中發揮一定的復合作用,與政府在清晰的分工定位下各司其職,參與醫療服務的行為約束和費用管控。為維持其公平性和穩定性,德國政府對其籌資和運營設置了一定的市場規則。在保險費率方面,保費僅在參保人進入時依據風險評估確定,不得超過政府設定的最高標準,也不得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14-15]。商業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的銜接,有效控制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并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具有對醫療行為的監督功能。在商業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聯合下,醫療機構會將重心放在醫療控費和提高患者滿意度上,并且商業保險為提升在醫療市場上的競爭力,會時刻監督、引導醫療機構的服務,由此形成商業保險與醫療機構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協調機制,推動醫療服務市場的良性運作與可持續發展[15]。
2.4 藥品控費 利用藥學服務進行藥品控費。美國衛生系統藥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system Pharmacist,ASHP)從藥品成本根源入手管控藥品,制定了臨床藥品使用規范,以降低藥品費用,該策略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采用。制定藥品管理目錄并將醫療項目與成本控費相結合,優化了醫療機構藥品管理,并從藥學角度合理控制醫療費用[16]。
3 對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誘導需求控制的思考
3.1 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在減少誘導需求中的作用與挑戰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醫療保險體制進行付費方式的改革,徹底規避大包大攬的傳統公費醫療模式;1998年《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發布,制定了醫療保險基金籌集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壓力,但是由于缺乏對供方的行為控制規范,改革過程中滋生了醫療供方的誘導現象[17]。新醫改中,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是對衛生體制總體控費和優化籌資結構、合理布局的有效策略與措施。劉巧等[18]對我國衛生費用趨勢進行分析,發現我國衛生費用增長的影響因素在趨勢上與歐美國家無差異,真正有差異的是直接與間接費用問題。我國間接衛生費用較發達國家更多,未包含在衛生總費用中。全科醫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門人”,處于衛生服務的最前沿,該階段增加的費用將會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國醫療服務的投入產出比。在全科醫生服務中的“間接費用”,可有效降低后期在上級綜合醫院產生的醫療費用,并從整體上控制我國衛生投入的總體費用。
近年來,我國各地區積極探索、推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在醫療服務方面不再局限于追求數量,更追求合理和最優配置,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隨著醫療改革的深入,大型公立醫院試點單位在實行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付費后,起到了明顯的醫療控費效果,藥廠藥品銷售的市場也隨即轉向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而社區相關管理缺乏明確制度規范,公立和非公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成為潛在的受益主體,某些私營非公立醫療機構的供方誘導需求扭曲了市場主體行為,醫改制度性缺失導致失去制約。因此,治療過度和誘導需求的防范和規制等均關乎醫改實施的成敗。
3.2 發揮市場引導作用、重視醫療服務質量有利于減少誘導需求 國外部分發達國家供方誘導需求并不嚴重的根本原因在于醫療服務的高度市場化,市場機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具有克服自身失靈的能力。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醫療服務市場,良好聲譽的價值遠大于短期的利益獲得,抑制自身的道德風險無需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是收獲長期利益的理性選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實行的醫療保障按績效付費方式,把是否提高醫療服務質量作為績效標準,對醫生誘導需求現象及合理費用控制起到了積極影響。同時,疾病預防與控制、使用醫療信息管理系統、增加患者滿意度這3項績效標準和醫療服務質量具有一定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醫療保障按績效付費制度在控制醫療費用的同時保障了醫療服務質量[19]。該方式是一個國家的醫療服務系統、醫療保障體系、評價監督體系等多方協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但這種付費方式值得借鑒。
4 對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誘導需求規制的措施建議
4.1 發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加強全科醫生培養 大力發展社區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增加全科醫生比例,同時重視醫務人員職業資質審查和教育培訓。制定行醫行為規范,提高醫生誘導需求的道德風險成本,同時滿足社區人力資源合理配置的需要,使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真正發揮“守門人”的職能。
4.2 增加激勵性約束 醫生的“收入需求”是引發“誘導需求”現象最直接原因,從單純的藥品提成和績效項目費用收入逐步轉變為將醫生的薪酬與患者滿意度掛鉤,提高醫療服務質量,讓市場競爭力對社區醫療行為進行宏觀調控。當患者可以自主選擇醫療機構和醫生,且其評價對于醫生的收入具有足夠大的影響力,社區的服務目標也會隨之轉變。
4.3 選擇性使用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 當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實行按人頭付費時,家庭醫生會以最少的服務量獲得最大的醫療效果,將縮短病程作為目標,以獲得長遠利潤,政府預先支付的費用與患者的實際消費無關,超支不補,理論上可以提高衛生資源的使用效率。但目前國內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醫療服務能力較弱,居民對社區家庭醫生的信任度較低,在社區實施按人頭付費的方式還需要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
4.4 廣泛開展健康教育,降低醫生創造額外需求的能力 MOHAMADLOO等[20]研究發現,患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減少誘導需求現象。當前的基層信息化建設為健康知識普及提供了平臺,患者因此獲得更多的選擇和對醫生決策的判斷,這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約束醫生誘導需求。
4.5 完善監督機制,加強信息披露 設立審查委員會,及時監督審查衛生服務合理使用情況;完善監督、評價體系,由政府主導,多部門參與評價并采納公眾媒體監督意見。建立質量評價結果的信息發布平臺,利用市場壓力推進醫療機構提高服務質量。
4.6 加強商業保險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協作與制約 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背景下,衛生服務定量配給意味著預算限制,限制一些人獲得有用或潛在有用的衛生服務。衛生市場和衛生服務的固有特點、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需求使得衛生服務必須實行定量配給。可以通過固定預算、“一攬子”福利來實現控制不合理衛生消費的目標。英國商業保險銜接基本醫療保險的經驗顯示,商業保險逐步銜接基本醫療保險,規范商業保險在公共服務定位下的自主運作行為,并加強商業保險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協作與制約關系是比較合理的路徑。
4.7 建立諸如衛生服務評價標準化,對供方誘導現象進行預測 參考VAN DE VOORDE等[21]提出的方法,對醫療資源供給量與醫療資源利用量間的相關性進行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簽約衛生服務人數作為醫療資源的供給量相匹配,從而判斷醫療供方導致醫療費用增長的影響程度。將人工智能網絡有關知識應用到醫療費用的估算和評價中,定量分析醫療保險基金受醫療供方誘導需求的影響程度[22]。
4.8 編輯基層藥品管理目錄 借鑒美國經驗,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可編輯等效處方目錄,提供不同成本的治療方案以供患者結合自身情況選擇,并進行社區藥品金額預算管理,提高藥師的控費意識。在處方的有效性方面,應大量征集臨床專家意見,篩選療效確切的藥物,從而確保在一定的時間和資源條件下疾病可以得到有效治療。
社區衛生服務中的誘導需求現象需要辯證看待,尤其在初級衛生保健中的按人頭付費可導致服務傾銷于“高風險”患者[23],這些患者經由誘導需求會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健康,減少疾病隱患,但會對健康狀況較好的患者存在服務不到位情況。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誘導需求對患者而言,是一種浪費。綜上所述,本文通過梳理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背景下的運營現狀,分析最可能產生誘導需求現象的市場環境、制度、道德等因素,總結國際規范制度經驗,提出規避基層醫生誘導需求的改革要素,以確保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更健康地發展。
作者貢獻:尹天露進行文章構思、文獻收集與整理、論文撰寫與修訂;高曉歡參與文獻檢索與整理;韓建軍負責文章審校。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