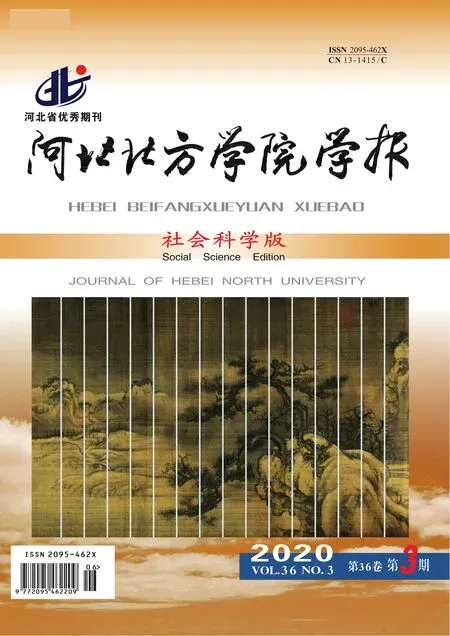元和士人的諷喻性詩歌創作
——以白居易、元稹與李紳為例
楊 藝 蕾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元和士人創作了大量蘊含豐富政治內容的諷喻性詩歌,這與他們的政治身份不無關系。白居易是該時期創作諷喻詩的代表詩人,他在創作時刻意強調自己的諫官身份,將諷喻性詩歌創作與諫官一職相聯系。元稹和李紳亦是該時期諷喻性詩歌創作的重要詩人,且曾與白居易集中進行過詩歌創作。考察這3位詩人的政治身份,揭橥元和士人的諫官身份和諫臣意識與諷喻性詩歌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元和年間的諷喻性詩歌創作。
一、白居易的諫官身份與諷喻詩創作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現實主義詩人,創作了大量的諷喻詩,被張為譽為“廣大教化主”。他秉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1]962的寫作觀點,通過詩歌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狀,以此“補察時政、泄導人情”[1]960。《新樂府》五十首是白居易諷喻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大力創作該類詩的一次實踐。白居易對《新樂府》詩歌的創作時間多有記載:“元和四年,予為左拾遺時作”[1]52;“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150首,謂之‘諷諭詩’”[1]964;“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1]962。由此可知,白居易明確標明了新樂府詩的創作時間,且特意強調創作之際自己的諫官身份。
(一)擔任拾遺——諷喻詩創作的契機
《舊唐書·白居易傳》:“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2]4340-4341“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于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3]唐代職官和使職并行不悖,兩者互相補充配合,構成唐朝的一代官制。在白居易這段任職經歷中,拾遺只是一個階官,用來定階位,掌俸祿;翰林學士是使職,相當于“特使”,需實際履職。所謂拾遺,即“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4],其職能是“掌供奉訥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于下,忠孝之不聞于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2]1845。拾遺是諫官體系中品階最低的官職,只有從八品上,于武則天垂拱年間(685)初次設立。雖然此官品階低,但地位“尤為清要”。白居易對此官職的設置有獨到的理解:
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后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1]1228-1229
在此他強調了拾遺的選官甚重,國家任命自己為拾遺是一種嘉獎,內心頗為感激;并認為“卑其秩”是為了“不惜身”,這才是國家設置拾遺的本意,即要求諫官有“不惜身”的精神。加之白居易擔任諫官屬于“非次擢拔”[2]4341,這更加深了他對國家委任其諫官一職的感激之情。《舊唐書》中記載:“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2]4341白居易通過創作諷喻詩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以此更好地履行諫官的職能,回報朝廷圣恩,這是白居易諷喻詩創作的契機和初衷。
(二)諷喻詩創作——履行諫官職能的補充
創作諷喻詩是白居易更好地履行諫官職能的具體實踐。首先,諷喻詩創作和進諫的目的性一致。諫官直接對皇帝負責,通過上呈奏疏的方式使帝王更加了解社會現狀和民生疾苦,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與弊補時闕的目的。諷喻詩創作亦是如此,白居易曾指出:“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1]52,又“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1]962。可見,他創作此類詩歌也是為帝王服務,即借詩歌傳達上諫時難以言說的內容,使皇帝更加了解民生民情。其次,諷喻詩與奏疏敘述或描寫的都是當時社會客觀現狀和突出矛盾。白居易身居諫官一職,多次向皇帝上疏言事,如《論制科人狀》針對“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1]1230發聲;《論和糴狀》根據“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1]1234所寫。諷喻詩創作要求內容有“實義”,即根據客觀真實事件而作,絕不是空泛地追求文學形式。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詩歌內容“核而實”,帶有明確的諷諫意味。每首詩的創作主旨也頗為明確,詩人在詩歌開頭就標明寫作緣由,在末尾又重申作詩的目的,通過這種強制性和明確性的創作要求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例如:《新樂府》首篇《七德舞》表明治國安邦的重要性,《立部妓》諷刺朝廷對雅樂的忽視,《胡旋女》勸導當今君王切勿沉迷舞蹈,《新豐折臂翁》反映了窮兵黷武對百姓的迫害。可見,上諫和諷喻詩創作相輔相成,是白居易履行其諫官職能的重要表現。唯一不同的是,上諫是通過奏疏直陳時政,諷喻詩是通過詩歌反映社會現狀和民生現實。
(三)諫官身份為諷喻詩創作提供合理支撐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拾遺軼滿后,改任京兆府戶曹參軍,“依前充翰林學士”。失去了諫官身份的依傍,其諫官精神和意識便失去了庇護,白居易成為政敵攻擊的對象。如其《請罷兵第三狀》是針對憲宗出兵征討河北叛鎮一事所作,他連上3狀且言辭激烈,得罪了很多權貴。所以,當時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2]4344為罪狀將他貶官。痛定思痛,白居易也逐漸認清問題癥結所在,即不應“越職言事”。因此,其在回憶性質的書信和文章里對曾經的上諫行為和諷喻詩寫作都主動加上了諫官身份,特別是在新樂府詩創作中著重強調自己的諫官身份。
二、李紳及元稹的諫臣意識與諷喻詩創作
元和年間,李紳和元稹也創作了大量諷喻社會時病與彌補政治缺失的詩歌,即新題樂府詩。兩人諷喻性詩歌創作時間與白居易相近,且3人有詩歌唱和的創作經歷。
(一)李紳和元稹以詩諫政的主張
李紳在元和四年(809)創作了《新題樂府二十首》,元稹也在同年創作了大量的新題樂府詩[5]。“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代之人”[6]256,新題樂府實際上是通過描摹時事來諷喻現實,是一組帶有政治諷喻性的詩歌。如李紳的《新題樂府二十首》,雖然這些詩歌今已佚,但從元稹對其“雅有所謂,不虛為文”的評價可看出,它們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元稹取“病時猶急者”和之,作《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更是從當時社會最為棘手的問題事件著手,希冀詩歌能夠發揮政教功用,解決社會的突出矛盾與主要問題。從題目上看,新題是不拘泥于古題,即事名篇,如《法曲》《陰山道》《縛戎人》和《西涼伎》等詩,都是根據時事自擬的題目。元稹和李紳新題樂府詩歌的寫作主要呈現兩大特點:“刺美見識”和“即事名篇”,即內容要諷喻現實且針砭時弊,形式要根據實際自擬新題,不拘泥于古題。值得注意的是,元稹《樂府古題序》稱:“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6]256,“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7]。可看出,他們都是借樂府詩的形式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針砭時弊。因此,元稹和李紳在諷喻性詩歌創作上有相同的詩歌理念,且都是以詩諫政的踐行者。
(二)李紳和元稹強烈的諫臣意識
李紳和元稹都曾擔任過諫官,但他們擔任諫官與創作諷喻性詩歌的時間并不對應。“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锜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锜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锜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锜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2]4477李紳在元和十四年(819)由幕府入諫官,這意味著諷喻性質的新題樂府詩創作要比他的諫官身份提前了10年。元稹在元和元年(806)參加制科考試,以第一名的身份擔任拾遺。《舊唐書》記載:“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2]4327《舊唐書》記載右拾遺有誤,因元稹在詩文中屢次以“左拾遺”自稱。但元稹的諫官生涯只維持了幾個月,不久便被貶為河南尉。在擔任拾遺期間,元稹并沒有大量創作新題樂府詩,僅有特意標明左拾遺時所作的詩歌《順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挽歌辭三首》和《含夕風》兩首。而這兩首詩歌在內容上并無諷喻性質,在此標明拾遺身份只是單純的一個時間節點。在創作新題樂府詩的元和四年(809),元稹時任監察御史,早已不是諫官。中唐是文學家任諫官最多的朝代,即使沒有擔任諫官的文學家,其諫臣意識也較此前文人更為強烈[8]298。李紳和元稹在創作之際雖沒有諫官身份,但具備強烈的諫臣意識。“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锜愛其才,辟掌書記。锜浸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9]5347李紳為人肆意瀟灑,因內心不喜便主動離職;還敢于直言上諫,他在李琦幕府任職時,與他人的膽怯沉默不同,他屢次勇敢地發表自己對時政的意見。《新唐書》載:“性明銳,遇事輒舉。”[9]5224元稹任拾遺不過數月,上諫表有數十通,并且直切要害,真正踐行了“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與“發憤效職忘軀之至”的諫官誓言,這使他遭遇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次貶謫。但脫離了諫官身份,元稹的諍臣之風猶存。白居易在《論元稹第三狀》中稱:“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1]1248,說明在創作新題樂府詩期間,元稹仍具備強烈的諫臣意識。所以講,李紳和元稹的諷喻性詩歌創作與其強烈的諫臣意識緊密相關。
(三)諫臣意識與諷喻性詩歌創作的關聯
元和四年(809),任秘書省校書郎的李紳和任監察御史的元稹,在強烈的諫臣意識影響下進行諷喻性詩歌創作。值得注意的是,諫臣意識作用于諷喻性詩歌創作的事例早已有之,尤其是陳子昂和杜甫。陳子昂的諫臣意識并沒有隨著諫官身份的遺失而消逝,《感遇詩三十八首》有一部分是其諫官生涯結束后所作;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別”等詩歌也作于諫官身份結束后,是其諫臣意識的延續。從陳子昂和杜甫的經歷看,諫官生涯結束并不代表諫臣意識的終結,他們反而創作出許多優秀的諷喻詩。元稹的諷喻性詩歌創作直接受陳子昂和杜甫的影響:喜愛陳子昂帶有風雅和比興意味的《感遇詩》,且有意識地模仿;贊賞杜甫“浩蕩無涯、處處臻到”[6]352的詩歌,并將其視為學習的楷模。另外,元稹還對陳子昂和杜甫的諫官身份及任職時間十分了解,并在詩文里反復提及,既飽含對自己與他們共同擔任拾遺職務的榮譽感,也懷有對兩人仕宦生涯止于拾遺的同情。
綜上,元稹在諫官生涯結束后,仍在強烈的諫臣意識促使下創作大量的諷喻性詩歌。李紳的新題樂府詩、元鎮仿照陳子昂詩歌所作的《寄思玄子詩》20首以及白居易任拾遺前創作的數十首意存諷賦的詩歌,都是諫臣意識先行于諫官身份在詩歌創作上的表現。質言之,他們認為即使不是諫官,強烈的兼濟天下之心也能促使詩人創作許多帶有政治色彩的詩篇。
三、元和年間諷喻性詩歌繁盛的政治原因
憲宗元和年間是唐代諫諍風氣比較活躍的時期,許多文人和政治家都以諫臣的姿態出現在政壇上[8]312。擁有諫臣姿態的不僅是正在諫職的諫官,還有具備諫臣意識的士人。當時獨特的政治環境是促使諷喻性詩歌創作繁盛的主要原因。
憲宗皇帝虛心納諫為諷喻性詩歌繁盛提供了歷史機遇。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道明他屢次上諫和試圖以詩歌補政治之缺的原因:“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1]962此處的皇帝指唐憲宗,他是唐朝中后期最為開明的帝王之一,與太宗和玄宗并稱“唐朝三君”,在位期間開創了“元和中興”的局面。元和初年(806),擔任諫職的官員大都尸位素餐,既不用奏事,也無需參加廷議。元稹曾針對這一現象呈《論諫職表》,反復陳說其中利害,希冀能夠改變這種令人堪憂的政治現狀。元和二年(807),憲宗皇帝發布詔書:“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2]423,以此表達他主動學習太宗廣開言路和希望諫臣能夠積極論諍的意愿。這條詔令的發表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表明憲宗開始重視諫官的職能。在處理朝廷事務時,憲宗“宜令群臣各隨所見利害狀以聞”[2]442,注重發揮群臣進諫的作用,鼓勵臣子積極上諫。因此,涌現出一批敢于上諫的朝臣,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和前進士李宗閔勇敢地指陳時政的缺失,無所避諱;御史中丞盧坦甚至對皇帝的褒慰熟視無睹,堅持上諫使皇帝處置柳晟;少室山人李渤雖然拒絕擔任左拾遺一職,但經常對朝政時事附奏陳論。可見,憲宗對諫諍行為的重視和支持提高了中唐士人的諫臣意識與參政熱情,他們嘗試用多種方式參與政治,創作諷喻性詩歌便是其中之一。
元和年間人才的選拔方式為文人參政提供了基礎,尤其是制科考試對文人諫臣意識的培養至關重要。元和元年(806),憲宗于尚書省開設制科考試。元稹和白居易就是通過這次考試被選拔出來的人才。元白兩人曾一起擔任秘書省校書郎,并在此結下“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1]245的友誼。校書郎軼滿后,他們一起準備制科考試,在華陽觀里“閉門累月,揣摩當代時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1]1287。制科考試以惡訐取榮為美,所以元稹和白居易“指病危言”,共同探討時代弊病,突出對于時局的關注與思考,并且把這些時事寫成策目,最終以文學形式呈現出來,這也為其諷喻性詩歌創作奠定了基礎。他們參加的科目是“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憲宗曾在頒布的《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問》中提及要借此科目遴選出讜直的人才。因此,準備這次考試還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元稹和白居易讜言直諫的品格。另外,白居易在給李紳的詩《渭村酬李十二見寄》中寫道:“不似華陽觀里時”[1]300,表明李紳曾和他們一起準備這次制科考試。可以看出,元和元年的制科考試對于白居易、元稹和李紳大力倡導和創作諷喻性詩歌尤為重要。
綜上所述,元和年間諷喻性詩歌的集中創作是由具備強烈諫臣意識的李紳和元稹創作詩歌所引發,并由諫官白居易推向最高潮的詩歌創作活動。推而論之,元和士人的諷喻性詩歌創作不僅與其諫官身份相聯系,也與他們強烈的諫臣意識息息相關。諷喻性詩歌創作繁盛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憲宗皇帝對諫諍行為的重視和制科考試的設置更促使了諷喻性詩歌創作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