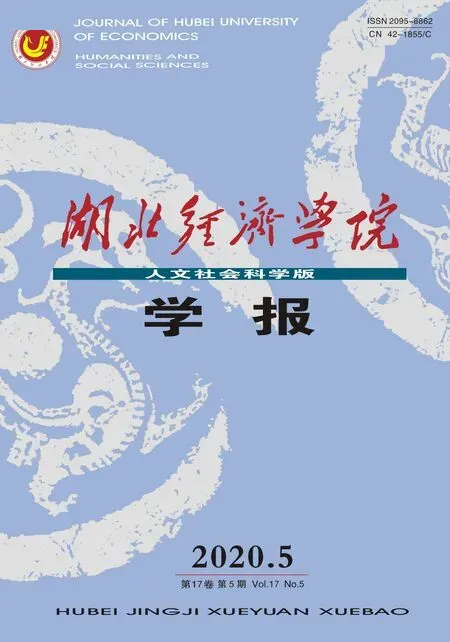喬伊·哈喬詩歌中的動物形象與種族意識
李宇笛(華中師范大學 外語學院大學英語教學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
當代女詩人、藝術家喬伊·哈喬是一位具有數個印第安部落血統的混血,從最初對個人身份和印第安文化的反感和抵觸,到逐漸接受自己的身份,再到以書寫和表現印第安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為驕傲,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寫詩,表達了美國印第安裔對自我和集體身份的認識和思考。美國印第安文學在歷史上一直以“口述”和“歌謠”方式流傳,但由于口頭文學的局限性和歐洲殖民者強大的書面文化的入侵和影響,它逐漸被邊緣化和沉默化了。直到20 世紀60 年代的“美國本土裔文藝復興”,才使印第安文學逐漸被主流文學所認識和發現。但直到今天,與美國華裔、猶太裔等族裔文學發展和成就相比,本土印第安裔文學的影響仍然有限。如何讓美國印第安裔記住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如何讓世代相傳的豐富生存經驗和生活哲理傳承下去,如何讓整個世界正視和尊重印第安文化,這些一直是具有歷史責任和民族意識的美國印第安裔作家和詩人共同關心的命題。縱觀哈喬的詩歌,不難發現在保留了傳統印第安文學充滿靈性的“大地情懷”與音樂性的特點之外,還充滿了豐富動物意象。她描寫了了許多動物形象,比如“鷹”“馬”“烏鴉”等,其中既有有客觀動物活動的描述,也有比喻和想象的產物。本文分析詩人如何用動物形象表現一個印第安女詩人在異化世界中對種族身份的認識和內心經驗,通過追溯歷史和記憶的痕跡,以本能的“部落意識”中的超然力量對抗殘酷現實。
一、印第安文化傳統影響下的動物形象
喬伊·哈喬是一位深受美國印第安民族的大地情懷和自然靈性傳統影響的詩人。印第安民族一直有崇尚自然、信仰自然的傳統,他們相信自然的力量和動物的靈性,自然地認為動物與人一樣擁有靈魂,傳說中的各種動物會相互轉換,印第安人也驕傲地把自己稱為熊族人或狼族人。現代社會中,印第安人也因為擁有豐富的自然知識被人們稱為“自然之子”。“由于原住民神話身受薩滿巫術文化影響,因此主要信仰與大自然的神靈相當接近,印地安人們不僅敬畏神明,也敬畏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相信即使是植物,也擁有自己的靈魂,因此值得受到人的尊重。對于動物神靈的崇拜,也衍生出了圖騰崇拜的信仰。”[1]在美國印第安民族的口述傳統中,含有豐富的對大自然的贊美,通過對生活中的美的贊頌,他們在精神上獲得一種自我修復的能力,去除痛苦的記憶,在迷失中重新尋找自我。
哈喬的詩歌以一個生活在現代都市的印第安女性眼中的世界為對象,與記憶中的民族部落文化、歷史故事相交織,將讀者帶入到一個神秘卻又現實的印第安詩人的內心世界,既有自己的親身經歷,又有家族和部落流傳下來的神秘傳說,也有近代以來印第安民族經歷的創傷經驗,還有代表整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符號和象征。動物形象在她的詩歌創作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時她以旁觀者的角度對自然界中的動物進行客觀的描寫,比如在詩歌“Conflicts Resolutions for Holy Beings”中,她在一開頭便使用循環式長句描寫獵豹:“A panther poised in the cypress tree about to jump is a panther poised in the cypress tree about to jump.”[2]但她從來不僅僅止于客觀描述,接下來的比喻賦予了獵豹超越自然的能力:“The panther is a poem of fire green eyes and a heart charged by four winds of four directions.”[3]又比如在“Eagle Poem”中她先描述蒼鷹飛過湖泊和藍天的景象:“Over Salt Lake. Circled in blue sky”,然后是鷹所帶來的心靈的洗禮:
In wind, swept our hearts clean
With sacred wings.
We see you, see ourselves and know
That we must take the utmost care
And kindness in all things.[4]
詩中的鷹成為了一個神圣的意象,它張開翅膀飛翔象征著大自然的無私包容和寬廣的胸懷,不僅使我們的心靈得到凈化,還讓我們意識到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充滿仁愛。
同樣,在詩集“She Had Some Horses”《她曾有幾匹馬》中,哈喬直接賦予動物以人性化的經歷和情感,表面上是寫各種性情不同的馬兒,實則是以它們各自不同的姿態和生存方式象征不同種族和人群。通過印第安口語化講述中典型的重復、聯想和比喻,讀者明顯感到詩人不僅僅是在寫動物,而是為了寄予個人的感情和思考,將動物與個人命運、種族未來、歷史記憶等問題聯系起來。
綜上所述,作者將印第安民族的時空觀、宇宙觀和自然靈性思想融入到現代形式的詩歌創作中,讓自然中的動物形象與現代西方文明進行對話。這些豐富的動物形象與神秘色彩的吟唱結合,讓她的詩歌蘊含了豐富的想象和聯想,將讀者帶入印第安民族的精神世界,體會到他們與自然母親的天然密切的聯系和身處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與掙扎。
二、動物形象表達身份意識
哈喬認為動物充滿靈性,可以與大地母親進行對話。她用動物的聲音和行為表現內心意識和情感,同時詩句充滿動物世界真實自然的韻律和節奏感,仿佛受到自然野性力量的驅使一般,帶動讀者和聽眾與大自然和動物們進行平等溝通。
詩歌“Ah, Ah”描寫烏鴉在陰沉的天空下飛翔,不畏刺骨的冷風,在大地和海洋之上呼喚太陽。詩歌的每一詩節都以烏鴉的嚎叫聲“Ah, Ah”開頭,只用短短兩行詩句就描述了一個堅韌、勇敢和樂觀的烏鴉的形象,反復的擬聲詞“Ah”不僅持續地引起我們對烏鴉的聲音和運動軌跡的注意,還表明了它的影響力在逐漸增強:從最開始的“cry”到“groan”,再到“beats our lungs”和“tattoos the engines”“calls the sun”,最后“scrapes the hull of my soul”。[5]烏鴉的聲音由外到內,由遠及近,帶領我飛過永恒的時間之網,引發我對于人類的靈魂和歷史的思考。
詩歌中的動物有時也沉默不語,這種壓抑和沉默體現了現代世界人類的異化,尤其是在白人社會中逐漸被同化而失去動物本性和自然靈性的印第安族裔。與動物的沉默有著明顯對比的是詩人在詩歌的獨特聲音。印第安文學的口述傳統賦予了哈喬的詩歌獨特的節奏和音樂性,使詩句充滿口語色彩。她的詩歌遵循人類呼吸和身體的自然節奏,并結合了印第安民族傳統的反復吟唱和祈禱的表現方式。T. Winder 和L. Coltelli 在與哈喬對話的記錄中說:“可以追溯到Joy Harjo 記憶中每一個言語行為,并將這個行為化成一種口述傳統,當故事陳述伴隨著傾聽,那一刻,詩人和聽眾也結合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6]詩歌的文本寫作也就成為了一種口語形態。詩歌“She Had Some Horses”將這種口語節奏發揮到了極致,全詩大部分詩句都采用同一句式,以“She had horse who”開頭,而且每個詩節又都以“She had some horses”[7]結尾,通過不斷的循環和重復,使語氣由弱增強,節奏如同馬兒在草原上由遠及進奔跑時的步伐,整首詩充滿自由和奔放的力量,借以表達詩人作為印第安女性所受到的壓迫和歧視等在內心的成長和宣泄。這種重復也呼應了本土裔的口述傳統,將詩大聲朗讀便會發現,詩人仿佛在進行一種充滿神秘力量的禱告,將與印第安民族生活中聯系最為密切的動物“馬”賦予了人性,體現了她勇敢獨立、自尊自愛、與邪惡勢力頑強抗爭的精神。
哈喬的詩歌多以美國西南部的生活為背景,講述個人生活的迷茫和困境的同時折射出整個部落的觀念、神話和信念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屬于個人的觀念也具有普遍性,體現了這一區域印第安人的身份焦慮和抗爭狀態。在殖民者的同化影響下,印第安民族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語言甚至觀念意識都發生了改變,這些現實變化讓他們感受到自己與整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割裂感,但在白人殖民者眼中,他們依舊不過是原始、無知的本土裔人,偏見和歧視依舊存在,由此產生出尖銳的矛盾和深深迷茫感。印第安詩人和作家常常表現的就是這種在“自我”和“它者”身份夾縫中生存的個體的矛盾和迷茫。喬伊·哈喬既是馬斯科吉克里克、切諾基等部落混血,也有法國、愛爾蘭等白人血統,身處兩種文化之間,她也曾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但印第安的民族意識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在Jane Ciabattari 對她的訪談中,哈喬曾說:“我來自勇敢的人民,來自帶著尊嚴站起來并還將繼續站著的人民。在這個所謂的”后殖民”時期,做一個馬斯科吉克里克族人或是任何一個部落的人都不容易。”后殖民”已不存在,它已經被集團化取代了”。[8]她并沒有刻意劃清自己與主流文化和社會之間的界限,而是以一種開放、融合的視角,用詩歌講述一個女性本土裔眼中的世界和個人感受,以此實現對個體身份的理解。
與印第安民族最密不可分的動物——馬的形象經常出現在哈喬的詩中。還是以“She Had Some Horses”為例,全詩共有8 小節,每一節側重描述馬的一種特質。馬的身體來大地和天空,肌膚與自然相連,正如信仰大地母親的印第安民族。哈喬以馬的多重形象象征了本土裔的身份危機,同時也表達了對個人身份的矛盾和迷茫。詩中的馬,身體強壯,具有摧毀的力量,有著驕傲的內心,世俗的情感,內心卻充滿恐懼和懦弱,還被剝奪了話語的權利。這是哈喬作為一個印第安女性對自我身份的理解:心有不甘,卻只能將自己的聲音埋藏在心底。然而從詩歌的最后幾節可以看出,在歷經折磨和創傷之后,詩人意識到屈從是無用的,馬兒依舊期待重生,仍然對生命充滿希望,正如詩人自己,雖對生活有過茫然和無助,但卻從未消極面對,總是以希望對抗現實世界的惡意。
由此可見,哈喬眼中的自己與普通女性無異,勇敢、堅韌且敏感,身為印第安女性,卻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男性眼中的弱者,白人眼中的“它者”,在現實社會中不免受到許多不公和偏見。面對異化的世界,她依然渴望愛和自由,內心也仍保持著樂觀希望。但正是由于那些矛盾和迷茫,才使她積極思考個人身份和種族命運,也是她為民族發聲,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尋找出路的開始。
三、動物形象與種族命運
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之后,白人征服占有這片大陸的功利心態和欲望與土著人的大地情懷在文化上產生強烈碰撞。印第安土著被歐洲人故意帶來并傳播的瘟疫奪去了四千多萬人的生命,隨后殖民者大肆驅趕、屠殺和掠奪印第安人,在短短300 年間,印第安人的數量從原本的五千萬到一億驟降為幾十萬人。不僅如此,為了給自己的屠殺掠奪行為尋找借口,白人社會中描繪的印第安土著一直是殘暴、野蠻的殺戮者形象,他們的文化是落后、野蠻充滿迷信的。這種主流文化對次文化的故意歪曲甚至虛假的描述不僅激起了種族之間的仇恨,更導致美國主流社會中印第安民族的長期“失聲”,即使在文化多元的當代美國,本土裔僅占總人口的0.9%,仍然是很少發聲的安靜一員。
哈喬以孤獨、沉默的動物形象表現了印第安民族在面對歷史暴行和精神創傷時,不得已選擇沉默不語的無奈現實,但她更為擔憂的則是在全球化的現代美國,自己的種族和部落文化傳統可能被遺忘,關于歷史暴行和精神創傷的記憶可能被抹去。“Invisible Fish”是一首隱喻短詩,講述了一條魚的命運:“Invisible fish swim this ghost ocean now described by waves of sand,by water-worn rock.Soon the fish will learn to walk.Then humans will come ashore and paint dreams on the dying stone.Then later,much later, the ocean floor will be punctuated by Chevy trucks,carrying the dreamers’descendants,who are going to the store.”[9]哈喬表面上在寫魚,實際在表達自己對祖先的文化遺產正在逐漸消失的擔憂。祖先的后裔如今是“看不見的”,海洋變成了沙灘和巖石,魚兒沒有了水,只能學著走路。這也象征了印第安種族在現代美國社會中的被迫同化的問題,新一代的印第安人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堅守和傳承已越來越少,年輕人過著與白人無異的生活。詩歌最后的兩句體現了哈喬對民族未來發展的擔憂,擔心印第安民族是夠會被完全同化,記憶是否會被全部抹掉?子孫后裔是否還能繼承祖先的文化遺產?對此她似乎有著隱隱的悲觀。
她的擔憂不無道理,在談到印第安文學所面對的傳統與現代張力中不斷演化時面對的困境和出路時,秦蘇鈺評論到:“如果沒有故事的講述者,沒有土著作家充滿想象的虛構,記憶就將被束之高閣,直至被永久遺忘,所以,對當代美國土著文學創作的研究與其說單純是一種文學的賞析,毋寧說更是一種社會記憶的解讀和傳承。”[10]印第安民族文學的口述傳統本來就置其文化保存和傳承于不利位置,因此,作為一位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的詩人,哈喬的詩歌不斷對民族歷史進行探尋,對西方文化霸權欺凌進行挑戰和蔑視,對種族記憶和創傷進行傾訴和撫慰,由此尋找解決印第安民族危機的方法。詩中的動物形象反映了她對于部落文化甚至整個印第安民族的現狀和未來的思考,認為只有回歸自然和正視民族傳統、保持樂觀精神才能使印第安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
首先,面對人類社會的異化,她主張回歸印第安部落傳統,研究部落文化,回歸部落的神話世界和充滿靈性的大地母親懷抱,回到那個從前人類與動物在大自然中共生的世界。哈荷曾經說過,要解決現代都市社會存在的令人不安又令人迷惑的問題,就要重新肯定傳統的部落身份和價值觀念。《狼勇士》中,她借用人類的祖輩狼之口對獵人講述地球生命正在滅絕的寓言,惟有人類繼續傳承民族經驗和傳統才能阻止那一天的到來。正如Ivanna Yi所認為的:“大地在當今的(印第安人)的故事講述中成為了一種去殖民化和文化延續的方法。”[11]大自然中的動物和大地母親都能夠給予現代人類心靈凈化和療傷的作用,人類應該多接觸自然,了解自然,保護自然,才能回歸本性中的純真善良,才能與自然和人類自己和諧相處。
其次,面對生命中的沖突和挫折,人們應該懷有寬廣包容的胸懷,始終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詩歌“Conflict Resolution for Holy Beings”表達了詩人對一切生命均是 神圣的看法,詩中的動物皆有靈性,與神靈相通。詩歌的第5 節,詩人描繪了獵豹與獵物的形象。獵豹靜靜地等候著獵物的出現,表現出對自然、對生活最敏銳的感知和領悟,它擁有強大到無法抵抗的力量,對于獵物冷酷無情。與之相反的是它的獵物,明知自己的命運卻還唱著死亡之歌前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sunrise.
I belong to the black cat with fire green eyes.
There, in the cypress tree near the morning star.[12]
這種即便面對殘酷命運也仍積極樂觀接受的精神正好呼應了小節標題“Eliminate Negative Attitudes During Conflict”,也反映了印第安民族的文化秉性,面對殘酷不公的命運,甚至死亡的來臨,都依舊熱愛這個世界,笑著積極面對。
綜上所述,哈喬以不同動物的運動軌跡、生存狀況和命運表現整個印第安族裔的歷史和生存現狀,將民族精神寄于動物形象之上,對種族命運和未來發展并寄予期望和憧憬,體現出詩人強烈的種族意識和責任感。通過多種動物形象和動物聲音的表達,哈喬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認識和身份的抗爭,并認為只有回歸自然和正視民族傳統、保持樂觀精神才能使印第安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