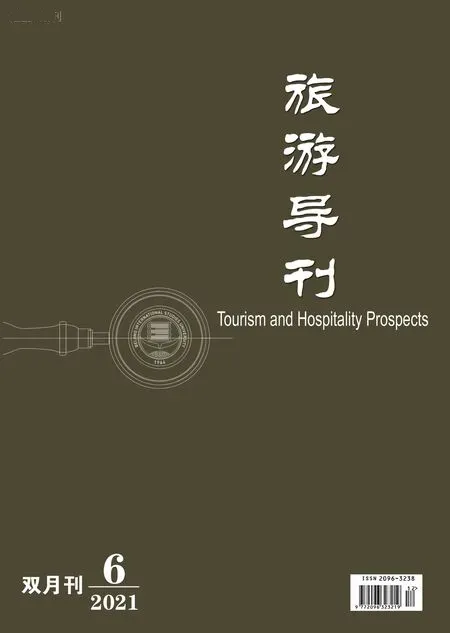玩也可以是認真的嗎?
——國外游憩專業化研究述評
劉 松 樓嘉軍
(1.常州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江蘇常州 213032;2.華東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上海 200241)
引言
現階段,居民的休閑支付能力不斷提高,閑暇時間結構得以優化,休閑游憩成為人們的重要生活內容。游憩活動是人們在閑暇時間所從事活動的統稱。隨著居民生活質量穩步提升,人們對于美好生活需要滿足的愿望漸趨強烈,使得游憩專業化傾向愈加明顯。游憩專業化是對居民游憩參與水平的衡量,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居民參與體驗滿足游憩需要的程度。在我國,居民游憩專業化的提升具備一定的潛力和可能性:一方面,從制度層面講,《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2015)》等系列政策的頒布,強調推進游憩基礎設施(如房車營地、郵輪碼頭等)的建設和特色休閑產品的開發,《休閑露營地建設與服務標準》等國家標準的相繼發布和實施,也為人們游憩活動實現專業化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從產業層面看,戶外裝備用品產業發展迅速,為人們參與專業化游憩活動提供了物質保障。
國外關于休閑和游憩的研究已逾百年,游憩專業化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內容,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理論架構,且得到學術界的持續追蹤研究。國內相關研究相對滯后,學者們主要探討了游憩專業化與深度休閑(serious leisure) (王志宏、張繼文,2013;劉松、樓嘉軍,2017)、地方依戀(趙宏杰、吳必虎,2012)和休閑約束(劉松、樓嘉軍,2016)的關系,游憩專業化在深度休閑與地方依戀關系中的中介作用(梁英文、曹勝雄,2007;湯澍、湯淏、陳玲玲,2014),游憩專業化對游憩參與類型偏好(歐雙盤、侯錦雄,2007)、游憩動機和地點屬性認知(李素馨,1984)的影響等。與國外研究相比,國內游憩專業化研究尚未完全展開,研究廣度和深度仍顯不足。鑒于此,本文基于對國外游憩專業化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分析和歸納,全面總結游憩專業化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進而結合我國國情和居民游憩活動情況給出國內游憩專業化研究的建議和方向。
一、文獻概況
1.文獻收集與年譜分析
筆者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數據庫”中以“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為檢索詞進行主題(包括標題、摘要、關鍵詞)檢索,共得到相關論文180 篇。從發文情況(見圖1)來看,國外關于游憩專業化的研究已有40 余年歷史并且關注度不斷提高,尤其是近10年研究成果數量增長速度明顯加快,說明游憩專業化逐漸成為國外休閑游憩研究的熱門話題。從文獻引用情況(見圖2)來看,2010年以后,文獻被引用的頻次大幅提升,說明游憩專業化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得到更多學者認可。

圖1 國外游憩專業化文獻發表情況年譜分析Fig.1 Chronologies analysis of foreign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圖2 國外游憩專業化文獻引用情況年譜分析Fig.2 Chronologies analysis of foreign cited literature o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2.文獻分布
本文對國外游憩專業化相關研究文獻的來源出版物、國家/地區、機構和作者情況進行了分析(見表1)。從來源出版物分布情況來看,發表在國外休閑游憩研究兩大主流期刊Leisure Sciences
和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的文章數量占到文獻總數的一半以上,說明游憩專業化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權威性。從國家/地區分布情況來看,來自美國的文章數量占到文獻總數的58.89%,其次是加拿大(17.78%)和澳大利亞(11.11%)。從機構分布情況來看,得克薩斯A&M 大學系統(Texas A&M University System)發表文章數量最多,占文獻總數的34.44%,其次是賓夕法尼亞州立高等教育系統(Pennsylvania Common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和 克 萊 姆 森 大 學(Clemson University),分別占比16.11%和10.00%。從作者來看,Scott、Oh和Ditton 3 位作者發表的文章數量均已超過10 篇,說明游憩專業化問題已得到國外學者持續和深入的研究。
表1 國外游憩專業化文獻相關分布Tab.1 Related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二、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來看,大致表現出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向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單一化向多元化、簡便化向復雜化轉變的趨勢。在資料收集方面,研究者除了使用觀察法、訪談法外,更多地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在資料或數據分析方面,早期主要使用歸納總結、邏輯推演、對比分析、統計描述等方法,后期廣泛使用了統計推斷、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回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型等量化研究方法。
在20 世紀70年代游憩專業化議題提出之初,Bryan(1977)、Chipman和Helfrich(1988)等學者主要基于歸納總結和經驗判斷,定性研究和探討游憩專業化的內涵和維度,嘗試構建游憩專業化的理論框架,這為游憩專業化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對該領域探討的持續深入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斷革新,自20 世紀90年代學者們嘗試使用社會統計量化分析方法展開研究,如McIntyre 和Pigram(1992)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車載露營者的游憩涉入程度,同時,在這一階段有關游憩專業化的定性討論仍然較多,Ditton、Loomis和Choi(1992),Scott 和Godbey(1994)甚至將社交圈(social world)的概念引介進來,以期將游憩專業化討論推向深入。進入21 世紀,社會統計分析成為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如Kuentzel 和Heberlein(2008)、Scott 和Lee(2010)、Needham 和Vaske(2013)等采用了方差分析、聚類分析、回歸分析等量化方法開展研究。結構方程模型方法近年來在研究中應用廣泛,Lee 和Scott(2004),Oh、Lyu 和Hammitt(2012),W?ran 和Arnberger(2012)等在研究中使用了這一方法。在這一階段,有關游憩專業化的定性討論仍未中斷,如Bryan(2000)對游憩專業化概念進行了再考察,Jun、Kyle 和Graefe 等(2015)則基于認同理論重新審視了游憩專業化的內涵和框架。
三、研究對象
1.群體類型劃分
Bryan(1977)在創立游憩專業化概念之初,基于設備和技能的使用及活動場所的偏好將鱒魚垂釣者劃分為4 個亞群體:偶爾垂釣者、多面手(generalist)、技術專家和技術設定(technique-setting)專家。從類似概念和邏輯出發,許多研究者對游憩參與群體進行了類型劃分:Chipman 和Helfrich(1988)根據漁場資源的使用、經驗、投資和生活中心化情況將弗吉尼亞的河流垂釣者劃分為6 種類型,以此研究游憩動機的群體差異;Cottrell、Graefe 和Confer(2004)根據參與度、設備、技能和相關興趣等維度將帆船和摩托艇游憩者劃分為日常型、觀光型和比賽型3 個層級,研究其游憩專業化的程度和范圍;Beardmore、Haider 和Hunt 等(2013)將垂釣者劃分為隨意型、積極型、高超型和忠實型4類,評估游憩專業化對于垂釣偏好和行為的解釋力;Needham 和Vaske(2013)在研究游憩專業化與活動替代選擇的關系時,將狩獵者劃分為隨意型、中間型、聚焦型(focused)和資深型4 類,認為資深型狩獵者可能以獵殺其他大型獵物作為替代選擇,而隨意型狩獵者則可能選擇釣魚作為替代活動。
參與風格是態度、行為和偏好的綜合反映,體現了人們對于游憩活動的涉入特征,因此依據參與風格也可以區分游憩專業化的不同類型。Scott 和Godbey(1994)將橋牌玩家按其游憩專業化水平劃分為錦標賽玩家、規則復制玩家、定期社交玩家和偶爾玩家。Fisher(1997)則根據參與度、垂釣經驗、是否為俱樂部成員、是否參加錦標賽、對管理規則的看法等因素劃分了4 類垂釣者類型,研究他們的游憩傾向和態度,進而為管理政策制定提供建議。
許多學者還將分類研究的量化工具應用于游憩專業化群體類型劃分中。Kerins、Scott 和Shafer(2007)運用自分類工具(self-classification tool),分析了游憩專業化連續統一體中的3 種參與類型:隨意型、積極型和深度型。Sorice、Oh 和Ditton(2009)同樣運用自分類測量方法,將潛水活動參與者劃分為隨意型、積極型和忠實型3 類群體。Waight 和Bath(2014)則運用聚類分析方法將加拿大紐芬蘭全地形車使用者劃分為隨意型、積極型和專注型3 個不同亞群體,并通過方差分析證實了跨群體游憩專業化的顯著差異。
2.活動類型圈定
自Bryan 以垂釣活動為例開創性地提出游憩專業化概念后,他將此概念進一步擴展運用到其他戶外游憩活動中,包括攝影、遠足和背包旅行、登山、滑雪、劃獨木舟、觀鳥和狩獵等(Bryan,1979)。經過后續30 多年的實證研究,游憩專業化研究者提升了對各種游憩群體的多樣性理解,并且為針對同一群體游憩參與差異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如Miller 和Graefe(2000)考察了7 種不同的狩獵活動(弓箭射鹿、步槍射鹿、前裝槍射鹿、松雞射殺、火雞射殺、野雞射殺和水禽射殺),認為游憩專業化的程度和范圍在不同狩獵活動中存在明顯差異。

表2 游憩專業化研究涉及的活動類型Tab.2 Types of activities involved i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research
游憩專業化研究涉及的活動類型見表2。相關研究存在如下特點:一是研究者對不同活動類型的游憩專業化研究的關注度有所差異,以關注親近自然、親近動物的游憩活動居多;二是許多研究者對同一游憩活動進行了持續性追蹤研究,如McFarlane(2004)、Lee 和Scott(2006)針對觀鳥游憩,Oh、Sutton 和Sorice(2013)針對垂釣活動,Needham、Scott 和Vaske(2013)針對狩獵活動等的研究。
四、研究內容
1.概念緣起
游憩活動參與者在承諾(commitment)和興趣上均存在異質性,因而將其細分為有意義的不同群體進行研究顯得尤為重要(Needham & Vaske,2013)。為此,Bryan 最早提出游憩專業化概念,將其作為識別、描述和管理游憩者子群體的一種方法,定義為“從一般到專業的行為的連續統一體,并通過用于運動或活動場所偏好的設施和技能予以反映”(Bryan,1977)。在游憩專業化連續體的一端是新手或非經常的參與者,他們認為既定活動不是生活興趣的中心或者對設施和技術沒有顯示出強烈的偏好,另一端則是狂熱的參與者,他們熱衷于既定活動,喜歡運用更為復雜的方式參與其中。
游憩專業化是一個線性連續的行為過程,也就是說,隨著游憩技能、裝備水平、參與狀況和承諾的提升,游憩者將進入專業化水平更高的階段。在游憩專業化早期研究中,這一觀點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Kuentzel 和Heberlein(1997)通過研究帆船活動的專業化過程,發現社會地位與游憩專業化并不相關,然而不同類型的帆船參與水平與參與者的自我發展狀態是相呼應的,因而證實了游憩專業化是線性連續過程的概念。不過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學者對游憩專業化的連續過程提出質疑,認為還需要基于更多的觀察來驗證(Kuentzel & Heberlein,2008)。Kuentzel 和Heberlein(2006)根據是否擁有船只、是否到其他大湖劃船、是否到其他海洋劃船、參與競賽、感知技能、興趣改變和退出7 個指標考察了劃船活動參與的穩定性,認為游憩專業化的連續過程是一種例外而非“鐵律”(the rule),休閑參與改變較游憩專業化改變更為復雜。
盡管如此,游憩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來自參與者本身和外界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其無法沿著線性的路徑持續增長。Oh、Sorice 和Ditton(2010)運用潛增長方法驗證了游憩專業化的連續性,發現其潛在維度存在顯著個體差異,游憩者專業化水平并非沿著連續統一體穩步發展,而是隨著時間和個體環境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與此類似,Scott 和Lee(2010)通過對游憩專業化水平改變的社會機制考察,也發現偶發事件和生活事件對游憩專業化產生干擾,從而使其發生相應變化。Backlund 和Kuentzel(2013)同樣認為游憩專業化從新手到專家的單向連續體更多地是一種例外,他指出了與游憩專業化相聯系的休閑資本投入的4 種機制:休閑機會的多樣化促使人們將休閑資本分散在更多活動上;個體能力、欲望或條件的限制可能使得人們只能進行隨意休閑活動或減少休閑參與;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展隨意休閑;生命歷程改變可能使得人們在新的生活階段中尋找更為合適的休閑活動。
部分學者還從其他理論視角切入,考察和界定游憩專業化概念。Ditton、Loomis 和Choi(1992)基于社交圈視角,認為游憩專業化是將游憩社交圈劃分為若干次社交圈,進而與游憩社交圈交叉再形成若干次社交圈的過程,同時次社交圈及其成員在次序安排上具有一定連續性。過往游憩專業化研究主要根據3 個因素構建其概念——意動(行為、技能和中心性)、認知(認同)和情感(吸引力)。Jun、Kyle 和Graefe 等(2015)認為認同層面影響意動和情感的專業化,他通過對阿巴拉契亞山徑徒步旅行者的研究證實了認同的表達和確認過程影響著徒步對旅行者的吸引力、徒步在旅行者生活中的角色等方面。
2.測量維度及應用
游憩專業化概念最初只是專業化水平連續統一體以及游憩活動涉入程度在行為層面的可操作定義,Lee 和Scott(2004)指出許多研究者是用行為指標來測量游憩專業化的(Ditton,Loomis & Choi,1992;Needham,Vaske & Donnelly,et al.,2007)。然而,體現涉入強度的卻是有關游憩意義的態度、價值觀以及中心性(centrality)個體認同的集合(Bryan & Graefe,2000),也就是說,行為和態度共同影響游憩者的設施配置、技能和場所偏好等(Wellman et al.,1982;Virden & Schreyer,1988;Kuentzel & Heberlein,1992;Kuentzel & McDonald,1992;Bricker & Kerstetter,2000)。McIntyre 和Pigram(1992)納入情感依附變量,并用持久涉入度(enduring involvement)衡量游憩專業化水平,通過情感依附、知識和過去經驗等指標對其進行綜合測度。Thapa、Graefe 和Meyer(2006)通過認知、行為和情感維度測量了水肺潛水者的游憩專業化,進而研究其與海洋環境行為的關系。Schroeder、Fulton 和Lawrence 等(2013)從認知、行為和心理維度測量了水禽獵殺者的游憩專業化,并研究身份認同是如何影響游憩專業化的,認為水禽獵殺者的身份認同程度與其游憩專業化水平保持一致。
基于前人研究成果,Scott 和Shafer(2001)建立了關于游憩專業化的嶄新概念體系,認為游憩專業化是行為、技能和承諾的連續過程。但是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他們認為行為需要根據游憩者在其他活動中的涉入狀況予以評估,技能、知識不應與經驗混淆,具有強烈行為承諾的人們更有可能將此游憩活動作為生活的中心 。Scott 和Shafer 構造的包含行為、技能、知識與承諾的游憩專業化三維測量模型在后續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Lee 和Scott(2004/2006)通過對觀鳥活動的實證研究檢驗了游憩專業化模型,研究了游憩專業化對觀鳥者的持久效益和自主感知成本的影響,發現游憩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觀鳥者感受到的效益超過成本。Miller(2014)則運用游憩專業化三維模型研究了游憩專業化對觀鳥者聲景觀偏好的影響,認為受技術和知識元素的影響,觀鳥者的聲景觀偏好存在明顯差異。
3.與相關議題的關系
(1)深度休閑
深度休閑指“休閑活動參與者專注系統地投入業余愛好或志愿者活動,并借此獲得及展現特殊技巧、知識與經驗的行為”(Stebbins,1982)。Stebbins指出,在許多深度休閑活動中,深度性(seriousness)維度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專業化傾向,因此可以嘗試運用游憩專業化來衡量隨意休閑—深度休閑連續統一體中深度性的屬性和程度。有學者對深度休閑與游憩專業化的結構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如Tsaur 和Liang(2008)最早研究兩者的關系,其中對深度休閑用Stebbins(1982)提出的毅力、休閑生涯、個人努力、持久效益、獨特氣質和強烈認同指標進行測量,對游憩專業化用過去經驗、生活中心性和經濟承諾指標進行測量,結果發現休閑生涯、個人努力和強烈認同對經濟承諾產生影響,而除獨特氣質外的其他5 個指標均與游憩者的過去經驗和生活中心化具有一定關聯。Lee 和Scott(2013)將深度休閑的4 個屬性(強烈認同、毅力、休閑生涯和個人努力)與游憩專業化的兩個層面(個人忠誠和行為忠誠)納入深度休閑分析框架中,實證研究了兩者的聯系。然而,Scott(2012)卻持懷疑的態度,他認為深度休閑和游憩專業化的優勢和差異有待進一步考察,并指出相同休閑活動參與者的涉入程度是不一樣的,游憩專業化連續過程中參與者個體間存在較大差異。
(2)地方依戀
隨著游憩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游憩者對特定資源的依賴愈加明顯,而地方依戀正體現了個體與特定地方的情感聯系。Oh、Lyu 和Hammitt(2012)證實了游憩專業化三維度模型與地方依戀的關系,并發現體驗偏好和消費傾向對兩者的關系發揮著中介效應。Morgan 和 Soucy(2009)研究了專業化與游憩涉入、地方依戀的關系,發現游憩專業化水平較高的參與者對公園資源關注更多。
(3)暢爽體驗
暢爽(flow)是人們在進行各種休閑或工作活動時產生的一種最佳體驗。在一個有預定目標和規則約束,并且行為者清楚地知道如何能做得更好的行為系統中,當行為者的技能能夠充分應付隨時到來的挑戰時,就會產生這種感覺(Csikszentmihalyi,1975)。游憩專業化與暢爽體驗的關系得到許多研究者的證實,如W?ran 和Arnberger(2012)通過對登山者的研究,發現隨著游憩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人們更有可能達到暢爽體驗;Wu、Scott 和Yang(2013)研究了在線游戲者的游憩專業化程度和暢爽體驗的關系,認為游憩專業化容易導致上癮傾向,同時也會對暢爽體驗的形成發揮作用。
4.個體行為及社會影響
(1)場所選擇和替換
游憩活動的參與需要依托一定的資源、設備和場所,而個體游憩專業化水平不同,對游憩活動場所的選擇也不一樣。McFarlane(2004)通過對車載露營者的考察,研究了游憩專業化中行為、認知和情感維度與場地選擇的聯系,發現生活中心化程度較高的游憩者更有可能選擇無管理(沒有設施和服務)場所,而家庭收入較高的游憩者在管理場所露營的可能性更高。Won、Bang 和Shonk(2008)研究發現,游憩專業化水平和消費狀況對游憩者區域滑雪目的地選擇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Oh、Sutton 和Sorice(2013)研究了游憩專業化對場所替換的影響,發現活動傾向和地方依戀在兩者關系中發揮著中介作用。Sutton和Oh(2015)通過對澳大利亞昆士蘭休閑垂釣者的研究,認為垂釣承諾通過經驗感知、消費取向和感知捕撈活動限制等中間變量,間接影響活動替代的意愿。Galloway(2012)通過考察激流皮劃艇、全能比賽和釣魚參與者的游憩專業化與動機對活動參與和場所偏好的影響發現:動機對活動參與和場所偏好影響較大,而游憩專業化作用甚微;與釣魚活動截然不同的是,激流皮劃艇和全能比賽參與者的動機和場所偏好具有相似性,并且與游憩專業化水平相比,活動屬性對參與動機和場所偏好能夠提供更大的解釋力。Bentz、Lopes 和Calado 等(2016)發現對于觀鯨者,游憩專業化水平較高的潛水員參與頻率更大。
(2)環境保護及管理行為
參與戶外游憩活動與環境保護具有某種關聯(Oh & Ditton,2008),而游憩專業化作為行為的衡量指標,無疑會對游憩參與者的環保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Thapa、Graefe 和Meyer(2005)認為環境教育有利于緩解潛水活動對珊瑚礁生態系統的不利影響,他們通過考察游憩專業化在海洋環境知識和潛水行為關系中的角色和影響,發現游憩專業化在兩者關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而調節作用并不明顯。Waight 和Bath(2014)研究了加拿大紐芬蘭全地形車使用者的游憩專業化水平對其環境和社會感知以及現有資源管理政策態度的影響,從而為制定既符合游憩參與者環境信條和價值觀又能實現環境保護目標的政策建議提供實證依據。Beardmore(2015)通過構造潛類別最大偏差聯合模型,研究了美國威斯康星州北部湖泊資源豐富區域劃船者的環境關注度和環境保護行為投入之間的關系,發現社會人口學特征、游憩專業化、地方依戀和管理態度共同影響劃船者的環境感知。Cheung、Lo 和Fok(2017)針對香港觀鳥者的研究發現,游憩專業化與環境親近態度存在直接正相關關系,而與生態責任行為則具有間接正相關關系。
游憩專業化理論一般認為專業化水平較高的參與者會給予管理規則更多支持,然而Salz 和Loomis(2005)卻發現,不同專業化水平的垂釣者對于海洋保護的態度沒有顯著差異,但所參與的游憩活動對資源的依賴性越強,則游憩者對規則的支持越明顯。Jett、Thapa 和Ko(2009)對美國佛羅里達州船只游憩對海牛影響的研究發現,游憩專業化與海洋保護態度呈負相關關系,即參與者的游憩專業化水平越高,越是對船只限速持不配合態度,并且參與者的游憩專業化水平對其行為意圖、自我報告合規行為以及管制速度差異沒有太大解釋力。
需要指出的是,管理規則的制定需要在資源保護和滿足游憩專業化需求之間作出平衡。Oh 和Ditton(2006)運用游憩專業化三維模型,將垂釣者劃分為隨意型、中間型和高水平型3 個群組,研究不同專業化水平垂釣者在捕撈約束方面的偏好差異,從而為制定管理規則提供建議。Sorice、Oh 和Ditton(2009)對隨意型、積極型和忠實型3 類潛水者在管理約束傾向上的差異進行考察,發現前兩類潛水者期望加大管理約束力度,而忠實型潛水者并不希望受到更多管理約束。Anderson 和Loomis(2012)比較了3 類不同游憩專業化水平的水肺潛水群體對美國佛羅里達群島珊瑚礁資源規范標準的態度,發現參與者的游憩專業化水平與其對此規范的態度緊密相關。Lessard、Morse 和Lepczyk 等(2018)研究發現,水禽捕獵者的專業化水平和認知、知識、態度對其動物保護行為有著積極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國內有關游憩專業化的研究明顯滯后,梳理和總結國外文獻能夠為國內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本文通過對“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數據庫”檢索到的180 篇文獻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進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結論:(1)20 世紀70年代國外已經提出游憩專業化概念及測量指標,之后經大量實證研究予以補充和完善。(2)研究方法呈現定性向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單一化向多元化、簡便化向復雜化轉變的趨勢,尤其以結構方程模型等社會統計方法使用為主。(3)國外從群體類型和活動屬性兩個層面,對游憩專業化議題展開研究。(4)研究內容主要聚焦于對游憩專業化的概念討論、測量維度及應用、與相關議題的關系、個體行為及社會影響等方面。
當前我國十分重視對游憩活動的引導和鼓勵,同時高度關注游憩體驗質量。我國居民游憩活動呈現出多元化特征,除運動性較強的戶外游憩活動,如騎乘、慢跑、潛水、攀巖、背包旅行、露營、滑雪等活動類型外,也存在偏靜態的垂釣、攝影、觀鳥、太極、棋牌等活動類型。另外,居民游憩活動的群體性差異較為明顯,徐燕、李愛菊和郭帥新等(2018)研究發現,與歐美國家現實狀況不同的是,我國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戶外游憩活動參與率較低,而老年人的公園游憩活動較多。結合我國國情和居民游憩活動現狀,基于休閑文化傳統、產業發展實際以及休閑游憩研究狀況,本文對我國游憩專業化研究建議如下:
第一,積極關注和開展游憩專業化研究。通過對國外文獻的年譜分析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于該領域的關注度穩步上升,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迅速提高,然而國內有關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國內學界應充分重視、大力拓展相關研究領域和成果,在作出應有學術貢獻的同時,為我國游憩產業發展和社會環境營造提供有益參考。
第二,在研究內容和方向上可切入的角度有:首先,對游憩專業化進行理論探討,即在國外研究框架基礎上,結合我國游憩活動狀況嘗試考察其適用性,進而予以修正和完善。其次,針對不同活動和群體開展專門性研究。受傳統文化和歷史因素影響,我國居民有著一些特定的游憩活動類型,如太極、棋牌、廣場舞等,這些活動對專業化的要求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從游憩專業化角度切入研究有著重要的學理和實踐價值。另外,我國居民游憩活動的群體特征明顯,同時與國外也有一定差異,有必要分群組開展游憩專業化研究。此外,因地理因素和生活環境使然,我國不同地區居民在文化特質和活動偏好等方面有所區別,因此居民游憩專業化的空間差異特征值得考察。最后,對游憩專業化的影響機理進行研究。哪些因素導致居民游憩的專業化要求?哪些因素影響居民游憩專業化的程度和水平?居民游憩專業化對個體行為、社會環境,甚或宏觀經濟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具有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有待研究者進行深入討論和實證研究。
第三,使用多元化研究方法,進行跨學科、多角度的理論審視和系統分析。以往國外研究主要將游憩專業化限定在行為層面進行考量,因此大多采用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然而,當前社會網絡聯結強化,學者間的社會交流日益頻繁,學術討論逐漸打破學科藩籬,學科交叉、領域交融的局面日益形成,因此,游憩專業化研究也應該嘗試進行拓展和延伸,從多學科角度采用多元方法展開研究。除了從個體行為層面出發將游憩專業化視為人們休閑生活的重要內容,采用社會學、統計學、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外,還可以基于游憩產業角度進行思考,借助經濟學、管理學和地理學等學科方法進行交叉分析和實證研究。另外,從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視角對游憩專業化進行考察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