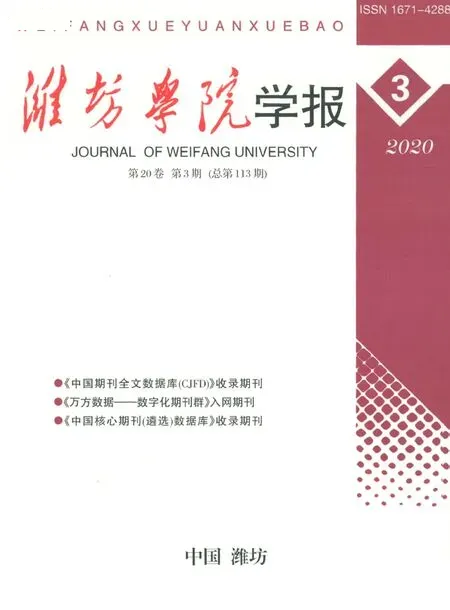莫言作品中的北海(濰坊)文化因素及其在英譯中的體現
明 明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一、北海(濰坊)文化綜述
(一)北海(濰坊)文化的歷史價值
1.北海(濰坊)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是中華文化的主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之一。
北海(濰坊)文化主要起源于東夷文化,而東夷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來源和構成因素之一。換言之,北海(濰坊)文化與中華文化始終是相伴相成的,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礎和底色。在堅定文化自信、中華文化“走出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新時代背景下,全面系統地挖掘和探討北海(濰坊)文化的這些歷史價值,既對歷史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評價,又對未來做出科學的規劃和展望,繼而促進地域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是我們肩負的文化使命。
2.北海(濰坊)文化是齊魯文化的混合體,是連接齊文化和魯文化的重要橋梁。
顧名思義,齊魯文化是由齊文化和魯文化融合而成的。但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講的齊魯文化主要成份是魯文化,齊文化的成份相對較少,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主要體現在魯文化之中。而北海(濰坊)文化的主要部分是齊文化。歷史上,濰坊是齊文化的中心地帶,而且處于齊魯文化的交界處。《山東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作方案》中指出,要著力建設齊文化傳承創新示范區、齊長城文化帶,加強東夷文化、齊文化特色文化研究。這些都為齊文化下一步的大發展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方針政策,而北海(濰坊)文化是重要的著力點和切入點。
3.北海(濰坊)文化為當代濰水文化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奠基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巨大的動力。
北海(濰坊)文化與當代濰水文化具有繼承和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是在不同時空領域的兩個階段。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北海(濰坊)文化中涌現出了管仲、晏子、賈思勰等為數眾多的文化名人,也留下了濰坊風箏、楊家埠木版年畫、高密撲灰年畫等光彩奪目的文化遺產,形成了獨特的北海(濰坊)文化理念和內涵。所有這一切都為當代濰水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讓我們在新的起點上,踏上新的征程,創造出不愧于時代的濰水文化。
(二)北海(濰坊)文化的當下意義
1.加強北海(濰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提升齊魯文化研究水平,促進濰坊文化事業大發展。
十八大以來,齊魯文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山東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作方案》中確立了“1558”的總思路,即“一個目標”“五大體系”“五大文化區域”“八大工程”。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齊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五年。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齊魯文化的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如今正在發揮齊魯文化資源豐厚的優勢,開拓文化強省新途徑。現在,“鄉村儒學”“孝心基金”“家風家訓”“四德榜”“新鄉賢”等已在齊魯大地形成滾滾熱流。齊魯文化蓬勃發展的勢頭為北海(濰坊)文化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應該乘勢而上,大膽作為,助推其向更高的層次發展,進而推動齊魯文化的更大發展。
2.補短板,強弱項,加快齊文化發展步伐。
按照補短板,強弱項的思路,齊文化是下一步發展的重點,而北海(濰坊)文化是新的增長點和突破口。北海(濰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發展藍色文化,強化藍黃文化的交叉對比研究,以此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拓展文化研究的內涵和外延,使文化研究更科學、全面、客觀。
3.北海(濰坊)文化的研究會加快地域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促進其與異質文化的交流。
任何一種文化要健康持續地發展,一方面需要自身不斷地進步和更新,與時俱進,與所處的時代接軌,強筋壯骨;另一方面需要走出去,參與交流,向其他文化學習自身所缺乏的東西。在強化內循環的同時,加強外循環。北海(濰坊)文化的發展也要遵循同樣的路徑,按照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在中華文化發展大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追求自己光明的前景。
二、北海(濰坊)文化的主要特質
(一)綿延不斷、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悠悠歲月
古老、悠久的北海(濰坊)文化起源于遙遠的東夷文化。它跨越歷史長河,歷經歲月滄桑,匯入春秋戰國時期的齊魯文化譜系,發展成為以齊文化為主、兼備魯文化的混合文化,同時具有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特質。這種文化生態一直延續到現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海(濰坊)文化作為齊文化的主要載體和重要力量,弘揚、傳承了齊文化,對齊文化的永續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二)胸懷寬廣、豁達堅毅、純樸豪爽的人格性情
人是文化發展的主體。創造了北海(濰坊)文化的人們,在漫長的歷史進化和征程中,逐漸養成了胸懷寬廣、豁達堅毅、純樸豪爽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性格。這種骨子里、血液中的秉性世代相傳,凝煉成了北海(濰坊)人的性格特征,成為北海(濰坊)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吐納并舉、既“我注六經”、又“六經注我”的文化胸襟
在齊魯文化大地,北海(濰坊)地區處于東西要塞,四通八達,各色人員川流不息,往來頻繁,各種文化、思想、觀點聚集于此,形成齊文化和魯文化兩大文化系統。在這個文化圈內,各種學派、思潮、學說異彩紛呈,以孔子、墨子、管子等為主要代表的諸子百家相繼登臺亮相,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生態。憑借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北海(濰坊)文化接納、吸收、融匯了各派學說之長,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色,實現了從“我注六經”到“六經注我”的質變。而這種文化氣度穿越時空,至今不衰。
三、北海(濰坊)文化在莫言作品中的體現
(一)北海(濰坊)文化特點對莫言的影響
“高密東北鄉”是莫言文學創作的來源和寶藏。莫言以“高密東北鄉”為宏大的背景,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辛勤耕耘,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個性鮮明、充滿張力的文學形象。“高密東北鄉”是虛構的,但體現出的文化是實實在在的。“高密東北鄉”不是地理名稱,而是文化符號。作為北海(濰坊)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開放、創新、包容的特點。這些文化特色深刻地體現在莫言身上。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莫言堅守文學信念,初心不改,一以貫之,終以累累碩果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名至實歸。漫漫征程中,由北海(濰坊)文化凝煉而成的文化定力起著巨大的支撐作用。
北海(濰坊)文化兼備齊文化與魯文化兩種文化資源,同時受到兩種文化的滋養和熏陶。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對北海(濰坊)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等各種思想文化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云集齊魯大地,展開了空前的大交流、大辯論、大碰撞,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成為雅斯貝爾斯所稱“軸心時代”的重要一極,創造了中國自己的“軸心時代”,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戰國時期,在齊國國都臨淄創建的“稷下學宮”,是齊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眾多的思想文化賢達巨子齊聚學宮,各敘己見,暢所欲言,指點江山,縱論天下,你方唱罷我登場,形成氣勢恢宏的洋洋大觀。齊都臨淄成了各種思想、學說的集散地。北海(濰坊)文化身在其中,近水樓臺,成了這場文化盛宴的享用者和受益者。
經歷了“百家爭鳴”“稷下學宮”洗禮的北海(濰坊)文化,成了集各種思想于一體的混合性文化,自身的吐納能力變得越來越強。
生活在群芳斗妍、萬紫千紅的北海(濰坊)文化環境里,莫言的文化理念、思維方式和知識譜系自然是開放的、多元的、動態的。在文學創作中,莫言將中國傳統文學的敘事方法與西方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將其中的多種創作風格消化吸收,提煉出一種獨特的創作原則和方法,將其應用到實踐中。在他的小說中,我們既能看到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遺留下來的寫作方法,又能看到福克納、馬爾克斯的那種時空倒錯、光怪陸離的現代主義寫法。為什么莫言能做到既“我注六經”,又“六經注我”?答案是文化使然。北海(濰坊)文化所具有的這種文化張力為莫言提供了原始基礎和動力。
(二)北海(濰坊)文化中人物性格特征在莫言作品中的體現
一提到莫言的作品,人們就會自然想起電影、電視劇《紅高粱》,對“我爺爺”“我奶奶”的藝術形象難以忘懷。演員們以一種視聽方式把這些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取得了巨大成功。《紅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說中描寫的悲壯蒼涼的情感故事、敢愛敢恨的人物性格、豪放曠達的生命追求,無不體現出北海(濰坊)文化中蘊藏的根底和基因。藝術創作的成功,說到底是文化的成功。而這些文化韻味也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形成了獨特的“這一個”。
四、莫言作品中的北海(濰坊)文化因素在英譯中的體現
莫言2012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文學界自不待說。人們開始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分析莫言獲獎的原因。答案是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中翻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說起翻譯,就不能不提美國著名翻譯家、莫言小說的英譯者葛浩文。這位英語世界莫言小說的首席翻譯家,無論是在數量、質量,還是影響方面,都可稱得上“第一人”。本文所選的《生死疲勞》英譯即出自葛浩文筆下。
(一)《生死疲老》英譯案例評析
案例1. 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發出肌肉爆裂的噼啪聲。
At that moment I wavered as my crisp body lay sprawled in a puddle of oil that was still popping and crackling.
案例2.買了十掛八百頭的鞭炮。
Buy ten strings of firecrackers, eight hundred in all.
案例3.金龍雙手端著收音機,仿佛孝子端著父親的骨灰盒,神色凝重地向村子走去。
Holding the radio in his hands like a filial son carrying his father’s ashes.[1]
評析:
案例1.“焦干”是方言,地域文化特色顯明,意為“極為干燥”,用“crisp”翻譯十分形象,有動感,與后文的描寫融合一體,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其背后的文化意象也歷歷在目。
案例2.“頭”是表示鞭炮聲響數的量詞,屬方言。800 頭就是800 響的意思,英譯中已經出現相應的翻譯,按照歸化法翻譯,就可以了,不必計較是一共800 響,還是每掛800 響。西方讀者不會在意這些細節問題。“800”所代表的民俗含義已經有了
案例3.句子中的“孝子”意為“守孝之子”,將“孝子”譯為“a filial son”是可以的。如果是個不孝之子,怎么能成為守孝之子呢?對英語讀者來說,理解到這一層,也就夠了。文化中的孝道精神也傳達到了。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3 例均出自宋慶偉《葛譯莫言小說方言誤譯探析》一文,但本文只同意宋文中的中文部分,基本采用,但不同意英語部分的分析及對葛譯的改動,本文認同葛譯并進行了評析,認為譯文較好地傳遞了譯出語的內容,語言和文化兩個層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傳遞效果,小說中的語言與文化特色較完整地展現給了目的語讀者。
(二)《生死疲老》英譯案例評析
案例:第二年初春她就為我生了龍鳳胎,男名西門金龍,女名西門寶鳳。
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 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 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 or Golden Dragon, 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Precious Phoenix. (Goldblatt,2008)[2]
評析:
同樣是翻譯《生死疲老》,葛浩文此處卻用了不同的方法,具體而言就是直譯+注解法:先將“龍鳳胎”直譯為“a boy and a girl”,然后用“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注解“龍鳳胎”,人名則采 用 漢 語 拼 音+“Golden Dragon”“Precious Phoenix”的方法,分別解釋“金龍”和“寶鳳”的含義。這種具有異化色彩的翻譯較完整地傳遞了譯出語的語言與文化信息,文化交流達到了較理想的狀態。“龍”“鳳”這一對文化符號得到了充分的詮釋。
(三)葛譯莫言小說評析
1.理論基礎
從功能/目的論的角度來看,任何一種翻譯行為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翻譯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它是發生在現實中的、具有明確目的、通過兩種語言的轉換來實現的一種文化行為。判斷翻譯的成與敗,好與壞,就要看翻譯是否達到了它預設的目的。如果按這個判斷標準來衡量葛譯莫言小說,無疑是成功的。最重要的標志是通過葛浩文的英譯,莫言的小說在英語界名聲大振,在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有了一塊基地和跳板,隨著莫言小說被陸續譯成法語、瑞典語等,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門向莫言慢慢地敞開了。
2.翻譯策略
為了達到預設的目的,葛浩文在翻譯實踐中采用了以歸化法為主、各種方法并用的翻譯策略,在組織結構、遣詞造句、創作風格等諸方面進行了他認為必要的改造和置換,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葛氏風格。可以說葛譯取得了成功,葛浩文成就了莫言,莫言也成就了葛浩文,譯者與作者在兩種文字的轉換中得到了雙重認可和提升。然而,葛譯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評、反對和詬病。有人說葛浩文的翻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充其量就是一種編譯,這跟當年林譯小說相似,屬于同一路數。在此,歸化與異化等問題又成了爭論的焦點。
(四)相關思考
葛浩文起初翻譯莫言小說的時候,中國文化還處于相對弱勢的情形,在那樣一個背景和狀態下,他選擇的以歸化為主兼顧其它的翻譯策略,是符合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內在規律的。因此,整體上葛譯是成功的。許多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然,采取歸化法也付出了不小代價。眾所周知,歸化法是以目的語讀者為對象的,這就造成譯出語中的一些異質文化信息和意象被遮蔽、扭曲和丟失,從而在某些方面影響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傳播的效果和質量也會打折扣,這樣會一定程度上堵塞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的路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采取這種翻譯策略和方法實屬不得已而為之。需要指出的是,翻譯策略和方法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和各種力量的強弱轉換,譯者也會進行相應的調整。作為著名漢學家、翻譯家的葛浩文深諳此理。換言之,翻譯是一種動態行為。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葛浩文也在不斷地變化自己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我們閱讀他的譯品,已經明顯感覺到了各種各樣的變化和交替,其中最明顯就是異化比例越來越高,譯出語的味道越來越濃,譯出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越來越多。這是符合規律和邏輯的,本文中所列案例也充分體現了這種變化。說到底,語言變化的背后是文化的變化,它會一直延續下去。
五、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大致可以獲得以下結論和啟示:
首先,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密切,兩者之間這種天然的、歷史的、邏輯的關聯為相關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機遇和空間。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該用新的理念、視角、方式對翻譯與文化相關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探索、定位,使其更加符合發展大勢,發揮出兩者的疊加效應。
其次,地域文化發展有利于國家整體文化的發展,同理,地域文化的對外傳播也有利于國家整體文化的對外傳播。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徑和窗口。
再次,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翻譯也在經歷“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3]的巨變。新時代需要我們站在新的角度,從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出發,思考和探索新的翻譯和文化理論,“創造大翻譯”[4],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用以指導火熱的翻譯實踐,在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互動中,形成文化自信、翻譯自信、語言自信三者的良性循環,繼而貫穿文化對外傳播的全過程,讓中華文化真正“走出去”“走進去”“融進去”,在與異質文化的交流中,生成“文化新質”[5],為文化交流、文明互鑒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