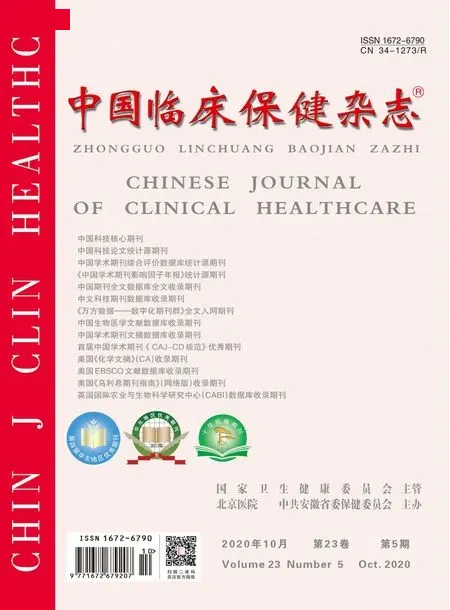癡呆癥患者精神行為癥狀的危險因素解析及應對技巧
孫雪蓮,董碧蓉
[國家老年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成都 610041]
癡呆癥是一種以認知功能障礙為核心癥狀的智能損害綜合征。其特點是獲得性、進行性;病情發展可累及精神、行為,有的可出現人格障礙。損害的是意識的內容,而非意識水平。全球癡呆癥局勢日益嚴峻,目前患病人數約5 000萬,每100位60歲及以上人口中就有5至8名癡呆癥患者,約每3秒就有1例新發患者。在國外,2000年至2018年間,美國的中風、心臟病等導致的死亡人數下降,而癡呆癥死亡人數卻增加了146.2%,成為65歲以上死亡的第五大原因[1]。據預測,在2030年,全球癡呆癥將達8 200萬,到2050年將達1.52億[2]。
癡呆癥精神行為癥狀(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BPSD)是指癡呆癥患者的感知、思維、情緒或行為等出現困擾的癥候群。表現為妄想、幻覺、焦慮、淡漠、抑郁、煩躁、欣快、激越、攻擊、易激惹、脫抑制、夜間行為、食欲和進食異常等[3-4]。BPSD的照護是最大的挑戰,照護者及家屬常合并嚴重的心理障礙[5],同時也增加患者肺炎、跌倒、骨折、住院及入住照護機構的概率,導致老人生命質量下降,過早喪失尊嚴[4-5]。
本文就BPSD在“患者-照護者-環境”多維危險因素,常見預防及應對策略方面進行闡述,為癡呆癥的照護及BPSD的應對提供參考。
1 關于BPSD
1.1 BPSD的特點 雖然認知障礙是癡呆癥的標志性癥狀,但BPSD在全病程都有占有重要地位[4-5]。70%~90%癡呆癥患者在認知退化的同時會發生至少1種BPSD癥狀[4],癥狀可呈單一性或以聚集性癥候群出現。其中,淡漠、抑郁、焦慮、攻擊、妄想、幻覺、進食異常最常發生[5]。在癡呆癥不同階段,BPSD表現出來癥狀類型和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焦慮和抑郁在早期癡呆癥中很常見,并可能隨著病情進展而惡化;激越可隨著疾病的嚴重程度而加重[5-6];淡漠是照護者最常報告的BPSP癥狀,隨著病程進展而惡化;妄想、幻覺和攻擊性呈現間歇性特點,在疾病中度至重度階段更常見[7]。此外,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癡呆癥與特定的BPSD癥候群具有密切的相關性[4-5]。例如阿爾茨海默病中妄想較常見,占43.5%;幻覺在路易體癡呆癥比在阿爾茨海默病更常見,高達80%;抑郁癥在血管性癡呆癥更常見,額顳葉癡呆癥患者常表現出執行及控制能力損害,如脫抑制、社交不當和淡漠[8-9]。
與癡呆癥認知和功能逐漸減退不同,多數BPSD癥狀呈現間歇性、長期性特點,增加了預防和管理的復雜性。也正是如此,癡呆癥總照護費用的三分之一都用在了BPSD的直接照護、日常看管、醫療及額外衛生服務上[10]。在2019年,美國超過1600萬家庭和近親屬照護者為癡呆癥BPSD患者提供了約186億小時的無償護理,照護價值近2 440億美元,醫療補助是非BPSD人群的23倍以上[11]。若考慮到BPSD引發的照護者情緒困擾、負面心理和身體健康等問題,成本將更高。據預計,美國2020年為65歲及以上癡呆癥患者提供的醫療保健、長期護理和臨終關懷服務的總支出約為3 050億美元[1,12]。
1.2 BPSD的危險影響因素概述 根據《2018中國癡呆癥與認知障礙診治指南》,癡呆癥不可干預的危險因素主要有:高齡、女性、致病基因和風險基因遺傳、由遺傳與環境因素作用下家族聚集性發病史;可干預的危險因素包括: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血脂總膽固醇或低密度膽固醇增高、2型糖尿病、體質量指數異常(中年期過高、老年期過低)、吸煙與飲酒、飲食中飽和脂肪酸過多、低教育水平、缺乏體力及腦力活動、腦外傷。
2 BPSD的危險影響因素介紹
2.1 患者本身因素 患者方面涉及癡呆癥神經病理、原有人格和精神障礙、其他共患病及潛在未診斷疾病、未滿足的需要、內心對患病的抗拒性、不能適應自身角色變化等因素。
癡呆癥神經病理涉及Aβ病理性蛋白沉積和神經纖維纏結,以及造成的多巴胺能、膽堿能及5-羥色胺能等神經遞質系統紊亂,這是BPSD重要的生物學因素[13]。
其他共患及潛在未診斷疾病也是引發BPSD的重要原因,如疼痛與攻擊行為相關,管理疼痛可使癥狀緩解[14]。居家及社區環境中36%BPSD癥狀與潛在未診斷的基礎疾病相關[15],共病多重用藥導致的藥物副作用也不容忽視。此外,患者潛在或顯性需求未得到滿足也是重要原因。“需求驅動的癡呆癥妥協行為”理論認為,BPSD是患者生理、心理、情感及社會等需求或目標未得到滿足的表現。他們通過語言來表達自身需求的能力退化,由此轉而通過各種行為來進行需求表達[16]。需要注意,患者內心對患病的抗拒性及不能適應自身角色變化[17],是兩項重要且關注度不夠的因素。
2.2 照護者相關因素 BPSD的復雜性還體現在與照護者狀態有關。在癡呆癥照護過程中,照護者會有經濟和社會壓力以及以心理問題(包括社會心理)為主的健康損害,即照護者負擔或照護者壓力,并且照護者的身心負擔超過經濟負擔。在管理BPSD時,照護者的壓力和抑郁會增加,反過來,這種負性狀態可觸發或加劇BPSD[18]。研究發現,與其他類型照護者相比,癡呆癥照護者的心理痛苦和壓力水平更高,自我照護效能評價、主觀幸福感和身體健康水平更低[19]。癡呆癥照護者中,抑郁癥發生率從23%到85%不等[5]。當照護者在身體、心理和照護技能上沒有做好準備,并持有與病程階段不匹配、過高照護預期時,其壓力和抑郁等負性狀態可能更為常見。
這種情況下,照護者容易出現否認患者病情的態度、情緒不穩定、煩躁、沮喪、焦慮、易怒、注意力分散、失眠,疲憊、乏力和社交困難等。例如,照護者會從意識上拒絕認為親人患有癡呆癥,變得孤僻且不愿與他人來往,對生活缺乏信心,對患者失去耐心并大聲吼叫,注意力分散難以完成復雜的工作,頻繁而強烈的無助感與無希望感。
照護者是癡呆癥管理的重要一環,這些負性因素更加容易引發患者的BPSD癥狀,形成惡性循環,這尤其不利于首要推薦的非藥物干預措施的實施。
2.3 環境因素 BPSD隨著癡呆癥病程階段和環境刺激的不同而呈現差異性。引發BPSD癥狀的環境因素可來源于不再適宜的居住環境、患者慣常生活方式的改變、身處的社會環境的變化或是環境中缺乏適量刺激因素等。例如房子空間過于狹窄、室內光線昏暗、噪聲過高等[4-5]。由于患者機體對環境刺激因素的處理能力呈進行性降低,而引發患者產生BPSD的刺激閾值也會降低,使之更容易出現幻覺、焦慮和激越等BPSD癥狀或使癥狀程度加重。此外,由于機體應對刺激因素的儲備能力降低,當接觸到單一刺激因素時,機體或能良好應對,如日常家庭日常物品和器具使用,但是卻難以在多水平因素間做好轉換、協調與平衡[5,17]。
3 患者-照護者-環境因素相互作用
癡呆癥腦病理及其他神經疾病因素,可累及控制行為和情感的大腦回路而引發BPSD,照護者和環境因素也可獨立觸發BPSD癥候群。實際上,BPSD危險因素概念模型研究[5]認為,更多情況下,BPSD是由三個維度因素相互作用而引發。危險因素群共同作用于抗打擊性及儲備力受損的機體,加劇癡呆癥神經病理退化,降低PBSD癥狀對刺激因素的感受閾值,誘發并加重BPSD癥狀,進而使照護者處于負性照護狀態并反作用于BPSD,最終,形成難以糾正的BPSD負性循環,導致不良結局。
4 預防及照護建議
根據《2018中國癡呆癥與認知障礙診治指南》,對常見BPSD癥狀的應對,應該以預防和改善癡呆癥危險因素開始:如適合的身體活動、戒煙、限酒或戒酒、“地中海”飲食干預、適合的認知訓練、融入社會及參與社交活動、避免超重和肥胖、控制“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管理抑郁癥及聽力損失。在此基礎之上,需針對如上BPSD的“患者-照護者-環境”危險因素網絡進行聯合預防及干預[2,16]。
根據不同BPSD癥狀的特點,干預分為三類:①需要精神類藥物緊急治療類,②需非藥物干預聯合短期精神類藥物類,③僅需非藥物干預類[4]。第一類包括:攻擊行為和激越;第二類包括:攻擊性言語、運動性激越、破壞性的行為、妄想、幻覺、抑郁、哭泣、欣快、焦慮、睡眠紊亂、脫抑制、性活動增強等;第三類包括人物和場景等錯認、愛跟隨照護者等游蕩行為、淡漠和進食異常行為等。需要強調的是,在抗癡呆癥藥物基礎上,多項指南及協會都推薦了非藥物干預作為首選措施,只有癥狀不能良好控制、患者難以配合照護者、患者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以及在情況緊急時,才應該進行適合的藥物干預。
總體上,照護者和(或)家屬應該具有“BPSD全病程照料意識”,隔離危險品,保護患者的安全,了解患者的個性、興趣、尚存的能力、過去的經歷等,并與專業團隊共同制定以患者為中心、以非藥物干預為首、聯合藥物治療的管理方案。進一步,在序貫開展的癡呆癥及BPSD預防及干預后,需要定期評估效果,不斷進行方案調整及照料方式改善[20]。
5 總結
癡呆癥及其BPSD癥狀對全社會提出挑戰,給患者、照護者及社會衛生經濟造成極大負擔,讓患者過早地喪失尊嚴,也讓照護者難以應對,讓無數家庭陷入痛苦。增進對BPSD特征、“患者-照護者-環境”危險因素群、基本預防及干預措施等的認識,有助于形成綜合管理團隊,攜手共同面對癡呆癥。未來的研究,一方面,需要重視如何將研究成果進行臨床轉化;另一方面,需要重視如何將研究成果以患者及照護者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到他們身邊。同時,在全球不斷加劇的癡呆癥患病趨勢下,急需大量掌握了科學照護方法的照護人員,這一需求的補足,需要大量的專業團隊通過互聯網等現代科技手段給予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