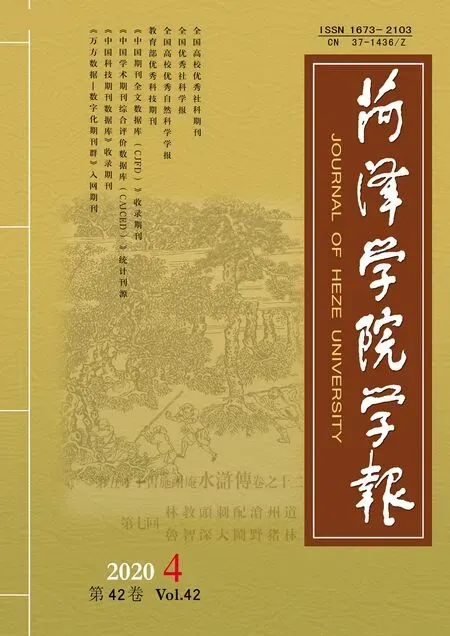論比較文學(xué)中的翻譯文學(xué)
盛永宏
(天津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天津 300384)
至今為止,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門(mén)學(xué)科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比較文學(xué)的內(nèi)部研究也更豐富。特別是在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隨著文化多元化時(shí)代的到來(lái),東方文學(xué)被納入到比較文學(xué)的視域,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范圍更加開(kāi)闊,語(yǔ)言的問(wèn)題也更為突出,于是,翻譯的重要性引起人們的重視,翻譯文學(xué)也隨之受到更多的關(guān)注。
在個(gè)案的對(duì)比研究中,因?yàn)槊褡逅哂械姆€(wěn)定性及其語(yǔ)言使用的獨(dú)特性,所以民族文學(xué)被認(rèn)為是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基點(diǎn)。在研究過(guò)程中,研究者所屬的民族文學(xué)與異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被放到一個(gè)平臺(tái)或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下進(jìn)行比較研究,此時(shí)的異國(guó)文學(xué)需要被翻譯成本民族的語(yǔ)言,即使研究者具備閱讀甚至評(píng)論的能力,但在形成文字時(shí)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將兩種語(yǔ)言統(tǒng)一成一種語(yǔ)言來(lái)進(jìn)行表述,于是翻譯文學(xué)就更為重要。因?yàn)橐粋€(gè)人無(wú)法熟練地掌握多種語(yǔ)言并進(jìn)行閱讀,所以對(duì)于大部分的讀者而言,翻譯是必備的。就如法國(guó)學(xué)者阿普特提出的:“把一種新的比較文學(xué)的前景置于翻譯的問(wèn)題中”[1],翻譯成為我們必須重視的問(wèn)題,而翻譯文學(xué)也需要我們重新認(rèn)識(shí)并給予它在學(xué)科中應(yīng)有的位置。
一、存在論意義上的不可或缺性
翻譯作為譯介活動(dòng)一直存在,從古至今翻譯在民間的交流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但很多時(shí)候人們并未認(rèn)識(shí)到這些,認(rèn)為翻譯僅是語(yǔ)言的轉(zhuǎn)換,類(lèi)似于工匠的手藝。“由于翻譯受到輕視,作為翻譯的一個(gè)類(lèi)型的翻譯文學(xué)自難幸免。”[2]翻譯文學(xué)對(duì)促進(jìn)民族間的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和價(jià)值,但人們對(duì)于翻譯文學(xué)的認(rèn)知也僅限于此,沒(méi)有做更深入地探究,在具體的操作中更多地表現(xiàn)在對(duì)翻譯標(biāo)準(zhǔn)、方法和原則等的研究上,其成果可謂卷帙浩繁。
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在國(guó)際比較文學(xué)進(jìn)入自身發(fā)展的第三個(gè)階段,面對(duì)理論大潮、東西比較文學(xué)的興起和文化研究的熱潮三股世界性潮流的沖擊,比較文學(xué)迎來(lái)了新的生機(jī)和挑戰(zhàn)。其中,東西比較文學(xué)的興起意味著比較文學(xué)研究對(duì)象范圍的擴(kuò)大,東方和西方處于兩個(gè)文化圈,在價(jià)值觀念、風(fēng)俗信仰上異大于同,語(yǔ)言上的差異尤其突出,由此,翻譯在這種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由于多元經(jīng)濟(jì)逐步替代寡頭經(jīng)濟(jì),殖民體系隨之瓦解,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來(lái)臨,世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歐洲中心論”趨于解體,而之前處于文化邊緣地位的東方文學(xué)開(kāi)始掙脫過(guò)去的從屬地位,“向中心移動(dòng),它們面臨著借鑒當(dāng)代意識(shí),賦予傳統(tǒng)以新意,使之發(fā)揚(yáng)光大的使命。”[3]與此相應(yīng),西方的一些學(xué)者也察覺(jué)到過(guò)去比較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的局限,認(rèn)識(shí)到東方文學(xué)的價(jià)值,將東西方文學(xué)間的比較納入到比較文學(xué)研究中,開(kāi)拓了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解決了之前的法國(guó)學(xué)派和美國(guó)學(xué)派間的爭(zhēng)論。于是,“在豐富而多元的當(dāng)代翻譯研究中,比較文學(xué)翻譯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4]“它不局限于某些語(yǔ)言現(xiàn)象的理解與表達(dá),也不參與評(píng)論其優(yōu)劣,它把翻譯中涉及的語(yǔ)言現(xiàn)象作為文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加以考察。”[5]它更加關(guān)注的是不同民族、文化是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下進(jìn)行的交流,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溝通和交融的,及產(chǎn)生了哪些誤讀或歪曲的現(xiàn)象,最終對(duì)文學(xué)間的交流或影響產(chǎn)生怎樣的作用,從這種意義上,翻譯研究和文學(xué)翻譯為比較文學(xué)開(kāi)拓了新的研究領(lǐng)域。
翻譯文學(xué)在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和文學(xué)研究中往往處于一種無(wú)所歸屬的處境,翻譯研究一般注重的是語(yǔ)言間的轉(zhuǎn)換、標(biāo)準(zhǔn)、效果等現(xiàn)象,并不關(guān)心它的文學(xué)地位;文學(xué)研究中往往只看到翻譯過(guò)來(lái)的外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而并不認(rèn)同它是民族文學(xué)的一個(gè)組成部分,這種現(xiàn)象持續(xù)了幾十年,直到上個(gè)世紀(jì)的90年代,張鐵夫先生提出“翻譯文學(xué)是民族文學(xué)的組成部分”[6]一說(shuō)。
然而,翻譯文學(xué)作為一種相對(duì)獨(dú)立的整體,它具有研究的價(jià)值:翻譯文學(xué)與譯語(yǔ)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有怎樣的關(guān)系?翻譯文學(xué)可以等同外國(guó)文學(xué)嗎?翻譯文學(xué)在譯語(yǔ)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史上應(yīng)該占有什么樣的地位?這些問(wèn)題的提出,涉及了翻譯作品的價(jià)值,翻譯者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加入了自己對(duì)作品的理解和再創(chuàng)造,延伸了作品的生命。文學(xué)翻譯是一種創(chuàng)造,對(duì)此我國(guó)的前輩學(xué)者對(duì)此曾有過(guò)肯定,如矛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等對(duì)于翻譯的看法:“翻譯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有時(shí)候翻譯比創(chuàng)作還要困難。”[7]而國(guó)際的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也持有類(lèi)似的看法,將翻譯文學(xué)視為民族文學(xué)(國(guó)別文學(xué))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如英國(guó)在20世紀(jì)50年代出版過(guò)的兩個(gè)版本的文學(xué)史,其中提到翻譯的地方多達(dá)200多處,翻譯者182人等。在我國(guó)一本作品有多種翻譯版本,比較經(jīng)典的就是《哈姆雷特》的翻譯,各不相同,但又各有特色。這些都體現(xiàn)了翻譯文學(xué)存在的必要性,對(duì)于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而言,不僅開(kāi)拓了研究領(lǐng)域,更是為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奠定了存在的前提基礎(chǔ)。
二、本體論意義上的創(chuàng)造性特質(zhì)
在文學(xué)翻譯的過(guò)程中,因?yàn)榉g者的個(gè)人風(fēng)格、語(yǔ)言習(xí)慣等因素的不同,所翻譯的作品也呈現(xiàn)不同的風(fēng)格。另外,譯著所處的時(shí)代和接受群體的不同也影響著作品的翻譯。所以,作品在被翻譯的過(guò)程中往往會(huì)出現(xiàn)與原著不同的地方,這些不同點(diǎn)出于不同的原因或隱或顯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即法國(guó)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家埃斯卡皮說(shuō)的:“翻譯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8]翻譯文學(xué)因?yàn)檫@種創(chuàng)造性形成了自己獨(dú)有的特色,創(chuàng)造性即是翻譯文學(xué)的本質(zhì)屬性。
在具體的翻譯過(guò)程中,創(chuàng)造性叛逆可分為有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和無(wú)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兩種。先看有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指翻譯者在面對(duì)原著時(shí),因?yàn)閭€(gè)人的翻譯原則、特殊的追求目標(biāo)及外在環(huán)境的影響因素等,采取了有意識(shí)的改變,如譯著采用的文體、選取的篇章、是否屬于轉(zhuǎn)譯等,這些方面都帶有個(gè)人的喜好。以拜倫詩(shī)歌的翻譯為例,馬君武使用的是七言古詩(shī)體,蘇曼殊使用的是五言古詩(shī)體,而胡適使用的是離騷體。在語(yǔ)言的表現(xiàn)形式上,幾位翻譯者都使用了不同的形式,形成的效果也不同,甚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形成了差異,這其中的變化就在于翻譯者的有意識(sh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另外,翻譯者在選擇原著進(jìn)行翻譯之前,也會(huì)根據(jù)接受環(huán)境和接受群體來(lái)選擇譯著所需要的詞匯和風(fēng)格。如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是迄今中國(guó)莎士比亞作品的最完整的、質(zhì)量較好的譯本。譯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nèi),保持原作之神韻”為宗旨,譯筆流暢、文辭華瞻。朱生豪先生的譯著主要在20世紀(jì)的30、40年代集中完成,那時(shí)時(shí)局動(dòng)蕩,朱生豪先生不愿為敵偽效勞,僅靠微薄稿費(fèi)維持極困難的生活,極盡忠實(shí)于原著,勝在“神韻”、文辭優(yōu)美。當(dāng)然這樣的評(píng)價(jià)來(lái)源于與其它譯本的比較。莎士比亞的作品,在人類(lèi)文學(xué)的藝術(shù)史上達(dá)到了一個(gè)頂峰,其中包括他對(duì)戲劇情節(jié)的設(shè)置、人物的刻畫(huà)及對(duì)人文精神的思考等,但在用詞的選擇、口語(yǔ)化的表達(dá)及民間手法的使用上都體現(xiàn)了迎合當(dāng)時(shí)的市民需求的特點(diǎn),并不完全高雅。但在朱生豪先生的譯本中原有的粗俗化的言語(yǔ)都被摒棄,形成了有意識(shí)的叛逆。當(dāng)然這與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是息息相關(guān)的,20世紀(jì)30、40年代,戰(zhàn)火紛飛、國(guó)恨家仇、民不聊生,但在觀念上整體比較傳統(tǒng)保守,特別是在當(dāng)時(shí)能夠接受教育的人群基本來(lái)自于有產(chǎn)階級(jí),高雅、正統(tǒng)、風(fēng)范等觀念植根于這類(lèi)人的骨子里,所以,朱生豪先生所采用的翻譯原則使得他的譯著廣受歡迎,影響延續(xù)至今。這類(lèi)主動(dòng)型的創(chuàng)造型叛逆為作品贏得了生機(jī),帶有翻譯者的個(gè)性。
在接受效果上,形成了歸化和異化兩者不同的效果:歸化即譯著在譯語(yǔ)文化中被吞并的現(xiàn)象,如傅雷先生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除了人物的名字讓人感覺(jué)生疏外,整部作品帶有濃烈的本土氣息。異化,即譯語(yǔ)文化屈從原著文化的現(xiàn)象,如魯迅先生主張的“硬譯”就是典型的事例。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如果遇到不能翻譯的詞匯等,就直接拿過(guò)來(lái),慢慢地這種被拿過(guò)來(lái)的詞匯也成為譯語(yǔ)詞匯文化的一部分了。最終,有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為文學(xué)自身的豐富和發(fā)展提供了養(yǎng)分。
無(wú)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是指翻譯者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因?yàn)殄e(cuò)誤理解原文或是偶然漏掉了某些部分而造成的叛逆。這種叛逆往往來(lái)源于對(duì)原著所屬的地域文化、風(fēng)俗等不甚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進(jìn)行翻譯,最終形成了“誤讀”現(xiàn)象。如生產(chǎn)生活中的一些意象被用來(lái)溝通交流時(shí),東西方對(duì)它們的理解是不同的。以動(dòng)物“狗”為例,雖然狗被認(rèn)為是人類(lèi)忠實(shí)的朋友,但在漢語(yǔ)的部分詞匯中卻表現(xiàn)出其他的意思,以帶有“狗”字的成語(yǔ)、歇后語(yǔ)為例:“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仗人勢(shì)”“狗急跳墻”“狗血噴頭”“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等,這表現(xiàn)出在漢語(yǔ)的語(yǔ)境中與“狗”相關(guān)的詞的貶義性。在這樣的語(yǔ)境中如果將“You are a luck dog”直接翻譯“你是一條幸運(yùn)狗”恐怕會(huì)引起禍端。類(lèi)似的現(xiàn)象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有很多,一些具有特定內(nèi)涵文化意象的傳遞問(wèn)題就更為復(fù)雜,所以這類(lèi)無(wú)意識(shí)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也會(huì)給文學(xué)間的交流提供素材。在這種意義上,“譯本不僅是原作簡(jiǎn)單的生命延續(xù)和跨文化意義上的文學(xué)新生命,也是文學(xué)性和作品所隱含的文化意蘊(yùn)的輻射和播散。”[9]
三、認(rèn)識(shí)論意義上的民族文學(xué)養(yǎng)分源泉及組成部分
民族文學(xué)因其在形成的過(guò)程中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受其民族自身社會(huì)、心理、語(yǔ)言等因素的影響,所以它往往反映的是本民族的審美心理和美學(xué)品格,具有相當(dāng)?shù)姆€(wěn)定性,由此也成為比較文學(xué)研究展開(kāi)的基點(diǎn)。但在長(zhǎng)期的歷史進(jìn)程中,民族文學(xué)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與外來(lái)文化碰撞交融的過(guò)程中不斷地豐富自身。特別是當(dāng)民族文學(xué)所處的時(shí)代出現(xiàn)動(dòng)蕩,在民族文學(xué)急于改變的形勢(shì)下,外來(lái)的文化往往就成民族文學(xué)汲取養(yǎng)分的源泉。
埃文-佐哈在《翻譯文學(xué)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的位置》中提到“翻譯文學(xué)可以部分或全部填補(bǔ)這一空缺”[10],此處的“空缺”指向的是民族文學(xué)中“迫切需要的技巧儲(chǔ)備”、新的文學(xué)樣式、精神內(nèi)質(zhì)等。埃文-佐哈先生認(rèn)為翻譯文學(xué)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根據(jù)不同的外在環(huán)境中翻譯文學(xué)所處的位置可區(qū)分為中心或邊緣兩種。其中處于邊緣位置時(shí),翻譯文學(xué)基本不被重視,一般是本民族文學(xué)發(fā)展的很快,遠(yuǎn)超于翻譯文學(xué),此時(shí)的翻譯文學(xué)對(duì)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的影響不大。我們主要來(lái)看當(dāng)翻譯文學(xué)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占據(jù)中心位置時(shí),“意味著它積極參與了多元系統(tǒng)核心的構(gòu)建”[11]。因?yàn)榇藭r(shí)的譯入者并沒(méi)有過(guò)多地考慮翻譯文學(xué)與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間的差別,基本將二者視為一體,看重的是翻譯文學(xué)中的一些全新的特征,如創(chuàng)造技巧、使用詞匯等。由此可以看出,翻譯文學(xué)為譯入語(yǔ)文學(xué)提供了養(yǎng)分。但就此會(huì)有人說(shuō),這些養(yǎng)分的來(lái)源實(shí)質(zhì)上是另一民族的文學(xué),而非翻譯文學(xué),由此我們來(lái)分析一下翻譯文學(xué)與民族文學(xué)間的關(guān)系。
翻譯文學(xué)的生成是由翻譯者決定的,翻譯者可以有兩類(lèi)人:第一類(lèi)是譯者將自身所屬民族的文學(xué)譯介給其他民族,此時(shí)譯者對(duì)自己民族非常熟悉,但對(duì)其他民族的熟悉度要低很多,所以此時(shí)譯者會(huì)選擇自己民族最為優(yōu)秀的作品進(jìn)行譯介,但譯入語(yǔ)民族并不完全認(rèn)同,由此導(dǎo)致翻譯文學(xué)處于邊緣位置,對(duì)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的影響小,成為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的點(diǎn)綴,僅為其民族文學(xué)增添一點(diǎn)異族文學(xué)的色彩而已,或可稱(chēng)其為不被直接需要的養(yǎng)料庫(kù)。第二類(lèi)是譯者將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學(xué)譯介給自己的民族,此時(shí)因?yàn)樽g者非常熟悉自己的民族習(xí)性、風(fēng)俗制度、接受習(xí)慣等,所以在選擇原著時(shí)會(huì)考慮讀者的接受習(xí)慣,或是會(huì)選擇與本民族文學(xué)風(fēng)格、美學(xué)追求等完全不同的原著,目的是借鑒學(xué)習(xí),汲取其中能為自身所用的養(yǎng)分。又因?yàn)樽g者對(duì)本民族的思維方式、生活習(xí)慣等極為熟悉,所以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盡可能地將原著的內(nèi)容本民族化,成為勞倫斯·韋努蒂在《翻譯、共同體、烏托邦》中指出的:“通過(guò)翻譯的任何交流都涉及某種本土殘余物的釋放,尤其是文學(xué)的翻譯。”[12]由此讀者看到的作品就很容易被吸引,此時(shí)的翻譯文學(xué)在本土化的過(guò)程中已經(jīng)注入了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的色彩,在這種意義上翻譯文學(xué)因?yàn)樽g者的因素,特別是上一部分中提到的創(chuàng)造性特征而使得翻譯文學(xué)成為民族文學(xué)的一部分。
翻譯文學(xué)與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往往處于邊緣與中心,或中心與邊緣的對(duì)立關(guān)系中,當(dāng)外在的多元系統(tǒng)發(fā)生變化時(shí),兩者間的關(guān)系就會(huì)發(fā)生調(diào)轉(zhuǎn),這與翻譯者的主觀選擇和個(gè)性特征相關(guān),“最終促成(翻譯)適當(dāng)性的條件與對(duì)等現(xiàn)實(shí)高度重合的狀態(tài)。”[13]譯入語(yǔ)民族文學(xué)吸收的養(yǎng)分,加速發(fā)展,翻譯文學(xué)因?yàn)闈饬业淖g入語(yǔ)民族氣息而融入民族文學(xué),成為其組成部分。
翻譯文學(xué)因其自身的存在價(jià)值為民族文學(xué)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分,但在長(zhǎng)期偏重于民族文學(xué)研究的歷史進(jìn)程中并未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使人們的關(guān)注點(diǎn)開(kāi)始轉(zhuǎn)變,翻譯文學(xué)受到關(guān)注,但對(duì)它的性質(zhì)、歸屬、走向仍然沒(méi)有明確的界定。作為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中的基本要素,在進(jìn)行具體的比較研究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翻譯文學(xué)與民族文學(xué)的交叉處,容易引起混淆,無(wú)法分清作為研究對(duì)象的異民族文學(xué)是翻譯文學(xué)或是外民族文學(xué)。由此,我們需要理清翻譯文學(xué)的內(nèi)涵和外延,重新界定翻譯文學(xué)在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中的位置,給翻譯文學(xué)以應(yīng)有的學(xué)科地位,使其不再歸屬、依附于其他學(xué)科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