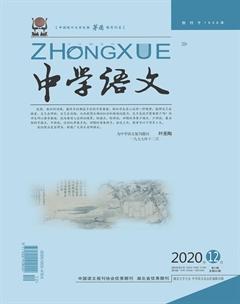記敘文寫作:在“尋常”與“反常”之間
戴啟江
夏丐尊、劉熏宇在《文章作法》中講道:“敘事文的特色在流動、變化。”“流動”“變化”不但是指語言技巧,還指記敘文承轉的方式。在常態的記敘文寫作中,我們常常在單線結構的“承”“轉”“起”“合”中下功夫,“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水。”(元代范德璣《詩格》)但絕大多數學生難以駕馭情節的“跌宕起伏”,普通的故事往往只能“普通”地講述,有時為了應對所謂的“出彩”要求,學生甚至不惜胡編亂造,故事面目全非,人物失真失神,毫無情理邏輯,記敘文寫作徹底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于是呈現了一種以“結果寫作”為寫作方式的教學方式,寫作只要講述故事,并且呈現所要反映的結果主題就可以了,這就導致了“靜態寫作”的泛濫。靜態寫作催生的是一批寫作故事老舊、貼標簽嚴重、缺少故事真正情節發展的記敘文,故事中的“反常”和“意外”都一無例外地被忽略了,而背后丟失的就是學生對記敘文寫作的熱情和信心。
榮維東教授指出:20世紀80年代,“過程寫作”開始進入寫作課程。在歐美等國,尤其是經過“國家寫作工程項目”的大力推廣,“過程寫作法”(Process Approach)與“批判性寫作”“創造性寫作”結合,風靡大中小學寫作課程和教學領域,形成了所謂的“過程寫作運動”。近30年來,經過這場寫作教學運動的洗禮,歐美一些國家的寫作課程和教學知識得以全面更新換代,“過程寫作”成為主流的寫作教學范式。目前歐美已經成功地實施了從“結果寫作”到“過程寫作”的“范式革命”。借助于“過程意識”讓教師了解學生寫作過程的動態變化過程,也能夠呈現學生寫作的程序和寫作脈絡。通過寫作過程的引入,記敘文寫作的過程性變化再一次被提了出來,唯有打破結果至上的扁平化寫作范式,才能夠真正喚醒學生去尋找寫作中的“常態”與“反常”的銜接設置和變化理解,唯有如此,才能在記敘文寫作中調動自己的感性與理性思維的開展,讓記敘的故事跳出一味講述與抒情的狹窄圈囿,能夠進一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生命成長的思考維度。
一、在尋常中把握反常,呈現故事的變化
葉黎明教授在《寫作內容教學論》講道:“寫實性的文學寫作,其教學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寫作內容(主要是情感)的喚醒,側重于喚起、促進寫作者對日常生活經驗與情緒的表達與反思,通過這種寫作認識自我,思考‘我是如何成為我之類的問題。”從寫作的主觀性上說,寫作認識中的反思意識是文章內容情節得以變化的重要原因,從客觀性上說,就是要發現寫作的故事之中曲折、沖突和變化的地方。由此主客觀結合,借由寫作故事中的反常變化,推及自己的寫作思考、獨特感受,來推動情節的進一步發展變化,繼而呈現故事的波瀾,推動抒情的更深一步。一般來說,學生記敘文多半選擇的是瑣碎平常的生活,由于過于熟悉而造成的“熟視無睹”或是“審美疲勞”現象十分常見,帶來的結果就是故事滑行向前,根本不會在意熟悉的故事里可能生發的變化以及背后值得思考的地方。如葉黎明教授所言,如何在“寫實性的文學寫作”中,讓學生對日常生活產生不同的審美興趣并獲得別樣的審美的情感體驗,在尋常的故事講述中把握反常的細節,來呈現故事講述的變化。下面以學生作文《迷信》為例。
外婆大概能說得上是有點迷信的人但是還沒有到向神明祈求治愈重病或者是財運亨通的地步。她有一個小口袋,專門用來存放一角硬幣,以備觀音每年三次的生日。每個月的初一、十五不吃帶成味的東西。我雖然對這樣迷信的事情不喜歡,卻也實在佩服外婆的自律,幾十年來從不遺忘和間斷。
她是一個這樣好說話的老太太,每每電視里、報紙上出現網絡暴力的事情的時候,她總要長嘆不止“風涼話說不得,老天都看著呢,當心有一天啊,風水輪流轉……”這是她說的最多的話。印象中的她從不發火,只有在家里的孩子浪費糧食的時候,她會重重地摔碗“作孽啊,這不是要天打了嘛!”只是因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她才時刻提醒自己,告誡晚輩,珍惜眼前,也善待別人。
每逢重大考試,她總會起個大早,去惠山頂的白云洞,她說那里供奉的是文殊菩薩,能保佑家里的孩子學業有成。我總會說:“那大家都去拜,全中國不要建滿清華北大才行,不然不是折了菩薩的面子啊!”外婆的回應是:“有些人,心不誠,菩薩明眼一看就知道,當然不會幫他們。”終于有一天,中考失利后我回家嚎啕大哭,不明就里的外婆剛從外面回來,開口就是:“妞妞,外婆給你求來了高中狀元簽……”話音未落,我再也忍不住壓抑的火氣:“人家外婆會知道把孩子送去補習班,你就只知道找菩薩,現在我考這么差,書都沒得念,你去問菩薩應該怎么辦……”我滿臉淚痕一口氣說完,外婆就愣在了那里。
不知過了多久,她才離開。直到天色很晚很晚才聽到屋外小腳傳來的輕微的腳步聲。
尋常的故事情節設置會沿著外婆的“迷信”一直講下去,寫外婆迷信的善良,對子女的關切與疼愛,故事自然順暢,寫出孫輩眼中的外婆形象,我們也能夠通過這些細節感受到作者的寫作素養。但是這樣的故事明顯缺少變化,缺少通過故事情節的反常來構造人物形象的轉變,故事的平面化帶來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不夠豐滿的缺陷會因此比較明顯。所以較為自然而又令人驚喜的是作者對情節變化的把握:在我們的生命成長過程中有沒有可能永遠一帆風順、波瀾不起?幾乎沒有。于是情節變化處自然就生出了“迷信”無用了該怎么辦?當然,處于困境中的自然是外婆。
家人問她去了哪里,她低頭喃喃自語,像是做了壞事的孩子:原來她去菩薩那里懺悔,責怪自己不夠誠心,有兩年因為生病缺席了菩薩的生日,希望菩薩能夠再給她孫女機會……那一刻全家人都沉默不語,而我哭的更加傷心了。
很多年以后我更加清楚那一天之于我的意義:為什么想寫外婆的故事呢?因為外婆老了,也因為有天我也長大了。我想起過去時常用學到的不多的知識去鄙夷外婆這些迷信的做法,認為她不過是思想落后的自我安慰。其實大可不必。中國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人,因為他們心中的神明,走向自律,懷揣真誠,生活才有了溫度。
我甚至有時候這樣覺得,這并不算是極端的迷信也許也是某種生活的智慧。等我老了,也想做一個外婆這樣可愛的迷信的老太太,以她的方式庇佑著她的孩子們。
故事一波三折,我們都會以為迷信的外婆在不知所措之中也會懷疑神明的真偽,但是她卻用更加虔誠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懺悔,渴望彌補的真誠。而我的成長也是行文變化的一大亮點:我在很多年后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一個人生道理,每個人都會有思想寄托,重要的是這樣的虔誠在于祈禱家人康健、日子和順,那么即便是迷信又有何害處?更重要的是隔著長遠的時間河流,我對外婆的理解和敬重日益深厚了起來。甚至自豪地相信外婆的迷信是一種生命的可愛,虔誠的姿態是生命的美好,繼而過渡到我自己的未來人生態度的選擇。故事波瀾起伏,帶人走向更廣闊的生命理解,也因此賦予了文本以感性和理性交織的生命力。
美國寫作研究者杰里·克利弗認為:好的故事包含三個要素:沖突、行動、結局。一個人遇到一個難題(沖突),他必須努力奮斗(行動),于是他成功了或者失敗了(結局)。沖突一旦解決,故事就結束了。是沖突推動了許多事情的發生,是沖突讓故事發生了種種變化,總之,沖突使故事產生出各類效果。克利弗把故事寫作知識做了簡化處理,簡化為“沖突”這一核心知識。因此,在尋常的故事講述中如何巧妙發現并且建構反常的情節,繼而構成故事敘述的沖突,是記敘文寫作的密碼,也因此帶來了學生情感和思考的轉變與升級。
二、在反常中思考,培養思辨力
高中記敘文的寫作目標是不是還如初中階段一樣只講求“具象”和感性的文采即可?顯然,這樣的教學目標已經遠遠落后于高中階段的寫作要求。鄧彤教授在《基于核心素養的寫作教學范式轉型寫作教學》中強調:作文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寫作學習者的發展為出發點。側重引導學生直面豐富復雜的生活,努力通過寫作學習,進而通過寫作思考、記錄或者影響生活,這樣的寫作教學能夠最大限度地培育學生的“社會參與、自主發展、文化修養”等核心素養。提醒學生保有“文章為時而作”的寫作姿態,要求學生積極思考、認真分析社會熱點問題。即便是故事寫作,高中階段也不應該滿足于故事講述的初級階段,應該思考故事為何而講,所講為何。通過對所講故事的理性思考,正確辨析故事講述的意義、價值,更好地利用故事情節的沖突變化構建自己的思辨的意識,形成獨立思考、獨立寫作的能力。
提到記敘文寫作中最為常見的一類題材“鄉村寫作”時,很多老師應該都有一種相同的感受:無論是有還是沒有鄉村經歷的孩子,都會虛構出一種時代變化、鄉土易容、人事變遷、美好不再的悲傷感。借助于這樣的故事營造流離失所、文化不再的濃郁感傷氛圍。不可否認,這樣的寫作易于生發感情,這與前兩年社會上影響很大的王開嶺等作家的《古典之殤》《江河之殤》《一個村莊里的中國》等等作品的感染也是密不可分的。下面以一篇常見的鄉村類作文為例。
離家還有幾站路,我卻著魔似的下了車。
下雨了。天地一片朦朧。我輕輕踩在小路上,手中的傘不愿撐起,怕打擾了這纖巧的舞蹈。只好跟隨著雨點的足跡,緩緩前行。原來人跡罕至的老街,也在雨的呢喃聲中,睜開了惺忪的睡眼。
江南是雨的家鄉。屋頂的瓦片是雨的溫床,也是雨的舞臺。潺潺而行的小河是雨的畫紙,雨是懂國畫的,烏篷船和青石臺是她揮毫的驚世之作。她在畫紙上渲染、浸濕,構成了江南仙境一般的美景。
老街的回憶也是雨編織的。記憶的碎片中有著劃水的槳櫓,有著石橋的倒影,有著采蓮女的繡花鞋,有著搗衣人蕩起的水花。雨在瓦上流淌下,在瓦尖打了個圈兒后欣然躍下。老街的巷子是在雨聲中,我聽到了荷葉的搖曳聲,聽到了歡笑的嬉戲聲,更聽到了雨中心底的回響。
曾幾何時,這些都隨流水徜徉而去。留下的只有雨聲。只有雨,寂寞地守著老街。世界對于雨越發地難以融合。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樓,一輛輛嶄新的轎車吐著煙霧,一幅幅光怪陸離的宣傳畫,一個個面色冰冷凝重的行人。這些,雨是融入不了的,只好回去守著回憶。
雨是自然賦予大地的精靈,但是,精靈在哭泣。因為人類的麻木和對希望的遺忘。
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拋棄了哺育我們的精神家園,又換回了什么?人類記憶中的美麗,又去了哪里?
我們已經習慣遺忘,遺忘碧綠的森林和清新的早晨,遺忘了真情的觸動和追求夢想的狂熱,遺忘了大自然,遺忘了自己最真實自然的生活。我聽著雨水嗚咽的哭泣聲,心頭只有無名的沉重在不停地回蕩。
雨漸漸地大了起來,我走出了老街,雨也沖走了我對老故事的回憶。我面對著紛繁嘈雜的馬路,雨水不停地拍打在我的臉上,我仿佛游離在世界之外。雨給了我一個選擇的機會。是要這嘈雜,還是要雨聲。而經歷了剛剛一番思考的我,答案不言而喻。
我仍然慢慢地沿路走著。期盼著雨下得大一點,再大一點。
雨,依然下著。而我,卻找不到回家的路。
當社會呼喚一種文化關切的時候,切莫我們也盲目地跟風寫作,最終變成一種狗尾續貂式的拷貝和續寫,這樣的寫作本質上是一種思維的抄襲,大行其道的是無思想、無自我的鼓吹。如陳興才老師所言:“許多教師、學生和擅長憂傷的作家們在共同構筑一種以悲憫為表象的,實質上是以美化原始鄉村的文藝筆調來滿足城市文明者自私的心靈需求的表達——大約相當于,過慣了浮躁喧囂的城市生活,希望有那么一個沉靜的鄉村,擺脫塵世,歲月靜好,永遠存在;看到她被打擾,變得熱鬧,心生惋惜。這種文化悲憫,說得尖刻一些,也是一種文化自私,以自我需求為中心,其實只不過它不是物質上的占有和需求,而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并暗示自己,這是一種高尚,是一種文化人特征,可算是一種文化優越感引發的居高臨下的同情。”
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農村的消逝固然令人痛心,但是消逝的是農村的全部還是農村生活中的某一種令人魂牽夢縈的美好?我們懷念農村的風土人情——那是建立在炊煙裊裊、生活富庶、民風淳樸之上的,那么多的爭執紛亂、鄰里斗惡又怎么能被忽視呢?我們懷念農村的山清水秀——那是建立在美好的鄉土風景修飾之上的,哪里有那么多山清水秀的農村呢?田塍橫貫自然是有的,小河傍家也是常見的,可是并不是河水透徹,溪水甘甜,農物毫無公害。甚至我們希望終其一生永遠依戀的江南小巷,也會因為我們走入城市發現它的逼仄狹窄、難以生活,風雨天氣里的晦明不分,潮濕冷寂,這些都不能成為一生永遠生活的幸福的土壤。我們抒發的是混凝土與鋼鐵讓城市人失血,無比的寂寞與精神的荒蕪,渴望找到寄寓之物,然后,不約而同地把向往與婉約之情獻給那個遠離城市的所謂質樸的鄉村。如陳興才老師所言:“由此發端,就有了與之同胞的‘鄉村原味癖,青苔,斷壁,雜草,土食,小屋,無車馬喧鬧的村落或山鄉,成了現代人懷想的地方。”我們不能任由這樣的慣性成了思維的套路。不能因為沈從文的《邊城》就交織著我們筆下的農村就是湘西;不能因為旅游之中短暫的鄉間游歷,就認為所有的鄉村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珍品。鄉村,不可否認的其實一直是個落后的存在,她之所以真切動人,是因為它承載了我們很多美好的回憶、很多精神的掛念、很多最美的美化。失去了反思的意識,沒有理性的思考與批判,那么文字再優美,也難掩其婉麗中做作、虛浮的本質。
三、由反常走向正常,回歸理性精神
吳格明教授在《理性:語文課程改革不應缺失的價值坐標——語文課程改革的深度反思》一文中談道:“語文課程改革張揚人文精神與理性并不是相對立的。人文主義有四個要點:1.肯定人的價值、特性和理想。2.反對宗教教義,注重人的現世生活。3.主張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反對封建等級觀念。4.推崇人的經驗和理性。而這些要點,均與人類理性密切相關,或者說均以人類理性為基礎。人文主義的核心就是張揚人類理性。倡導人文主義而進行文藝復興,本身就是理性反思的輝煌經典。誠如于桂芝、安啟念所說:文藝復興運動。它把獲得理性生活、爭取自由平等、追求人的尊嚴和權利視為崇高的價值,實質就是對人的理性的高度弘揚。”因此,寫作中表現出來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一味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愛與善,更不是未經任何省視的愛與憎,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應該是理性的精神內核。我們常常評判一篇優秀記敘文的重要標準之一是它的感情抒發是否豐富與深刻,卻不曾思考“豐富”意味著走出單一的思維陷阱;“深刻”本身意味著一種反思理性。
鄭和鈞老師把高中生的心理特點概括為“五性”,幾乎都指向高中生的“自我覺醒”:自主性,自我意識的明顯加強……前瞻性,迫切地追求自我實現……進取性,富于進取……社會性,思考的問題已遠遠超出學校的范圍……正是因為這樣的“理性思維”的覺醒,才讓高中作文更顯其深刻特點,告別初中記敘文記敘抒情的淺表性寫作,更能呈現出故事中的理性思維的精神回歸。從記敘文寫作的故事講述而言,“沖突”“變化”不只是一種“技”,以帶來故事講述的“反常”效果,“反常”的背后是思考的銜接,是理性思維開始生根的契機,但是最終依然要指向的是人的生命的成長。如果我們停留在“反常”上有所思而無所得、無所解,那么這樣的“反常”可能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虛設,而非寫作上的積極有效的嘗試。下面以一篇寫親情的文章為例。
在這一刻之前,我還未來得及體會那種徹骨的悲傷,直到觸碰到真正的冰冷,我一瞬間淚如雨下。
外公在我的印象中是個高大的人,好像我也只能形容出高大這個形象。因為我和他的接觸太少了,加之他的寡言,以至于我聽到消息的時候除了一瞬間的不知所措竟再無他感。
送別故人已經被一套標準化流程所規范,以至于我像個木偶,一步一步做著我該做的悼念。猶然記得我初次直面那具冰冷,心里慌亂,但我表面平靜,一旁的舅舅笑著對我說,“別怕,外公只是睡著了。”微微一愣,我想我該安慰他,可他在笑著,我的悲傷無處言說。
葬禮有三天,外公一直在大堂中,但我也一直不敢靠近,不是恐懼,而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感覺。我站在窗戶邊,向樓下看,看到舅舅笑著迎客,他讓我看不出父親的逝去該有的悲痛,我曾疑惑不解,難道他父親的離世沒有給他任何一絲悲傷?更多的是一種世俗和責任。母親一直在哭,她的支柱,她的庇護沒有了。那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別離。至今我猶記得母親悲傷到極致時的一句話,“我再也沒有爸爸了。”這種絕望無從安慰。
這樣的悲傷在我心里才是正常的,相比舅舅的冷靜,母親才能讓我感受到該有的情感。愛與不愛,深不深刻總要有一個發泄口。
行文到此刻,我們能夠感受到故事的內在張力:舅舅與母親愛與傷、痛與笑的矛盾;我的不解與疑惑,甚至舅舅身上的反常,都織成了一張網,網住了世俗人情,網住了愛恨情怨,在這樣的矛盾沖突中呈現我感性上的困惑與不解。伴隨著思考帶來的解惑是本文得以深刻的前提,從感性的哀傷探討背后理性的分析是作者生命成長的重要方式,唯有如此,文章才能橫貫感性與理性的兩側,走向一種自然的升華。
那一個夜晚,帶著一種月亮的明亮,在這種明亮中外公要出殯了。舅舅舉著牌位走在人群的前端,火葬場一進一出,外公就真正走了。在外的等待是漫長的,這里除了悲傷就是無言。良久,舅舅是被人扶著出來的。
那一刻,我有些疑惑,他不是不悲傷,只是強忍著?
我和母親在散步,頭頂的星星很多,閃耀著無限的希望。母親說外公也一定在里面。我問母親舅舅怎么能做到笑著迎客辦喪,母親說因為他想好好的送外公最后一程。他必須笑著面對這一切,因為這就是生活。生活不是一面真正的鏡子,鏡子能映出你的哭與笑,但鏡子看不到你內心的傷與痛,而生活可以。舅舅是這場葬禮的支柱,如果他把悲傷彰顯無遺,那誰來支撐?他必須笑著面對,因為就算你哭,生活也回不到你期望的樣子。一切塵埃落定,不顯山不露水的悲傷一觸即發。舅舅也許比母親有更深更痛的感情,但葬禮上的舅舅就已經不再是外公的兒子那么簡單的身份,這個男人的悲痛比誰都要深刻,深刻到令所有人揪心。但他身上有著一種世俗人情和責任堅守的要求,感情的崩塌卻依然憑借著理智的堅持,讓他擔負起長子的責任。子送父,中國的傳統所給他的責任和義務,他絲毫不動地支撐到最后一刻。
所有的不解,在這一刻化為煙云。“謙恭孝悌”“人倫常理”何嘗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得以富庶安民的前提和保障?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中的忠孝沖突都在考驗著人們的感性與理性交織的勝負,難能可貴的是文章通過“痛與克制”“兒子與家族”等不同情感、理智、身份上的對立去呈現“舅舅”豐富的形象,通過這樣的反常與沖突,我們看到一個“正常”的“兒子”“舅舅”“主持法事的男人”,唯有將這些身份對立統一起來,才能更好地通過這樣的故事去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下的長子形象。當然,故事最成功的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作者的成長,他經歷了“反常”的講述走向了“正常”的理解,并借此獲得了自身的成長。這樣的成長不是一味感性上的接納,而是伴隨著感性的明了,獲得了理性上的接受與成熟。我們在寫作中所倡導的人文關懷,同樣也是出于理性的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和愛。如吳格明教授所言:“一個理性淡漠的人,不可能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不可能有凜然的正義感和深刻的民主精神,也不可能有追求和堅持真理的高尚情懷。更不可能有思考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只有具備健全理性的人,才能自覺地追求真善美,才能有高尚的價值觀和博大的胸襟。”
[作者通聯:江蘇無錫市輔仁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