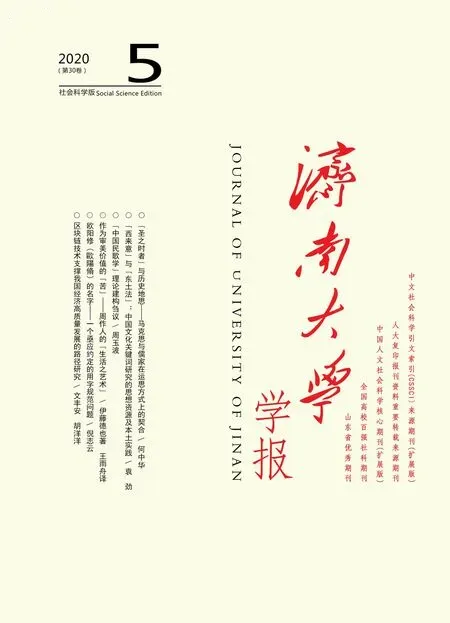教學技術的價值悖論及其人文規約
付 強
(濟南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22)
在科技盛行的現代社會,技術滲透在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人的思想、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二十世紀起,人類社會就進入了“第一個以技術起決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確定的時代,并且開始使技術知識從掌握自然力量擴展為掌握社會生活,所有這一切都是成熟的標志,或者也可以說,是我們文明危機的標志。”(1)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頁。從本質上來看,“技術”所承載的已不再只是單純的改造自然的工具,而成為我們當今的一種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甚至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人的存在方式。可以說,“技術也許是理解我們當前處境的主題。不能低估現代技術的侵入及其對全部生活問題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2)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頁。現代教育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技術的影響。一方面,各種先進媒體和信息技術介入到教學中,甚至不斷的融入到教學生活中,深刻影響著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生關系。從另一方面來看,技術化思維日漸成為教學活動的主導思想,教學的技術理性占據了教師專業化發展的重要位置,教學世界中的人們生活在這個看似無形卻又無所不在的技術之中,我們在享受著技術的便利和效率同時,卻忽視了技術給我們的身心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教學技術的價值悖論釋義
在技術學中,技術悖論(technological paradox)由法國學者圣·塞尼(M·B·Saint-Sernin)提出,他認為,“技術在作用于現實社會時,一方面服務于它所要實現的技術目的,同時又以本身的性質來改變現實,產生與技術目的相對立的技術后果。”(3)錢學成,喬寬元:《技術學手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頁。反觀教學技術,教學技術源自提高教學活動效率,體現教學思想的操作流程以及工具、手段、方法,但教學技術的應用又會偏離教學的本真意蘊。正如拉普談到的技術活動悖論一樣,“這些活動在細節上是合理規劃與執行的,但作為整體,這些活動及其后果與它們的發起者無關,從而表現為一種異己的力量。”(4)G·羅波爾:《技術決定論批判》,《科學與哲學》,1986年第6期。對于教學技術的應用來說,教學技術悖論就是指教學技術在服務于教學效率、解放教學中的人、解決教學問題等目的的同時,教學技術又反過來影響著教學生活,產生了違背教學技術目的的后果。
雅克·埃呂爾認為,“技術的不良后果與有益影響是不可分離的,隱含著無法預料的后果,一切技術進步都是有其代價的;技術提出的問題要比它解決的問題更多。”(5)J.Elull,The Technological Order,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3,p.132.教學技術同樣也具有不可預知的一面,教學技術既影響教學主體追求的目的,也影響使用這些技術的人。教學技術給教學活動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不僅改變了教學方式,影響了教學感受,而且改變著教學主體的思維方式。“技術的最直接和最簡單的表現形態是技術產品。這也是人們將技術的本質簡單化為工具性,并從而得出技術中立性的認識論來源之一。然而,如果我們將技術活動放入“社會—技術”系統的框架下,就會發現,技術產品不僅通過幫助我們認識世界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思想和活動方式,而且也因為其獨特的功能直接地表達和體現了我們的活動方式。”(6)王國豫,胡比希:《社會—技術系統框架下的技術倫理學—論羅波爾的功利主義技術倫理觀》,《哲學研究》,2007年第6期。教學技術往往關注提高教學的效率問題,卻忽視教學過程對于人的意義問題,先進的教學技術與教學意義、教學價值隔離開來,導致教學技術與教學的人文意蘊日益分離,如果教學技術的發展失去了教學價值的導引,那么將造成技術理性不斷膨脹、價值理性的逐漸失落,所以,在教學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為人的教學自身面臨著種種困境。
二、教學技術的價值悖論表現
教學技術的價值悖論與教學的意義和價值密切相關。教學技術服務于教學實踐,教學技術的價值實現與否都要由教學的價值體現與否來判定,技術下的教學意義與價值最終要落實到人的層面,從教師的主體地位、價值理性、教學意義等層面上,我們對教學技術的價值悖論進行梳理和剖析,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解放與控制
技術是必然的秩序和確定的過程,技術的效果是反對行動自由的。按照技術理性的一般邏輯,標準化和定量計算意味著專業合理,但其后果是造成超驗價值體系的崩塌,也反過來僭越了人的經驗感受的具體內容。教學技術在使得教學表現為專業化、現代化的同時,教學也陷入了程式化、去經驗化的困境。教學技術的目的性、規范性、程序性、可控性等工具理性與教學自身的多樣性、特異性、開放性、生成性等人文性相沖突。教學的豐富意義被抽取掉,師生在毫無生氣的課堂中感受不到思想的快樂,剩下只是知識的分解、操練和堆積,技術下的教師更多的失去了自身的獨特性、教學個性和教學自由。其根源在于技術本身具有的內在規范性。技術行為的作用在于盡可能合目的地介入有關系統的運動之中,并以根據技術方案組織起來的有計劃的程序取代技術過程。
教學不是技術可以決定的,但是現代教學的技術化、技能化表明,教學生活實質上已經托付給了教育專家系統,被整合進專家系統所設置的教學行為和方式中。“教學技術統治理性與工具理性,也在教學領域自身中發生作用,并且日益嚴重地降低教師在課程的開發與計劃以及課堂教學的決策與實施方面的自主性。”(7)亨利·A·吉魯:《教師作為知識分子—邁向批判教育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1頁。日常教學生活中的許多知識和經驗被程式化、概念化,成為教育專家的專門知識,專家系統通過專業知識的生產與運用重構了教學生活。此外,教學技術權威性背后是具有技術話語權者的價值觀。技術對教學系統的全面控制意味著專家系統對人們生活的全面接管,普遍統一的、標準化的科學知識逐漸取代個體的經驗知識,并不斷轉化為統一化的教學方式和教學環節。絕大部分教學技術掌握在少數專家、學者手里,“在這里,高居于認識能力頂峰寶座之上的,不是靠良心和經驗從事自己職業的‘專業人員’,而是‘專家’。專家被認為能夠根據自己的知識做出恰當的診斷,而他的知識僅僅是計算性的和嚴格專業化的知識。”(8)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 生境、生命、習性與組織》,秦海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學理論工作者的追隨者。長期以來,教師與教學理論工作者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地位上,他們之間的交往日益呈現出表面化、功能化、功利化傾向。而教學技術中的教師“往往被看作科學控制的一般對象,……教師處于無權的低層地位,只能被動地聽從管理者、課程論專家、教材編輯者和大學教師的指導,自己的意見無足輕重,從而導致自己的形象毫無專業意義。”(9)胡福貞:《論教師的個人話語權》,《教育研究與實驗》,2002年第3期。
教學技術中的專家化現象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也是教學科學化的必然。“技術理性的工具主義、實證主義、單面性、功利主義以及對現實的順從態度等特征使它自身成為統治的工具,成為意識形態。”(10)李桂花:《科技哲思—科技異化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馬爾庫塞認為,“抽象的技術理性已經擴展到社會的總體結構,成為組織化的統治原則。”(11)陳振明:《法蘭克福學派與科學技術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在技術思維形態下,教師淪為技術產品的“消費者”,喪失了對技術的批判與創造。一定程度上,教師自我的困惑、主體性的喪失,使教師失去了個體性,成為教學的工具或機器。在這層意義上,教學技術就成為了一種“單一技術”,它是服務于效率優先的、專家主義的技術。當我們有意識的反思若僅限于教學活動的技巧方法,則是遠遠不夠的,尚未觸及教學的意義或根本價值所在。
(二)高效與失效
馬克斯·韋伯認為社會生活的問題都源于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對立與張力,是同一社會實踐活動的不同側面。工具合理性往往關注的是手段對實現特定目的的效果,而不關注其背后的終極價值,注重的是解決手段而不是手段、目的的價值意義。與此相反,價值合理性是在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對價值及其追求的自覺意識,是“人類所獨有的用以調節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為的一種精神力量”(12)吳增基:《理性精神的呼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可以說,工具合理性的技術手段是排除終極價值判斷的,價值合理性的技術則是以價值判斷為前提的。正如現代科學只是關心那些可以衡量的東西以及它在技術上的應用,而不再去問這些事物的人文意義,只問如何運用技術手段去工作,而不去關心技術本身的目的,從而產生出被扭曲的科學(13)詹頌生:《科學技術的兩個關懷與兩個限度》,《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3年第1期。。當我們以“效率”為發展技術的首要標準時,我們要追求的終極目的往往被對“效率”的無限制追求所遮蔽,“效率卻是一種普遍的價值并且本身就服從于理性的一致性。而且隨著對效率的關注蔓延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它為社會生活提供了一個強制性的框架。”(14)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陸俊,嚴耕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頁。“高效”的技術就會僭越存在的意義,技術追求就成為人類的絕對價值訴求本身。
在筆者看來,在教學技術發展中存在著上述同樣的問題,教學技術關心的是什么樣的目的是能夠實現的,以及怎樣達到這一目的。教學技術以技術方法、手段的有效性為目的,它關注的是對教學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教學“與其說是一種致思方式和生存性活動,不如說它是一種已經技術化了的、科學化了的工具或手段,它已經在方法、技術、制度、管理以至精神方面深刻地打下了科學與技術的烙印……”(15)高偉:《生存論教育哲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頁。教學技術是關心問題、目標,而不是教學背后的價值、意義。如量化是一種對教學的檢查,它所關注的是人的可計量“素質”未來和當下教學的“產出”。“量化的結果不僅使所有的教育方面從屬于技術性的教育方面,也徹底地改變了人們的整個教育觀念,恰恰在這里教育失去了它的本性,曾經從本質的角度加以界定的教育,轉而從考試分數的角度加以界定。”(16)小威廉姆 E·多爾:《后現代課程觀》,王紅宇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頁。在這種以分數作為評價教學質量的衡量標準下,教學就成為某種功利性行為,“當人們參與某種社會性活動,僅僅為了獲取活動之外的利益,那么這種活動可能只是技術性的、工具性的。”(17)王凱:《教學作為德性實踐—基于麥金太爾實踐概念的教學理解》,《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10期。以數量化作為衡量教學質量的唯一標準的同時,教師更傾向于追求各項具體指標而忽略了授課中靈魂性的東西,以及教師本人對教學的價值與精神追求,教學就成為一種純技術的操作。
教學技術的現代化并沒有帶來課堂教學的根本革命,我們在獲取教學技術的方便、高效同時,我們失去了教學的人文意蘊,教學技術的實用價值被放大、夸大,教學技術在一定程度規范和奴役著師生,“技術的建構使人從屬于技術,接受技術的塑造與調制,以獲取技術效益。”(18)王伯魯:《技術困境及其超越問題探析》,《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第2期。這與人們僅僅注重教學技術的工具價值有密切關系,并壓倒了其他價值,教學技術的功用遮蔽了教學中人的價值、地位、角色,在教學技術的工具理性過度膨脹下,教學的價值合理性不再為人們關注,人們關注的不再是教學的價值與意義,而是對教學技術手段價值的功利性追逐。教學不是通過技術的使用和對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增加效率,從教學技術的本質上看,教學技術活動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教學技術除了具有教學的工具、手段價值,它本身就是人類傳承文化、培養人的智慧實踐。教學技術的價值負荷論認為教學技術在政治、文化、倫理上不是中性的,教學技術本身都蘊含著一定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即教學技術負載著特定的社會和人的價值觀。教學技術的工具理性是建立在科學、有效的理念之上,是對人類學習方面的探究,但教學更需要一種人文的價值理性規約。教學技術是精細的操作方法、手段,屬于“科學理性”的應用范疇,如果教學技術的應用遠離了師生的生命體驗、交往,那么教學就會成為一種僵化的科學教條和技術規訓。
隨著教學技術的“目的—工具”合理性行為的不斷擴大化,一旦當目的合理性超越了價值合理性,則表現為教學意義的迷失。技術理性下的教學遠離了教學所崇尚的自由、自主、求是的精神,忘記了教學的真、善、美的品格,教學漸漸蛻去了靈魂喚醒的高尚、純凈,而變得貪求效率、功利。我們認為,人文性是教學技術的內在基礎和根基。正是由于人文性意識的逐漸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與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內在的支撐和動力,使得教學的終極關懷遠不如效率關懷那么重要。教學的技術化發展傾向,使教學出現了方向性偏失,背離教學的本質和目的,使具有豐富意義和無窮生機的教學本真意蘊被祛除。
(三)存在與虛無
正如技術哲學中的實體理論所主張的,技術的應用對人性和自然所造成的結果要遠遠大于其表面的目標。技術對人、文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誠如,“‘快餐’代替傳統家庭的晚餐可以看作是技術的無意識的文化后果的一種簡單例子。每天晚上從儀式上一再得到證實的家庭和睦不再擁有表達的類似場合。沒有人認為快餐的興起實際上導致了傳統家庭的衰落,但這種相互關聯意味著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的出現。”(19)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韓連慶,曹觀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之所以造成這種影響,是我們沒有認清技術的文化涵義。正如在大機器技術時代,技術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技術活動不再是滿足掌握技術的人(工匠、農夫)的自身需求,也不是用來滿足奴隸主和地主的需求,而是最大限度獲取剩余價值的手段。從更深層來看,技術是主體目的性活動的序列或方式,因此,人的技術化本質上就是理性化的過程。我們應該看到,現代教學技術成為當下教學生活正常運作的必需手段,同時也改變著教學生活的樣態,僭越了教學的本性。現代人對教學的定位深深地受到技術理性的影響,教學本質與意義迷失在我們自己設計的教學技術里,教學越來越遠離其本真。
此外,現代教師的專業定位也受到技術理性的影響,對教學本質與意義的理解也受到干擾。教師專業化的發展往往是以教育知識與教學技能的熟練性為標準,專業化的教師被看作是一個“技術熟練者”的形象,專業能力受著專業知識和教育學原理與技術的制約,而教學實踐無非就是知識、原理與技術的合理組織與運用。教師專業化的研究也難以脫離唯技術理性的窠臼,一些研究者對教師專業化發展所需的技能進行了條分縷析的羅列,卻往往缺乏對于當下的真實的教學生活與教師文化的關照,按照這樣的理論來培養教師的專業素質往往收效甚微(20)徐繼存,車麗娜:《教學文化研究引論》,《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7年第4期。。當教學成為一種異化行為后,使教師的內在價值變異、缺失,教師蛻變成單純的“知識”操作工,進而教師的一些非工具性精神活動(如形而上的沉思,信仰及藝術情感等)受冷落,傳統教學中深厚的人文底蘊被徹底消解。教師在教學中的人性內涵被大大削弱,喪失了教師的存在意義,成為“虛無”的師者。教學技術化下的教學成為人“不在場”的講授,教師工作也往往就成為了一種復制他人的過程,教學生活也因此失去了一定的意義和幸福感。
教學技術本身體現了人類對教學活動的科學旨趣,然而教學的人文意義與價值卻不可能由它來決定,教學技術并不能體現對教學終極價值的關懷。“要想關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體,我們不僅需要科學,而且需要倫理學、藝術和哲學。”(21)丹尼爾:《科學史》,李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1頁。教學技術是影響課堂教學師生狀態的關鍵因素。教學技術外在表現為對教學諸環節進行科學的規范和細化操作,教學已被統一在理性化的本質之中,當它成為人的行為規范、思緒定勢時,教學技術也就成了規約人的“隱性”技術,教學中人的精神活動的價值被泯滅,甚至被“貶低為一種技術的能力”(22)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這只會讓教師變成異化了的技工,基本上失去對教學環境的控制權……教師會發現他們的教學工作越來越繁復和越來越具壓迫性的控制(23)華勒斯坦:《學科·知識·權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32-133頁。。
正如技術的烏托邦觀點將技術視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藥”,為人們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片面功利化、片面科學規范化的教學導致了教師的“精神”與知識的分離。教師的教學生活就不再是教師人性的表達,而更多地是在表達著教學技術、教學制度和教學規則,教師往往過著一種“虛假”的生活,教學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亦蕩然無存。“教育本身在教學技術的操縱下成了一種非生命的形式。現代教育是技術形式的,而非生命形式的……在教育無所限制地從屬于科學與技術之際,教育也就將‘生命’形態交付于技術形態。”(24)高偉:《生存論教育哲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進而,教學生活意義的真實意蘊被遮蔽。當下職業專業化和價值世俗化使教師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甚至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對教學的評價和對教師的認可也傾向于從教師的專業知識、教學技能、學生的課業成績來判斷,并將評價指標最大程度地量化、標準化和程式化,而對于師者的品格與德行的重視程度卻有所淡化,教師的權威性不再僅僅依賴于德性的支撐,教師教化天下的飽滿熱情和知識分子的神圣使命感被消磨殆盡,其價值取向開始趨向于世俗和功利(25)陳思:《論教學認識的嬗變與反思》,《教育理論與實踐》,2012年第4期。。
當教師以教學技術來不斷消除教學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在獲得教師專業化的自我認同感的同時,也是充滿了矛盾的,一方面,教學技術對教學世界的描述與控制讓教學過程變得可知可控,但是另一方面它與傳統的生活知識體系相比,顯得更加單一和抽象,它并未把握教學的全部本質,反而抽掉了教學世界本有的其他意義和價值。正如馬克斯·舍勒談到的,“世界不再是真實的和有機的‘家園’,不再是愛和沉思的對象,而是變成了冷靜計算的對象和工作進取的對象。”(26)馬克斯·舍勒:《知識社會學現象》,艾彥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教學對象成為可量度、可計算、可預測的“物體”,這種對教學過程的技術化控制、管理,帶來了規范和高效,但作為代價,教育為人的發展本命卻被扭曲。其結果,雖然功利化的工具理性提高了教學效率,但同時也使教學活動喪失了人性的光彩,甚或使教師在教學技術中將喪失人之所以區別于機器的本質屬性。
三、教學技術與人的關系規約
雅克·埃呂爾認為,提出技術問題的可能解決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人們的出發點必須是現在的情境。回到過去的逃避不過是逃向夢幻之地,不會有改變的機會。而當下社會又是如此打上技術的烙印,以致我們不知道怎樣擺脫它,以便去判斷它,以便能夠最終對技術有所限制(27)E.舒爾曼:《科技文明與人類未來—在哲學深層的挑戰》,李小兵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解決教學技術悖論的路徑不是回避教學技術,而是將教學技術與教學中的人協調一致起來,兩者的關系不是對立的,教學技術是教學中的人使用的技術,即技術作用的顯現離不開人的作用。當教學不斷依靠技術來進行時,教學就已經和技術融為了一體,離開技術的現代教學是不可想象的,而用新技術解決教學技術的問題途徑必然會帶來更多未知的影響。教學的返樸歸真與技術的拯救不是同一進程,可以說,教學的返樸是教師人性力量的重現,而技術的拯救就是依靠技術的發展來實現教育的目的,用新的技術來彌補技術的異化。我們要解決技術中的教學困境,就是要發揮教學技術中人的智慧與力量。
(一)發揮技術中教師的主體性
教學技術的實施不能完全遵從科學理性,要確立人在教學技術中的主體性地位,簡單的制度規范和約束,不是解決教學質量問題的關鍵,更重要的是真正把教師解放,指導他們進行教學創新,變革教學理念,真正調動起教師的自主性、能動性。而我們往往在教學中,失去了中心,迷失了方向,將教師作為教學的機器人,“把教師設定為預定生成程序與技術的執行者,而不是作為具備理論意識和理性能力的課程變革主體”(28)程良宏:《生成性教學技術主義傾向批判》,《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5期。,忽視了教師應有的人格魅力、智慧情感甚至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品性。教師的主體性得不到展現,體會不到教學的幸福感、成就感,在教學技術的應用中,教師與教學技術的關系趨于疏離,教學具有很大的惰性往往就不可避免。
技術所展開的每一種可能性空間,都必然會遮蔽和遺忘更多的可能性,使豐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單一化。教學技術的標準化、數量化把教學中的人的整體精神發展變成了呆板的機械性變化,剝奪了他們的自主精神,使其完全淪為教學行為的附屬品,他們的個性、自由、責任等則為教學技術所抑制,他們的意愿、興趣、情感和態度等也被教學技術遮蔽起來。因此,作為生命的個體體會不到教學的幸福感。在現實教學中,由于受到種種外部因素的制約,教師的教學行為在既定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手段等教學技術的作用下,在知識的傳授上具備了一定的教學技能,成為熟練的、優秀的職業教學能手,這可以說是一名職前教師快速成長為專業化教師的必要過程。他們經過教學技能的專業化訓練,在對學科知識理解把握的基礎上能進行“大綱式”的標準嫻熟講解,但作為“為人”的教師的實踐智慧、教學活動的人文意蘊和人文價值難以有效顯現,教師往往淪為可任意替換的“角色”。
在專業化分工中,“每一種工作都有一個附屬的綱要,它精確規定了要做什么工作,怎樣做和何時做。每一個了解這個綱要、精通本項工作需求的技藝的人都能完成它。”(29)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倫理學》,張成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2頁。在這樣的技術化操作中,教師僅僅是一個“角色”,而且并非不可替代。教學成為規范的操作流程,個人不可避免地“服從”于權威,“順從”于集體性的程式化教學中。正如雅斯貝爾斯談到,“本質的人性還原為普遍的人性,還原到作為功能性肉體存在的生命力,還原到瑣碎的恣情享樂上。勞動和樂趣的分離剝奪了生活的可能的嚴肅性。”(30)雅斯貝爾斯:《現時代的人》,周曉亮,宋祖良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教學技術的運用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教師在教學技術活動中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教學技術的價值體現在本質上就是人的價值實現過程。教師是真正在充滿不確定性、價值性、多變性的具體教學場景中進行教學實踐的主體。教師的專業成長是一個漫長而又復雜的過程,只有喚起了教師內心的真正行動意愿,激發起學生學習動力的教學,才是教師專業良性發展的價值所在。
如果我們無視教師在課堂中應有的自主權,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把教師的工作置于管理者、督導和研究人員的控制之下。教師不同于律師、醫生的職業群體,律師和醫生主要是以個體的方式提供專業技術服務,而作為培養人的教學離不開教師群體的努力,是以集體的方式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需要如此緊密合作的工作環境下,必要的溝通和協作是成功實施培養人的關鍵,而決定教學行為的關鍵是教育價值觀,不同的教育價值觀會導致教學行為的分裂,這就需要教育價值觀的認同教育。而我們所一直沿襲下來的教師職業技能訓練只是一種教學行為的強化練習,而忽視了教師對于教學價值、教學意義的反思教育。依附型的教師職業觀教育抽掉了教師職業的基石,消解了教師的自主性。在技術的制約下,我們往往在使用教學技術中將人放置在被動的地位,教師的教學成為去主體意識的機械行為,其應有的教學主體的理性自覺和理論批判能力被日漸消解磨滅。
要激發教師使用教學技術的能動性,而不是成為技術的附庸。基于現代教學技術的教學,相比于傳統教學,教師面臨更大的挑戰。現代教學技術的應用,意味著教師與教學慣習的決裂。通過借助教學技術,可以使得教師轉變過去的知識源角色,成為學生的學習指導者、學習伙伴。更重要的是教師能主動利用教學技術,養成較好的教學技術素養,即能夠理解先進的現代教學技術,能夠促使他們愿意接受和采用現代的教學技術進行創新,并且有能力將教學技術熟練的應用到學科教學中。教師利用教學技術進行教學系統設計,增強學生的學習體驗,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同時,教師運用技術提高教學工作效率,促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實現教學技術在提高教學效率的同時,既能體現教師的育人價值,張揚教師的個性,又能保證教學技術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服務。
教學技術要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重視教師這一實踐主體的能力和素質,重視教師在教學技術中的能動作用。所有的教學技術作用實際上都是教師的作用,是通過教學技術作用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教師的作用(31)徐繼存:《教學技術化及其批判》,《教育理論與實踐》,2004年第2期。。可以說,教學的人文性在實踐中表現為個體主義。只有為人的、有靈魂的教學,才是人的教育成長之路。教學活動是一種人與人的交往、對話的實踐過程,教學的為人目的決定了教學不僅僅是熟練施展教學技術的過程,勢必要滲透著教學主體的情感、理念、道德、價值觀等因素。
(二)展現技術中教師的存在價值
在技術哲學中,技術的人文性發展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焦點。正如弗洛姆研究技術人道化的目的就是要喚醒困境中的人們,擺脫對機械和技術的盲目崇拜和依賴,重新建立對生命的熱愛和對自由的追求。弗洛姆的技術人道主義就是使人相信人的目的是造就自己,而達到這一目的的條件是:人一定是自為的人( man for himself )(32)劉敏:《技術與人性—弗洛姆技術人道化思想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弗洛姆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人道主義倫理學,促成一個健全的社會,健全社會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的全面、健康、自由的發展。在對技術社會的改造中,技術人文主義學派、技術批判理論學派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他們在對技術進行人文化呼吁的同時,揭示技術在政治、文化上對人性的統治和奴役,他們認為科學技術被進一步作為價值理性來主導人的生活,一切符合技術合理性的生存方式被認定為一種合理的生存,這就使人生活在嚴重的異化狀態之下,逐漸喪失了理性批判的能力。為此,他們通過批判反思來喚醒人的“存在感”意識,恢復人的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從而,重新將機器、技術和整個社會系統置于人的控制之下。正如人文主義者芒福德所說的,技術進步的目標應該是關注人類成長過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只關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類活動的基礎是精神,人類要想在現代技術“巨機器”面前有尊嚴的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給技術,而應該審慎地考慮人類本性與技術的關系(33)向淑君:《敞開與遮蔽—新媒介時代的隱私問題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頁。。技術背后是一種固定的、規范化的行為模式,具有較強的工具理性,正如弗洛姆所說的,那種“對人的替代、否定、控制、強迫和漠視,究其根源就在于技術理性的泛濫。”(34)劉敏:《技術與人性—弗洛姆技術人道化思想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人的作用是教學技術發揮作用的核心力量,忽視、漠視了教學技術下人的價值、地位、尊嚴,忽視教師的個性、自由,漠視學生的興趣、個性發展,技術也就成為了奴役人的物。
展現教學技術中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目的是教學技術理性在施展其組織、管理、改造精神世界的過程中接受教學價值理性的引導。彰顯教學技術的人文性,就是要發揮人在教學技術中的作用,體現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若幾乎所有人成為技術勞動過程的環節,那勞動組織就成為對人之在的疑問。因為對人而言終極之物是人而非技術,應該技術服務于人而非人服務于技術……”(35)卡爾·雅斯貝斯:《卡爾·雅斯貝斯文集》,朱更生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頁。。教學技術的應用要受制于心理、情感、價值等諸多因素,教學技術的應用應該考慮到師生作為人存在的意義和精神訴求,體現在技術中作為人存在的價值和地位。
在教學技術外顯的技術理性目的下,教師是被教學技術所控制約束的操作者,學生不是教學技術的另一作用主體,更成為教學技術的改造物。師生在教學技術中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我們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體現人的價值。在技術時代,人類個體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是某些技術及其工序的對象。正如在現代教學中,以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為載體的計算機教學、網絡教學被認為是自主學習、高效互動的教學組織形式,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成為當前教學改革的新趨向,使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進行教學成為教師掌握現代教學技術的基本要求,不同于信息技術在生產、生活中的高效、自動化等應用目的,教學在信息技術下也變得自動化和常規化,在提高教學工作效率的同時,教師也不斷適應技術的要求,將自己的教學活動簡化成虛擬的對話甚至是虛擬的存在,教學的意義和價值趨于功利。
教學技術對教學本質的遮蔽與對人的支配,使得它本身的工具理性成為一種片面的合理性,尤其是當它成為教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它就轉化為壟斷教學生活的合理性本身。教學技術要在教學活動中體現出人的價值,也就是說,我們的教學技術是沒有生命的,但人可以賦予教學技術人文特性。在精神上達到控制技術,在人文主義學者看來就是重新喚起人們的價值理性和對維護人性尊嚴、人性解放的自覺意識。正如大多數人文主義學者所堅信的,喚起人們對自己生命價值理性的關注和人類命運的最終的人文關懷,就能正確地引導技術的運用和發展,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光明前途。就是依靠主體精神(政治的、倫理的、宗教的)因素來克服技術理性的惡性擴張,同時抵制其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滲透(36)劉大椿:《從辯護到審度:馬克思科學觀與當代科學論》,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頁。。
雖然教師的專業化是以教師職業的知識作為基礎的,具有一定的技術性,如果教學職業不轉化為一定的技術,那么這個職業的現實性和可靠性就足以令人懷疑。但專業化的教師不是單指教學技術的熟練者,只會教書的教書匠,而是在為人的教學生活中,具有一定職業素養,擁有人格魅力,關照生命成長的導師。人性力量在教學技術中的作用,可以說是對教學技術活動的精神性力量。“人性不是一部可以按照固定模式建造,并能精確按照程序工作的機器。人性宛如一棵樹,在內部力量的作用下,充分地發展各個方面,成為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事物”(37)約翰·密爾:《論自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70頁。。作為為人的教學技術更需要從價值層面思考,從整體角度去理解生命、理解成長、理解育人。因此,教學技術的人文性不只是在教學設備、教學設計、實施技術的工具層面,還應提升到尊重生命、關愛人的情感、精神的價值層面。
技術不能體現生命的意義,必須是以教學主體而不是技術作為價值的根源,教學技術的人文訴求,離不開教學中的人的生命意志實現自我超越。教學生活中的師生,“只有當他以自己本然的活力行動時,他才能在當下真正感覺到自我的存在。”(38)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24頁,第44頁。教學過程是師生主體間的交往與對話,滲透著彼此的情感、經驗、態度、價值觀等豐富的人文因素,教學應然的指向教師、學生自身,激發其主體性的意識,實現其價值性。
彰顯教學技術中人的價值,既不是要摒棄教學技術使教學活動回歸原始,也不是要崇拜教學技術,盲目使用教學技術失去理性,而是要提倡教學技術在發揮作用時,使工具屬性與其內在的人文價值屬性之間保持應有的平衡,從而使教學技術中的人的價值得到完美彰顯。教學活動一方面要借助技術來擴展人的能力,同時又要保持自身的價值追求—使人成為人。教學作為一種屬人的、為人的實踐活動,是價值負載的、“用生命點燃生命”、用生命激揚生命的交往活動,它不僅需要教師的認識、思維等理性因素的參與,更離不開教師的情感、態度、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參與。
誠如雅斯貝爾斯所談到的,“真正的教育應先獲得自身的本質。教育須有信仰,沒有信仰就不能成其為教育,而只是教學的技術而已。”(39)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24頁,第44頁。為此,要突破教學的技術化困境,為人的教學就要從這種單一技術觀中解放出來,首先要做的是轉變教學技術是教學的工具手段的觀念,把教學技術放到生活指向的技術—生命技術的背景上去理解,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更深層次上使技術重新服務于人類文化,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教師是教學技術的實施者,只有摒棄“功利化”的技術理性,充分發揮教師的教學智慧,激發教師的生命活力,對學生的發展潛能進行細心呵護,才會是超越技術層面的教學,從而為教學尋找一個意義,尋找一個比教學行為本身更高的意義。教學技術不單單是對知識的呈現與傳播,更關注對教學行為的有效性、可控性、精細化管理。教師對教學技術的有效性追求,已經和為人的教學本身無關,而變成一種極其功利的行為。早在1965年,美國學者費尼就意識到信息時代的教育問題,他們認為,“隨著計算機的時代繼續前進,研究者們的注意最后會轉向教育問題。對教育的注意是信息時代的時代精神的另一個方面。”(40)普萊西:《程序教學和教學機器》,劉范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324頁。為此,我們期許一種超越技術化的教學,即教學是人性的張揚,精神的弘揚,思想火花的碰撞,是生命力的綻放。
在柏拉圖看來,任何技藝都缺乏某種德性或功能。這種德性或功能只能由“精神”提供。教學技術應該彰顯教師的自我存在感,而不是游離于技術之外的陌生人。教學技術不僅是教學實施的手段、方法,也是教師發揮個人潛能、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任何對教學技術的機械套用,都是對教學意義的漠視與僭越。教學的意義不在于知識的傳授效率,而是取決于知識對于人的生存意義。而現代教學“越來越專注于一種量化的、操作性的認知和一種分成小塊的、分離的認識,越來越多地被要求積累在數據庫和學生的大腦中。”(41)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生境、生命、習性與組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頁。成為學生身心的填充物而非內在生命的一部分。帕克·帕爾默(Parker J. Palmer)認為熟練掌握教學技巧的教學還是不夠的,特別“當與學生面對面交流時,唯一能供我立即利用的資源是:我的自身認同,我的自我的個性,還有身為人師的‘我’的意識—如果我沒有這種意識,我就意識不到學習者‘你’的地位……真正好的教學不能降低到技術層面,真正好的教學來自于教師的自身認同與自身完整。”(42)帕克·帕爾默:《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吳國珍,余巍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教師作為教學技術的實施者要認識到技術的雙面性,真正能意識到個體在教學技術中的價值,發揮教學主體的能動作用,據此才能彰顯教學技術應然的人文性。
從日益智能化的教學技術發展來看,教學離不開教師生命個體的自我展現。和機器自動化只是把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相反,芒福德認為,以生活為中心的技術最有益的貢獻,就是使人完全在自愿的基礎上從事有教育意義的、自我實現的勞動,從而使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這將會是對普遍自動化不可或缺的一種平衡(43)轉引自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頁。。關注人、關注培養智慧、強調教師人格力量在教學中的地位的呼聲漸高,使“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凸顯,實踐的智慧才重新得以個性張揚(44)楊啟亮:《規約與釋放:教學實踐智慧的選擇》,《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年第11期。。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不是在于他們對教學技術的熟練應用,沉湎于教學技巧的練就。展現教師作為生命個體在教學技術中的人性魅力,重要的是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不斷進行教學反思,不僅要思考如何教學,教學效果怎么樣,更重要的是思考教學的意義,以此來指引教學技術的應用,而不是循規蹈矩的依照教學技術的規范教學。教師的個體價值在于超越教學的技術層面,而不是畏縮在教學技術的強大作用下,為教學技術的外在價值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