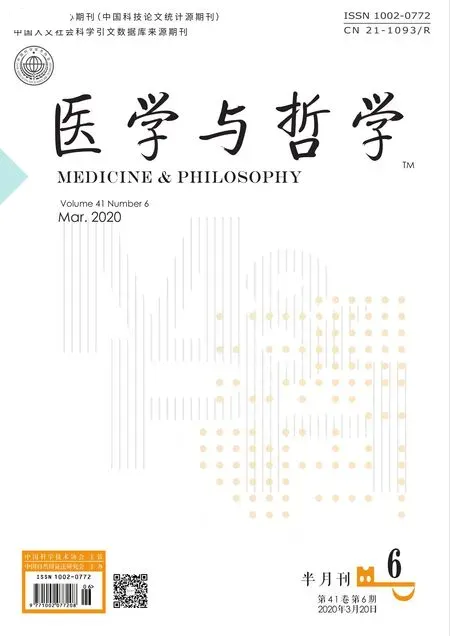心靈的挑戰:醫生責任倫理問題與訴求*
劉海文 張錦英
道德赤字,人性虧損是當代社會最大的危機[1],醫療領域也是如此,法律與倫理是醫療行為的基本要求。然而,單純法律制度、倫理原則已難以管控醫生的真實醫療行為,現代醫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沖擊和人性挑戰。作為一種新道德思維,醫學責任倫理具有新的精神氣質和新的倫理追求,它超越傳統的道德思維局限性,以他者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醫學責任,開辟了一條解決現代醫學面臨的道德難題的新路徑。責任倫理不僅涉及執行倫理規范和不執行倫理規范的責任,也涉及履行規范但效果不佳的責任,責任倫理是實踐倫理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是整個倫理建設中的重要課題,它對醫學提出了更高、更深層次的要求,也是對醫生道德與良知的嚴峻挑戰。
1 醫生責任倫理問題:道德赤字、人性虧損
1.1 重視技術自主性發展,忽略醫學前瞻性責任
科技時代的快速崛起,技術成為醫學的主體,自主發展的技術忽略了醫學仁學宗旨、控制了醫學理性,并以其帶來的經濟利益影響著醫學的意識形態,致使醫學的目的與手段發生了換位。為了治好疾病去尋求技術和為了發展技術去治療疾病,兩者似乎只有順序的不同,但實質上卻有本質的差別。現今很多技術應用的目的在于后者,這也是過度醫療盛行的原因之一。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給人類帶來福祉,也可以給人類帶來災難。“不傷害”是醫學倫理原則之一,但真正做到不傷害或無傷害是難以實現的,因為所有醫療技術,不論打針、吃藥還是手術治療,都具有一定傷害性,基因技術、克隆技術等應用更是后果難料,其關鍵在于醫生如何應用技術。技術自主化狀態讓技術的未來結果難以預測,而醫學需要對醫療遠期后果承擔倫理責任。
技術自主化發展給醫學帶來諸多負面后果[2],醫患關系全面物化,醫生責任意識缺乏,重視技術的既得利益,輕視技術產生的負面效應;無限制的技術干預導致人類機體內部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如基因干預、人造器官、混合胚胎,以及濫用抗生素、抗癌藥物等。現代很多技術結果是不確定的,而將人作為工具的技術行為常常因缺乏前瞻性、預防性評估而使其結果善惡難分。技術的無限探索也讓人體生命碎片化、醫生只見病而忽略了人,醫學人性淡化,道德責任缺乏。同時,單純依賴技術的生物醫學也是一種對人類健康不負責任的醫療行為。
1.2 重視經濟目標導向,忽略醫療公益性責任
當今醫學的顯著特征之一是資本主體化,醫療目標轉變是其主要表現,各個醫院的中心任務是提高經濟效益,多少億的年收入成為醫院的追求目標,這種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醫療活動引發的主要負面效應就是過度醫療普遍化和常態化,醫院之間的利益競爭嚴重損害了患者的尊嚴和利益,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受到嚴重干擾,整體醫療的公平性與可及性遭遇危機。如以前醫學希望患者越治越少,而今天醫院卻希望患者越多越好,各大醫院憑借技術優勢壟斷醫療市場,經濟導向不僅使“看病貴、看病難”狀態不斷加劇,也大大損害了醫學公益性原則。
責任倫理是現代醫學務必關注的重要維度,面對當今醫學資本帶來的道德虧損,如何協調資本經濟效益與醫學公益性之間關系也是當代醫學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醫學也需要資本支持,但與其他商業資本的顯著差別是醫學資本涉及的是人的健康與生命。因此,醫療技術促銷是背離醫學宗旨的,如果讓不應該吃藥的人吃藥、讓不需要檢查的人接受檢查、讓不用手術的人接受手術等,那就是一種背離醫學倫理的罪惡活動。
1.3 重視醫療法律責任,缺乏主動承擔責任的意識
依法行醫和在行醫中守法是醫生的基本底線,但單純的守法并不能給患者帶來真正的福祉,如對于“可救可不救的患者一律不救,可做可不做的檢查一律要做”就是一種缺乏道德的醫療行為。遺憾的是,這些行為在臨床上并非少見。為了避免醫患糾紛,很多醫生只遵循規定的醫療程序,接診、問診、檢查、開單、取藥,但對患者心理狀態漠不關心,甚至因為害怕承擔風險而有意推諉或躲避危重患者。從表面上看這些行為并不“違法”,但卻背離了倫理原則,缺乏主動承擔醫療風險的責任意識。以前,醫療法律是為了規范醫生的醫療行為,從而維護患者權益。今天,依法行醫更多的是為了保護醫生自己,但卻常常無意識地損害了患者權益。如手術或重大診療之前,醫生要履行“知情同意”義務,其本意是尊重患者的醫療選擇權,但實際結果卻常常只是為了規避醫療糾紛,甚至是“推脫”醫療責任。
可見,由于知識的不對稱性、醫學的不確定性、行為與內心的不統一性,任何完善的機制、體制與規范也難以完全規范醫生的診療行為。就過度醫療干預而言,很多情況下“過度”的界定并非易事,如常規技術有效,但醫生給患者應用高新技術、高檔耗材、高價藥物等也很難定為“違規”,并且醫生常常會根據“診療規范”、“科學證據”等給出很多“合理”的專業解釋。因此,踐行人性化的醫療需要醫生內在的良知,需要勇于承擔醫療責任的精神。
1.4 重視醫療局部責任,忽略醫學整體性責任
現代醫學專業細化,各個專業科室只重視本專業的疾病治療,而缺乏對相關科室疾病的考量;著眼局部病變而忽略醫學整合理念和整體醫學責任,如治療肝臟疾病忽略了腎臟功能保護;治療顱腦疾病忽略了心臟功能;治療外科疾病忽略了內科考量等,多學科協作理念淡化,對生命的有限性考慮不足。例如,對一個冠心病患者來講,其治療方案常常取決于其就醫的科室,外科可能會采取搭橋手術,內科可能會采取支架治療,而中醫科可能會建議藥物或飲食調整等保守治療,盡管每個醫生都有自己的專業理由,但對于患者來說應該只有一個是最適宜的方法,醫生需要有整合意識,從整體上進行醫療責任考量。
忽略醫學的整體性責任的行為還表現在:過度醫療干預增加醫療的二次傷害;濫用抗生素導致機體自然力下降;超量超范圍應用“殺傷性”藥物導致正常器官損害;生命的有限性在技術的無限干預下持續受到干擾,甚至忽略醫學人道精神,將患者當成技術研究的客體,為了提高技術水平而過度使用現代技術,以及單純重視醫學生物學責任,將臨床醫療“科學化、數字化、指標化、標準化”,忽略對患者心理與情感的關護責任等,如此種種行為都是醫學整體觀的缺失,醫學整體性責任的缺失。
1.5 重視個人既得利益,忽略醫學的道德責任
醫學是維護生命與健康的神圣職業,如今卻成為社會資本的主要成員,不僅醫院成為資本開發的重要領地,醫療也成為醫生牟利的主要手段,在各種利益的誘惑下,醫生的職業追求也在發生巨大變化,以至于醫療腐敗盛行并呈現普遍化趨勢。例如,福建漳州醫療腐敗案,73家醫院無一幸免,涉案人員包括全市1 088名醫務人員、133名行政管理人員,近90%醫務人員涉及醫療腐敗[3]。近年來,藥品提成、耗材回扣盛行,醫療腐敗的群體性特征明顯,呈現“一查就是一窩”的惡性影響[4],這反映出當今醫學的經濟化走向已經嚴重偏離醫學方向,致使醫學倫理缺失、道德淪喪。
醫療腐敗涉及醫院領導和醫務人員兩大利益主體,盡管腐敗現象有多種形式,而“利益”是其共同的接合點,醫生在醫療中直接獲取個人經濟利益,如收受紅包、藥品回扣、耗材提成等腐敗行為,而領導者則是在非醫療中間接獲取經濟利益,如基建工程、設備購置、藥品及耗材審批、醫院人員聘用和職務晉升等方面的腐敗行為,但不論利益來源如何,最終都來自患者利益的損害。當今醫學資本化、商業化帶來無節制的自由和私欲膨脹,各種利益吞噬著醫學的人性,導致醫學去道德化傾向,道德權威淪喪、德性受到貶損和邊緣化[5]。
2 醫生責任倫理訴求:一種新的道德思維
2.1 醫學責任倫理訴求及其當代價值
責任倫理的創立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由于行為后果預見和行為自身價值之間有很大距離,責任倫理應將對客觀世界的認定和認知作為重點,在行為選擇時,行動者要十分慎重,并要對行為后果承擔責任[6]。然而,直到20世紀中葉,早期的這種責任倫理才開始受到關注。隨著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引發諸多負面效應,人們不得不對醫學進行哲學反思,倫理與道德缺失是醫學面臨的主要危機,很多專家與學者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但人們卻仍然很難找到化解危機的有效方法,因此,責任或良知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醫生的責任倫理訴求受到廣泛重視并日益興起,20世紀90年代,責任倫理研究也在中國展開。
建立一種新的道德思維是責任倫理的價值所在。它超越了局限性的“自我”思維模式,以“他者”的思維方式對自身行動進行考量,對解決當代醫學倫理難題具有積極推動意義[7]。由于當代醫學活動性質已發生巨大變化,很多醫學技術是面對未來的,醫療活動的目的和結果之間常常存有難以預測的復雜聯系,責任倫理超越傳統倫理的簡單思維模式,強調人們必須對自身行為的可能后果進行考量,并自愿地、主動地、自覺地承擔行為后果。因此,責任倫理的核心是樹立責任意識,以一種不求回報的、發自內心的良知,履行一種特殊模式的善舉與道德。
2.2 從追溯責任走向前瞻責任
傳統倫理責任的基本形式是事后責任追究,即一種追溯性責任。傳統倫理將行為目的與結果之間視為簡單的因果關系,即通過行為動機評估可以預測行為結果的善惡,不良醫療后果就是由不良醫療行為所引發的。如出現醫療糾紛時,常常是通過醫療事故鑒定來確定事故原因,從而給予相應處理。然而,現代醫療活動卻是十分繁雜的系統過程,其最終結果和行動目的之間常常具有很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8]。如基因改造技術就有可能在幾百年之后對后代人的利益產生損害,而判斷行動的利害結果卻只能依賴當代人的意志進行預測,這就需要醫學拓展倫理思維、尋求一種具有預見性的倫理模式,而只關注當前醫療效果不考慮以后可能帶來的不良結果是對人類的不負責任。
責任倫理的興起是傳統倫理的發展,以行動主體的最終結果為導向,要求人們開發和應用不確定性技術時要特別慎重,其所承擔的是一種預防性責任或前瞻性責任,在不良結果出現之前就要充分預測到其對未來的影響,并承擔由此帶來的倫理與道德責任。如對早發現的腫瘤就要早期“殺死”或“毒死”,但其中有很多微小腫瘤以后未必就會成為“癌”而危及生命,就如小時候淘氣的孩子長大后不一定成為壞人一樣,如果統統從小就“趕盡殺絕”豈不是過猶不及。今天,盡管人們還不能準確預測現代醫學技術可能帶來的未來風險,但至少要有責任意識、風險意識,知道自己能做和不能做什么,審慎選擇和應用臨床效果不確定的新技術,并盡可能應用那些風險確定、效果良好、副作用少的適宜技術,只有在傳統技術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才可以考慮嘗試這些新技術。
2.3 從有限性責任走向無限性責任
責任倫理秉承的是對自然可持續和對人類未來負責的思想,要求醫生自覺地為自己設定責任限度。近期責任或有限責任是醫學倫理基本要求,醫生要對患者治療過程負責、對自己選擇的醫療技術負責、對患者的生命安全負責等。傳統倫理準則主要關注“圍醫療期”的有限責任,重視醫生的職業義務、展現醫生的職業良心和對患者的忠誠,但僅僅做好治病救人的醫療工作還是遠遠不夠的。就腫瘤治療來講,外科醫生不能僅著眼于切除腫瘤或器官,還要對手術的遠期效果進行考量,決不能發生類似手術很成功,患者卻因為“自身因素”而死亡的悲慘結果。同樣,基因干預技術已經讓很多癌癥患者獲益,但由于癌癥的機制仍不清楚,醫學也要對該技術遠期影響負責,決不能給子孫后代留下遺憾。可見,醫生只有拓寬自己的倫理思維,才能讓現代醫學真正成為人類健康的守護者。
醫療活動對社會和人類未來所承擔的普遍責任是醫學的遠期責任或無限責任,要求醫生在做好近期醫療工作的同時,更要關注醫學對人類未來生存狀態、社會可持續狀態的遠期責任,對全人類的健康和福祉負責。例如,治療現存疾病要避免損害正常器官;應用抗生素要避免整體菌群失調;殺滅癌細胞要避免傷害機體免疫功能;醫療干預要避免降低機體的自然力;應用不確定性技術要考慮其遠期影響等。因此,醫學責任倫理的視野更廣闊,它正從近期的有限責任向遠期的無限責任擴展。
2.4 從個體性責任走向集體性責任
醫療主體應盡的醫療義務是傳統倫理的主要責任,要求醫生遵守基本的倫理原則和醫療規范,對于違反醫療原則而引發的醫療傷害,醫生要承擔相應醫療責任和經濟補償責任。這種傳統的倫理責任主要是針對醫生個體行為的應當性。然而,現代醫療技術活動常常是一種集體行為,醫療活動的行為主體可以是一個多環節、多主體的“聯合體”,對于具體醫療事件常常難以找到確切的追責對象,如按醫院規定引發的過度醫療;按“指南”規范產生的不良反應;按“科學”標準出現的誤診情況等,盡管患者受到損害,但醫生卻不是唯一的責任主體。
鑒于當今醫療風險問題并非是醫生個體所能把握的,醫療責任也需要從個體性責任向集體性責任轉化,承擔醫學責任的主體不僅僅是醫生,也包括整個醫療活動各相關利益集團,如過度醫療干預的責任主體并非只有醫生個體,也包括醫療機構、醫療器械、醫藥公司以及政府機關等,應進行集體反思并承擔相應責任。當今大量醫學責任問題是個體性倫理規約所難以解決的,而是需要整個醫學相關主體共同努力,責任主體不僅要履行臨床醫療職能,也要主動接受社會監督與檢查,并承擔集體性責任。
2.5 從“自我”思維走向“他者”思維
傳統倫理是以“自我”為圓心的道德思維,所謂“推己及人”就是以“己”為邏輯起點進行道德判斷,即一種以身為度、以己量人的思維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就是說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能強加給別人,或自己認為好的東西才能給別人用。但實際上,醫生認為好的患者不一定認為好;醫生證明有效的方法給患者用了不一定有效;醫生認為治療效果很成功,但患者可能感覺不是最滿意。這種道德思維的問題在于缺乏“他者”維度,以“自我”為圓心,將他人納入自己的圓圈內,把自己當作同類的領導者,這種道德思維的實質就是權威者的獨白,反映的是“領導者”意愿。
在“自我”之外發現了“他者”是責任倫理核心,并將“他者”視為責任倫理的邏輯起點[9],站在“他者”的立場上,以“他者”的需求決定自己的行為目標,從而矯正以“己”為邏輯起點的思維偏差。責任倫理強調“他者”的差異性思維,“他者”是不可簡約的、不可類比和不可同化的。他人始終是一個他者,不能以“我”或另一個存在者的屬性作為衡量“他”的標準。每個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獨特感受,彼此都是他者,每個他者都是一個圓的圓心。責任倫理主張對話倫理,它不接受權威的獨白,也不接受先驗自我的獨白,而是強調真正的對話。就醫學而言,不是科學證明的就是真理,不是“證據”證明的就是診斷標準,現在認為有利的技術在未來不一定都正確,最終要以實際的真實世界做裁決,要站在他者立場上,認真考慮患者的意愿、未來的影響、遠期的效果以及對機體自然力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作用。
3 結語
當今醫學危機主要源于醫學的資本主義走向,源于醫學倫理責任的匱乏與淡出,而倫理責任是化解醫學風險的著力點,一切醫療制度與實踐行為都要出于責任而非僅僅是符合責任。責任倫理是一種高尚的倫理思維,它超越傳統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將自身責任視為一個非對等、非對稱的自愿責任,是一種自然的、先定的、絕對的發自內心的道德責任[10]。盡管這種新的理論思維在實踐層面上仍面臨重重困難[11],但我們必須超越自我,提高責任意識,踐行一種不求回報的責任倫理;挑戰心靈,建立善性理念,履行主動承擔的醫療責任,為社會可持續、為人類健康與后代造福。可見,責任倫理的精神氣質正應了裘法祖老先生的一句格言,“德不近佛者不可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為醫”。要成為一名好醫生不僅需要具備精湛的醫術,更要具有善良的人格,在預測技術存在未來風險時,絕不能把整個人類健康拿來當賭注,必須讓科學技術真正對人類未來和子孫后代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