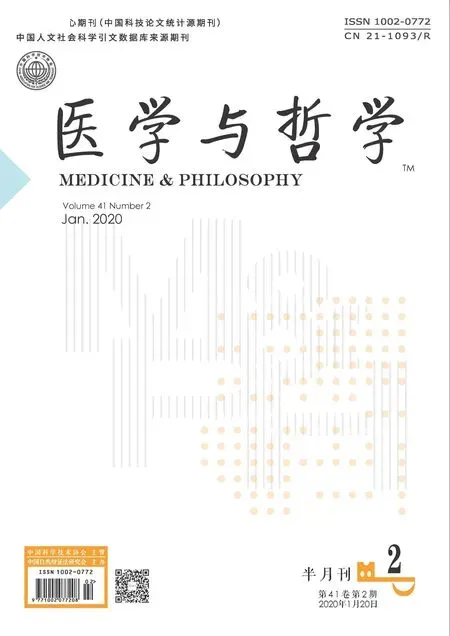預立醫療照護計劃在重癥醫學科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周 軍 王莎莎 孫 璇
不斷改進的機器、技術、新藥和侵入性干預措施是重癥醫學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特點[1],在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2]的今天,醫療技術的提高給人們帶來了莫大的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對部分患者來說也許是一種痛苦的延長,特別是在ICU許多終末期患者僅靠先進醫療設備來維持僅有的生命體征,但最終仍逃不過死亡的現實,不僅增加了患者痛苦,還給家屬帶來了一定負擔。這一現象由多種原因引起,與患者及家屬的價值觀和死亡態度聯系最為緊密。預立醫療照護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在國內是一個較新的名詞,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患者的治療意愿和價值觀,當這種意愿能付諸實踐時就會減少過度治療的現象,讓患者有尊嚴地離開。
1 ACP相關概念
ACP是一個反思、討論和溝通的過程,是在患者有決策行為能力的時候為自己未來的醫療意愿進行決策,闡明關于維持生命治療和結束生命治療的護理偏好,并確定醫療決策代理人,從而保證患者自主決定權和知情同意權,體現患者自身的生命價值觀[3]。
預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是在ACP形成的基礎上將患者的意愿和偏好形成的一份完整的具有一定法律效應的書面文件[4]。由于在概念上沒有進行明確定義,有學者也將AD稱為生前遺囑或醫療授權委托書。
2 ACP國內外應用現狀
2.1 ACP國外應用現狀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受人口老齡化[5]和醫療資源的壓力以及不同思想文化的影響,ACP廣為接受,隨著法律文件的誕生,ACP得到了進一步快速發展,在美國、德國、澳大利亞、意大利等國家ACP發展已經比較成熟[6]。在德國一項單中心橫斷面研究中調查了998名ICU患者,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有521名患者已經完成ACP文件,也就是說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將接受ACP,且2007年~2014年ACP在ICU的使用率逐年增加[1];美國是率先通過立法來保障ACP開展的國家,美國ICU醫療資源壓力較大以及財政負擔占比高,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美國ICU護理成本占美國醫療成本的13.4%,占國家衛生支出的4.1%[7],所以ACP在美國不斷得到推進,相關法律文件也在不斷完善,同時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宣布,將為討論ACP提供補償[8],2000年~2010年,美國死亡患者中有AD的比例從47%上升到72%[9];2014年,在挪威所有的療養院中進行一項關于ACP實施情況調查研究,有57%的護理人員接受了調查,結果表明其中2/3的人在療養院進行ACP,1/3的人已經有了書面的AD[10]。亞洲國家由于受不同文化影響,人們對醫療決定的認識不同,AD發展較慢,西方國家注重患者自我決定,強調獨立自主,而亞洲國家傾向于家庭決策,2016年韓國一項研究表明,隨著人們對生存質量認識的深入,人們對醫療自主權的意愿逐漸強烈,許多人表示贊同ACP的推進[11],包括日本也一樣,在ACP推進的過程中和韓國一樣沒有美國、德國發展的迅速,在立法保障上也較缺乏,自2016年以來,日本醫學會一直鼓勵初級保健醫師組織推廣包括ACP在內的培訓方案,并于2018年3月發布了一份向日本公民介紹ACP的文件[12]。通過研究不難看出,在ACP上東西方有一定差距。
2.2 ACP國內應用現狀
在我國一項全國多中心調查研究發現,我國只有38.3%的人聽說過ACP[13],人們對ACP的知曉度仍然較低,ACP的概念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在中國,大多數人仍然不愿意談論死亡和生命終結的相關決定,因為這是一個讓他們感到不舒服的禁忌話題。但是在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ACP發展較快,“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頒布[14]以及老年群體合適文化的ACP策略探討,推動了ACP的發展,2013年臺灣地區提出只要有1名關系最親近的家屬見證即可完成ACP[15]。在我國香港雖然ACP長期以非立法的形式存在[16],但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接受。在ACP臨床應用上我國主要在腫瘤科開展較多,其次是老年病科,有少數學者研究癡呆患者及兒童終末期患者,在ICU目前研究寥寥無幾,縱觀西方國家的研究發現,ICU的ACP應用價值較大,值得進行研究。
3 ICU推行ACP的價值意義
3.1 減輕患者和家屬心理壓力,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在我國目前的醫療發展下,各大醫院的ICU成了許多終末期患者度過臨終生命的場所,特別是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反復進出ICU,家屬只能在外面慢慢等候不能陪伴,不僅增加了患者和家屬的心理壓力[17],同時也增加了家庭經濟負擔。由于ICU醫療技術和設備先進、24小時醫護照看,醫療費用較普通病房要貴,對于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家庭往往最后人財兩空。ACP可以根據患者和家屬的意見選擇適合自己的治療方式,從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入住ICU的次數和ICU住院時間[18],減輕一定的家庭經濟負擔[19]和家屬人文負擔。
3.2 提高醫療資源利用率,降低患者痛苦
先進設備、先進技術、燈火通明成了ICU的代名詞,許多ICU住院患者出院后對ICU產生了恐懼感,感覺自己被醫療儀器所包圍,沒有白天和黑夜,產生了心理創傷[20],一些ICU的過度治療可能違背了患者的治療意愿,僅僅依靠先進醫療設備來維持僅有的生命體征對醫院來說是一種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特別是許多侵入性操作增加了患者痛苦。ACP有利于患者自身治療意愿的表達,不進行過多延長生命的侵入操作及治療,對患者來說可以減輕痛苦[7],對醫療來說可以提高醫療資源的利用率和減少浪費。
3.3 減少決策沖突的發生
在國外一項研究顯示,當ICU住院患者沒有AD,發生緊急情況需要搶救的時候家屬間的決策往往會產生沖突,這會使得家屬心理產生悔感,因為在事先不了解患者治療意愿時家屬處于治療不足和治療過度的矛盾心理,這種決策沖突引起的心理壓力遲遲不易消去[21]。在國外往往通過AD或者決策代理人來解決這件事,在國內由于文化差異,ACP一般以家庭為中心并結合患者自身意愿進行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少了家庭決策沖突[22]。
3.4 降低ICU的醫療成本
美國一項研究統計發現,2005年急救護理成本估計為820億美元,占住院醫院成本的13%,醫療資源大部分用于危重患者的護理[18],而且其中一部分醫療成本花在了死亡患者身上,為了緩解這一資源壓力美國極力推行ACP的發展,首先在立法上進行保障,這也是美國ACP發展迅速的一個原因。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快,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增加,給ICU帶來了挑戰,ICU患者病情重變化較快,如果沒有ACP就會使得治療過度從而增加醫療成本。
3.5 促進安寧療護的發展
ACP是安寧療護的一個部分,是安寧療護發展的前提準備,在ICU推進ACP的實施是對國家安寧療護的積極響應,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安寧療護的發展,2017年,國家衛健委發文明確要求要規范安寧療護服務,使患者能夠優逝[23]。ACP的開展有利于推動安寧療護的發展。
4 中西方文化差異對ACP的影響
4.1 文化影響生死觀
西方國家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就不斷進行思想解放運動,這些思想解放運動對他們的生死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他們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權至高無上。同時宗教信仰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對生死觀、生命價值觀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思想認為人的生命來源于上帝創造與恩賜[24],生命是神圣的,是自由的,人是上帝的代表,應該獨立自由的存在,上帝的意志才是最終極的價值標準,對生命的保存并不是毫無條件的,死亡是與上帝的合一,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一種更美的復活[25],死亡不是令人害怕的仇敵,而是人脫離塵世的希望,死亡是由上帝決定的,人為地延長生命可能違背上帝的意愿。因此,在既有的思想基礎加上宗教文化的影響,西方國家對待生死是坦然的態度,生而自由,死不畏懼。這種生死觀念恰好與ACP思想一致,因此ACP被西方國家廣為接受。
在我國受傳統文化影響,人們總體上是一種內斂、保守的觀念。傳統儒家文化對我國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人們總是“樂生”而“惡死”,民眾普遍追求陽壽,渴望壽命的延續[26],再加上受民間鬼魂文化影響,逃避死亡,恐懼死亡,認為死是不吉利的,在社會生活中, 人們都極力回避與死亡相關的話題, 甚至對“死亡”一詞予以回避[27]。久而久之形成了生而不言死的觀念。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主流,但是在面對死亡觀、疾病觀時卻存在過激的判定,即當父母生病時子女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生命,如果選擇放棄治療就會背上不孝的罵名,會遭受輿論的譴責,因此各大醫院過度治療的情況比比皆是,醫療壓力巨大。當然這種對孝道的理解相對于目前的醫學模式來說是過激的,但人們思想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因此ACP會隨著人們生死觀的轉變逐漸被接受。
4.2 文化影響決策權
在西方文化中人人生而自由、人人享有自主權利,即使病情危重自己有權利知曉自己病情,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選擇,這種知情權和自主權都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他們也樂意決定自己的偏好,因此西方國家鼓勵人們簽訂AD,人們也愿意接受ACP。我國受家文化影響,強調集體或家庭主義,家庭凝聚力高于個人偏好,人們傾向相信家庭成員的醫療決定,當然他們不認為這是對自由權的剝奪,而是看作是對自己關心的標志。因此大部分的醫療決策就會由家屬來決定,同時在某些地方有隱瞞病情的習俗,但是這種隱瞞病情的習俗被人們接受為善意的謊言。由此可見文化的差異影響著醫療決策。
5 在ICU開展ACP的影響因素分析
5.1 文化因素
受我國傳統文化影響,人們對死亡有一定恐懼感,人們總是忌諱談論死亡[28],認為談論死亡是不吉祥的,在這種思想長期引導下人們對死亡缺乏正確的認識,當疾病來臨威脅生命的時候缺乏應對能力,不知所措。同時在我國孝文化的背景下,不管疾病預后怎樣家屬總是竭盡全力治療,如果不進行積極治療會承受不孝之義,人們對孝道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延長生命的階段,也未考慮患者真實意愿以及無畏的過度治療會增加患者痛苦。
5.2 認知不足
由于ACP普及不夠,許多患者及家屬對ACP認識不足,沒有真正理解ACP的價值意義,在他們理解中ACP等于放棄治療,剝奪了患者生命希望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加上患者和家屬對許多疾病缺乏認識,特別是對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認識不足,認為只要治療就有希望、所有的治療都是有利的。此外由于醫護人員未接受專業培訓對ACP的理解不夠深入[29],在向患者及家屬解釋的時候缺乏技巧,不能很好把握ACP開展的時機,導致ACP開展困難。
5.3 法律政策缺乏
缺乏法律政策保障,法律是支撐我們開展ACP的根本基石[30],目前我國ACP立法處于探索階段,還沒有明文的法律規定,同時ACP也未納入醫療保險體系,這是影響ACP的重要因素。
5.4 ICU患者病情緊急危重
由于ICU比較特殊,患者病情重,病情變化快,對醫生的專業技能要求較高,很多時候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在加上ICU許多患者入科時意識不清甚至昏迷,醫療意愿完全掌握在家屬手里,這就對患者及家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醫護人員來說也是一種挑戰。
6 推行以家庭為中心,家屬共同決策模式的ACP
在我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家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人們往往很少宣揚個人主義,大部分都是強調集體或家庭主義,這在我國醫療上也體現得非常明顯[31],當患者生病時家屬被視為最信任的人、最了解的人,在ICU患者往往沒有了自主決策的能力,此時家屬所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因此在ICU實施家屬共同決策模式[28]是很有意義的,家屬共同決定模式有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患者入科后醫護人員要盡快與家屬及患者建立信任關系,在建立信任關系的過程中要逐漸全面評估患者及家屬,了解他們的基本情況其中包括患者及家屬的死亡觀、疾病觀、家庭觀[32],家屬的情況收集可以在入院24小時內以簡單會議進行,此次會議以傾聽解答為主。其次,掌握基本情況后召開第二次會議,此次會議要求護士參加[33],逐漸引入主題講解ACP,循序漸進引導家屬結合患者意愿進行選擇,護士此時應傾聽家屬的想法,當家屬模棱兩可的時候適當將患者在病房的意愿傳遞給家屬,并通過醫務人員的角度進行誘導分析[34],此過程中講解盡量通俗易懂讓家屬理解,如果家屬還是不能決定時不要盲目強求決定,散會后留給家屬一個時間段讓其考慮好決定,最后家屬決定后達成書面協議實施ACP方案。對于ICU入科就喪失決策行為能力的患者,此時醫護人員要根據病情判斷引導家屬早做決定[34],此類患者生命有限,也許緊接的醫療操作就會增加患者痛苦,因此盡早實施ACP對患者對家屬都是有益的。
7 結語
ACP目前在我國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很多知識仍在探索,通過國外的研究成果不難看出ACP的價值意義深遠,在我國是值得推行的,目前推行階段有一定困難,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國家層面需要立法來保障其合法性;醫療保險層面需要逐漸將ACP納入醫保范圍;教育層次需要加大對國民的死亡教育以及ACP的教育;社會單位或者組織要大力宣傳ACP知識;醫療單位要組織醫護人員進行ACP專業知識培訓,培養一批ACP專科醫護人員;推行試點工作探索經驗;個人層面我們要敢于接受新的知識,積極響應政策號召。在國內目前的研究中涉及ACP的文獻數量有限,說明我們對ACP的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多是關于腫瘤患者,并且多涉及現狀分析,研究層次有待擴展,一些調查研究缺乏大數據支撐,在以后的研究中學者們可以朝著這些方面進行深層次研究,為我國ACP的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