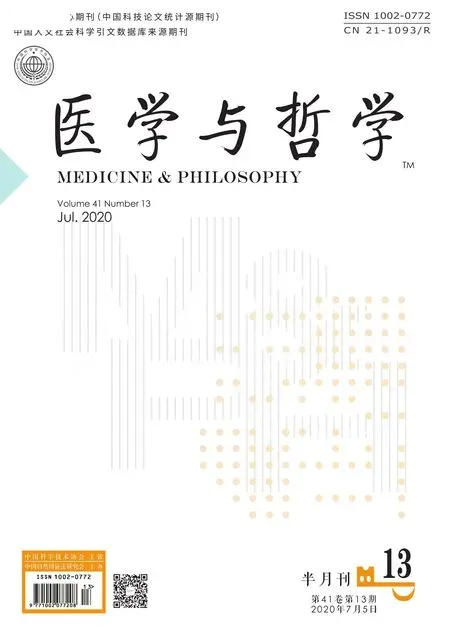生命危象中的敘事倫理*——非典疫情下的人文反思
凌志海 楊曉霖
1 敘事醫學與生命倫理
意大利詩人但丁說:“一個知識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彌補,而一個道德不全的人卻難以用知識去彌補。”《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里的蘇格拉底也提到:盡量使用你擁有的任何知識,但是要看出知識的有限性。光有知識不夠,知識沒有心。再多的知識也不能滋養或支撐你的心靈,它永遠也無法帶給你終極的幸福或平靜。生命必須在倫理和德性智識的引導下采取正確的行動,才能讓知識活過來。根據美國國家衛生院的定義,生命倫理是倫理學之下與生命科學和生命醫學知識相關的一個分支學科,倫理幫助人們決定如何行動和如何對待他人[1]。換句話說,生命倫理是人類在面對身體和環境的多變性所引發的難題進行權衡和內心掙扎過程中所受的指引。
那么,在醫學科學和專業知識教育之外,我們如何開展生命倫理教育和反思呢?建安七子之冠王粲:“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布羅茨基說:“文學乃是倫理之母。”他堅信:“文學故事是倫理辨別力的最偉大導師,阻礙人們從文學中獲取倫理教益會讓社會進化步伐變慢,最終面臨危險。”筆者在南方醫科大學開展課程思政的過程中,發現敘事醫學涉及的醫學史上的人文故事、文學中的生老病死故事、臨床現實中的醫護敘事和患者視角的疾病敘事四類敘事具有非常好的生命倫理教化功能,能夠用于不同的醫學教學語境中,引發倫理反思。
本文通過分析華裔作家林浩聰(Vincent Lam)的短篇故事《疫情跟蹤記錄》中的敘事倫理來闡述敘事作品對生命倫理教育的重要作用。華裔作家林浩聰是多倫多醫院的急診醫生,他利用業余時間進行文學創作,曾榮獲加拿大最高文學獎——“吉勒獎”,成為獲此殊榮的首位華裔作家。林浩聰在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鼓勵下開始虛構創作。短篇故事集《醫生這件事》圍繞作者在醫學院學習和做職業醫生的經歷展開,講述菲茨杰拉德、阿明、小陳和斯力四位年輕醫學生在現實生活和臨床工作中遇到的認知挑戰、道德困境和生命反思。
林浩聰在十六歲時閱讀海明威的《尼克·亞當斯故事集》,被“文學敘事”的魔力深深吸引,同時也對醫生職業有了最初的了解。林浩聰最終在家人建議下選擇了醫學,但仍然懷有文學夢想。一次考察林浩聰遇上了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阿特伍德,受其鼓舞,開始在醫生工作之余創作與醫護人員日常狀態相關的短篇小說。《醫生這件事》成稿后,林浩聰寄給阿特伍德,被其直薦給文學經紀人,促成了這部集子的出版。
《醫生這件事》里面講述了幾位從世界不同地方聚集到溫哥華醫學院學醫的年輕人努力學習最后成為南多倫多綜合醫院的醫生期間發生的故事。當他們一踏進這個職業時總要面對一具一具需要努力修復的軀體,他們要與時間賽跑更要爭分奪秒般地與死神搏斗,賭注的結果往往是他人或者自己的生命。然而,在突如其來的致命傳染疾病面前,當醫生成為罹患重疾的患者時,他們所學的科學知識和臨床技能似乎一下子變得毫無用處,面對這場非典疫情危機,他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脆弱性[2]和醫學的不確定性。
小說集中的《疫情跟蹤記錄》是林浩聰醫生根據自己的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間在醫院隔離病房工作的經歷創作的故事。本文主要以這個故事為出發點,以生命危象中的敘事倫理為框架,講述年輕的醫護人員面對突如其來的致命疫情所承受的巨大心身壓力,以及在他們變成疫情下的患者后,兼有醫生和患者雙重身份的他們如何與恐懼和無力作斗爭的故事。在疫情這面放大鏡前,重讀《追蹤密切接觸者》能夠更深刻地揭示疫情下的人性考驗和醫護人員的職業倫理反思。
2 當醫生成為患者:疫情下的生命選擇
故事發生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間,年輕醫生菲茨杰拉德和小陳在瘟疫流行初期不幸染病住進隔離病房。這時的菲茨杰拉德和小陳醫生不得不接受從醫生變成患者的角色轉換。故事里,菲茨杰拉德不希望他們再叫他醫生,因為他覺得“醫生”這個詞意味著凌駕于疾病之上,并且附加了全力救治他人的責任和使命。然而,如今菲茨杰拉德卻被疾病降伏,淪落成“患者的菲茨杰拉德已經沒有精力和能力去履行‘醫生’這個稱呼所賦予的職責了”。同時,菲茨杰拉德又害怕放棄自己的醫生身份,因為這也許是他找到治愈方法的唯一機會。
在這場殘酷無情的瘟疫中,菲茨杰拉德醫生在染病前首先被派往中國廣東深圳擔任空中救援醫生,負責轉運非典感染者到溫哥華,在救治感染者的過程中,自己也中了招。這之后,菲茨杰拉德聽說在廣州和多倫多不斷有患者在疫情中死去,然而,他和另一位被他感染的年輕同事小陳醫生卻只能作為患者而不是醫生的身份呆在隔離病房里。兩位年輕醫生的病床被一堵像魚缸一樣的玻璃墻隔開,在負壓玻璃隔離病房里,他們只能通過電話互相鼓勵,互相支持。
隔離期間,他們共同回憶起救治過的病例和同事,一幕又一幕的場景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他們,在這次疫情中,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是如此近距離般地更接近死亡。他們無法相信昔日的同事居然會毫無預兆地染上非典,進而悄無聲息地離他們而去,再也無法一起搶救患者。最為關鍵的是,他們始終無法相信,卻也不得不相信自己可能就是下一個即將要死去的人,盡管他們的職業身份都是醫生,但是在疫情面前,人人平等。
當醫生變成患者,某種張力就出現了,疾病的生命醫學視角不得不與疾痛的個人視角合并,藉此,原來的醫生身份進入一種“患者-醫生閾界狀態”[3]84。在突如其來的致命傳染疾病面前,菲茨杰拉德醫生昔日所學的科學知識和臨床技能似乎一下子變得毫無用處,以前所接受的各種專業的醫學教育和各種醫學技能培訓也似乎在一剎那間成了一個殘酷的笑話。
他們發燒、咳嗽、氣短、胸悶,需要同事對他們進行退燒和供氧。盡管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職業醫生身份,按照以前慣例,他們會經常給發燒患者開退燒藥。但是當他們真正成為患者后,他們卻不遵照醫囑,不去服用醫生同僚給他們開的退燒藥,因為他們更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肝臟承受不了那些藥物。當兩位年輕醫生成為患者后,他們逐漸學會了放棄“醫學能治愈一切疾病”的神話,真正理解了生命的復雜和不確定性,以及醫學的局限性,他們更加理解了什么是“人性之人性”的內涵[3]80,[4]。
在兩位醫生的對話中提到,雖然醫護人員都盡力使用最先進的設備和最有效的藥物投入到對感染患者的救助當中去,諸如插管、呼吸機、心肺復蘇術等全部用上,但是大多數人還是逃脫不了最終走向死亡的命運。他們也意識到,當代醫學在抓住人類生命最為核心的方面,如希望、恐懼、愛恨、嫉妒、虛弱、痛苦等認知性情感上是如此的無能為力。小說里有段很經典的話:“我們什么時候也沒有真正打敗過大流行的傳染病,他們自行蔓延,自行消亡。問題不過是多少人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犧牲品。對人類而言,瘟疫比戰爭更殘酷。”
菲茨杰拉德醫生和小陳醫生雖是醫學院的同窗,但他們并不是好朋友,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曾經的情敵。然而,在疫情和死亡面前,在隔離期間,兩位“醫生病友”卻結為“死黨”,每天都在互相打氣,互相鼓勵,共同研究如何抵御疾病。他們回憶與罹患胰腺癌死去的老朋友斯力(Sri)之間的往事。斯力醫生從確診到去世不到一年時間。他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醫生,斯力甚至為了實現肺癌末期患者歐拉夫的心愿,親自做了一款叫“班尼迪克”的檸檬汁煎蛋。歐拉夫在品嘗了煎蛋之后不久去世了,接著斯力也去世了。在遺體告別儀式上,菲茨杰拉德和小陳醫生才發現,無論你是醫生,還是患者,死去時都是一樣的。
這次疫情使兩位年輕醫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身為職業醫生的自己原來距離死亡是那么的近。他們談及作為一名醫生后所承受的種種壓力,也冷靜地談論著自己的死亡以及他們參與治療的方式;他們同病相憐,也談論那些過往歲月里曾經讓他們感到悔恨和愧疚的事情,他們也推心置腹地深刻剖析了自身性格的陰暗面。以前,在醫生與醫生之間他們習慣談論的是手術和治療的成功、患者的感謝等,但是現在,他們談論得更多的是自己作為醫生的失敗案例,比如,在公園里對一位垂死的流浪漢見死不救,一位年老的女性患者在大半夜死去之后,醫生為了獲得睡眠時間,到第二天早上才通知她的兒女,并宣布患者剛剛離世,等等。
這里可以看到,正是疾病或者死亡的逼近才給了兩位年輕醫生得以重新反思生命、反思職業、反思自我的契機。正如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所言,死亡是“雙面的雅努斯(雅努斯是兩面神,年輕的面孔表示新生與未來,衰老的面孔代表死亡與消失。)”。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則說死亡是世上“最好的醫生”[5]。兩位醫生患者在講述和傾聽各自以前不愿提及的故事的過程中,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治愈。這些故事如果不講述出來,將成為讓他們永遠感到羞恥的心靈烙印。
從敘事醫學的視角來看,非典疾病使得菲茨杰拉德醫生和陳醫生能夠獲得停下匆忙腳步的機會,把注意力重新帶回到內在,并能不斷去反思自己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人生路。在某種意義上講,接近死亡的體驗可幫助人們走上對自我和對生命的重新認知之路。針對非典疫情使兩位年輕的醫生成為患者的經歷完全改變了他們之前對死亡的態度,同時疾病和死亡也教會了他們如何思考人生。
之前天天酗酒的菲茨杰拉德醫生的病情每況愈下,為了避免在被搶救的時候把病毒傳染給他的同事和朋友,他主動要求簽署一份“拒絕心肺復蘇同意書”,他希望能夠通過犧牲自己,保全其他醫生。菲茨杰拉德醫生說,他已經接受了自己會死于疾病的事實,他不想被救活。他告訴陳醫生:“這并不是壞事,如果我們和幾百個人一起死,我們將成為非典的烈士;如果成千上萬的人生病了,但之后他們找到了治愈的方法,我們的死亡也能提供幫助,那么我們將死得其所;萬一這件事失控,全世界數百萬人死亡,那么我們將面臨最糟糕的時刻。明白嗎?我們不能認輸。”[6]
3 隔離病房里的醫生與護士:疫情下的人性反思
故事中的另外兩個角色是照顧菲茨杰拉德和小陳的澤恩基醫生和隔離區護士多洛雷斯。澤恩基醫生是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南多倫多綜合醫院傳染科的非典特別顧問,他已經有26年傳染病防治經驗。通過閱讀澤恩基醫生不斷更新的非典患者“病情跟蹤筆記”,可以了解到非典患者的疾病發展進程、醫護人員照料和治療非典患者的整個過程,同時也可以直觀地學習到用于嘗試和治療這種瘟疫的藥物與臨床程序。菲茨杰拉德和小陳醫生在隔離病房的情況也被記錄得非常細致全面,包括菲茨杰拉德比較罕見的寒顫癥狀等。
在這份“病情跟蹤筆記”中最后記錄的是關于澤恩基醫生自己的病況和入院通知,由醫院同事將他的口述轉成文字。從他的口述中,了解到這位資深傳染病專家也是一位野外自然風景的攝影愛好者。在開始出現咳嗽、氣短等癥狀后,澤恩基醫生仍保持幽默的口吻,說自己也許啥事都沒有,只是換上了社交多疑癥和良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當然也不排除罹患非典這一可能。因而,為公眾安全起見,他為自己開具了非典隔離病區入院單,準備“水手與船共存亡”,并安排沃特曼醫生接替他的醫務工作。
然而幾天后,非典疫情行動管理小組發布了澤恩基醫生在罹患非典后不久去世的消息簡報,并對曾與澤恩基醫生密切接觸過的醫務人員實行隔離,而事實上,他的妻子已成為非典患者在隔離專區住下了,而他的同事們也都在隔離病區工作著。簡報也提醒大家,權威專家澤恩基醫生都敗在非典死神的鐮刀下,其他醫務人員必須加強防范,并發出了氣溶膠可導致傳染可能性的警告。
《疫情跟蹤記錄》里講述了隔離區工作的護士在疫情期間的故事。在非典大流行期間,如果護士逃離崗位或者辭職,他們將失去原本應有的退休福利,如果護士拒絕護理非典患者,他們將失去執業資格,只有接近退休年齡的護士可以提出提早退休并保留退休福利。在所有決定離開和早退的護士簽名之后,剩下的護士通過抽簽來決定誰進入隔離病房。
在這種背景下,剛剛成為單親媽媽,盡管有三個孩子要照顧的多洛雷斯護士已經有過12年的護士資質,但是如果她不服從疫情安排,就要面臨重新就業的問題,這將直接導致孩子的撫養費和房子的按揭貸款都會面臨危機,可能就100%地失去了生存的能力與可能性。而非典感染率似乎低于這種可能性,何況也不一定真正抽到自己。權衡之后,多洛雷斯護士決定留下來抽簽,試試運氣。抽到黃標簽的護士們如釋重負,露出輕松的表情,而抽到紅標簽的護士面面相覷,有的當場哭出聲來,有的則背過身去默默啜泣。主持抽簽工作的工會領導這時跟大家說,隔壁房間有疏導心理創傷的顧問,然后就離開了。
多洛雷斯也抽到了代表必須進入隔離專區工作的紅色簽。盡管她內心非常抵觸,但只能認命接受。世界衛生組織檔案顯示:絕大多數感染病例發生在醫務工作者、醫務工作者的家屬和與患者密切接觸過的人當中。口罩短缺、防護服短缺、強制隔離和密切接觸者不斷確診和更新死亡病例的新聞讓全世界都彌漫著恐怖的氣息,這一切都呼應著當下疫情語境中的種種現狀。
然而,已經在隔離專區工作的多洛雷斯除了要面對致命疾病的傳染威脅外,還要應對種種污名化和歧視。剛開始,在托兒所的兩個孩子告訴她,其他孩子們都不愿意跟他們一起玩,后來,托兒所負責人甚至直接通知多洛雷斯將孩子接回家。盡管多洛雷斯反復解釋,自己每天都在醫院接受掃描檢查,體溫檢測也沒有任何異常,孩子也不可能被感染,但是托兒所負責人依然拒絕讓多洛雷斯的孩子繼續入托。托兒所負責人說,介意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其他家長們會感到不安,甚至是抗議。多洛雷斯只好花錢找了一個保姆照顧孩子,并且交代孩子們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媽媽的職業是護士。
受到歧視,被大家視為瘟神,又與患者近距離接觸的多洛雷斯內心也開始走向崩潰。多洛雷斯非常想念托給保姆照看的孩子,想在下班時讓保姆將孩子送回家,但一想到非典報道中說傳染物可能在攜帶者體外生存數天,就千方百計不讓孩子回家,因為她感覺家里已經成為傳染源了。在焦慮和恐懼下,她不斷懷疑自己已經感染了這種可怕的、必死無疑的疾病——感覺自己在發燒,并忍不住要咳嗽。她害怕自己感染了,孩子再也沒有人照顧,也害怕自己再也不能活著見到孩子。然而,當她每次膽戰心驚地沖回家卻發現自己的體溫是正常的。
故事中,作者對該人物的細致描寫加深了讀者對醫生和護士這一神圣而崇高職業的敬仰之情。撇開外在的與患者身體密切接觸的危險不談,單就醫務工作者一方面既要踐行自己的職業使命感和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另一方面還要能夠頂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去拯救患者于生死存亡之際,這早已非常人所能及了。其實,多洛雷斯這個角色也就是人性的一個縮影,她只不過就是想一天一天地努力渡過疫情的難關,無非就是想保護好自己的家庭和家人而已,這是人性最基本的訴求。
4 結語
林浩聰在《疫情跟蹤記錄》這個故事提出了兩個關鍵的生命倫理難題:護理和治療義務的邊界在哪里?醫護人員是否應該為了他人的健康而做好犧牲自己生命的準備?也可以說這個故事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可怕的流行病出現,醫院里會發生什么?在故事中,隨著非典疫情的暴發,醫生和護士都各自重新評估了他們與醫療衛生系統的關系。這個故事揭示的正是傳染病暴發期間的醫療狀態,闡明的是關于醫療從業者的道德定位,以及他們作為醫學專業人士的反思,對一些讀者而言,也可以說是作為患者本人的反思[7]。
在對林浩聰的《醫生這件事》進行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尼克松和巴茨提到,“林浩聰的故事作為生命倫理課程的培訓工具非常適合。倫理決策的首要一步就是要第一時間使醫護人員所遇到的道德困境通過不同形式的發聲(對于林浩聰而言,是通過創作敘事作品的方式)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他的每一個短篇故事都嵌入了無法簡單概括和簡單評斷的倫理困惑,這個鮮明的特點讓短篇故事集里的許多故事都蘊含了有助于我們對生命倫理的話題開展教育和反思的潛質。”[8]
《疫情跟蹤記錄》是生命倫理學家感興趣的話題,在《醫生這件事》全書中,林浩聰透過文學敘事的策略深刻地詮釋了貫穿整個小說集的主題,即醫護人員在生命危象中的倫理抉擇。此外,這個短篇故事也闡明了醫生視角下醫學的不確定性。正如林浩聰在故事集后記中所引用的現代臨床醫學教育之父威廉·奧斯勒爵士的那句經典名言“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9],醫生并非神,更非萬能的上帝,醫學是一門需要醫護人員踐行的人文藝術,更是一門實踐科學。
公眾對醫生并不陌生,但對醫生的真實生活未必了解,平常的我們常常都只看到醫生的專業技能和職業使命,卻忽略了醫生作為普通人所展露的人性脆弱的一面,他們也需要我們的關注和安撫,特魯多墓志銘上的經典名句“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不是單純說給患者或者患者家屬聽的,醫護人員也同樣需要這句經典名言,因為當他們脫去圣潔的白大褂時,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也不過是普羅大眾中的一員,他們既沒有三頭六臂,也不是什么神,他們也有自己人性最脆弱的一面,他們也有自己的愛恨情仇,他們每天也要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
林浩聰的作品呈現給讀者一個嶄新的世界,使人們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醫護人員也要面臨各種內心沖突和種種痛苦掙扎。對于那些尚未正式步入醫學職業生涯的醫學生而言,這更是一部能增強自己職業認同感的醫學短篇故事集[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