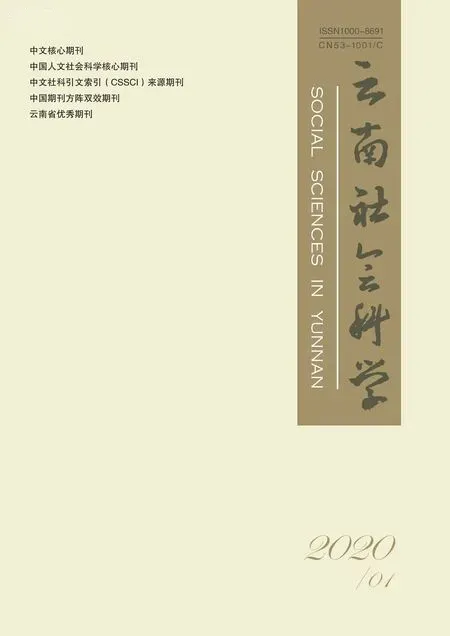遺產過程的兩分路徑:“成為遺產”和“成為遺產之后”
尹 凱
一、問題的提出:被表述的遺產
從最初的含義來看,遺產(heritage)指的是繼承物和繼承事實①根據《簡編牛津英語詞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詞條來看,遺產指的是已經繼承或可以繼承;繼承和世襲繼承的事實;給予和接受的恰當所有物;繼承的任何份額。。遺產研究中的遺產概念雖與之大相徑庭,但是這種代代相傳的穩定屬性和祖產的不可分割性似乎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繼承與延續,即假定物件、地方與實踐的固有價值。這種“遺產自決”的理念并未將遺產視為一套知識體系,而是一種與主觀情感有關的文化體系,頗有德國浪漫主義之風。
隨后,以《威尼斯憲章》(1964)、《世界遺產公約》(1972)為代表的國際文件構成了遺產認知的權威與標準。這些國際文件和官方標準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將普世主義確立為全球倫理的基本法則。②UNESCO,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airs: UNESCO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46﹒就遺產而言,普世主義價值體系制造了遺產的二元結構關系:地方的、直覺的、經驗的、屬于文化領域的遺產和認知的、理性的、全球的、屬于文明領域的遺產。③Thomas Ericksen,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A Critical of the UNESCO Concept of Culture,” in Jane Cowen﹒ed﹒,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Robert Shepherd,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and the Chinese State: Whose Heritage and for Whom,” Heritage Management, Vol﹒2, issue﹒1(Spring 2009), PP﹒ 55-61﹒從“遺產自決”到“遺產名錄”不僅意味著名相的變更,而且重置了遺產認知與闡釋的背后邏輯,即千姿百態的遺產樣態和不證自明的價值被等級結構與技術權威所裹挾。由此,一種基于西方進步觀念和文明演進的遺產合法性建構起來,并成為有關遺產及其價值的保護、分類與認定的典范。隨后的劇情圍繞著遺產的二元結構關系鋪陳開來。基于“文化”與“非西方”的遺產觀念質疑基于“文明”和“西方”的遺產論調,并最終實現了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在國際層面上的平衡與并置。這場東西方的文化與政治博弈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兩個結果:一方面是加速有形文化遺產等諸多實踐在無形文化領域的挪用,吞噬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促使無形文化遺產走向制度化道路和標準化程序,消解了原初的變革精神與活力。
如果采取羅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的遺產分類模式的話,上述兩種遺產形態都屬于國家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官方遺產。另外一類遺產是自下而上的非官方遺產,即在地方層面上,以人、物、空間和記憶之間的關系為根基形塑而成。①Rodney Harriso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之于前者,宋奕曾撰文系統爬梳過近四十年來“文化遺產話語”在國際層面上的歷史軌跡,著眼于不同時期的國際文件,討論特定語境下遺產的言說與實踐體系。②宋奕:《“世界文化遺產”40年:由“物”到“人”再到“整合”的軌跡》,《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0期;宋奕:《話語中的文化遺產:來自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啟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8期。之于后者,強調邊緣敘事、社區導向的遺產運動和社會博物館學關注社區參與、文化賦權和政治民主等相關議題。③William Nitzky, Entanglements of “Living Heritage”: Ecomuseu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14, P﹒ 1﹒這兩種書寫模式對權威遺產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進行分而論之的剖析與研究,呈現了自我修正與他者反叛的學術景觀。
在“人人皆有個人遺產權利”的當代社會,遺產建構的社會參與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有關遺產研究的二元對立結構關系的復雜性。換句話說,在上述努力下,當代社會的物件、地方與實踐獲得遺產資格,并被遺產世界所接納變得更加多樣。為此,從微觀層面分析遺產制造的過程變得尤為關鍵。本文以批判性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e)入手,討論某個物件、地方和實踐是如何從一種日常生活的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s)轉變成為一種具有保護、研究與展示需求的遺產產品(Heritage Output)的。
二、從資源到遺產:遺產的過程路徑
批判性話語分析的領軍人物勞拉簡·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曾斷言:“事實上,并不存在 所 謂 的 遺 產”(There is, really, no such thing as heritage)。④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1﹒史密斯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沒有遺產的話,國際上的遺產組織究竟在做什么呢?在隨后的段落中,史密斯自問自答,給出了問題的答案:“遺產‘凝視’的主體并非是具有價值和意義體系的某種存在。遺產最終是一種文化實踐,涉及到一系列價值和認知的建構與管理。”⑤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P﹒ 11﹒從遺產研究的脈絡來看,史密斯挑戰與解構的是以權威遺產話語為代表的遺產模式,即將遺產價值作為固定不變的本質主義。
從遺產的本質主義到遺產的建構學說僅僅是批判性遺產研究的開始,接下來是尋找一種理解遺產本質的新路徑。在眾多的替代性路徑中,過程論的分析框架因其對本質主義和結構主義的修正而被挪用到遺產研究領域。將“遺產作為一種文化過程”來理解的過程路徑吸引了大批遺產研究學者的支持: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認為,遺產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文化意義的溝通實踐。⑥Bella Dicks,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People: Circuits of Communication at a Local Heritage Museum,”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5, no﹒1(March 2000), PP﹒ 61-78﹒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將遺產定義為一個與人類行為和能動性有關的動詞形式,并進一步指出遺產是一個與國家和其他文化或社會認同的權力合法化密切相關的過程。⑦David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7, no﹒4(December 2001), P﹒ 327﹒史密斯認為,遺產是一個與記憶行為建立密切關系的文化過程,以此構建理解現在和參與現在的機會,因此,物件、地方與實踐并非是遺產本身,而是促進遺產生成過程的文化工具。①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P﹒ 44﹒這些研究視角略有差異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遺產的過程路徑的共同旨趣:一方面強調參與主體和行動者的角色與地位,關注其在遺產過程中的參與性與能動性;另一方面則將社會情境引入到遺產的文化維度,關注不同文化體系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商榷、互動與對話過程。
與上述有關過程路徑的認識論共識不同,杰拉德·科賽(Gerard Corsane)從操作論的視角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過程框架。在《遺產、博物館與美術館的相關議題》一文中,科賽繪制了從資源到遺產的意義生成過程。②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5﹒在筆者看來,從資源到遺產的過程論述不僅在實踐層面規范了遺產制造與管理的步驟,而且在理論層面構成遺產學術研究的基礎與底色。為此,筆者將在科賽建構的遺產運作的總體過程模式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經驗,討論從文化資源到遺產產品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要談及遺產的操作過程,遺產制造動機是率先考慮的要素,究竟是教育、學習,是經濟、消費,亦或是賦權、民主呢?作為“回到過去”的表征③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馮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4頁。,遺產猶如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不得不讓人們求助于遺產制造動機背后的主體及其歷史語境。根據簡·尼德文·皮特爾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對文化表征的認同主體的歷史性梳理來看,21世紀的全球化思潮帶來了認同主體的多元化,即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帝國和現代擴展到地方、區域、大陸、跨國與全球。④Jan Nerderveen Pieterse, “Multiculturalism and Museums: Discourses about Other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PP﹒ 179-20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歷史維度的變遷不是更迭與替代的進化,而是一種在當代并存與互動的關系。也就是說,遺產制造動機也會因為諸多參與主體的互動、協商與對話而變得模糊,甚至會隨著過程的進行而發生變動。無論如何,把握遺產制造的復雜動機及其主體是操作與理解遺產過程的首要環節。
隨后,遺產過程進入到第二個環節,即物件、地方與實踐等有形或無形文化資源的調查與記錄階段。就調查與記錄的方法來說,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因其文化整體觀、參與觀察、深描等專業技能的訓練而成為方法論層面上的不二選擇。就調查與記錄的對象來說,嵌入日常生活和傳統敘事的文化資源不僅具有可挑選的代表性,而且緊密編織在當地的“意義之網”中。為此,形塑文化資源價值與意義的自然、社會、文化、政治情境及其彼此之間的關系是調查的先決條件。在記錄文化資源的一般或特殊信息時,自然生態、建筑環境、系列物件、檔案材料、藝術形式、知識系統、信仰模式、口述傳統、民歌、舞蹈、儀式、技藝、生活方式⑤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等內容都需要記錄在案,這構成了后續深入研究和信息挑選的素材。
其實從上述有關文化資源的記錄開始,遺產過程即已經進入物件、地方與實踐等資源的保護和管理范疇。這一環節主要由兩個前后相繼的階段組成:資源的具體研究和信息材料的過濾篩選。具體研究指的是聚焦于物件、地方與實踐本身,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更加詳實而具體的證據與價值,比如在博物館運作中,解讀藏品信息的研究功能就屬于這一階段。需要指出的是,物件、地方與實踐等資源類型不同意味著不同研究學科和專家的介入:動植物標本需要自然史專家,出土材料需要考古學家,建筑形制需要古建專家,表演習俗需要民俗學家……任何物件、地方與實踐等資源的背后信息是非常復雜的,包括起源、歷史、功能、內容、形式、知識等。如果資源要成為遺產,并進入可展示與可參觀的狀態,那么就意味著與之相關的資源信息的過濾與篩選。
至此,開始了遺產生成的最后一個階段,即遺產的溝通與闡釋環節。如果將物件、地方與實踐作為具有社會生命的資源,那么成為可參觀的遺產無疑意味著第二次生命的開始。在這一生命歷程中,處于舞臺中心的、被參觀的遺產需要表述自己,并與觀者建立溝通關系的策略。一般而言,推出遺產的機構和個人會為了達成溝通與闡釋的效果,有意識地建構交流路徑,包括陳列與展覽、教育活動、活態闡釋、導游參觀、學術出版和信息服務等。①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從操作層面來看,從資源到遺產的過程已經進入尾聲,但是從認識層面來看,遺產的闡釋和溝通尚未結束。根據傳播學理論和建構主義學說,觀者早已不再是信息傳播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意義建構的能動參與者。②Rhiannon Mason, “Museums, Galleries and Heritage: Sites of Meaning-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21-237﹒為此,無論遺產溝通與闡釋的內容具有地方特殊性,亦或具有文化普世性,觀者個體或群體對遺產意義的解讀也是理解遺產過程路徑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上所述,嵌入日常生活中的資源經過動員與介入、調查與記錄、研究與挑選、溝通與闡釋等一系列過程的包裝而成為一種可參觀的遺產。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僅僅是一種基于諸多經驗而歸納的理想類型。無論有關遺產制造之路的模式多么詳盡,也無法窮盡圍繞遺產所上演的復雜劇情。既然如此,這些思考是不是可以作為無用的知識而丟進垃圾桶里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從資源到遺產的過程路徑不僅構成了實踐遺產的參考方法,而且有助于評估、分析與理解遺產的本質。
“成為遺產”并不意味著操作層面上的完結,甚至在學術層面上,有關遺產本質的理解之戰才剛剛打響。在下文中,筆者將著眼于從遺產過程中生成的關鍵議題,討論遺產的本質及其爭論。
三、從過程到議題:生成中的遺產思考
已有對遺產的研究具有一定內在的矛盾性:一來,遺產研究的開放性為諸多理論假說打開自由出入的大門;二來,遺產研究的內卷化基本上框定了學術思考的范式。換句話說,遺產研究并非自由之地,是有一定門檻的。只需稍微列舉一下有關遺產議題的成熟思考,就可理解學者所面對的棘手局面。
之于遺產本質而言,格雷戈里·阿什沃思(Gregory Ashworth)、 約 翰· 坦 布 里 奇(John Tunbridge)的“遺產失調”(Heritage Dissonance)理論和迪克斯對遺產固有張力的洞悉奠定了遺產認知的基礎。前者認為遺產的本質即是在意義與表征上呈現得不一致③John Tunbridge and Gregory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Chichester: Wiley, 1996﹒;后者則提出遺產內部以游客為導向的市場關系和呈現、歌頌真實文化之間的糾葛關系④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第124頁。。之于遺產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大衛·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對兩者進行了區分,歷史試圖呈現真實的過去,而遺產則坦率地捏造并且遺忘。⑤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1﹒李軍以科學和信仰分別比附歷史與遺產,并提出了遺產是一種政治分類的論斷。⑥李軍:《文化遺產與政治》,《美術館》2009年第1期。之于遺產與記憶之間的關系,麥夏蘭(Sharon Macdonald)直面殘酷和恥辱的過去,從身份認同的分析視角出發,討論黑色遺產的自我披露所帶來的道德效果。⑦沙倫·麥克唐納:《騷動不安的記憶——對棘手的公共遺跡的干預與爭論》,陳春莉譯,《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8年第2期;麥夏蘭:《“棘手遺產”是否依舊“棘手”?——為何公開承認往日惡行不再顛覆集體身份認同》,申屠神悅譯,《國際博物館(全球中文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之于遺產的功用而言,布萊恩·格雷厄姆(Brian Graham)等人提出了作為經濟資源和作為社會政治資源的遺產之爭,并試圖從意識形態、階級、性別和族群性等維度的分化與混雜對其進行診斷。⑧Brian Graham, Gregory Ashworth and John Tunbridge,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eritage,”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28-40﹒上述由遺產所衍生出來的關鍵議題已經逐漸被學界所接受,體現在對一些基于經驗材料的個案分析中。當然還有其他尚未提及的遺產議題,由于版面所限,筆者暫不贅述。
雖然上述任何一個議題都值得深入探討,但是筆者意不在此。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有關意義之網和闡釋人類學①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王銘銘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克利福德·格爾茨:《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的分析對該問題的深入探討具有啟發作用。在格爾茨看來,文化闡釋的關鍵在于從文化體系中找到一個“關鍵詞”,之后則循著從“關鍵詞”到“要素范疇”再到“文化體系”的分析路徑展開,從而編織出所謂的意義之網。這與第二部分所述的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資源,從而經過一系列過程從而制造遺產的過程非常相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文化闡釋或遺產過程路徑的終點。格爾茨認為,接下來的步驟尤為關鍵,即讓編織成的意義之網反向流動,進而去解釋最早發現的“關鍵詞”,從而達成一種完整的闡釋循環。如果將此觀點運用到遺產研究領域,那么,從資源到遺產僅僅是過程路徑的半個循環,另外半個循環即是“成為遺產之后”的進程。如果在操作論和認識論層面上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將其聯系在一起考慮,那么,一個理解遺產本質的完整的過程路徑便可奏效。筆者就此展開討論,主要聚焦于如下兩個議題:一方面,“成為遺產”意味著什么;另一方面,“成為遺產之后”又會發生什么。
近日,浙江師范大學教授陳華文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實踐是“通過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還非遺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②陳華文:《文化生態保護區:非遺保護的中國實踐》,《光明日報》2018年6月2日,第12版。。持此種樂觀態度的學者不在少數,其基本共識在于,從資源到遺產的過程是一個保護傳統、傳承文化、振興鄉村的有效舉措。這種論斷遮蔽了遺產面臨的真正困境,還需要重新進行思考。
實際上,每一個從資源到遺產的過程都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物件、地方與實踐在所有權、話語權、闡釋權上的全面分離。如韋伯·恩多羅(Webber Ndoro)和基爾伯特·皮韋迪(Gilbert Pwiti)對南部非洲的物件、地方與實踐是如何一步步完成遺產化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③Webber Ndoro and Gilbert Pwiti, “Heritage Management in South Africa: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PP﹒ 154-168﹒,該過程也是地方社會被逐步剝奪與排斥的歷史。其實,上述現象在世界范圍內都在發生,即“成為遺產”意味著對物件、地方與實踐等資源的捕獲,同時發生的是對當地社會和群體的剝奪與排斥。學界所熟知的博物館化即生成了物件、地方與實踐的脫嵌:一方面從原初文化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價值的變遷。④尹凱:《物的詮釋與溝通——當代博物館藏品的學術思考》,見《中國民族博物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7頁。雖然新博物館學和遺產運動對此去情境化的困境有所反思,并試圖以露天博物館、遺產中心、主題公園、遺址公園等在地化的實踐來修正博物館化對當地社會的剝奪與排斥,然而收效甚微。只要一種資源被發現具有遺產價值的建構潛力,那么隨之而來的就是當地人群的轉移、搬遷,遺產規劃對時間的凍結,物件、土地所有權的轉讓,遺產可參觀性的制造,遺產名錄的生成,去日常化的官方闡釋等一系列過程。即便是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一遺產過程在實現與國際理念接軌的同時,也在地方層面實現脫軌。
如果說“成為遺產”意味著遺產與地方社會的分離,那么“成為遺產之后”的階段則是地方社會能動策略得以彰顯的過程,即以另一種姿態再次占有、整合遺產。 這時,地方社會能夠動員政治議程、自我意識、生存策略作出應對,并以新的面貌重新影響當地社會。這一能動策略可能是隨即出現的,也有可能有一定的滯后性,無須擔心它在歷史上的缺席。
20世紀70年代,有關隨葬品、宗教圣物、儀式用具等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文物返還訴求,以及有關人體遺存的遷葬議題便是如此。諸多討論試圖從普世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夾縫中尋求出路,進而實現認同尊重和文化和解。⑤約翰·梅里曼編:《帝國主義、藝術與文物返還》,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在此,筆者更為關注的是歸還所生成的遺產過程議題,不能否認的是,當地社會對遺產的再次占有與遺產的重要性密切相關。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當地社區因為先前被剝奪與排斥的事實而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這導致了與遺產相關的衍生現象的出現,即借遺產之名行土地、自決、認同、話語之實。當重新獲得失去已久的遺產之后,當地社會面臨的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局面,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與調適被打破的文化體系。這就涉及到遺產歸還之后的地方社會何去何從的議題,有些地方群體就遺產歸屬展開爭奪,有些群體則借遺產之名建構泛化的普遍認同,甚至導致了群體認同與群體關系的劇烈變動。①Jane Hubert and Cressida Fforde, “The Reburial Issu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16-132﹒“成為遺產之后”所發生的種種現象不僅體現了當地社會的能動策略,而且還涉及到了地方文化的重新整合。
就理論層面而言,當地社會的能動策略一般應出現在“成為遺產”的過程中,與國際標準、專業知識共同協商、對話,共同制造遺產產品。然而,在實際的操作層面,制度化機構、科學知識體系、理性與實證精神、秩序化訴求等外部聲音讓當地社會處于沉默狀態,由此而來的是自我表述和能動策略在破除認為“成為遺產之后”的重新崛起。當地社會經由遺產賦予的光環而“制造”文化、進而追求經濟收益的行動隨處可見,這不能被輕易認定為是遺產的經濟功效,而應該放置在整個遺產過程路徑中來予以理解。
四、余 論
從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到樹木保護法規(Tree Preservation Order),從官方層面到個體層面,人類會發明不同的機制來保護那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物件、地方與實踐。②Peter Davis, “Places, ‘Cultural Touchstones’ and the Ecomuseum,”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405﹒對于保護事實來看,基于宗教、性別、年齡、階層的傳統機制與基于文明的遺產機制在本質上是具有同等效力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的特殊重要性來自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情感、地方體驗與地方精神,而后者的特殊重要性則是一種外在于當地社會的科學知識、文明理念和價值標準。這種固有的張力有可能導致如下情況的出現: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且被當地人認為是有價值的鮮活資源難以被遺產價值體系承認;一些在喪失地方特色,且被該地方的人認為早已經失去生命力的資源卻獲得遺產價值體系的青睞。不能否認的,特殊重要性的內外認知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即被認定的遺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對地方社會來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資源。
遺產議題與生態博物館學其實有很多的相似性。在生態博物館學領域,加拿大博物館學家皮埃爾·米蘭達(Pierre Mayrand)提出了“生態博物館的創意三角”(The Ecomuseum Creativity Triangle)。③Peter Davis, “Places, ‘Cultural Touchstones’ and the Ecomuseum,”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10﹒在經由闡釋提升某個地域的公共意識和知名度,隨之建立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又會帶來有關當地社會和專家學者的反饋,進而反饋給闡釋,如此循環反復。這與“成為遺產”和“成為遺產之后”的兩個過程路徑如出一轍。
在遺產項目中,民族國家、身份政治、地方政府、經濟利益等要素將介入其中。無論是遺產研究還是生態博物館領域,在具體的項目與實踐操作中,當地人在從資源到遺產的制造過程中似乎是沉默失聲的。這種看法恐怕小看了當地人的能動策略和生存哲學。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破除認為“成為遺產”即意味著遺產過程的完結的想法。在筆者看來,遺產的過程路徑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成為遺產”的過程,二是“成為遺產之后”的過程,兩者共同構成了循環而完整的遺產過程路徑。“成為遺產”意味著遺產與當地社會的脫嵌與分離:這種分離有時候體現為可見的資源遷徙與入藏,有時候體現為不可見的資源解讀與闡釋。此外,“成為遺產”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剝奪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景觀:這種剝奪有時候以異地搬遷的形式出現,有時候則呈現為新的建筑形態對土地的占有。當某個物件、地方與實踐被認定為遺產,并成為遺產之后,隨之而來的是長久以來被壓制的當地聲音的吶喊。這種憑借所有權、闡釋權和文化權利等手段而合法化的地方話語往往要求對遺產的重新占有、整合和挪用。這種地方社會的生存智慧有多種意圖:有時候要求物件的返還,有時候要求土地的權利,有時候要求經濟的收益,有時候要求文化的自決。因此,在具體的能動策略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比如根據自身考量重塑某些物件、地方與實踐的真實性,根據觀者需求操弄文化的展示與表演,根據遺產的光暈壟斷地方的生意與經營。在上一個過程中被剝奪與消費的當地社會,在這一個過程中卻奇跡般地成為能動的生產者,它根據自身的諸多訴求而將遺產這個外來的異質元素重新整合到自己熟悉的文化體系中,完成文化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