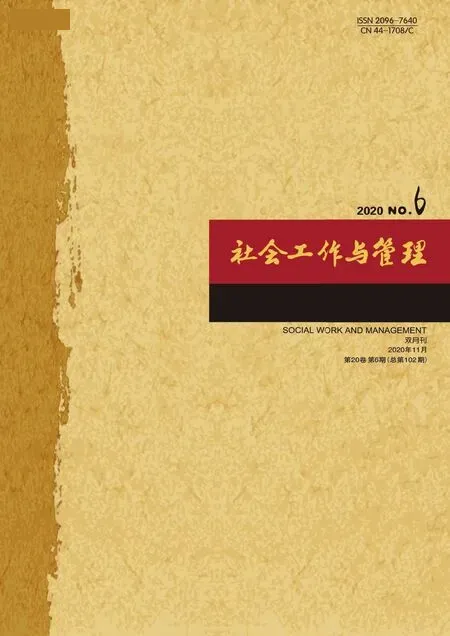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的源流、框架及其展望:不確定時代的專業責任
楊 锃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上海,200444)
一、問題提出
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而人們恰恰是在生活世界的行動中,在應對種種偶然事件和充滿挫折的實踐中,追尋著確定性的認知。[1]62020年年初以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世界,令人陷入不安,甚至莫名焦慮。當我們時而擔心當下、時而恐懼未來時,當我們時而猜忌他者、時而孤獨無助時,當我們甚至感到話語世界充滿荒誕時,那必定是觸及到了人的“存在性危機”。作為探究存在意義并試圖化解存在不安和焦慮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存在主義一直引人注目。雖然在社會工作理論中,存在主義從未成為其理論中的主流,但必須承認的是,這股思潮對社會工作仍產生著不可低估的持續影響。
在本土實務運用和對社會工作的理論探討中,理論與實務并行的取向正逐漸顯現出來。在理論探討方面,通常是基于哲學基礎與價值觀,以追尋存在主義對社會工作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人本主義則被認為是社會工作的四大哲理基礎之一,而薩特把存在主義哲學與真正的人本主義結合起來,這一立場因而注重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尊重個人對自身經歷的理解和解釋,其觀點構成了以實踐為核心的社會工作的價值基礎之一。[2]值得指出的是,存在主義更多聚焦于個體層面,鮮有直接指向宏觀整體層面。在實務研究中,雖也有運用存在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并試圖展開本土生命教育的實踐,但基于存在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主要運用在臨終關懷上。在這一領域,存在主義為本土社會工作實務提供了價值基礎,也對重新建立受助者的意義圖景具有啟發功能。在以存在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探討方面,存在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試圖用不同方法去理解個體的內心世界,強調對人的完整理解,但似乎尚未發展出成熟的實務體系。
但不可否認的是,就加深對人類心靈的理解并給予深層關懷而言,存在主義尤其是其現象學的面向是極其值得重視的。當今,無論是作為對抗系統論而登場的社會建構主義,還是被社會工作理論所重視的“敘事療法”,就其方法論的根基而言,無不與現象學理論及其運用有著深刻的聯系。當我們探索存在主義對社會工作產生的影響時,有必要將其重新放置于現象學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近10年來,有研究也嘗試運用存在主義理論開展社會工作實踐探索。回顧并反思實務探索,已有社會工作研究將存在主義運用到對邊緣人群的援助中,以期對他們重新構建自我意識、控制力和未來取向做出有力應對。[3]面對遭受天災人禍、身患疾病陷入苦境、甚至飽受喪親之痛的人們,社會工作者常感肩負著責任,并投入到精神健康服務與社會心理援助中。比如,為理解癌癥末期患者的生存狀態,有研究試圖通過考察患者自身存在狀態,并歸納出從體驗疾痛的存在狀態到改變存在狀態的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的洞察,并依據所歸納的模式以期對臨終關懷社會工作提供有益啟示。[4]在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技術化的心理治療正在日漸興起,但社會治理體系中仍缺乏對心靈治理的深入關注。[5]個體被拋入某種受助者從未遭遇的充滿不確定性的、甚至是危機的情景之中,也就意味著進入一個需要持續修正主觀認知的過程,換言之是一個持續展開自我心理建設的過程。而面對人們普遍遭遇的疾痛,尤其是“社會苦痛”以及這類社會苦痛導致的群體性精神狀態時,社會工作就有必要借助存在主義理論,總結出對實務行動有益的應對方式。
當然,采用存在主義立場的社會工作者自身在面對“服務成效如何”的問題時,也會產生某種存在價值的焦慮。這恰恰是為“規訓社會”向“績效社會”的轉向提供了反思契機。[6]在面對績效主體要求提供有成效證明時,類似于打造“有用”的自我形象,社會工作者是否屈從,就意味著選擇了某種存在的模式。
而存在主義的重要之處在于,可促進社會工作者自覺其作為援助者的立場和責任,對理解援助方案、援助方法及具體援助情景提供重要啟示。社會工作被認為是一個專業助人的專業,其基本內涵是具有福利性的專業助人活動。[7]可以說,利他性質的專業“援助(helping)”,即增進福祉的專業助人構成了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這一影響首先體現在存在?人本主義的心理治療上。在歐美,隨著維克多?弗蘭克爾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療普及,心理治療發展為一種意義療法。[8]115-120這一追問人存在意義的存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也被社會工作在提供援助時所采用;特別表現在當受助者所面對的問題或者苦痛無法以醫療途徑解決時,比如患有不治之癥,或因故殘障,或即將面臨死亡而墜入絕望感,或因親人離世而悲痛萬分。當人們面對客觀上無法改變的艱難處境之時,人何以“存在”的問題就會凸顯出來。盡管存在主義理論無法完全、也不可能在治療時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對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義的深刻洞察,足以啟示其改變處置這類問題的主觀態度。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著重探討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存在主義譜系之中“存在”的含義,并理解其“人觀”,進而探討其對社會工作專業援助的啟示意義。二是理清存在主義社會工作中的核心概念,并提示其援助過程中的一般化框架。三是基于歐美社會工作研究,探討存在主義產生的主要影響。四是討論存在主義對社會工作發展的可能性。
二、存在主義改變人觀
存在主義源自逐漸世俗化的近現代社會。這一思潮是思考人存在的意義而形成的一股曾經席卷西方的社會思潮。丹麥的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創始人。正因為“創始”,也常常被列在現代存在主義發展的主線之外。作為創始者,克爾凱郭爾是孤獨的,又擁有虔誠的信仰。他強烈質疑黑格爾所建構的哲學體系,即在廣義上對人的能力(尤其是理性和智慧)所表現出的徹底信賴以及樂觀,認為依賴這一理性的力量能夠把握自然和社會法則,即所謂黑格爾式的辯證法,尤其對被狄爾泰概括為“客觀觀念論”的理性觀念論表達了猛烈批判。在他看來,理性觀念論所認為的,唯有普遍理性的客觀存在及其運動才是本質和真實的觀點,恰恰是非真實的;而每一個個體的個別性,才是一種客觀而普遍的本質,對其存在的探究才是真實的。[9]
從克爾凱郭爾對黑格爾觀念論的反對之中可以看出,存在主義不在于追求人類普遍而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試圖確立起人的“存在先于本質”的觀念。面對抽象的普遍理性與客觀法則,存在主義關注的是面對具體現實時,作為感受到具體存在意義的個體各自在現實情景中如何理解自身存在的問題。重視從個體出發的克爾凱郭爾顯然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用“存在的(existential)”一詞來特指個體不得不面對的社會生活。由于個體的獨自性,這一日常存在的自我拒絕被同化,試圖堅持做自己。因而導致這一自我是憂慮的,正如其所感慨的那樣:“憂慮是自由的眩暈。”[10]31
(一) 理解存在
因此,追溯存在主義的發源,令人意識到,理解存在主義就必須理解受其影響而構筑的人的觀念(以下簡稱人觀)的變化。作為一位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早年被克爾凱郭爾獨立反抗宏大敘事哲學的勇氣和精神所吸引。在他那里,克爾凱郭爾式的存在得到了進一步強調。他摒棄了克爾凱郭爾思想中濃厚的宗教層面的內容,但繼承了反抗精神,試圖在關注選擇、行動和自我肯定中,建構出“存在”的新意涵。
對人的存在的絕對性上,薩特強調的是人的自由與選擇。在他看來,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通過自由承擔責任,任何人在體現一種人的類型的同時也體現出了他自己。[11]26因此,在作為自我承擔責任、作為存在選擇其“自由存在(free being)”與“絕對存在”之間也就沒有了區別。結合薩特一貫的無神論立場,正如蓋伊所評述的那樣,人類在沒有神的世俗生活中,感到了新的自由,但同時也強化了責任;甚至可以說,在強調人的責任這一點上,存在主義也是最嚴苛的。[12]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存在主義試圖構建一種“嶄新的人觀”。正如薩特所強調的那樣,在存在主義者眼中,人是由其自身造就的——即意味著,人通過自己的道德選擇進而形塑了他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種道德選擇,這其中主要有來自環境對他的壓力。[11]29因此,存在主義的人觀并非傾向于談論某種普遍的“人性”,而是更積極關注并洞察“人的處境”。的確,以助人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也同樣需要細致把握受助者及其被拋入的具體處境和應負的責任。從這一意義上說,存在主義式對具體人的處境的體察是展開社會工作介入的先決條件之一。
啟發性還包含在存在主義者的價值選擇之中。在薩特看來,存在主義者還必須具有一定的價值選擇,因此其強調,存在主義者“永遠不會把人作為目的”,因為存在主義堅信人始終在“形成之中”。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者是指人始終處在自身之外,依靠自己跳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存在;另一方面,人則是依靠追求卓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的。[11]35因此,對照上述價值選擇,樹立起利他主義價值觀的社會工作者,在反身性地對待自身的援助過程和援助目標時,不妨也可汲取存在主義式的人道主義觀的豐富養分。
總而言之,從存在主義的思想譜系中概括什么是存在主義并非易事。不過參照貝克韋爾的概括,對上述存在主義者是可以加以定義的。其一,存在主義者關心個人,是具體的人類存在。其二,他們認為,人類存在是特殊的,因為“作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選擇我想讓自己成為的樣子,我是自由的”。其三,因此,我對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負有責任,這一事實會導致一種焦慮——這種焦慮與人類存在本身密不可分。其四,人只有在境遇中才是自由的,這一境遇不僅包括人的身心狀況,而且還包括人被拋入的世界中的那些物質、歷史和社會變量。其五,如果從現象學角度看待這一境遇中的存在主義者,會傾向于關注描述生活經驗本身的樣子。其六,通過充分描述生活經驗,人希望能夠理解這種存在,以喚醒自身去過更真實的生活。[10]49-50
那么,何為存在本身?這一問題在出生于德國梅斯基爾希的海德格爾那里得到了系統詮釋。他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箍桶匠兼教堂執事,而祖父則是一名鞋匠。據他成年后的回憶,作為匠人的子弟,童年的家庭生活對其一生影響深遠,令他無法忘卻因此而喚起對那個匠人世界的忠誠。[13]他的思想也總是回到家鄉的黑森林,因而為其著作之一冠以《林中路》的名字。在其代表作中,海德格爾試圖總結“存在”的含義: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者,即不是任何可被定義或描述的實體,為此需要專門區分任何單一實體(Seiende)和特定存在所擁有的“存在(Sein,Being)”①——這是他所強調的一種本體論上的區別,也就是研究“存在”的學問。[14]存在與存在者的不同之處在于難以指明,因而容易“忘卻”。因此,他提醒,作為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這不僅意味著從“存在”起步,而且對“我”這一自身存在有待質疑的存在,要保持恒常的警惕和細致的洞察。在這一意義上,海德格爾式的存在主義為生活在戰爭間歇期的動蕩時代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強大而個體化的哲學。不過,這只是存在主義其中一個側面。而另一方面海德格爾則認為,始終保持恒常的警惕和細致的洞察是勞心勞力的,所以個體的存在可能陷入到某種“煩膩”的精神狀態之中,這是構成“多重神經失調”的原因。
因此,海德格爾極為關注精神層面出現的某種意義崩塌的狀態。這類崩塌可大可小:小到一根釘子在錘子釘打時的彎曲,大到面對最嚴重的不公正(比如慘遭死亡的可能性)。在一些人的遭遇之中,日常在世存在的崩塌,令其感受到了平常漠視狀態之下從未產生過的突兀、脫節,甚至斷裂。這樣的經歷堪稱“精神崩潰”,導致神經失調癥的發生。[10]99-100海德格爾考察存在問題時運用了現象學的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與胡塞爾所指的現象學是有所不同的。在他看來,現象學不是一種單單被稱為某某學(-ology)的分支性學科,而是關心“事情是如何被切近的”,即現象學作為一種“照亮式”的方法,試圖通過揭開隱藏著的或遮蔽著的東西,讓我們能夠看見。[15]
按照精神病理學家艾倫伯格的理解,對于“存在(being)”與“存有(existence)”的區別已有了更明晰的區分。[16]150首先來自狄爾泰,他認為,死氣沉沉的物體與人的存在之間必定是不同的。海德格爾哲學正是在狄爾泰解釋學的基礎上比較了作為“現成存在(Vorhandensein)”的與作為“此在(Dasein)”存在的事物,并指明了“此在”是人類存在的特有形式,因而才有了“存在的問題只能通過存在本身得以理順”的判斷。因此,在精神病理的臨床層面,存在主義的心理學與現象學的精神醫學之間相互關聯,在20世紀60年底前后形成了一種從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進路來理解和開展治療的探索。
(二) 現象學的精神醫學與存在主義的心理學
存在主義對臨床精神醫學和心理學都產生了不小影響。按照羅洛?梅的概括,其首先促成了存在主義心理學的發展;同時對F?斯托奇、H?昆茨等精神病理學家產生了影響;以賓斯萬格為代表的存在分析為代表,實質上建構了一種新的精神病學體系。[16]151而就20世紀60年代而言,當時受存在主義現象學影響而展開的臨床精神病學探索,則為社會工作者理解精神障礙以及探究精神障礙者的意義世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國的精神病理學家萊茵。
萊茵深受弗洛伊德、薩特等人的影響,形成了“存在主義與現象學相結合”的精神衛生觀。他曾選擇了11位患者在實驗病房展開了心理治療,使所有患者都出院了,但未滿一年后,這些患者又都重返醫院了。[17]這一臨床實踐的經歷令他關注造成精神障礙的社會根源。在此后,他試圖建立起一種完全有別于克萊普林(Emil Kraepelin)式的所謂“科學的”精神病學,而主張重新確立起一種對瘋狂意義的新理解。
在萊茵看來,人或是向外在空間展開探索,或是向內在空間進行自省,都易陷入“存在的不安”。但人們往往把“陷入內在空間與時間的做法認為是反社會的逃避”。[18]因此,他提議,開啟精神醫學的新時代就是意味著應允許人對其內在空間的探究。萊茵認為,自我在內在空間探究之中是有可能“自愈”的。他甚至把精神障礙者自愈的過程比作自我“航海”,而精神醫生的立場則是援助其出航,理解并不斷鼓勵“航海者”。因而在他的眼中,這一內在空間的航海過程正是重整自我的過程,有必要得到周圍人的援助。精神科醫生就應當擔負起這一過程的支持者角色,成為“航海者”的引路人、守護人和援助者。可以說,萊茵的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基于對被現代理性主義所異化的人際關系及其欺騙性的揭露,也重塑了一種臨床精神治療的關系觀,其嶄新的精神衛生觀及其臨床實踐超越了傳統精神病學觀念,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芒。[19]
存在?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師的立場也與萊茵所強調的“引路人、守護人和援助者”的角色有著諸多相通之處。這首先體現在對“對話”的重視上。無論是莫里斯?弗里德曼(Friedman)[20]13在治理中引入實現心理功能的“對話”方法,還是亞隆重視安全與親密的治療關系,[21]均受到了布伯所凝練的“我?汝”關系的啟發,強調在治療師與來訪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基于對等人格的信賴關系。只有這樣的關系才能實現來訪者的改變與成長。這不禁令人想起布伯對如何讓荒蕪的人格真正重獲生機的闡述:“能夠做成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通過醫生的那種偉大眼神,把這顆受苦的靈魂的已然被掩埋的沉寂的統一看在眼里,而要做到這一點,一定是采取人格面對人格的那種伙伴式的態度,決不是當成客體來觀察、研究。”[22]122-123這一“人格面對人格的伙伴式態度而構筑的關系”可謂是對社會工作專業關系的最佳注釋之一。生命影響生命之所以能夠實現,即依賴于這種關系的建立。其次是明確心理治療的目標,即協助來訪者根據他們的理想去實現他們的生命意義。在治療過程中,來訪者要征服過往的障礙,終結類似海德格爾所指的“意義崩塌”的精神狀態,重新煥發生命活力,有著一系列可能路徑。或可采用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或可協助來訪者想象新場景、內在資源、具體行動,或者加以角色扮演;或可協助其反映其夢境、與夢相關聯的符號、模式和情感等;或協助其挑戰自我,到更具現實情景之中去獲得新的能力。總之,這些協助來訪者的探索都是為了在激勵其體驗生命活動之中,去調動起對生命意義的主體性感知。[20]81-82無論是萊茵,還是施耐德等人,都強調建立起一種新的援助關系。這充分體現出存在主義既看重培養個人內在主體性,又關注助人者與受助者人際關系的核心立場。
因此,當面對的是豐富而復雜的人性問題時,存在主義對人的理解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對現代人觀的形塑有以下兩方面的積極意義。一是存在主義人觀的核心是在自由選擇中成為對自己負責的人;二是作為行動的學說,存在主義是樂觀派,主張人是有“希望”的。[11]36即便如此理解,存在主義的人觀仍顯得不太能“清晰化”呈現出來。其中的主要分歧、甚至爭論是尖銳的,指向概念意涵、并帶有價值取向:對于實證主義者而言,存在之所以無法構成一個概念,乃是因為其空洞、稀薄了,最終也就失去了意義。但依照克爾凱郭爾的觀點,“我的存在”之所以不是一個概念,乃是因為它“太稠密、太豐富、太具體”了,因而不能夠由一具心理圖像充分地加以表象。[23]399之所以提出“存在主義的人觀”,是由于存在主義豐富了對人的理解,對思考人的價值、尊嚴和自由是極具啟發意義的。
三、存在主義社會工作:核心概念與援助框架
存在主義思潮真正進入社會工作領域并展開實踐探索要晚于心理學和臨床精神病學。在社會工作層面,所謂存在主義社會工作,通常被理解為,從個人的基本自律、選擇自由和支配性的社會慣習中得以解放,從苦痛中引發改變的意識,通過必要的對話,并尊重受助者自我決定之中,強調社會工作介入的一種理論視角。[24]150
(一) 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的核心概念
克里爾是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參照克里爾的觀點,存在主義社會工作有5大核心概念,即選擇自由(freedom of choice)、幻滅(disillusionment)、苦痛的意義(meaning in suffering)、對話的必要性(necessity of dialogue)以及承諾(commitment)。上述每個概念在存在主義中都有一定的具體含義。[25]251-259
理解“選擇自由”就必須是基于存在主義的人觀。存在主義認為,當下的此時此地所存在的我是一切的出發點。在這一時空中,自身存在無法與他者進行交換,其存在方式和發出行為體現出當下的唯一性(一次性)。人的行為是連續選擇的結果,而行為的一次性,注定了人常常面對所逼近的選擇,在此時此地不得不做出無法重新再來的“一次性”選擇。行為的選擇因而有可能是自由意志所做出的,也有可能是被強制做出的。在行為選擇這一點上,其“行為——選擇——形成行為體現”與“行為——判斷——選擇”之間,自然會受到或是處于慣習、或是基于意志、或是主動抑或為被動的“價值判斷”體系的支撐。正是基于上述意義,在行為上,人總是不時地在選擇中呈現出反映這一選擇的價值判斷。無論人是有意識地做出選擇,還是在無意識中做出了選擇,都是在情景中,通過對人自身行為及其存在所賦予的意義加以批判分析的路徑才得以呈現出來。
需要對核心概念“幻滅”進行理解。幻滅常發生在人所無法面對的新的情景之時,在這一情景中,一貫沿用的價值體系不再起作用了。幻滅與無聊、絕望、虛無等對一切價值和意義的否定相通。幻滅往往發生在人直面死亡、衰老、病痛以及遭遇殘障而陷入苦痛的時候,在這些遭遇面前的人對以往所堅信的價值觀表示出懷疑,產生幻滅感。而存在主義恰恰可以說,是在人經歷著絕望、虛無等經驗過程中強調對人的內在世界的理解和表白之中產生的。而所產生的幻滅感和懷疑則能夠成為對自身以往日常性存在的批判性根據。尤其對于介入援助的社會工作者而言,須要理解人所遭遇的幻滅及其導致幻滅感的原因。通常苦痛源自人所處的客觀狀況與主觀感受的意義和價值之間的落差。這一落差越大,所產生的苦痛感則越強。在外部提供援助與治療時,當無法改變客觀狀況時,就有必要運用存在主義的進路,援助者須嘗試建立起與受助者之間的對話,通過對話,援助其探索新的價值和信念系統。在這一介入路徑之中,受助者所遭受的苦痛在援助者那里需要重新確定出一種肯定性的意涵,即正是在遭遇這一系列的幻滅之中,受助者有了重新構建價值系統的契機,也正是在克服和超越這一幻滅感的過程中,才能實現真正的成長。
在幻滅之前,人通常首先體驗到的是無法順利處置的“苦痛”。因此第三個核心概念是“苦痛的意義”。人生在世,必然會遭遇苦難。如果面對苦難,無法構建起對苦痛意義的積極理解,就容易跌落入虛無主義抑或快樂主義之中;如果逃避苦痛,僅僅追求快樂,則容易陷入快樂主義;而如果為了追求治愈,直到最終追求治療的可能性,則其態度往往顯得逃避苦痛,甚至拒絕思考苦痛的意義而陷入虛無。相反,在遭遇和經歷苦痛時,如能夠挖掘苦難的意義,并能夠轉變為發現存在價值的契機,則有可能促使苦難轉變成為成長過程中的寶貴財富。但是,現實中,極少有人能夠通過自己獨自的努力而實現對苦難理解的改變。能夠如愿將苦難轉變為改造其價值系統的源泉,通常需要有他者的援助。
當陷入苦惱時,人就有需要聆聽和傾訴的對象,“對話的必要性”就此產生了。如果有一位樂于傾聽、能夠理解其苦痛的人能夠出現在苦難者的身旁,那就促使陷入苦難中的人或意識到新的可能:此時此刻的苦惱將啟示其人生下一階段的方向。也就是說,人是在回應導致苦難的狀況之中形塑自身的意義系統的。這一意義的形塑將成為行為選擇的基礎。那一時刻,為了能夠擺脫困境、獲得成長,就有必要獲得對自身的新認知。這一認知不是自身憑空想象所能確立的,而是依靠聆聽者的反饋而感知。這就要求產生對話的對方必須是受過訓練的、出色的聆聽者。只有能夠同理訴苦者,切實理解其困苦的狀況,才有可能在開放式的對話中,令苦惱者平復情緒,感受到被理解的同時整理自身的思緒,并經歷重新點燃生命意義之火的過程。存在主義的進路,之所以強調對話的必要性,與重視主體間關系化存在的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存在主義社會工作就是基于這種人際的關系性,通過對話的過程,發現本真、追求價值轉換,實現通過主體間的聯結力,最終發揮助人的作用。
通過對話產生的主要功能是實現“承諾”。承諾指向被援助者通過對話的過程,最終對自身處境和生活方式有了重新認識,并有了從自我哀憐和無力改變的狀況中脫離出來的積極性,也常在此時向援助者主動做出對自己負責的承諾。這一實現承諾的過程,體現出在臨床社會工作之中,專業援助關系建立的原則——即一種“助人自助”的關系性基礎。其中突出體現出建立專業的援助關系時引發被援助者產生積極改變的本質性要素。
(二) 基于存在主義的一般化援助過程
如前所述,基于5大核心概念之間的相互關聯可見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的一般化援助過程:被援助者從“自由選擇”到產生“幻滅”,再到理解“苦痛的意義”,進而認識到“對話的必要性”,最終在與援助者的援助關系建立過程之中,實現對自己負責任的“承諾”。上述一般化的過程,始終體現出被援助者為中心的立場,這一立場與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立場是密切相通而契合的。這一過程中,被援助者如果能夠在專業社會工作者的援助關系之中,通過對原有自身價值系統的不斷反思,進而努力建立起新的價值和意義系統,就能在援助者適當的回應與陪伴中,主動做出適合自身的選擇。
四、社會工作對存在主義的應用
(一) 歐美存在主義社會工作的探索
在歐美,存在主義對社會工作理論及其實務研究帶來了持續影響。這一影響首先是有其時代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美諸國都采取了加快經濟發展為主的合理性政策。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雖然經濟改善帶來了物質充裕的狀況,卻似乎并沒有充分改變個人主觀幸福感受。相反,因人的主體性未被重視,社會心態則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最初對存在主義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弗蘭克爾的著作《一個心理學家所經歷的集中營》(EinPsycholog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1953),被翻譯成英文版Man's Search for Meaning(1963)進入英美之后一版再版。在20世紀60—70年代歐美社會在世代之間的代際割裂、社會運動高漲、越戰泥潭以及“水門事件”和石油危機等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劇烈變動的背景之下,弗蘭克爾自身在納粹集中營中的經驗體驗,受到了公眾們的廣泛關注。
存在主義受到關注并獲得一定影響力,與20世紀50—60年代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在這股人本主義的潮流中,不僅有K. Horney、C. G. Jung、Moustakas,還有A. Maslow、C. R. Rogers和G. Allport等心理學家。存在主義被運用到各種心理治療和心理援助過程之中,比如格式塔療法、理性情緒療法,同時也影響了以萊茵為代表的現象學的精神醫學。[19]
不過,在社會工作領域,圍繞存在主義展開的代表性論文則集中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根據梳理,David Weiss、Donald Krill、Gerald Rubin、Robert Sinsheinmer和Margery Fronhberg等人就在社會工作的相關專業期刊上發表了若干論文,討論如何將存在主義哲學運用到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之中。[26]184最初出現的著作是Bradford所撰寫的《存在主義與個案工作》。[27]此著作對存在主義與社會工作以及心理治療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并對當時的一些探索做了概括。進入20世紀70年代,至少有4本主要的著作與存在主義社會工作密切相關。最初對存在主義的運用在探討小組工作的著作中,展現出小組工作中存在主義的要素。[28]其后,Whittaker在其著作中對存在主義做了充分肯定,認為其構成了對社會工作最具貢獻的4大理論之一。[29]Weiss則在《存在的人際關系》(1975)之中具體探討了社會工作所開展的各個層面都可以應用存在主義哲學。[30]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當屬《存在主義社會工作》(1978)。[25]在該著中,Krill面向社會工作者,對存在主義產生影響的心理與系統兩個層面都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探討。此后,該書也不斷再版,2014年刊出了最新版本。
(二) 存在主義社會工作
上述研究展現出存在主義在社會工作中有著廣闊而豐富的應用,其中主要影響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在對人援助的關系建立中,基于存在主義立場,理解作為存在的人;二是在社會工作專業性的研究中,通過基于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對專業援助關系建立中的“理解”、“接納”和“共情”等概念嘗試進行再解釋,并指導專業實務工作的開展。
第一,基于存在主義,有助于在援助者與被援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深層次的援助關系。這一援助關系的建立,首先有賴于社會工作者在援助的現場,能夠建立起對“作為存在的人”的被援助者之理解。對人援助的場合中,最令被援助者感受到“實存”狀態的,就是在他/她處于臨終的時期。此時的人不再關心抽象的、觀念意義上的人的一般的死的意義,而在于當直面“我之死”的時候,產生了對“我之生”意義的追尋。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現實具體的個體“存在”是先于抽象意義上的存在“本質”的。海德格爾在分析人的現實存在狀態時,就將“人之死”提到本體論的高度,認為“向死而在”才能獲得人的真正自由,而獲得這一自由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先行體會“我之死”,即令自身“先行到(死)的可能性中去”。[31]一方面,由于臨近死亡的人是沒有將來的,因此就必然專注于回憶過去,在回顧過去的過程中,試圖對其存在給予一個“整體性”的認識。而另一方面,由于對死的自覺,就會對原本一直感覺到親近的日常生活產生距離感,覺察到其中的虛妄,因而對一直以來所處的日常世界,即對那種以往被認為是“自然而然的態度”開始有了批判的眼光。對日常生存的批判,通過有限的、“向死而在的我”進而成就“本真的自我”,或者說引導其邁向追求不滅的永恒。這意味著,有限的存在促進了本真性的發現,進而促使作為存在內核——“靈性”的覺醒。
因此,靈性的覺醒常被社會工作所重視。靈性意味著我們在存在意義的表達之中,對神圣的事物所做出的一系列回應。[32]這些回應直面死亡,意識到從死的來臨的人的存在狀態生發出對生命意義的探究、對日常性的批判、對本真自我的發現以及試圖重返整體性和本真性的努力,即意味著試圖從有限的生命邁向追求永恒的超越。這些價值系統實現的轉換對于面臨問題而思考存在意義的人而言,將構成其重要的課題。對于社會工作而言,存在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僅僅面對被服務對象是面臨死亡的人。只要在服務的現場,面對的是有關存在價值、意義及其超越性的主題,社會工作者都可以基于存在主義理論,通過和被援助者的對話,共同探索如何實現價值系統的轉換。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存在主義有助于使社會工作者與被援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更深層次的互動關系。因為,存在主義社會工作一方面極為重視與被援助者的問題相關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則將被援助者視為人格對等的人,在充滿人性化的援助過程之中,試圖建立起類似馬丁?布伯所倡導的應當達成的“我?汝”關系。[22]這一關系的基本經驗模式就是“對話”。“對話”使被援助者真正“參與”其中。這一關系又類似亞隆所強調的咨詢者與被咨詢者之間的關系。對話的實現既不是由社會工作者創造出了參與感,也不是激勵被援助者去參與,而是在對話中,令其心中本來就存在的參與生活的愿望被激發出來。在這一關系之中,社會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是其自身,通過自身與被援助者建立起深刻的、真誠的對話關系,并指導其與他者建立關系;在援助者進而認同與社會工作者之間所建立起的信賴關系的時候,也正是社會工作實現專業使命、促進被援助者的成長、幫助其建立起新的認知去尋找意義的時候。[21]511
對比上述互動關系的建立,中國人常被認為有著獨特的“關系性人格”。相比西方的人際互動,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宗法家庭”才是構成人與人之間的存在之基。[33]而中國人之所以有著獨有的社會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由于基于對宗族和家庭中“人倫”的重視。中國人找到其自我存在的位置,是由于他在最基本的人倫關系中找到了明確的位置。一個人先要成為一種同親同族的共在,履行好在家族和宗族中的義務,才會成為他自己。[34]這恰恰對理解中國社會工作專業關系的建立路徑提供了重要啟示。在關注被援助者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去關注他的社會生命之根——其家庭系統和家庭生活。
第二,從存在主義視角理解援助關系,可以增進對社會工作專業性的理解。其一,基于存在主義的援助過程,一旦能夠達成受助者價值系統的轉變,就必須依賴于社會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所形成的援助關系。唯有援助關系,才是構成導致受助者價值觀變化的根本性要素。這時,選擇存在主義進路的社會工作所體現的專業性,首先呈現在受助者及其作為問題的、那些無法被置換的、且具有獨特性的、在認識自身成長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意義理解之中,即世界觀和價值觀之中。其二,存在主義為理解社會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的援助關系提供了理論啟示。當社會工作者意識到與受助者所建立起援助關系之時,社會工作者作為援助者的專業性才開始呈現出來。社會工作者從自身的生活經驗和意義世界出發,對受助者所產生的同理、共情,實際上是需要將受助者的生活經驗、意義世界作為鏡子來加以對照的。只有在這一映照之中,才能理解受助者及其所處的情景,也正是在這一與受助者同行和陪伴之中,才有相互作用,進而使受助者感受到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價值觀,對利他精神的純粹助人舉動產生信賴感。
總之,在援助者與受助者的援助關系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在社會工作幾乎所有的援助活動中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正是由于這一普遍性,在幾乎所有的社會工作理論中,援助者與受助者之間的關系建立成為助人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也正是在這一前提和基礎上,存在主義的進路為尋找更具文化感受性意義的社會工作實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五、結論與討論:存在主義社會工作再檢討
20世紀60年代以來,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之間發生了幾乎白熱化的論爭。結構主義從某種科學認識論向一種思想立場轉變,而存在主義被認為是在為主體中心思想做最后的辯護。對傳統思想的抗拒,導致結構主義必然向著新的、探索一種“結構的哲學”而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人的主體或者說主觀性,既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成為形成世界的能動者,相反,“人”這一主體則僅被認為是結構中的一個要素,成了結構所形成的各種關系之中的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承認,結構主義或者說關系主義成為了導致現代人觀和社會觀發生轉換的導火索。由于結構主義使得包含有存在主義的思想大廈之基松動了,就社會工作中的應用而言,存在主義社會工作遭受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存在主義因其價值立場而回避了實證傾向的社會調查;其次,主流存在主義由于缺乏具體的人格理論,而顯得過分強調主體性和獨自性;再次,存在主義體現出過度的價值關懷。上述這些因素都導致運用存在主義開展結構化研究是有其困難的。這也導致存在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影響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存在主義社會工作把握個體的“苦難意義”,理解具體“對話”的必要性。這恰恰構成了去物化的“人觀”理解,蘊含著某種非結構化的結構,也指向一種去普遍化的普遍性。正如雅斯貝斯所斷言:存在哲學在再次包含“某種相信我們知道人是什么的信念”時,就會立刻死亡。[35]我們面對的依然是一個處處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世界。而人存在于諸多不確定性之中,常常陷入“不知道”、甚至精神焦慮的狀態。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存在主義依然可提供一種研究人的生活綱領,也持續影響著面對人而展開的社會工作。一方面,在理論層面,為了理清其思想譜系,存在主義作為反結構主義認識論的代表,我們對其依然有必要開展批判性的檢討。面對結構主義中的結構概念,更進一步而言,是對結構主義所隱秘設定的“存在觀”的諸問題,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另一方面,在社會工作的實務及其探索層面,我們開展的是對個別化的“人”的、具有“人格”特質的工作,因此無論是“主體”,抑或是“關系”,都可被理解為某種“存在”。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每個個體作為與他者絕對有所不同的“個別化”存在,是無法用形式化、抽象化為普遍志向的“理論”所能全然處理的。
那么,面對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存在主義開啟了怎樣的進路?一方面,是對存在中積極面向的挖掘。值得強調的是,確定性的未來有時意味著絕望;反之,因不確定性,絕望才是不可能的。[36]換言之,不確定性中才真正蘊含著“希望”。另一方面,存在主義強調了自由選擇與責任的密切關系。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存在主義最初被本土社會工作領域所接納,是由于能加深對個別化的人的存在意義的理解。之后,這一思潮被社會工作理論所吸納。究其原因,除了存在主義強調人的存在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主張人是可以做出自由選擇、并有能力、也有責任主動塑造其自身的。借助弗蘭克爾的話,他開展的心理療法就是使人認識到自我責任,令對方明白“負責任乃是人類存在的本質”[8]133。這一點對本土社會工作而言尤其重要,也與社會工作所倡導“助人自助”有著價值層面的高度一致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社會工作是這樣一種專業,她使受助者成為對自我負責的人。
注釋
①作為本體論的區別,由于沒有類似德語中“Seiende- Sein”式成對的術語,因而英文中只能區分大小寫,Seiende常被翻譯為Being,與之相對Sein則譯為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