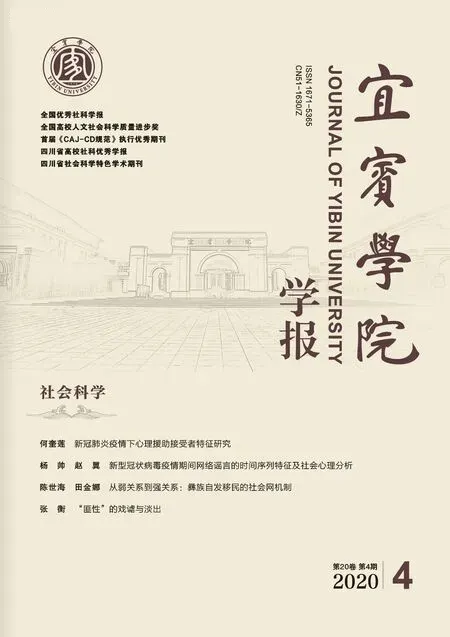本源視域中的孔子天命觀再考察
張應平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8)
“天命”是中國遠古以來即有的觀念。在殷人的觀念中,其祖先乃是依天命而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商湯舉“天命”以論證其伐夏之合法性:“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湯誓》)因此天命在殷商時期具有強烈的神性色彩。周代之時,周人認為“天命靡常”(《詩經·小雅》),在觀念上“絕地天通”,破除人神雜糅的狀態,斬斷了人間與神際的血緣關系,主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從而進入到了人神之別的形上學原創時代。不僅如此,作為軸心時期的道家、墨家等都有相應的天命觀,只不過其命名不同,如老子謂之為“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墨子謂之為“天志”:“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墨子·天志上》)這說明“天命”思想在先秦時代具有其可對應的觀念和語義平臺。
“天命”觀念在孔子的思想中有其賡續與發展,從而形成孔子自己獨特的“天命觀”。這種“天命”觀念卻常被后起學者以義理性的把握和闡述為某種形而上的超越實體,如馮友蘭、牟宗三、徐復觀等先生之從西學角度所進行的格義即為如此,后世多數學者大抵承襲馮友蘭先生的“天有五義”之說(見后文),如郭沫若認為孔子所說的天其實只是自然,所謂“命”是自然之數或自然的必然性[1]358;湯一介將“天”之意義總結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與義理之天[2]29;趙法生認為孔子天命觀是一種中道的超越觀[3]。這固然符合軸心期以后形而上學建構的觀念史實情,自孟子言“盡心知性以知天”《孟子·盡心上》),到宋明理學的心性本體的建構,及至現代新儒家所理解之天命觀念以及當代儒學學者的超越性闡釋,其中雖有內容上之差異,然而他們的共同之處都還是處在形而上學的明朗化、凝固化思想視域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孔子所領悟的那種混沌的、本源的“天命”以及“知天命、畏天命”的本源情感表達,無法透顯孔子思想顯示出的豐富層級性言說(也有部分學者注意到孔子“天命”與“時命”的關系,但尚未能明確揭示出這種本源性視域①)。本文通過分析上述形上學天命觀的理論困境,嘗試揭示孔子天命觀的本源性視域,由此助益于啟發我們從學理上打破前現代形而上學觀念,立身于現代社會生存思考儒學的當代重建問題。
一、 孔子天命觀的幾種闡釋
孔子罕言“命”,從記錄其言談的《論語》觀之,亦不可謂不寡言“天”。雖然如此,“天命”的問題在孔子思想里亦是極其重要的觀念,茲舉兩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語·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論語·季氏》)
對孔子此“天命”歷來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是以例言之:
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中認為,在中國文字中,所謂天有五義,是為物質之天、主宰之天、運命之天、自然之天、義理之天,而“《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4]35。也就是說,上述二例中所謂“天命”之“天”,在馮友蘭看來是指主宰之天,也就是他所說的“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是某種有位格的人格神、終極性的存在者。因此,這樣看來,所謂“知天命”“畏天命”,不過就是一個事先設定的主體的人,去感知、敬畏、追懷與其相對相隔的一個外在終極存在者。
而在徐復觀先生看來,“孔子的所謂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簡捷的語言表達出來,實際是指道德的超經驗地性格而言……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說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實內容”[5]88。也就是說,孔子的天命是指內在化的道德實體,或者說道德本體。這顯然有別于馮友蘭先生所理解的宗教性的人格神存在者。
徐復觀進一步說,孔子之天命“是道德性之天命,非宗教性之天命”,“天命對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實際是‘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這不僅與周初人格神的天命實有本質的分別;并且與春秋時代所出現的抽象性的概念性的道德法則性的天、天命,也大大地不同。孔子是從自己具體生命中所開辟出的內在的人格世界,而他人僅系概念性的構造。”[5]90-91
于是,徐復觀認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知’,是‘證知’的知,是他從十五志學以后,不斷的‘下學而上達’,從經驗的積累中,從實踐的上達中,證知了道德的超經驗性”[5]88。而“他(孔子)之畏天命,實即是對自己內在的人格世界中無限的道德要求、責任而來的敬畏。性與天道的融合,是一個內在的人格世界的完成,即是人的完成”[5]91。所以,在徐復觀的觀念里,孔子的“知天命”,就是某個經驗性的主體由“下學”而通達那個超經驗的內在的道德實體,也就是“性”,達到某種證知;然后因為這種道德實體的要求而引起對天命的敬畏,這也是一種“知”。也就是他說的“若不知天命,即不知畏天命”[5]89。
牟宗三先生認為,“盡管在儒家思想中天命、天道確有‘形上實體’的含義…但孔子所說的‘知我其天’,‘知天命’與‘畏天命’的天,都不必只是形上實體的意義。因為孔子的生命與超越者的遙契關系實比較近乎宗教意識……因此,孔子所說的天比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意味”[6]33。
進而,“我們可以說,在孔子的踐仁過程中,其所遙契的天實可有兩重意義。從理上說,它是形上的實體。從情上說,它是人格神”。牟宗三把孔子與“性與天道”的遙遠的契合分為兩種意義:超越的遙契和內在的遙契。“內在的遙契,不是把天命、天道推遠,而是一方把它收進來作為自己的性,一方又把它轉化而為形上的實體……孔子對天的超越遙契,是比較富有宗教意味的,而發展至《中庸》講內在遙契,消除了宗教意味,而透顯了濃烈的哲學意味。超越的遙契是嚴肅的、渾沌的、神圣的宗教意味,而內在的遙契則是親切的明朗的哲學意味。”[6]34就是說,“天命、天道的傳統觀念,發展至《中庸》,已轉為‘形而上的實體’一義”[6]37。因此,關于孔子所說的“天命”,在牟宗三的觀念里就同時具有外在和內在的雙重意味,同時兼具宗教和哲學意味。這顯然也區別于馮友蘭先生理解的外在終極存在者,也區別于徐復觀的內在化的“性”即道德實體,而是兼具二者之義。
而“知天命”就是要通過“下學”的踐仁功夫,而上達“天命”,“使自己的生命與天的生命相契接”“天人的生命互相感通”“孔子的下學上達,便是希冀與天成為知己”[6]32。“但是知天的知,必然引生敬畏的意識,敬畏是宗教意識。天道高高在上,人只能遙遙地與它相契接,又怎能沒有敬畏呢?故此敬畏的意識是從遙契而來的。從知天命而至畏天命,表示仁者的生命與超越者的關系。”[6]33牟宗三又說,“君子有三畏……‘畏’是敬畏之畏,非畏懼之畏,敬畏與虔敬或虔誠,都是宗教意識,表示對超越者的歸依。所謂超越者,在西方是God,在中國儒家則規定是天命與天道。孔子的‘三畏’思想,便是認為一個健康的人格,首先必要敬畏天命”[6]27。因此,這樣的一種“知”和“畏”,仍是由某一個形而下的主體,也就是牟宗三所指謂的“仁者”,生發出情感去感通、契接那個內在的或外在的終極實體。
觀之馮友蘭、徐復觀、牟宗三之于孔子天命觀的看法,內容詳之確有差異,然其共通之處亦是顯而易見,也就是他們都是從中西哲學的格義中解讀儒家的傳統學說;這種解讀可以說仍然是在形而上學本體論視域中展開的,其特點仍然是在一種“主—客”的觀念架構下,去思考“存在者整體”或者說“存在者之為存在者”[7]68。這當然也是整個現代新儒家共有的思想視域,同時也是符合軸心期以來、特別是思孟以后進行形而上學建構的觀念實情的。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意思是天命給定人的叫作性。這其實是在儒家性情論的觀念下的理解。在這種性情論中,性為體,是形而上者;情為用,是形而下者。“天命”被領悟為某種形而上的存在者。這其實是中國哲學形而上學化的體現。又如,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孟子·盡心上》)此之謂“天”,則是盡心知性的主體內在化,是“天”與心性之體的合而為一。那么,此之“天”,即是內在的普遍的道德形上實體。孟子又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孟子·盡心上》),這個“我”即是通過盡心知性而“立其大者”,知“我”也就是“知天”。這樣的“天”其實就是形而上的終極存在者,是眾多的形而下存在者所追問的所謂的“一”。這就是孟子心性論對“天”之理解的內在化、實體化。
宋明儒學如朱熹,則將孔子的“天命”理解為天理。“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8]172(《論語·季氏》)其所言之天理,亦是指謂為形而上的存在者,其內容與思孟相異,其思想架構仍是承接思孟以來的“性情論”哲學,其實質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哲學形態。所謂“性”者,是形而上之本體,“情”者,為形而下的主體性之“情”。由之形而下之“情”,去追問、領受、通達那個形而上之“性”,也即“天命”。
而現代新儒家亦是沿著宋明的理學系統和心學系統而來,他們所做的西學格義功夫,亦仍屬于西學二元相隔的形而上學傳統思路。現代新儒學固然是現代性生存方式轉進之后,儒學所發生的“自新”形態,然而這樣一種“自新”,現代新儒家“內圣開出新外王”這樣一種努力,仍然是軸心期以來傳統形而上學、性情論系統的接續,他們也一樣地遮蔽了孔子天命觀的本源性。
二、 孔子天命觀的思想視域問題
上文論及自思孟以來而至于現代新儒家都是在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視域下,對孔子的“天命”思想進行存在者化、對象化的把握,錯失了孔子思想的本源層級。因此,有必要就此問題進行簡略闡述。
我們知道,牟宗三先生等現代新儒家是在與近現代西方哲學的比附格義中建立的現代新儒家理論形態,尤其是借鑒于西方哲學先驗論的致思進路,如牟宗三即是主要借鑒康德哲學。但是近代西方哲學不管是經驗論還是先驗論,都面臨著“認識論困境”問題。“‘認識論困境’有兩層意思:第一,你如何能夠確證客觀實在?第二,即使能夠確證,主觀的意識又如何能夠穿透‘真空’去達到那個客觀實在?”[9]44經驗論的認識起點是感覺,對于感覺以外的事物無能為力,而且不同個體之間的“感覺”共同性也無法保證統一,其最終導向休謨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先驗論采取的是理性主義的進路,笛卡爾將“我思”作為認識論的一個確定自明的起點,但是心、物二元的統一性和確定性是需要預置上帝觀念來保障的;康德主張現象與物自體的二元論,我們的認識只能擁有關于“現象”的知識,而作為本體界的物自體在康德哲學中本身就是不可知的概念。因此,先驗論本身就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借鑒先驗論邏輯而開展哲學致思的現代新儒家也面臨同樣的理論困境。
而上述的“認識論困境”,在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看來,本質上就是形而上學思維的結果。根據這種形而上學思維,它給出了眾多相對的形而下存在者與唯一絕對的形而上存在者之間的分際。在諸多的形下存在者之間也存在著分際,所謂“物際劃分”,就是存在者劃界。我們在現實中,總是將這些存在者表現為“自我”與“他者”的對置,也就是一種“主—客”架構,因而建構起形而下的知識學和倫理學。同時,這樣形而下的主體性存在者,總是去追問一個相對存在者背后的絕對本體即形而上的存在者,諸如西方哲學中的實體和上帝,中國哲學中的心性本體,這就是形而上學的基本觀念形態。而且我們總是處在這么一種領會中,就是這些形而下存在者、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然而我們要追問:這樣一種存在者的存在何以可能?不僅形而下的存在者何以可能,而且形而上的存在者何以可能?也就是說,形而上學的觀念形態不追問這些問題,因而海德格爾認為以柏拉圖主義為開端和根本特征的“存在者”化的形而上學走向“終結”[7]70,因為傳統形而上學長久地遺忘了“存在”本身。由此,海德格爾試圖“解構”傳統形而上學而追問“存在”問題,或者說為形而上學重新“建構”一個“地基”,這個地基就是“基礎存在論”,也即“此在的生存論”;但是這一“基礎存在論”是以此在的生存分析作為優先地位和入手前提的,存在只有通過此在的生存才能展現出來[10]14-18,而“此在”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者卻成為生存的先行觀念,也即此在作為主體性尚缺乏本源性的奠基,從而海德格爾也陷入了形而上學的循環論證之中。
因此,我們需要超越這種“主—客”架構的二元論形而上學思維,切入一種“生活—存在”的本源性視域:“這種視域不僅追問‘形而下學何以可能’,而且追問‘形而上學何以可能’;這種視域追問‘主體性何以可能’‘存在者何以可能’;這種視域之所思,是存在本身、生存本身、生活本身。如此這般的生活—存在,是一切物與人的大本大源所在,是一切存在者與主體性的源頭活水所在。”[11]220在這種視域中,存在不是一個存在者,存在、生存、生活沒有區別,生活即是存在,存在即是生活;生活首先不是某種主體(比如此在)的生活,相反主體總是處在生活之中、在生活中領會生存、在生活中顯現自身;這一本源視域顯示出這樣的奠基關系:存在本身、生活本身先在于并且給出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
在孔子的思想里,這個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它顯現為本源性的情感:仁愛。是本源性的仁愛情感,先行并給出了形而下的主體性存在者,從而去追尋形而上的存在者。而孔子所說的“天命”即等同于這個層級上的“仁”,其實就是生活本身,存在本身,而不是一個存在者意義。雖然牟宗三對孔子的“天命”與“仁”也進行了某種等同,但是他將它們指稱為一個“形而上的實體”[6]37,這其實是對孔子思想的遮蔽。這意味著,軸心期以后的兩千多年以來,人們都是處在這樣一種存在者化的思維方式中,只會思“有”,喪失了思“無”的能力。老子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12]110“無”即是存在本身,是它給出了形而上的存在者“有”,給出了形而下的存在者“天下萬物”。 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和老子都擁有相似的觀念層級和思想視域(只是在觀念層級的顯現樣式上不同而已)。我們應該回到那個“無”,以一種相同之情來重新理解軸心期及其之前的觀念,這樣才能解脫形而上學的凝固化思維,解決現代新儒家“老內圣”開不出“新外王”的理論困境,從而切入現代中國人的當下生活,重建儒家形上學、形下學。而要透徹理解孔子的天命觀,同樣需要這樣的本源性視域。
三、 孔子的本源天命觀
在觀念和符號誕生之初,這樣一種本源性的思想視域就存在于我們先民的原初體驗中,因而我們可就本文的“天”與“命”進行字源分析,在符號意義上來考察一下它們的含義以及蘊含的觀念視域。
(一)“天”和“命”的字源
1.天
許慎言:“天,顛也……從一從大。”[13](《說文解字·一部》)“天”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像人形,如許慎所言:“大象人形。”(《說文解字·大部》)在“大”字頭上加一頭,就是“顛”。許慎又言:“顛,頂也。”(《說文解字·頁部》)這就是說,“天”表示一種最高之處。這種最高之處,只是一種指示本身,而非實體觀念,不是存在者化、對象化、現成化的觀念。從造字的角度看,在“天”字頭上,并沒有其他符號來表示一個存在者,它的原初體驗并不是指向某個存在者。
因此,這樣的“天”,在符號誕生之開初并非就是直接指涉涵攝日月、風雨、雷電等自然事物的“天空”,亦非一個主宰之“天”,而是遠古先民在生活領悟中,產生了“天”這樣的觀念由此而構造“天”這樣的符號,從而符號化、對象化為某種存在者。這樣的生活,是混沌,是“無”,是恍兮惚兮的狀態。本源性的“天”,就是這樣的一種“無”,是它生成了人的主體性,從而在這樣的生活中把本源性的“天”領悟為形而上的“天”、形而下的“天”,領悟及構造為某種存在者。
2.命
命者,許慎解釋為:“使也,從口從令。”[13](《說文解字·口部》)命,就是令,某種“發號施令”。關于令,傅斯年遍考周代金文說:“歸納以上令字之用,不出王令、天令之二端”[14]18。王令,自然是一種存在者的號令;天令,即天命,天之號令。周代王令之出,自亦是要聽“天令”。這樣的“天令”來源于周人對生活情境的領悟。前述已言,“天”在本源意義上非一個存在者,因此,天令或者天命即不是一個存在者之號令,而是生活本身的衍流,促迫之使然之,自然如此。而此天命,形之于國之大事則領受為王令。因此,在本源意義上的“命”就是使之然也,并非是誰、是什么使之然,而是生活本身即自自然然,自己如此。
綜上,“天”與“命”的符號誕生,凝聚著遠古先民本源性的觀念。此觀念來源于對生活本身的領悟。是生活本身(天命)生成了主體性的人,因而有了人之言(符號),才有“天”和“命”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因此,本源之“天命”就是一種無言之令,是生活本身的流淌和顯現。
(二)孔子天命觀的內涵
本源之“天命”是符號誕生之初的原初體驗,孔子的天命觀是契接于這樣的領悟的。當然,孔子的天命觀亦不是直接就產生。孔子之前的時代就已經存在天命之思想,只是這些思想把天命更多地表達為某種人格神或者形而上的實體。如,《尚書·召誥》言:“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15]213這樣的“天”就是形而上之“天”,由這個唯一的絕對的存在者給出眾多的相對存在者也就是“吉兇”等之現象。又如,在孔子之前,古人常常把“天”與“帝”放在一起進行表達:“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16]503(《詩經·大雅·文王》)這里的天、帝就是一個人格神的意味。
孔子對前代的天命思想不是照搬承繼,而是對其有所發展和改造的。在《論語》中,我們很少見及孔子將“天”與“帝”進行勾連,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說,孔子對以往作為對象化、存在者化、現成化的人格神進行了淡化和消解,是敬而遠之的態度。這與其主張的“祭神如神在”并不矛盾。后者所強調的是人與神的共在性,人、神這樣的存在者都是在生活境遇中生成的,是本源性的至誠情感的顯現,就是本源之“天命”。因之,孔子所說的“天命”,就絕非一個存在者的含義,在孔子那里這種存在者化的理解恰恰是他要消解的。孔子之“天命”是遙契于遠古先民構造符號的原初體驗,這樣的“天命”就是生活本身之“命”,之使然。這就意味著,“天”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然(nature),而是中國意義上的自然,自己如此。天命就是天令、天言,生活本身之促迫,不是上天、上帝的號令,亦非人言,因為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一切存在者都是在這樣的“天命”里成己、成物。
“天命”既是生活本身之促迫,則我們應該首先“聽天命”,傾聽生活。前述已明,我們傾聽的并非是一個天帝的號令,一個存在者之號令,而是傾聽天之言,無言之言,傾聽生活之流淌。孔子之被稱為“圣人”,是因為他時常聽天命而順天命。嵇考“圣”(聖)字,《說文解字》云:“圣,通也。從耳,呈聲。”[13]那么圣就是用“耳”傾聽。傾聽什么呢?傾聽生活,傾聽本源之“天命”,而非傾聽某一個現成的存在物的號令。傾聽生活也就是孔子所謂的“耳順”,由之而“通”也,通達生活本身、存在本身。只有這樣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進入一種自如的境界。
聽天命,由此而知天命。這樣的知,不是認知之知,不是知識論、倫理學意義的知;也不是徐復觀所說的“證知”,經驗的積累,實踐的上達。這樣的理解,仍然是事先設定了一個主體性的人,和客體化的“天命”,在一種“主—客”架構下去進行對象化打量。孔子所說的“知”根本不是一個對象化的感知、認知,我們已經說過,“天命”在孔子那里不是一個存在者。因此,“知天命”,就是因為聽到了“天命”,聽到了生活本身的流淌,在孔子的話語里就是本源情感的涌流,由此我們感知到了“天命”,這種感知是情感之知,就是有覺解的生活領悟。這種情感之知,就是所謂的“至誠”,是情感的本真之觸及,無可欺瞞。孔子說“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面對那一份本然的情感生發,我們無可逃遁,無可回避,只能去領受這份“天命”,感知這份“天命”。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
知天命作為一種無可逃遁、本然生發的情感之知,必然顯現為一種敬畏之情,就是孔子所說的“畏天命”。這種敬畏也并非是有所畏之畏,也就不是前文提到的馮友蘭、徐復觀、牟宗三所理解的敬畏,因為他們所說的敬畏都是指向了一個終極的存在者,這樣的敬畏仍是傳統性情論下的人的主體性形下之情,是對本源之情的遮蔽。而孔子之謂“畏天命”乃是無所畏之畏,本源之情感觸發。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命、天道就是這樣的至誠之情;“畏天命”其實乃是“自誠明”“誠則明矣”(《中庸》),由之而生成出人本身的主體性;同時又需“反身而誠”(《孟子·盡心上》),返回到那樣的本源之誠,成為“人之道”。也因此,傾聽天命,傾聽生活,傾聽本源情感的涌動,才可能產生圣人之言,也才可能有“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這樣的主體性情感。所謂“圣人”,也就是傾聽天命,知天命,成圣人之言,傳語于人。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小人乃是蔽于物化而遺忘了這樣的本源情感。
總而言之,孔子所言之“天命”是本源層級上的言說,相應于老子所說的“無”。
這種本源顯現為孔子常言之至誠的仁愛情感,知天命與畏天命亦是情感之知、情感之畏,是仁愛情感的顯現。這就不是一種存在者化和對象化的領會,而是生活境遇下的當下構成之“無可無不可”之境,因此孔子被稱為“圣之時者也”,就在于孔子思想的本源言說所達到的深遠境界。此天命之境界誠如《詩經·周頌》所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是子貢之所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結語
本文認為思孟以來對“天命”思想的理解乃是一種形而上學化的觀念,其遮蔽了孔子天命觀的本源性,此處尚需對此作一個說明。
在思孟那里,其實也存在本源性的天命觀。如上文已言,《中庸》之謂“誠者,天之道也”就是一種本源性的表達;孟子思想中關于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的言說(《孟子·公孫丑上》),也是本真的情感發動。他們都不缺乏本源性的表達。這似乎與前文的批評是一個矛盾的說法。在這里需澄清,考察整個觀念史,從思孟以來儒學本身確實在進行一種形而上學建構,因而對本源性的“天命”逐漸把握為、分化為形而上的本體和形而下的道德情感,也就是性情論架構。但是在這種把握中,并沒有完全遺忘本源性的“天命”。只是說,正如前述所引牟宗三先生的話,這種把握具有更明朗的哲學意味。明朗之意,便是一種存在者化的觀念,以至于后來者遺忘了非存在者化這種本源性的觀念。
同時,我們批評自思孟到宋明儒學到現代新儒家的形上學觀念,并不意味著完全否定形上學。恰恰相反,形上學化、存在者化的思維是我們逃避不了的;而且他們在建構儒家形上學的過程中也取得了非常偉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形而上學觀念下所預設的存在者,他們本身是需要奠基的,需要被追問何以可能的。一切的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給出,由生活本身給出的。孔子所表達的天命觀正是這樣的本源性觀念,它是契接于“天”與“命”的符號誕生之初的原初體驗和生活領悟;在這種生活領悟中,聽天命的過程中產生了人的主體性,由此才可能有主體性之情和進行存在者化的打量。而我們今天的思想研究就是要回到這樣的本源觀念,回到最遠的也是最近的原初體驗,回到這樣的大本大源,從而切入我們當下的生活,重新建構因應于當下生活的形上學、形下學,展開我們的生活意義。這就是考察孔子天命觀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注 釋:
①此觀點可參見:晁福林《“時命”與“時中”:孔子天命觀的重要命題》,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第39-47頁;陳晨捷《“德命”與“時命”:孔子天命觀新論》,載于《東岳論叢》,2018年第2期,第35-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