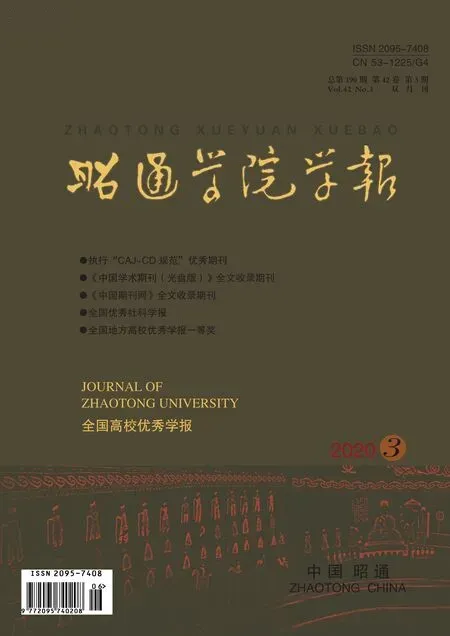陸機擬古詩研究
(昭通學院 學報編輯部,云南 昭通 657000)
一、陸機擬古詩寫作時間
關于陸機擬古詩的創作時間,一直是個難題。姜亮夫先生在《陸平原年譜》里做了一個推斷說“不類壯歲以后飽經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構也。”[1]40這個說法有不小的影響,不過這也只是姜先生的推測。劉運好在《陸士衡文集校注》里說“從內容看,當非一時一地之作,然所抒多為懷鄉之情愫,所寫多為北方之景物,可以基本斷定為入洛后所作。”[2]436劉運好從擬詩的內容所涉及的風物來做出判斷,基本斷定為入洛之后作是比較可信的。因陸機早年是在南方東吳生活,當時多個政權并存與敵對的情況下,陸機作為一個吳地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去到北方的可能性極小。陸機在吳亡國之后退居讀書,之后無奈入洛,這才有可能去北方。陳家紅認為陸機的擬古詩大約作于入洛之前的擬詩有三首《擬今日良宴會》、《擬涉江采芙蓉》、《擬蘭若生朝陽》。大約作于入洛之后的擬詩有十首。[3]陳家紅雖然對擬古詩每一篇目是什么時候作的都做了說明,但大多是就詩歌內容來做的一個簡單推斷,說服力并不強。
筆者認為陸機擬古詩的寫作時間應為入洛之后。其一,陸機早年雖然也遭遇大變,但其生命感受的復雜度與深度還是入洛之后更甚。漢末古詩作者多為亂世游離之人,這與陸機入洛羈旅的生命感悟相類似,因此古詩才能打動陸機,陸機從而模擬古詩。其二,古詩的作者是漢末無名氏,古詩的寫作時間與陸機所處的時期間隔不算長。古代交通不便,因此相對來說信息傳播的速度要慢一點。正如木齋、尚雪二人所說的古詩在陸機來到洛陽之前還沒有流傳到南方,因此陸機是很難接觸到古詩的。另外,陸機入洛前后的詩作不同。入洛前詩文主要是賦、四言詩,而曹魏獨特的抒情五言詩是陸機入洛之后才有機會學習的。[4]其三,陸機擬古詩所涉及的風物也多是北方之物,只有陸機入洛才有機會感受北方風物。
二、陸機擬古詩創作的影響因素
(一)言意之辯理論的影響
魏晉時期玄風盛行,陸機受玄學影響在所難免。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中記載葛洪《抱樸子》云“諸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5]說明陸機對玄學是有研究的。如果說《北堂書鈔》所記載的不一定可靠,那么《晉書》上關于陸云帶有玄幻色彩的記述應該是可以說明二陸是接觸過玄學的。“初,云嘗行,逗宿故人家,……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云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6]
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辯理論對陸機有不小的影響,從理論到擬古詩的創作實踐都可見其影響。其《文賦》序云:“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涉及了言、意和物的關系。也就是說,陸機《文賦》的理論構建與魏晉言意之辯理論有關系。就陸機的擬古詩來說“魏晉玄學對于‘言意之辨’理論的探討,尤其是王弼‘言不盡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現,正為擬古詩作的涌現和蔚興奠定了理論基礎。”[7]但是言意之辯理論促進了文學在理論上的進步,給擬古詩的創作帶來了思想指導的同時也受到了言意之辯理論的束縛,付出雖有名家但“少有佳作”的代價。
陸機擬古詩的創作受到了魏晉玄學“言意之辨”的理論的啟發和影響,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與“得意忘言”相類的“師其意而變其辭”的創作方法上。陸機模擬古詩時大多抽取古詩之“意”,然后用自己新的“言”和“象”進行置換,也就是“師其意而變其辭”。正如蔡彥峰所說的“西晉文人的創作注重立意,如擬古詩、擬樂府就往往采用師其意而變其辭的方法,與“得意忘言”的方法若同符契。”[8]這種方法是有可取之處的,但陸機的問題就是“將詩歌的語言詩歌的意象簡單地符號化。”[7]雖然看起來詩歌中的意象與語言具有符號的性質,但它們不能和一般意義上的符號一樣單獨地隨意抽取與置換,這會對詩歌的審美特質造成一定的影響。“將意象和語言當作可以轉換的符號形式,實質上取消了詩歌的感性特征。”[9]也就是說把詩歌的意象當成了一般符號一樣轉移到其他地方,它的意義是會有變化的。正如錢鐘書先生所指出的:“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立言,是無詩矣,變象易言,是別為一詩甚且非詩矣。”[10]12這也是陸機《擬古詩》被后人批評對原詩“亦步亦趨”,“性情不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過這種現象在魏晉南北朝文學里并不是個例,除了陸機在謝靈運、鮑照等人的擬作中也有存在,其思想根源就是言意之辯理論。
(二)魏晉文學中的模擬風氣
西晉人在面對之前的藝術高峰時,在該如何后來居上這個問題上,他們找到的一個解決方法是竭力摹擬前代詩歌。這是魏晉文學模擬風氣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陸機的擬古詩是當時文學模擬風氣盛行的一個體現,也是眾多擬作中的代表之作。擬作也不是魏晉所獨有,漢代有模擬屈原《離騷》的騷體賦,又有“七體”等追蹤枚乘、司馬相如的賦作。劉勰《文心雕龍》就有說:“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又云:“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只是魏晉時期擬古之風更盛行,如三曹等就創作了不少的擬樂府作品,左思的《三都賦》也是“擬議數家,傳辭會義”。傅玄作《擬馬防詩》,張華作《擬古詩》等。陸機大力模擬古詩更是開啟了擬古詩的風潮。
從文學的發展史來看,建安之后就難以再現建安文學的那種骨氣與風力,于是就嘗試轉向正始阮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但殘酷的現實終究讓他們不能真正的浪漫下去,于是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古典主義。“對于古典主義來講,認可、繼承、研究文學遺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前人的作品成為他們創作的出發點。”[11]對西晉文人來說該如何繼承認可和研究經學及前人的文學,這是個很重要也很現實的課題。
陸機在《文賦》里主張“襲故而彌新”。要做到“襲故而彌新”也就需要“游文章之林府”。模擬是一種“游文章之林府”的方式,也是一種學習的方式。學習前人的經驗,吸收前人文章之精華,通過這種方式賦予作品新的生命,從而出新出彩。“藝術創新必須以舊典為抬步向上的基階,這便是模擬之所以值得肯定和激勵的藝術哲學依據。”[12]181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以陸機為代表的太康詩人大量模擬前人作品的重要文學意義之所在。
這個時期的擬作是對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也是一種新變。這種新變醞釀著更大的新變。如陸機的擬古詩與古詩的諸多不同之處所體現出來的就是與古詩爭勝,力爭創新,出新出彩,故而變古詩的質樸風格為擬詩的華麗,講求辭藻排偶,其影響流被南朝及隋唐。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講求華麗的文風負面的影響不小,但也正因為有了這個時期對文學音律辭藻、表現手法的探究,才會有后世文學的大發展與繁榮。因此陸機的擬古詩雖然在藝術價值方面與古詩相差很大,但其在文學辭藻和表現手法等方面的探究之功是不容忽視的。另外,文學模擬風氣在魏晉盛行,一方面反映了漢魏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和經典作品的接受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人對文學的重視,從側面體現了當時文人對文學審美特質認識的不斷加深,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學的自覺。
(三)充滿悲情的人生際遇
西晉時期政治多變殺戮極重,“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這就造成了當時的人們生活極度壓抑。于是“‘擬古’一類的詩題,便常常成為詩人難言之情、隱匿情懷的寄托和表達。”[13]后人說陸機擬古詩“性情不出”,其實詩人選擇模擬對象的時候是會體現自己的性情的。陸機是有意識地選擇古詩作為模擬對象的。陸機借擬古詩隱喻自己的情志,有懷鄉、羈宦、思人、遷逝、不遇等,這些情志是古詩歌詠過的,也是陸機本人親身經歷而“心有戚戚焉”的。“其實陸機擬古之作并非沒有性情的流露,只不過性情的流露是寄托在先行作品原有的情感指向中,他選擇了什么樣的先行作品來進行擬作,這種選擇之中己包含了他的深意。”[14]“在陸機的擬作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詩人的失落感和孤獨感。他能夠悉心模擬《古詩十九首》中的大部分作品,它們‘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格無疑是感染陸機的重要原因。”[15]從陸機的人生際遇來看,古詩“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格特點,很切合陸機的為文旨趣和人生境況。
陸機才高,作文尚麗,這也是當時的文學風氣。至于悲,可以說就是陸機的一個人生底色了。陸機身處魏晉之際的亂世,當時的社會戰爭頻繁,政治波瀾詭橘動蕩不安。他的人生可謂是大起大落,入洛之后想重振家風,于是醉心功業但又壯志未酬。陸機由吳入晉,乃一亡國之余,無奈入洛。這就喪失了在南方的優越感,同時又不為北方士子所容。入洛之后和他在入洛途中所擔心的一樣,仕途很是不順,陸機先后依附了楊駿、愍懷太子、賈謐、趙王倫、吳王晏和成都王穎等人。盡管如此也還是動輒就有九錫文事件之類的性命之憂。雖有張華等人的賞識,但更多的是北方士人的輕視和侮辱。如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范陽盧志于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類似的人還有潘岳、劉道真、孟超等。面對這些人的挑釁、輕視和侮辱,一個普通人尚且不忿,何況于他這么一個有極高才學和極好家世的人。在注重門第講究聲望聲名的魏晉時期,陸機作為吳地士族代表之一,也只能選擇抗擊。“譏嘲的言詞對被嘲弄的人的確是一種嚴重可怕的懲罰,它可使被嘲弄者極端難堪、痛苦而感到無地自容。最嚴重的等于被社會放逐。”[16]16面對諸多的挑釁、輕視和侮辱陸機有強烈的反擊,也獲得了不少的勝利,當然這也是他的悲劇的源頭。
陸機父祖俱是東吳重臣吳郡望族,可謂是家學淵源,本人是“少有異才,文章冠世”的人。前后身份的巨大變化,北人的輕辱,追求功名但又碌碌無功,心中之苦悶,可想而知。陸機入洛之后,生存環境艱險,孫惠、顧榮、戴若思這些鄉黨友朋都勸其回吳。但是陸機“負其才望”,他也確實是有才的。說他“志匡世難”,不如說是他想建功立業,重振家風,光耀門楣。只是他看不透一個入洛南人想在北人圈子里建功立業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他堅持留在北方,于是其后華亭鶴唳不得聞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陸機亡國之余的悲痛與恥辱,離鄉入洛的愁思與苦悶,不被北人所重又處政治漩渦擺脫不得的壯志難酬的悲憤,諸多傷感與年華易逝的無奈等情感的交織。于是就與身處亂世漢末文人的感情相通了,然后產生惺惺相惜之情,選擇模擬“意悲而遠”的古詩也就自然而然了。正如劉師培所說的“模擬古人之文須先溝通其性情之相近者。”[17]145于是有《擬行行重行行》中“游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的傷感。有《擬東城一何高》里“易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的無奈等等。
(四)逞才成名的現實需求
陸云謂其兄:“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與兄平原書》)說是模擬前人作品“能事可見”容易出名,更有與前人爭勝之意,讓古人“不得全其高名”。可以說陸機模擬古詩就是為了逞才以成名“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也是為了與古人一爭高下。王瑤先生說:“這種風氣既盛,作者也想在同一題材上,嘗試與前人一較短長,所以擬作的風氣便越盛了。”[18]73典型例子就有左思的《三都賦》等。盡管陸機的擬古詩藝術成就確實不如古詩,但就從“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這一點來說陸機他還是成功了。在《文選》里他的擬古詩是“雜擬”類之首。鐘嶸在《詩品·序》大贊:“士衡《擬古》……斯皆五言之警策。”
陸機本人少負才名,入洛之后也是不甘人后“意欲逞博”(沈德潛《古詩源》)的。陸機為什么急于逞才成名?從陸機的外部因素來看,其一,在文學上理論上,曹丕《典論·論文》中說文章是“不朽之盛事。”立言是“三不朽”之一,這個說法在《左傳》里就有,但從理論上提高文章地位的是從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始的。作為當時文人代表的陸機自然是不甘人后的。其二,從魏晉人的生命意識來看,魏晉人生逢亂世,生命不永,于是生命意識勃發。他們不敢也不能期待長久的生命,于是享受生命,拓寬生命的厚度與寬度也就自然而然了。重于情,極于性,正所謂“情之所鐘,正在吾輩”。他們想讓自己的生命顯得更有意義,通過立言、立功、立德讓自己“不朽”。
就陸機個人來說,他“伏膺儒術”受儒家思想影響,因此有著很強的功名意識,逞才成名是他的內心的渴望,也是他重振家風的需要。在《思親賦》、《述先賦》、《祖德賦》等諸多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內心當中充滿了追求功名與重振家風的焦慮。另外,入洛之后陸機要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就是作為一個南人,一亡國之余,如何才能在北方立足呢?“魏晉南朝詩壇,普遍存在著逞競才學、游戲文字的創作情境。此種情形之形成,與其時張揚才學的社會文化氛圍、帝王權貴常常招聚文士酬唱的風氣以及寒士以文才求仕進的現實密切相關。”[19]魏晉人重名望,想真正融入北方就需要名望,更大的名望。在入洛之前能給他帶來名望的出身與家世,在入洛之后就不是能給他帶來名望的優勢了,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劣勢了。如何改變自己的亡國之余的身份標簽,在北地新的政治環境下獲得不錯的政治資本以自立,逞才以成名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于是逞才成名也就成了陸機迫切的現實需求。當然,陸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文章也是他所擅長的。他“才多”也是他能逞才的關鍵,當然這也是他所熟悉的方式。因此陸機大力模擬藝術價值極高的古詩也就是應有之意了。除了擬古詩之外,陸機其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影響力較大有《文賦》、《演連珠》等,相對于他短暫的人生來說也是著述頗豐了。
三、陸機擬古詩特點
(一)繁縟綺靡
陸云說陸機“綺語頗多”。沈約在說陸機的文章“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宋書·謝靈運傳論》)也就是說陸機詩文藻采繁密,格調華麗。陸機的擬古詩就化古詩的簡約為繁縟。如《擬東城一何高》寫音樂“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擬作化為六句“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歡,再唱梁塵飛”。再如《擬迢迢牽牛星》專寫織女等等,變得更加典雅華美。
陸機的擬古詩與古詩相對照來看,表現出的是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是一種表現手法的創新。與漢末古詩的古樸自然不同,陸機的擬古詩追求華麗,講求修辭手法,表現得更加含蓄與細膩。陸機擬古詩中有運用通感的例子。如《擬西北有高樓》“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還有如《擬今日良宴會》“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陸機以前的所有詩人,也沒有一個象他這樣較大量地、有意識地使用‘通感’手法。”[20]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至于其他的方面,如《擬行行重行行》和《擬今日良宴會》與古詩相比結構比原作更為嚴整,也比原作更講究語言的錘煉,徹底改變了原作口語化的語言風格,變樸素為典雅,情感表現更含蓄,鋪陳更加嚴重。[21]這些都是陸機繁縟綺靡的表現,當然也是陸機在表現手法方面表現出創新性的表現。
陸機繁縟風格的形成與陸機的文學觀念有關。陸云就說陸機:“往日論文,先辭而后情。”(《全晉文》卷一百二)陸機首先考慮的是文采,又喜逞才。《文賦》云“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這就是陸機為文的追求。陸機的擬古詩大膽嘗試,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努力打破前人的寫法,事物描繪追求窮形盡相,是很大膽很豪氣也很有創新意識的。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中指出:“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也就是說魏晉時期以陸機為代表的文人講求文辭華美,體現了五言詩由俗到雅的轉變,體現了詩歌發展的規律。在這個過程中陸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陸機擬古詩是陸機的主要作品之一。
(二)師其意不師其辭
如上文所說言意之辯理論對陸機的擬古詩有不小的影響。陸機的擬古詩被當時人所接受并取得不小聲譽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是魏晉的言意之辯理論。正如唐劉知幾《史通·模擬》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意思就是說詩意相類而表現形式不一致是模擬的上品。套用唐韓愈《答劉正夫書》里的說法就是:“師其義不師其辭。”當然,后人評價陸機《擬古詩》說“亦步亦趨”、“性情不出”很大程度上也是與此相關。不過陸機對古詩也并不完完全全的師古詩之意,正如伽達默爾說的“誰要模仿,誰就要刪去一些東西和突出一些東西。”[22]612陸機選擇古詩來作為模擬對象,也不可能完全和古詩一致。就表現來看,至少擬詩表現手法很多與古詩不同,在詩意上要說完全一致也不見得,還是有一些變化的。《六臣注文選》說陸機的擬古詩“比古志以明今情”[23]575俞士玲說陸機與《古詩》表現的情感主題產生極大的共鳴,“因而擬而作之,在其中注入一己之情懷。”[24]214陸機出生于魏晉吳地世家大族,國破之后,無奈入洛后,希望重振家風,然一介南人亡國之余,雖有才名,終不為北方士人所重,生存環境艱險。又少負異才,難免心有戚戚,有感而發。如《擬今日良宴會》、《擬青青陵上柏》集中表現對功名的渴望;《擬蘭若生春陽》、《擬涉江采芙蓉》突出表現忠貞與思鄉之情;《擬迢迢牽牛星》、《擬庭中有奇樹》加入了時間流逝的焦慮感等等。對于這種現象,赫兆豐歸納說“在抒情過程中綜合運用融入身世體驗、淡化提純、增強時間流逝感的藝術手法,對原作主題或深化或異化。”[25]因此陸機的擬古詩雖然相比于原作是有相似相類之處,但也不全是“亦步亦趨”的模仿。
四、陸機擬古詩的評價
(一)褒貶不一的評價
對于陸機的擬古詩,總體來說唐前人對擬古態度比較寬容,因此評價都還不錯。鐘嶸說陸機的擬古詩是“五言之警策者也”(《詩品序》)。蕭統編《昭明文選》“雜擬”部將其置于篇首。唐劉知幾篇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史通·模擬》)又韓愈云:“`師其義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到了明之后就反過來了,評價極低。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王夫之說“步趨如一。”(《古詩評選》卷四)許學夷說“擬古皆逐句模仿,則情性窘縛。”(《詩源辨體》卷三)賀貽孫、李重華、方東樹等人也有類似批評。近代雖然也有評價還不錯的如錢基博在其《中國文學史》中認為陸機“猶有建安遺韻”,但還是否定的居多。朱自清說:“陸機擬古詩差不多亦步亦趨。”(《古詩十九首釋》)胡適、陸侃如、鄭振鐸等也多是否定的觀點。其后文學研究所和游國恩版的《中國文學史》都評價說是“走向形式主義。”是“只略為變換詞句而已 ”等等。不過80年代以來,又有了新的變化。如毛慶《怎樣評價陸機的擬古詩》和陳欣、張帆《陸機擬古詩新探》等。相對來說評價較為客觀,評價較高。
(二)評價不一的原因
在唐前,模擬詩并不排斥與前人的詩意相同,正所謂“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劉知幾《史通·模擬》)也就是說,唐前人們對模擬的看法與后世是不同的。另外,陸機的擬古詩把古詩的風格由質樸變為文雅,體現了陸機的創新能力和才華,同時其華麗文風也與唐前人喜好華麗文風的風氣相符合,因此受到贊揚。雖然也有如張華就覺得陸機“更患其多” (《晉書·陸機傳》),陸云因“雅好清省”而提出批評的情況。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相比較而言,陸機的擬古詩是當時擬詩之中比較好的。其產生與它特殊的歷史時期有關,評價它需要結合當時的文學發展去考慮。
正如毛慶所說魏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期,一方面文學剛從經學里獨立出來。另一方面如何繼承之前的文學遺產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們都想尋找答案,研究其中的規律,于是也就有了眾多的文學理論著作如《典論·論文》、《文賦》、《文章流別論》等。對于創作來說,大家都知道不創新就沒有生命力,但想創新,能不能創新,具不具備創新能力都不是一回事。如何從前人作品中吸取養分,模擬是一個好方法,也無非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而已。孫月峰《文選集評》中說“若擬古詩道自進”,就說得很明白。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以陸機為代表的魏晉人是解決得比較好的。無獨有偶,唐代不少著名的大詩人都是寫擬詩的名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但他們同時也都是創新的典范與高峰。
陸機的擬古詩客觀上證明了提高詩藝,摹擬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陸機無論是對文學認識的深度還是繼承與創新上都得到了大多數時人的認可,得到了唐前文人的認可。他的擬古詩是通過模擬這種方式,學習和提高詩藝的樣板,也是體現他創新的一個方面。陸機的擬古詩雖然體現出繁縟綺靡的特點,但在文辭與表現手法上確實是有創新之處的,體現了陸機對詩歌語言形式的探索。因而陸機的擬古詩受到了文人們的推崇與研究,受到唐前詩論家的廣泛的贊譽也就不奇怪了。當然在一些如明清時期主張復古的批評家看來,這種探索是華而不實的。不過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他的這種探索是有意義的,代表了詩歌的一種發展趨勢。
當然,陸機的擬古詩也是有缺陷的。其一,雖然有情但情不夠深,不足以動人。陸云《與兄平原書》云:“一分生于愁思,遂復文。”又云“往日論文,先辭而后情。”太康時代的創作情形大多如此。他們有很強的創作意識也有情,但關注點不在情感的深度的表現上,情少而文多。這也就是包括陸機在內的大多數西晉詩人,其詩文缺乏動人的深度,為后人詬病的地方。其二,陸機的擬古詩太過注重文辭。雖然唐前詩人大都注重文采,故受到大家的歡迎。不過當時代變化,文學的審美趣味文學風氣發生變化時,陸機的擬古詩被貶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三)評價應注意的問題
首先,“模擬應該被理解為一動態的過程,擬作者選擇擬作對象的方向以及對于原作的介入性閱讀以及模擬時對于原作的取舍,都應納入考察范圍之中,這樣才能超越簡單片面的價值判斷。”[26]陸機擬古詩的藝術價值確實是比不上古詩。可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只是把擬作作品單獨拿出來考量,這樣的話就會遺漏很多東西。陸機擬古詩的形成與評價包含的社會和時代文化風氣因素,陸機的人生價值觀、審美觀、生命觀以及詩學觀等都是需要考慮的,更不能忽視其在文學和詩學發展史上的影響與地位。
其次,陸機的擬古詩不管怎么樣還是擬詩,與陸機自己正式的創作還是有一定區別,也有它的特殊性,至少是與古詩有不小的聯系,古詩對其有一定的制約性。另外,不同時代的古人對擬古的態度也不一致。總體來說唐前文人更多的是把擬古作為一種學習的方式的同時也作為一種與古人爭勝表現才學的手段。他們“并不以‘古’作為唯一的審美價值取向,而是將當代的審美興趣貫注到擬古詩創作中。”[27]而之后的文人,就少了與前人爭勝的意味,多是學古了。這一點在評價時也是需要考慮的。
最后,“文人擬作構筑了具有互文性意義的宏大景觀,它向我們顯示了創新本身所具有的摹擬特質和摹擬本身同樣具有的創新意義。具有互文性特征的相似體式的文本增值,促成了某種文體慣例或文類形式的形成。”[28]無數模擬文本的誕生,它們鞏固、發展和完善了模擬對象所具有的體制形態,轉化成為一種人們普遍認同的文學形式,也就是文學模擬對象經典化的過程和經典作品的接受過程。正如錢志熙所說“魏晉之際的詩壇上,擬古的風氣逐漸流行開來。這種擬古的現象……從詩歌史自身的發展規律來看,正標志著漢魏詩歌經典地位的確立。”[29]同時文人在模擬過程中也有可能導致新的文體樣式的產生,產生新的文類。如《昭明文選》中的雜擬類這一個文體類別的誕生,如《演連珠》與連珠體的形成與形制的確立等。因此在模擬過程中雖然也受到模擬對象的限制,但是也會有新變。模擬的這種限制與新變,既保持了文學的傳統性,也促成了文學的新變與發展。也就是說擬作的發生與形成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文學接受與文體學方面,尤其是在經典文本的形成過程與新的文學樣式的確立上有著獨特的研究價值。就陸機的擬古詩來說,與古詩和《昭明文選》里的其他雜擬類作品的關系是很值得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