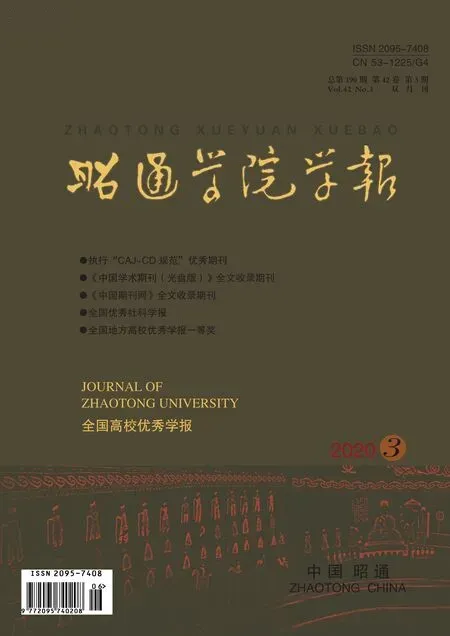悲苦是蜜,全憑心釀
——評遲子建小說《候鳥的勇敢》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候鳥的勇敢》作為遲子建最長的一部中篇小說,延續了她以往的創作風格,依舊沒有描寫如火如荼的大事件,而是用悲憫的眼光去描繪蕓蕓眾生中社會最底層人民的百態人生。
小說以候鳥管護站與娘娘廟為敘事基點,通過對候鳥命運的敘述表現了人世的悲歡離合。透過小說我們發現遲子建展示給我們的縱然有憂傷,但又透著一抹溫情的亮色。他們處于物欲橫流的社會,但依然保守著內心的那方凈土;他們的人生中充滿苦難,但內心始終向往塵世的美好;他們渴望愛意與溫情,便去追逐這愛意與溫情。這就使得他們灰暗的人生不再灰暗,使得所有苦難終將得到消解。
一、對自我人格的堅守
遲子建在小說后記中寫道:“無論善良的還是作惡的,無論貧窮的還是富有的,無論衙門里還是廟宇中人,多處于精神迷途之中。”[1]202透過作品我們不難發現,生活在瓦城這片藍天之下的人們,無論是候鳥人還是留守人他們或追逐功名或追逐利益,均在塵世中迷失了自我,而能夠守住本心的恐怕也只有候鳥管護站的張黑臉與娘娘廟的慧雪師太。他們二人一個在塵世一個在空門,無論世俗如何變幻,他們依然堅守著自我高尚的人格,從他們的生命形態中讓我們看到了盡善盡美的一面,體悟到了人性的善與溫暖。
張黑臉可謂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人物,先是因一場森林大火使自己變得癡呆,繼而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而在女兒張闊眼中他只不過充當了提款機,毫無親情可言。自從癡呆之后,“他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能奇妙地預知風雪雷電甚至洪水和旱災的發生,但對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斷力,卻直線下降,靈光不再。”[1]003因為這場災難使他喪失了對世俗的感知,同時也讓他遠離了世俗的爭權奪利,保持了人性中最可貴的率性坦然,對于我們而言生命的意義也正在于此,所以遲子建在張黑臉身上寄寓了理想人性,讓我們在蒼涼的現實中看到一抹溫情的亮色。因為在大火中被東方白鸛救過命,所以他對候鳥有著十分熾熱的感情,當他發現周鐵牙有獵殺候鳥的可疑行跡后,便“罷免”了周鐵牙的站長職務,看似呆傻的張黑臉,卻讓我們從他的言行中看到了淳樸善良,而這種淳樸善良也最貼近自然的秉性。遲子建通過對張黑臉璞玉渾金品格的塑造,將世間人性的丑惡展現的淋漓盡致。
《候鳥的勇敢》中對慧雪師太著墨并不多,但她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娘娘廟本應是塵世中的一方凈土,卻沾染了世俗的習氣,扮演著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角色,而與云果和德秀兩位師傅相比,也只有慧雪師太堅守著自己的本心不為塵世所累。當面對婆娑眾生的困惑:人生苦楚眾多為什么是八苦?作為新貴的候鳥人,他們總是沐浴在春風之中,菩薩能否讓苦寒之地四季無冬,讓無法遷徙的窮人避開人生的風寒?慧雪師太以其超凡脫俗的智慧勸誡眾生:“浮沉煙云,總歸幻象。悲苦是蜜,全憑心釀。”......“所有的問題,在時間面前都不是問題了。”慧雪師太以超然的智慧看透世事,洞悉生命的本質。“她給予俗眾的指引,也是作者給予讀者的指引,更是作者給予自己的指引。生命也許永遠無法與時間對抗,然而正是時間的限制讓生命在有限的長度內盡力獲得充實與圓滿。”[2]在喧囂的塵世,慧雪師太不僅沒有像云果與德秀兩位師傅一樣眷戀紅塵,反而以其無上的智慧喚醒了迷惘的眾生。
瓦城這個世界無疑是一片渾濁之地,而張黑臉與慧雪師太的存在正是使人性重建的希望之光,他們以其自身的高尚品格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眾生指引方向。從張黑臉身上我們總是能夠看到一絲蒼涼的暖,他生活在社會底層,但心存善念,以自己的善來感化這個波瀾重重的世界,即使看到人性的惡但依然對人性充滿期許的善;慧雪師太因感念眾生遁入空門,她以悲憫的情懷給予生活在負俗之累中的瓦城人民以指引,道出生命雖然有時而盡,但浮沉煙云終歸是空,唯有守住本心才能夠超越時間的限制,綻放人生的光芒。整部作品也因這兩人的存在而讓人不再感到人生的無望與生命的荒寒。
二、對苦難命運的超越
陳曉明曾指出:“沒有苦難,何以有文學?”而苦難書寫也一直是遲子建文學創作的母題,特別對女性的苦難命運書寫更具有時代特色。遲子建著眼于現實,以女性的視角聚焦社會中女性所面對的重重困境,有來自家庭的也有社會的。前者如《白雪烏鴉》中的翟桂芳,后者如《候鳥的勇敢》中的云果與德秀,她們帶著一顆傷殘的心在人世間隱忍的活著,并以頑強的意志去超越生命的苦難,尋找人生的真諦。對于生活在苦難中女性的描寫遲子建傾注了更多的悲憫情懷,引人思考。
娘娘廟中的云果師傅是一位頗具傳奇性的人物,她究竟為何出家?她的的身世又如何?我們無從知曉,關于她的傳說眾說紛紜,而遲子建最終也沒能夠給讀者一個確切的答案,但透過文本我們可以感知她生活的不幸。當香客問她來處,“云果師傅總是一挑眉毛說:‘出家人只有去處,哪有來處。’雖然她說的禪意深厚,但因她愛挑眉毛,香客們說她修行不深。”[1]22從她挑眉這一動作可見香客觸碰到了她最為脆弱的內心;對石秉德產生朦朧的愛意卻愛而不能令她悵然若失;在慧雪師太講座中眾人對她的質疑又可以窺見她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風雨人生;她沒有慧雪師太那種超然物外的人生智慧,也不像德秀師傅有可以傾訴的對象,她只能在青燈古佛前默默自我救贖。當所有的苦難化為佛前的一縷青煙她便完成了自我救贖,所以第18 章遲子建寫到了云果師傅的云游,云果師傅沒有說自己去哪兒,但說會在落雪之前回來,到最后紛紛揚揚的大雪飄落人間,但云果師傅并沒有回來,給讀者留下了一個謎一樣的結局,但我們更愿意相信她在完成自我救贖后重返人間,去追尋屬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如果說云果師傅的人生苦難是隱性的,那么德秀師傅的人生苦難便是顯性的。德秀師傅先后有過三任丈夫,前兩任丈夫的離世,使她背負上了克夫的罪名,所以她主動與第三任丈夫解除了婚約。當女兒也將自己坎坷的命運歸罪于她,母女關系走向末路,德秀師傅便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在哪,然而她又沒有勇氣面對死亡,所以最終在瓦城政府的動員下皈依佛門。德秀師傅雖身在寺院,然而卻難以戒除塵穢,始終徘徊在世內與世外的邊緣,當她看到波光里鳧游的野鴨,內心也不免會陣陣嘆息,她既慨嘆野鴨的相知相守又慨嘆“出家人無喜無悲”。凡此種種可以看出德秀師傅選擇走上這條救贖之路并不是出于本心,她不是為了尋求身形上的解脫,而是心靈上的超越。遲子建曾說:“心靈自由了,就沒那么多的怨艾和煩惱了”,[3]但是清規戒律未曾使她心靈自由,真正使她的苦難得到超越的是塵寰的溫情。當她真正體會到什么是愛與被愛,所有的苦難便開始得到消解,她雖然時時的懺悔與自責,但依舊渴望來自張黑臉的那份溫存,在見證東方白鸛“夫妻”至死不渝的愛情后,她生命中的所有苦難終于得到了凈化。
雖然云果師傅與德秀師傅所承受的苦難有所不同,但苦難的根源卻出奇的相似,她們的生存困境均與男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換言之她們所承受的苦難均是來自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形態,在將希望寄托于愛情與婚姻的同時又被愛情與婚姻所摧殘。遲子建以溫情而又感傷的敘述給予苦難者以關懷,寫出了女性的生存之苦與精神之困,但她并沒有將她們囿于這無盡的苦難之中,而是在苦難中讓人看到希望之光,她們在經歷了重重困苦之后得到解脫,這也是遲子建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所具有的悲憫情懷。
三、對溫情愛意的渴望
愛情作為一個永恒的話題存在于文本敘事中,遲子建同樣善于描繪人世間的愛與被愛,但是她筆下的愛情是一種凄美的愛情,《親親土豆》中秦山夫婦的愛情,《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的愛情,以及《候鳥的勇敢》中張黑臉與德秀師傅的愛情,均是一種凄婉而美好的愛情,這或許跟作者的人生體驗有關。在 《候鳥的勇敢》封面上有這樣兩句話,“紅塵佛面,寒來暑往。所有的翅膀都渴望著飛翔。”渴望飛翔的不僅僅是那對東方白鸛“夫妻”,更是飽經風霜的張黑臉與德秀師傅。
遲子建在《候鳥的勇敢》中著重描寫了一對相濡以沫的東方白鸛“夫妻”,這對“神鳥”不僅是張黑臉的救命恩人,也存在于遲子建的生命之中。通過對東方白鸛的描寫牽引出憨厚的張黑臉與苦命的德秀師傅的愛情故事。東方白鸛的出現使張黑臉的意識逐漸清醒,同時也對德秀師傅漸生情愫,終于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兩顆傷痕累累的心碰撞在了一起。他們渴望愛情卻又難以走出內心的圍城,所以彼此在犯下“禁忌”后都等待著上天的懲罰,此時他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既擔心上天的懲罰又渴望著下一次的相見。既然無法預知來世如何,那么就應該把握住今世的幸福,所以沒有等到上天懲罰的德秀師傅主動去找了張黑臉,然而張黑臉卻拒絕了德秀師傅,他在等德秀師傅還俗,能夠體體面面的和她過日子,這對于張黑臉而言可能是一種無比幸福的期待,但對于德秀師傅而言卻是無比的煎熬。相對于張黑臉的清醒認知,德秀師傅顯然陷入了迷惘之中,她認為作為佛門中人破戒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終將有一天會得到上天的懲罰,或許是明天,或許是明年,或許是來世……
《候鳥的勇敢》中東方白鸛的凄美愛情與張黑臉和德秀師傅的凄美愛情相互映襯。因人類的無恥偷獵使得雄性白鸛受傷,雖然得到了候鳥管護站的救治,但始終沒能完全恢復,霜越來越重,雌性白鸛在送走它們的三個孩子后返回到它的愛侶身邊,“它們以河岸為根據地,雌性白鸛一次次領飛,受傷的白鸛一遍遍跟進,越飛越遠,越飛越高。”[1]198當我們都為它們的成功遷徙而慶幸時,卻不知它們終究沒有逃出命運的暴風雪,它們在雪地里翅膀貼著翅膀相擁而“眠”。張黑臉與德秀師傅用自己的雙手為兩只替他們贖罪的白鸛挖墓穴,十指流出的鮮血猶如梅花落在了它們的白羽之上,使它們帶著鮮艷的殮衣歸于塵土。在一切儀式結束后他們饑腸轆轆,而此時狂風卷積著飛雪使他們辨別不出來時的路,沒有北斗星與哪一處人間的燈火作為他們前行的路標。小說到此戛然而止,盡管我們期待他們的結局如同遷徙成功的候鳥一樣,能夠找到回家的方向,“可是生活的真相告訴我們,我們所期待的,與我們所看到的,往往背道而馳。”[4]在文中張黑臉與德秀師傅既成就了那對東方白鸛,東方白鸛也成就了他們二人,他們勇敢的去追求這份溫情與愛意,但注定不會為世俗所容,這一結局固然凄涼但也讓我們領會到了什么是人間大愛。
遲子建在《候鳥的勇敢》后記中寫道:“我寫的最令自己動情的一章,就是結局,兩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鳥兒,沒有逃脫命運的暴風雪,而埋葬它們的兩個人,在獲得混沌幸福的時刻,卻找不到來時的路。”[1]202雖然他們無法找到來時的路,但此時的幸福是那樣的真切,也許這就是他們所尋求的救贖之路,此刻他們不在恐懼,而是給人一種甜蜜的溫馨感,就如同劉艷所說:“愈是滄桑中的溫情與愛意,越能給寂寞的人心和蒼涼世界一抹亮光。”[5]這讓蒼涼世界中的眾生在生死面前看到了希望之光,而這希望之光正是人性中對愛的勇敢追求。
四、結語
想必遲子建在寫作《候鳥的勇敢》時與寫作《群山之巔》有同樣的感觸吧!作為遲子建近年來比較重要的兩部作品,它們在敘事中有著眾多相似之處,例如:對于小人物悲慘命運的描繪;對冥冥之中無法把握自我命運的嘆息等。在讀《候鳥的勇敢》結尾處不禁讓人想起《群山之巔》結尾時的景象,安雪兒在土地祠經歷了生死輪回,無助的她極力呼喊,然而“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喊!”[6]同樣是漫天的大雪,同樣是上演著人間凄苦的悲劇,讓人頓生“一種莫名的空虛和徹骨的悲涼!”[6]然而,遲子建對于故事的講述有一種溫度蘊含其中,這便是她的人性關懷。《候鳥的勇敢》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行善的還是作惡的;無論是貧窮的還是富有的,遲子建均給予他們人性關懷,讓行善的與貧窮的在困苦中看到希望;讓作惡的與富有的在感受世事無常中有所醒悟。這也讓每一位讀者為之動容,讓我們從中領悟生命的真諦——“悲苦是蜜,全憑心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