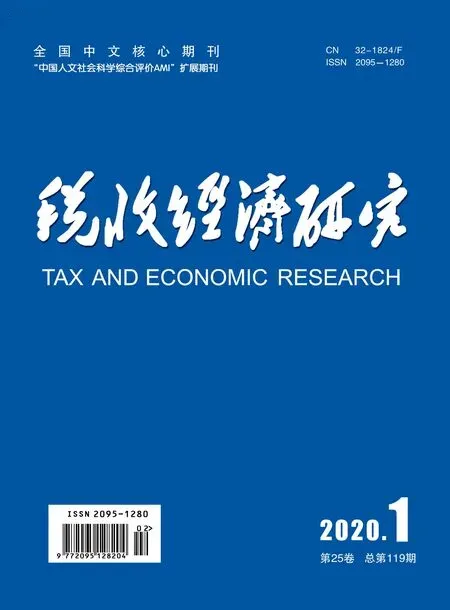環境稅政治可行性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周志波
內容提要:有關環境稅政治經濟學問題的文獻主要分析環境稅政治可行性的影響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這些文獻在環境稅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不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還為提高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最大限度發揮其環境政策效應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文章梳理環境稅政治可行性影響因素的既有文獻,重點從政權結構和政治博弈、制度效率和效應預期、改革模式和實施方式等三個方面進行歸納,并就現有研究的貢獻和不足做出評述,為環境稅理論更好地應用于政策實踐提供決策參考。
緩解和應對氣候問題的環境政策,特別是環境稅政策,面臨經濟效率約束(Economic Efficiency Constraint)和政治經濟約束(Political Economy Constraints)。前者規定緩解與氣候相關的外部性的社會成本不超過社會效益,后者則要求緩解氣候問題等負外部性的相關私人成本不超過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各種政治經濟約束(Aidt,1998;Jenkins,2014),①這種政治經濟約束有很多形式,包括對具有較高資產專用性的工業部門的福利損失的限制、對汽油、燃氣等要素價格上漲進而影響家庭支出的限制以及對稅制改革導致的家庭成本凈增加的限制等。這些實際上就是影響環境稅改革政治可行性的因素,屬于環境稅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有關環境稅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釋為什么環境稅優先于其他環境政策調控手段(Buchanan &Tullock,1975;Dijkstra,1998;Aidt & Dutta,2004),它們如何以及為什么偏離了Pigou(1920)的理想(Pearson,1995;Fredriksson,1997;Fredriksson & Millimet,2004;Fredriksson &Sterner,2005),或者有什么空子可以鉆(Polk & Schmutzler,2005),此后相關研究逐漸聚焦環境稅制度的政治可行性問題。已有的文獻發現,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特別是社會可接受性,主要受到國家政治權力結構和政治博弈、環境稅改革模式和實施方式、制度效率和效應預期、環保意識和公眾認知等因素的影響②但是,國家政權結構和政治博弈、改革方式和實施方式、制度效率和效應預期、環保意識和公眾認知等因素,都是從比較宏觀的層面進行概括,具體是什么因素影響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以及通過什么機制或渠道影響、影響的力度有多大,這一系列的問題,學術界尚無十分明確的結論。(Oates & Portney,2003;Aidt & Dutta,2004;Ercolano,Gaeta &Romano,2014;Davis,2017)。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環境稅政治可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做一梳理歸納,并就已有文獻做出評述,對未來研究做出預測。
一、政權結構和政治博弈對環境稅政治可行性的影響
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被看作一個理性的政治決策過程的結果,受到黨派政治、意識形態、組織結構、部門利益、決策程序等政權結構方面的因素影響,在這個過程中,選民、政治家、特殊利益集團和官僚的利益得到權衡和緩和(Aidt,2013)。Cremer,Donder & Gahvari(2008)根據Roemer(2001)的政治競爭理論提出了一個符合美國低排放稅率的政治經濟模型,分析了民主黨與共和黨合作維持低稅率以提高環境稅(排放稅)政治可行性的現象。①在模型中,選民投票決定環境稅稅率和預算規則,規定如何重新分配稅收收入,他們的投票決策因工資和資本收入不同而有所區別;而政黨關心他們提出的政策以及選舉獲勝的可能性,最終實現政黨一致納什均衡(PUNE)。他們使用美國數據校準模型并計算政黨一致納什均衡(Party Unanimous Nash Equilibrium,PUNE),結果出現兩種均衡狀態:一種均衡反映兩黨激進分子的偏好,兩黨均提出非常高的稅率,民主黨人通常打敗共和黨人達到均衡;另一種均衡更受那些最關心贏得選舉的機會主義者支配,他們既提供環境稅補貼,又有機會贏得選舉。但在政治決策實踐中,兩黨的利益沖突得到調和,一致支持不提高環境稅稅率,并提高了環境稅的公眾接受度。Ashworth,Geys & Heyndels(2006)、Ashworth等(2014)就西方國家的多黨政治對環境稅改革的影響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環境稅改革要求實施一種新的稅收,具有潛在的成本,各個政治派別都要做出權衡;②他們基于1991—1999年間佛蘭德地區308個城市實施新環境稅的分析發現,在大選期間實施環境稅改革的可能性較平時小得多,但如果在地理位置或意識形態上比較接近的國家已經開征環境稅,那么這種可能性就會明顯提升。研究發現,政府內部的分裂程度越大,新開征環境稅的可能性就越低,這一結論符合通常的認知。
關于政權結構和政治博弈影響環境稅政治可行性問題的文獻,Brett & Keen(2000)、Clinch,Dunnea & Dresner(2006)、Davis(2017)等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Brett & Keen(2000)認為,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主要受政治不確定性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包括在政府中不同政黨的政治力量對比、各政黨對綠色稅制改革(Green Tax Reform)的傾向、不同的執政理念等。他們的研究強調了不同政黨在國家政權組織中的力量對比對于環境稅改革政治可行性的影響,發現在實踐中往往是少數黨派對于綠色稅收具有明顯的傾向,并且少數黨派的積極推動會促成環境稅的實際稅率雖然低于庇古稅率但卻高于通常的政治程序確定的稅率。Clinch,Dunne & Dresner(2006)認為,環境稅改革在政治可行性方面主要受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政黨和議會權力結構。一國議會的組成以及各政黨的相對實力將對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造成很大的影響,在聯合執政的國家,實力較小的“綠黨”(Green Parties)可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從而加速環境稅改革的推進(Clinch &Dunne,2006)。二是部門利益博弈。環境績效的責任往往與環境部門有關,稅收政策通常由財政部門負責,二者在環境稅政策問題上往往意見相左,③財政部門一般不愿意接受環境稅改革的擔保原則(Principle of Hypothecation)。降低了環境稅改革的政治可行性。三是基于經濟環境考量的政治妥協。宏觀經濟條件可能會影響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④如果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期,國內失業率上升,刺激就業的政策可能會變得更有吸引力,特別是當實際收入下降的時期,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就面臨很大的挑戰。與宏觀經濟狀況密切相關的是關于環境稅影響競爭力的擔憂,能源密集型公司通常是受環境稅沖擊最嚴重的企業,但這些企業往往又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政府部門中發出最為響亮的聲音,對政府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⑤因而,通常的結果是,環境稅改革在初期對這些企業實施豁免或減免政策,但實踐證明這種政治妥協有助于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四是配套調節制度。如果在實施環境稅改革的同時,制定一些配套制度保護低收入群體等弱勢階層,將有助于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⑥環境稅改革需要建立一個比較全面的配套制度體系來保護弱勢群體因環境稅潛在的累退效應而利益受損。處于貧困線邊緣的群體對燃料定價十分敏感,而這些人可能本身也不屬于繳稅的群體,因而不會因環境稅收入用于勞動稅收減稅而受益。Jenkins(2014)指出,環境稅等應對氣候問題的政策,可能由于資產密集型行業的激烈反對引發各政治集團的博弈,而遭受政治經濟學上的考驗。Davis(2017)研究發現,環境政策決策還受到選民黨派傾向、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的影響,如果各黨派的差異過大,可能會導致環境稅改革決策程序低效、周期變長,并在制度設計上出現公眾或選民接受度較低的問題。
實際上,從是否對決策有利的角度,可以將政權結構因素分為政治妥協類因素和利益沖突類因素(Zhang,2017)。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妥協在很大程度上會提高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則會降低這種政治可行性(Clinch,Dunnea & Dresner,2006)。Aidt(2015)也指出,很多文獻強調組織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團(通常為受環境稅影響較大的大型企業或財團)在環境稅的實施中起著支配作用,但不同政治集團之間以及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妥協會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①這暗示了對環境稅等環境激勵政策強烈的政治偏見,但發達國家正在實施的環境稅改革給這一觀念提出了挑戰,因為這些國家正在通過更加雄心勃勃的環境目標、增加公共資金的邊際成本以及更加強調通過收入返還和免費分配可交易許可證來換取環境稅的政治可接受性。Deroubaixa & Lévèque(2006)分析了法國生態稅改革從實施到取消的全過程,②環境稅改革本該成為法國左翼聯合政府最主要的政治決策和成功,但當法國憲法法院于2000年12月決定停止實施環境稅之后,這一決策成為其最大的敗筆。并研究了其背后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通過從焦點小組(Focus Group)收集的意見及對企業人士和決策者的訪談,發現法國環境稅改革最終被憲法法院判決違反憲法、遭遇政治上的失敗,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決策者缺乏關于公眾和企業意見的關鍵信息,有關環境稅改革的一些關鍵爭議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決策程序上沒有做出提高環境稅政治可行性的努力,并且未能及時地解決相關利益集團的矛盾;二是政府相關行政部門之間存在意見沖突,缺乏必要的政治妥協,特別是財政部門和環境部門在環境稅的稅基問題上存在很大的爭議。Hysing(2015)研究了瑞典哥德堡市引入擁擠稅(環境稅的一種形式)的政治決策過程,重點分析了政府提高擁擠稅合法性的策略。他們發現,盡管政府認為擁擠稅是改善城市環境和健康問題的有效政策措施,但事實證明擁擠稅很難被公眾接受。哥德堡市的擁擠稅主要通過市議會的廣泛支持而實現合法化,而市議會為了確保其合法化,將擁擠稅與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結合起來,但在整個過程中沒有讓公眾直接參與政策決策程序(包括公眾聽證、咨詢、投票等)。③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決定可能得到公眾的接受,但所采用的程序也可能證明不利于擁擠稅的未來實施,并破壞對民主機構的信任。
此外,一些研究者還分析了環境稅提高其他稅收制度改革政治可行性的作用和機制。比如,Giménez & Rodr?guez(2010)就發現,如果考慮到同時進行的“次優稅制”(Sub-optimal Taxation System)的改革,環境稅可能在減輕現有稅制扭曲問題面臨的政治約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個優勢已經被一些早期在該領域很有影響力的學者所認可,如Bovenberg & Goulder(2002),他們斷言“環境稅是潤滑油,它使得稅制改革成為可能,以消除特別糟糕的稅收”。
二、制度效率和效應預期對環境稅政治可行性的影響
在實施環境稅改革之前,決策者應當而且必須回答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即這項稅收制度與排放或技術標準等其他環境政策相比,在效率上是否具有優勢(Helming,1997;Kleinhanss,Becker & Schleef,1997;S?derholm & Christiernsson,2008),對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具有怎樣的預期效應。環境稅的制度效率,其核心問題是制度的收益成本問題(B?cher,2012),如果環境稅改革的收益高于其成本,那么環境稅就具有制度效率。在環境經濟學領域,關于稅收政策獨立于支出政策一般具有效率的論證非常重要,環境稅的開征會帶來社會凈收益或社會凈成本(環境維度的收益除外),也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Ashworth,Geys &Heyndels,2006)。當然,環境稅的制度效率有多個維度,一般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環境稅改革是否有利于降低其他稅種的扭曲效應(Distortion Effects),從而提高整個稅制的效率。第二,環境稅改革是否有利于促進污染減排,從而改善環境質量,實現政府的環境政策目標。第三,環境稅是否能夠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或者刺激經濟增長,促進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第四,環境稅是否有益于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比如刺激就業、促進公平等。實際上,環境稅制度效率的諸多維度,都指向了理論界的一個核心概念——“雙重紅利”效應(也稱“雙重紅利”假說)。
所謂“雙重紅利”效應,是指環境稅除了可以促進控污減排、獲得環境維度的紅利效應之外,還能獲得促進經濟效率提升、收入分配公平的紅利效應(Bovenberg & Ploeg,1998)。一方面,環境稅如果通過激勵減排改善環境(Hourcade & Robinson,1996;S?len & Kallbekken,2011),獲得了“第一重紅利”(也稱綠色紅利或環境紅利);另一方面,環境稅如果通過扭曲性稅種結構性減稅,利用價格傳導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增加社會就業等(Galarraga,Abadie &Ansuategi,2013;周志波、張衛國,2018),獲得了“第二重紅利”(也稱藍色紅利或非環境紅利)。換言之,環境稅如果能夠改善環境,就獲得了環境紅利;如果能夠提升經濟效率或促進社會公平,就獲得了非環境紅利;如果環境紅利和非環境紅利同時存在,就稱環境稅獲得了“雙重紅利”效應(Pearce,1991;Dresner,Dunne,Clinch & Beuermann,2006;劉曄、周志波,2015)。Goulder(1995a)界定了兩種類型的“雙重紅利”:(1)強式雙重紅利,即當環境稅改革利用環境稅收入為更為扭曲的稅種減稅籌資,不僅可以改善環境質量,還可以在總體上改善社會福利水平,因而環境稅改革的總體成本很低甚至為零;(2)弱式雙重紅利,即與一次性轉移支付相比,環境稅收入如果用于扭曲性稅種的結構性減稅,環境稅改革的成本會更低,同時環境質量也可以得到改善。已有的文獻表明,弱式雙重紅利效應一般沒有太大爭議,而強式雙重紅利效應是否成立并無一致意見,一般認為其結果往往取決于經濟的稅收結構(Ercolano,Gaeta & Romano,2014)。
一些文獻表明,環境稅改革的政治可行性,還受到政策效應預期的影響。環境稅“雙重紅利”效應,既是環境稅制度效率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涵蓋了環境稅政策預期效應的主要內容。早期有關“雙重紅利”的討論主要基于環境的視角(如Tullock,1967;Terkla,1984;Lee & Misiolek,1986;Pearce,1991等),更多地關注環境稅對環境質量的預期效應和對扭曲性稅制的制度效率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相關研究主要基于公共財政的視角,在Sandmo(1975)建立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最優環境稅問題,并將環境稅改善環境質量視為理所當然,主要關注其在經濟維度的制度效率問題(Ercolano,Gaeta & Romano,2014)。OECD國家的實踐表明,“雙重紅利”假說成為1990年代環境稅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如果“雙重紅利”假說成立,環境稅在政治可行性方面將獲得極大的提升,即便在環境稅改革飽受爭議的國家,公眾對其接受度會因事實上的“雙重紅利”效應而得到顯著改善。
三、改革模式和實施方式對環境稅政治可行性的影響
在歐盟和美洲國家的環境稅改革實踐中,很多學者觀察到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即環境稅的稅率與理論上最優的稅率差距較大,無法有效補償外部性成本。導致實際稅率與最優稅率背離的原因,除了污染減排成本和污染邊際損害成本具有不確定性之外(Brett & Keen,2000;Jenkins,2014),最主要的就是社會公眾反對(Public Opposition)(Gaunt,Rye & Allen,2007)。所謂公眾反對,就是公眾(包括企業和個體)反對政府實施環境稅改革,①公眾反對的核心問題在于,環境稅可能損害他們自身的利益,可能成為政府“與民爭利”的工具,甚至成為滋生腐敗問題的溫床,也可能在公共支出方面不能實現其作為環境經濟政策的初衷。一方面反對環境稅增加自身承擔的稅負,可能是選民反對環境稅負擔被轉嫁到消費環節,也可能是相關利益集團或行業反對環境稅直接減少資本回報(Deroubaixa & Lévèque,2006);另一方面反對環境稅淪為政府籌集公共支出的手段,成為政府財政的“提款機”,而弱化了保護環境的政策合法性(Dharshing,Hille &Wüstenhagen,2017)。而公眾反對的背后,折射出影響環境稅改革政治可行性的兩大制度性問題:一是改革模式的設計問題,①總體而言,環境稅改革的模式有三種,即財政收入增加模式、財政收入中性模式和財政收入減少模式。在財政收入增加模式下,環境稅的實施增加了居民和企業的總體稅收負擔,宏觀稅負上升;在財政收入中性模式下,實施環境稅的同時通過一次總付稅返還、扭曲性稅種結構性減稅等方式,保持財政收入總體穩定;在財政收入減少模式下,實施環境稅的同時,通過其他稅種的減稅或更大力度的收入返還或補貼計劃,實現財政收入的總體下降。二是改革實施方式的選擇問題。②總體而言,一項改革或政策的實施,政府可以選擇即期實施和遠期實施。即期實施的環境稅改革,在政府做出決策之后,較短時間內正式施行;遠期實施的環境稅改革,在政府做出決策之后,先進行“政策預告”,并預留較長的“政策預告”期,讓企業和居民形成比較穩定的政策預期后,在規定的未來某一個時間開始正式實施。
已有的文獻表明,稅收綠化可以使環境外部性內生化并增加財政收入,但環境稅改革的模式選擇對其政治可行性具有重要影響(Cremer,De Donder & Gahvari,2008;Jones,Clark &Malesios,2015)。Cremer,De Donder & Gahvari(2004)發現,環境稅收入是否返還對其政治可接受性具有明顯的影響,提高環境稅收入返還率可以提高中間選民(Median Voter)對環境稅的接受度和支持率。Fredriksson & Sterner(2005)、Sterner & Isaksson(2006)、Fredriksson,Matschke & Minier(2010)發現,環境稅改革如果設計了收入返還機制,具有減排技術的企業會提高對高稅率環境稅的接受度,再次驗證了Cremer,De Donder & Gahvari(2004)的結論。Aidt(2010)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將環境外部性內生化和財政收入增加作為特殊利益和選舉政治的內生性結果,比較研究了環境稅收入用于所得稅減免(財政收入中性)、額外公共支出(財政收入增加)和對污染者的稅負補償(財政收入減少)三種模式下的政治可行性,結果表明:污染游說團體(Polluting Lobbying Group)可以游說政府將環境稅收入返還給選民而不是其成員,財政收入中性模式的環境稅改革更具有政治可行性。其內在邏輯:游說團體為稅收綠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通過支持一項令選民滿意的退稅規則得到顯著的降低,將環境稅收入用于所得稅減免返還給廣大選民,可以提高環境稅改革的社會公眾接受度和政治可行性。
一些研究發現,環境稅改革的實施方式也是考察其政治可行性的一個重要維度(Barker等,2009)。比如,OECD(2012)的報告指出,OECD國家在推行環境稅改革的過程中,公眾接受度較高,進展比較順利,得益于其政策預告制度和漸進改革方式。丹麥1988年就對其1993年實施的能源稅改革進行了預告,自1993—1997年逐年提高能源稅的稅率;德國1999—2003年的環境稅改革,也采取了“漸進的”實施方式,逐步提高各個稅目的稅率(黃玉林等,2014)。同時,研究者發現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環境稅改革在正式實施之前,有一個“試運行”階段,如果在“試運行”階段運轉良好,社會公眾接受度比較高,其政治可行性就會相應較高。比如,Cherry,Kallbekken & Kroll(2014)就發現,“試運行”的改革實施方式,可以有效避免改革初期的納稅逃避等問題,并提高改革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和社會的接受度。
此外,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發現,上下文信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的任意差別會導致在相同決策中的偏好改變(Tversky & Kahneman,1989),違背了Neumann &Morgenstern(1947)提出的“不變性原理”(Principle of Invariance),這就造成了所謂的框架效應③所謂框架效應,最早由Tversky和Kahneman于1981年提出,是指人們對一個客觀上相同問題的不同描述,做出了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決策判斷。相同的客觀問題,通過變換框架,將得到可預知的不同結果。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收益和損失完全是以認知參照點為依據的,參照點不一樣,人們決策的方式也不一樣。一個具體的例子:讓人們對下列情景進行決策(被試N=150)。情景一:如果一筆生意可以穩賺800美元,另一筆生意有85%的機會賺1000美元,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賺。情景二:如果一筆生意要穩賠800美元,另一筆生意有85%的可能賠1000美元,但相應地也有15%的可能不賠錢。結果表明,在第一種情況下,84%的人選擇穩賺800美元,表現在對風險的規避,而在第二種情況下87%的人則傾向于選擇“有85%的可能賠1000美元,但相應地也有15%的可能不賠錢”的那筆生意,表現為對風險的追求。(Framing Effects)。Dharshing,Hille & Wüstenhagen(2017)的研究證實,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還受到改革方案的框架效應影響,即對同一種改革方案的不同描述,會導致改革在政治可行性方面的不同結果,比較積極、正面的方案描述,獲得的支持率明顯高于比較消極、負面的方案描述。而這種框架效應的強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取向(Chong & Druckman,2007、2012;Faricy & Ellis,2014),這與有關個體差異的文獻研究結果一致(如Smith & Levin,1996;Le Boeuf & Shafir,2003)。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實際上說明,決策者對于政策或制度設計的描述方式非常重要,完全相同的一種政策方案,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可能獲得截然不同的結果,這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制度設計的“技術層面”,屬于公共決策的“藝術層面”。
四、文獻述評和研究展望
任何一項制度或政策,不僅要關注其在實體層面對外界的效應問題,更要關注其程序層面自身的設計問題,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程序性問題。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是其出臺實施并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只有被政府、公眾和社會廣泛認同,共同接受的制度和政策才有現實的生命力,才有實現政策目標、保障公眾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換言之,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是其有效性的基礎和前提。
長期以來,有關環境稅的研究在分析環境稅改革的政策效應、預測環境稅改革對經濟的影響、模擬環境稅運行的效果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對于環境稅本身的關注仍然不夠,一方面表現在對環境稅制度本身的程序性問題關注不夠,另一方面表現在對環境稅政策的政治、社會、文化等維度的研究不多。換言之,早期研究的焦點在于環境稅會對經濟運行、社會公平等產生什么影響,強調其對外界的作用;而對環境稅自身的關注不多,特別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其決策程序、政治可行性、影響其實施的因素方面還存在研究短板。近年來,理論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問題給予高度的關切,本身是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和進展,符合理論研究的特點和規律,也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果。
總體而言,現有的關于環境稅政治可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貢獻。第一,在環境政策和公共財政視角之外,引入了環境稅研究的第三種視角——政治經濟學框架,為環境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第二,從關注環境稅對外界的影響,轉向研究環境稅自身的可行性問題,讓有關環境稅的研究沿著“由外向內、由表及里”的方向發展,有利于發現更深層次的本質問題。第三,為進一步研究如何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進而為環境稅改革決策提供建議,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研究基礎。但與此同時,現有的研究也還存在一些局限性,最明顯的不足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于相關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二是對于如何在政策實踐中避免決策失誤、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尚無系統的思考。可以大膽預測,這兩個方面的不足即是未來研究的方向。特別是,關于如何提升環境稅的政治可行性問題,Buchanan(1963)、Acemoglu(2009)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