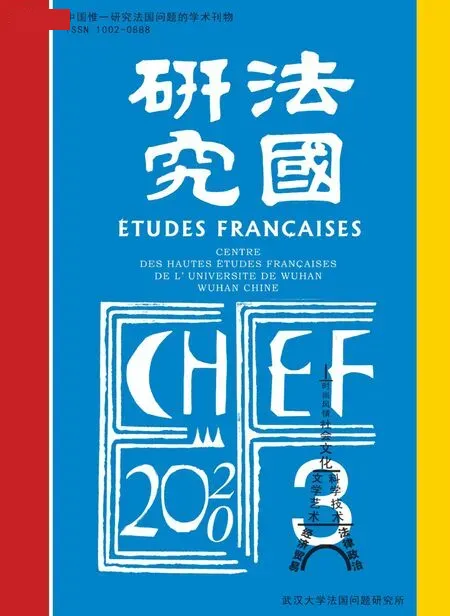試論20 世紀(jì)法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新寓言派
杜佳澍 王冰冰
何為“新寓言”派?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法國涌現(xiàn)出一批作家,他們善于在古典神話題材中尋找寫作靈感,在對神話故事改寫的基礎(chǔ)上,他們將對現(xiàn)代生活的反思、對某些人文價值觀的追求植入作品中,從而使作品飽含哲理寓意。不同于19 世紀(jì)的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象征主義等,更有別于20 世紀(jì)的超現(xiàn)實主義,以及同時期的新小說派,新寓言派并沒有一致的文學(xué)宣言,被歸為新寓言派的作家之間也無任何程度結(jié)社性的聯(lián)系和交往。他們是獨(dú)立的寫作個體,各自從事寫作事業(yè),寫作主題、風(fēng)格、題材不盡相同,但相同的寫作傾向?qū)⑺麄兙蹫橐惑w。
一、“新寓言”派溯源
“新寓言”派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1979 年法國文學(xué)評論家Jacques Brenner 編撰的 《法國文學(xué)史1940 年至今》一書中,“新寓言派的標(biāo)簽將一批獨(dú)立寫作的作家聚集在一起。對神話題材的改寫融入小說構(gòu)思中,表達(dá)了一種完全自由的精神”①Brenner Jacque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e 1940 à nos jours. Paris : Fayard, 1978, p. 529.。1982 年出版的《從1968年以來的法國文學(xué)》中,作者將這一類作家歸為新古典主義(Les nouveaux classiques)代表,這其中包括米歇爾?圖爾尼埃(Michel Tournier)、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讓?吉奧諾(Jean Giono)和勒?克萊齊奧(J.M.G. Le Clézio)等(Vercier:39-79),首次系統(tǒng)歸納了新寓言派作家。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 Xavier Darcos 編撰的《法國文學(xué)史》更將此類文學(xué)作品稱為神話小說(Le roman mythologique)②Darcos Xavier,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Paris : Hachette, 2013, p. 375-376., 并著力介紹代表人物米歇爾?圖爾尼埃的相關(guān)作品, 從而進(jìn)一步明確了新寓言派的文學(xué)地位。而后多部法國文學(xué)史專著都將新寓言派作為一個文學(xué)流派現(xiàn)象加以研究③Blanckeman Bruno, Le roman depui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 PUF, 2011, p. 172-180. Touret Michèl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Xe siècle(Tome II). Rennes : Presse Université de Rennes, 2008, p. 431-432. Viart Dominique and Vercier Bruno,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au présent. Paris : Bordas, 2005, p. 211-219.,可見其在當(dāng)今法國文學(xué)界不可忽視的地位。
我國文學(xué)界對新寓言派的認(rèn)識最早源于柳鳴九先生1998 年發(fā)表的文章《色彩繽紛的睿智——“新寓言”派作家圖爾尼埃及其短篇作品》。文中特別提到作者與圖爾尼埃的一次采訪對話④柳鳴九:《色彩繽紛的睿智——“新寓言”派作家圖爾尼埃及其短篇作品》, 載《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1998 年1 期,148 頁。,圖爾尼埃稱自己樂于與莫迪亞諾、勒克萊齊奧、格拉克等作家歸為一派,還把較早期的尤瑟納爾也劃歸這一流派。“新寓言派”這一中文譯名也取自于本文,這很好地呼應(yīng)了法國文論界對這一流派最初的稱謂:1979 年《法國文學(xué)史1940 年至今》一書中即用La nouvelle fable,中文直譯“新寓言派”來定義的。
新寓言派作家承襲了傳統(tǒng)古典小說風(fēng)格,是福樓拜現(xiàn)實主義寫作特征在20 世紀(jì)的延續(xù),注重情節(jié)的流暢和內(nèi)容的易讀。這與同時期法國文學(xué)代表新小說派大相徑庭。某種意義上,新寓言派作家力求講明白故事,更易引導(dǎo)讀者發(fā)現(xiàn)故事背后所蘊(yùn)藏的哲理。法國18世紀(jì)以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為代表的哲理小說中寓意是從具有明顯主觀意圖的故事中凸顯出來。換言之,啟蒙思想家是先思考好哲理,再通過特定的形象加以突出,這也是傳統(tǒng)寓言的寫作特征。但新寓言派作品的哲理既不如傳統(tǒng)寓言文學(xué),如啟蒙思想著作或拉封丹寓言故事那樣調(diào)動夸張甚至荒誕的情節(jié)和非人化的動物來演繹,也不像存在主義文學(xué)作品那樣構(gòu)成明確的主義,形成完整的哲學(xué)體系。新寓言派小說多描述各類人物點點滴滴的生活狀態(tài),哲理寓意往往通過生活情節(jié)的演繹,自然地流露出來,無需人為刻意的安排。星星點點的哲思更讓讀者在玩味中自省。正如柳鳴九先生所言:“寓意的流露以至故事情節(jié)的演繹,似乎往往也就無需敘述上帝從外而內(nèi)的人工安排與刻意造作……歸根說來,是從日常的現(xiàn)實生活領(lǐng)悟出了哲理意蘊(yùn),然后再將生活形象籍蘊(yùn)著哲理和盤托出,而不是先思考出哲理,然后再調(diào)用非同一般的形象加以突顯。”(柳鳴九,1998:153)
新寓言派風(fēng)格另一特征是“對圣經(jīng)、古希臘神話、民間傳說等神話的改寫,使傳統(tǒng)的神話題材與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驗,感知,思想相適應(yīng)”①Touret Michèl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Xe siècle(Tome II). Rennes : Presse Université de Rennes, 2008, p. 432., 從而產(chǎn)生現(xiàn)代的神話形式。“神話傳說往往是現(xiàn)代主義作家喜歡使用的手段。當(dāng)世界的混亂現(xiàn)象無法從因果關(guān)系上理出頭緒時,神話傳說卻可以演繹這些現(xiàn)象。”②唐珍:《圖爾尼埃短片小說的現(xiàn)代主義意義》, 載《外國文學(xué)研究》,1994 年4 期,84-88 頁。20 世紀(jì)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人類文明進(jìn)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然而物質(zhì)文明并沒有為人類帶來滿足感和安全感,相反人們卻時刻受到社會飛速發(fā)展所帶來的混亂與荒誕的折磨。在此背景下,西方現(xiàn)代文學(xué)往往提倡從人的心理感受出發(fā),表現(xiàn)生活對人的扭曲和壓抑,通過荒誕性、象征性和意識流表現(xiàn)荒誕世界里人的危機(jī)意識。而新寓言派作品卻另辟蹊徑,回歸神話文本中,逆向性走向了自我神圣化的道路。 榮格集體無意識理論談到:“神話原型是人類祖先在處于神話思維階段(即遠(yuǎn)古時代)所輸入的,并隨著人類文明發(fā)展不斷強(qiáng)化的信息。在人類進(jìn)入理性、抽象思維模式之后,神話原型就以生理形式儲存于人類心靈深處,一代又一代的遺傳,待到時機(jī)便會轉(zhuǎn)化為形象出現(xiàn),因此成為一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心理基礎(chǔ)。”③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 年,104-105 頁。在嚴(yán)峻的現(xiàn)實面前,文學(xué)家承載著憂患意識,用“神話原型”④榮格認(rèn)為,在無意識心理領(lǐng)域中,除了存在個人無意識以外,還積存著許多原始祖先的經(jīng)驗,稱之為“集體無意識”。他指出,“這種集體無意識并不依賴個人而得到發(fā)展,而是遺傳的。它由各種預(yù)先存在的形式即原型所組成。”“神話原型”是“一種形象,或為妖魔,或為人,或為某種活動,它們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重現(xiàn),凡是創(chuàng)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現(xiàn)的地方,就有它們的蹤影,因而它們基本上是一種神話的形象。”可見新寓言派作家選擇神話作為藍(lán)本加以改寫,何嘗不是對榮格神話原型理論的證實。的方式喚起了人們心中沉睡的原型沉淀意識。新寓言小說中主題、情節(jié)、人物設(shè)定、背景,甚至人名、地名等都可成為神話寓意的寄宿體。從閱讀的角度而言,這更能激發(fā)讀者在似曾相識的情節(jié)之上尋找多種象征意義,現(xiàn)代神話由此產(chǎn)生。
綜上所述,新寓言派主要寫作特征有二:一則是作家在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描寫中貫穿了零散、多樣的哲理寓意,讓閱讀的體會變得豐富多彩,意猶未盡;二則即是對傳統(tǒng)神話、民間故事和歷史典故的重寫。通過神話文本的引入以及對神話題材的解構(gòu)和現(xiàn)代意義上的重構(gòu),新寓言派構(gòu)建出現(xiàn)代的神話形式。
二、新寓言派神話重寫歷程
何為神話,弗萊(Northrop Frye)在《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中將神話定義為:“一種敘述,其中的某些形象是超人的存在,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發(fā)生在故事中’,因而是一種與真實性或‘現(xiàn)實主義’不完全相符的傳統(tǒng)化或程式化的敘述。”①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 年,13 頁。新寓言派作品的神話重寫主要涉及到圣經(jīng)故事、古希臘羅馬神話、中世紀(jì)傳說,以及新寓言派作家所知的異國文明神話。新寓言派對神話的重寫可歸納為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對神話進(jìn)行改寫,原本的神話情節(jié)以現(xiàn)代的方式重新闡釋,哲理思考因運(yùn)而生,交匯其中;二是通過互文的形式,將神話主題貫穿人物生活中,神話與人物生活因此成為了兩條相互相承的小說主線。
正如上文提到,尤瑟納爾被視為新寓言派的先鋒,早年詩集《幻想的樂園》(Le Jardin des chimères),《眾神未死》(Les dieux ne sont pas morts)已顯現(xiàn)出其寫作的獨(dú)特技巧。詩集中作家重新詮釋古希臘神話,使神話主題與現(xiàn)實世界產(chǎn)生聯(lián)系。出版于1951 年的代表作《哈德良回憶錄》(Mémoires d'Hadrien)是一部虛構(gòu)的羅馬皇帝哈德良自傳。另一部歷史題材小說《苦煉》(L'?uvre au noir)則描寫了文藝復(fù)興時期的煉金術(shù)士澤諾的生活。作家落筆之處是歷史故事,起筆之處卻盡是穿越古今的現(xiàn)代意義。通過重新理解和體驗哈德良作為一個皇帝對其寵兒的感受來介入時代和愛情,通過哈德良或哲人澤諾對人類的盡責(zé)來和智慧、仁慈、純樸、正義感相結(jié)合……尤瑟納爾正是通過對各類歷史人物的重新詮釋,使之與作家寫作思想以及現(xiàn)代社會訴求相統(tǒng)一。作家借筆下人物的經(jīng)歷來表達(dá)對世界現(xiàn)狀的某種看法。“舊瓶裝新酒”②柳鳴九:《超越荒誕:法國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史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年,323 頁。這是國內(nèi)學(xué)者對新寓言派最簡練精準(zhǔn)的描述。在尤瑟納爾的作品中此風(fēng)格已初見端倪。
新寓言派另一位代表作家圖爾尼埃則是神話改編方面的集大成者。首部作品 、《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改編自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典故事《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é)。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魯濱遜是不懼艱險、勇于開拓的早期資本主義殖民統(tǒng)治者形象代表。圖爾尼埃的魯濱遜漂流記與原著在文學(xué)思想、表達(dá)形式以及寫作目的上有天壤之別。作家借用了傳統(tǒng)故事的框架,撰寫富有現(xiàn)代意義的魯濱遜荒島神話。
小說前半部中,雖然主人公仍立志通過勞動成為荒島統(tǒng)治者,卻不時受到周遭萬物的感染,漸漸感悟成為自然中的一份子“自然本原一分子”(moi élémentaire)③[法]米歇爾·圖爾尼埃:《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 王道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86 頁。,與島上一樹一花、每一個動物無等級差別地平等相處。星期五的到來以及對其潛移默化的影響,黑火藥庫的爆炸摧毀了島上一切物質(zhì)設(shè)施,一系列的變故促使魯濱遜最終放棄了作為萬物統(tǒng)治者的優(yōu)越性,與自然融為一體。于是我們在小說中讀到魯濱遜與希望島情同母子,他鉆進(jìn)了島上的狹窄洞穴的文字勾勒出一個停留在希望島這位母親子宮里的嬰兒魯濱遜形象;隨后魯濱遜與希望島又親密如愛人,島上滿山遍野的曼德拉草被視為他們愛情的結(jié)晶;在一次攀爬大樹的經(jīng)歷中,隨著魯濱遜越爬越高,他對樹“肢體的搖曳擺動變得更加敏感”(圖爾尼埃,2001:158)。魯濱遜成為樹的一部分,在風(fēng)中愉悅的搖曳、呼吸著;小說結(jié)尾處,魯濱遜更是在心靈的升華中化身成太陽神明……小說中諸如此類的描寫層出不窮,均凸顯了主人公不同于原著的形象:追求返璞歸真,逆西方現(xiàn)代社會而行,探索人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
圖爾尼埃的后期作品對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的整體改寫趨勢就更明顯了。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重新解讀圣經(jīng)中東方三博士朝圣的《四博士》(Gaspard, Melchior et Balthazar),描寫百年英法戰(zhàn)爭中貞德事跡的《吉爾和貞德》(Gilles et Jeanne)都是這一時期代表作。訪談中作家談到《四博士》一書的寫作動機(jī)時,回憶道:“我兒時閱讀圣經(jīng)就時常想,東方三博士不遠(yuǎn)萬里而來,究竟是怎樣的動機(jī)和經(jīng)歷促使他們踏上這條道路。”①M(fèi)ichel Tournier, Marianne Payot, “Le western biblique de Tournier”, Lire. Paris, 1996, p. 154.圣經(jīng)原文對三博士的描述寥寥幾筆:耶穌出生三位博士在東方看見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上有一顆金星,于是他們帶來黃金、乳香、歿藥,跟著金星來到了耶穌基督的出生地。小說中作家卻大膽構(gòu)思,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著力描述主人公們的生存困境與突破,以及最終踏上朝圣之路的種種啟示。 眾所周知,貞德是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的女英雄,吉爾(吉爾?德?萊斯)則是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法國元帥,是參加貞德隊伍的將領(lǐng)之一。巴黎受圍攻時,他與貞德并肩作戰(zhàn)。貞德被俘以后,他退隱并沉迷煉金術(shù),將300 多名兒童折磨致死,因此被施以火刑。在這一史實基礎(chǔ)上作家虛構(gòu)出了吉爾與貞德的親密關(guān)系。吉爾對貞德的敬佩使他渴望成為貞德般的英雄人物。在并肩作戰(zhàn)中吉爾驍勇善戰(zhàn),化身成貞德形象。而在貞德被處于火刑后,吉爾嗜血如命,暴虐成性,將對故人的思念轉(zhuǎn)化為一種罪惡的情緒宣泄。作家將主人公的罪惡真實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超越法律道德的審判,探討惡的起源及內(nèi)涵,并試圖在這種顛倒的價值觀中獲得某種純粹的情感。小說結(jié)尾吉爾被處以火刑,熊熊火焰中他卻露出一絲笑容,他所欣慰的是能和貞德走向共同的結(jié)局。
近現(xiàn)代法國文學(xué)中大量作品涉及神話主題。然而多數(shù)都是借神話推演文學(xué)思想。例如加繆(Albert Camus)的《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就是借希臘神話中日復(fù)一日將石頭重新推上山頂?shù)奈魑鞲バ蜗髞肀憩F(xiàn)人類現(xiàn)實的荒謬與困境。這類借古喻今的作品往往是先思考哲理,再通過人為主觀的主題篩選,從神話故事中尋求和所表達(dá)思想匹配的形象加以突出,作家身在其中,具備上帝視角,點明寓意,統(tǒng)領(lǐng)全文。
新寓言派作家的神話改寫歷程卻不如此。作家試圖從整體上挖掘神話的現(xiàn)代意義,將神話情節(jié)演變?yōu)樾≌f人物的生存現(xiàn)狀,在深度層面上體會人物的生存困境,最終為古老的形象找到一條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出路或解讀。“在米歇爾?圖爾尼埃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特點中,往往借用以往文學(xué)中既有的故事題材,內(nèi)容成分與人物符號,加以創(chuàng)作性的藝術(shù)處理。注入自己獨(dú)特的哲理寓意,使舊題材、舊成分、舊人物煥然一新,不,說煥然一新還不夠,應(yīng)該說是另外獲得了新的生命 。”②柳鳴九:《超越荒誕:法國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史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年,323 頁。某種意義而言,柳鳴九先生對圖爾尼埃作品鞭辟向里的分析亦是對新寓言派改寫神話這一寫作特征的概括。新寓言派作家志在創(chuàng)作屬于這個時代的神話。
在新寓言派作品重寫神話的寫作現(xiàn)象中,筆者還觀察到一種神話主題與小說情節(jié)并存的表達(dá)形式。勒?克萊齊奧的代表作《沙漠》(Désert)即是一部同時包含兩者的雙主線作品。通過章節(jié)交替的形式,作家在小說中講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歷史上非洲游牧民族首領(lǐng)馬?埃爾?阿依尼納率領(lǐng)族人英勇抗擊西方殖民者的斗爭,另一則是現(xiàn)實中逃婚的游牧女孩拉拉在法國大城市的生活際遇,以及她反抗不公正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孤立無援的斗爭。作者巧妙地將兩種斗爭融合一體,兩者相輔相成,一方面是拉拉的祖先藍(lán)面人部落對殖民統(tǒng)治的抗?fàn)帲硪环矫媸抢鳛椴柯浜蟠鷮Ψ▏诎惮F(xiàn)實的揭示。小說中關(guān)于部落首領(lǐng)帶領(lǐng)族人抗?fàn)幍纳裨拏髡f,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解釋了拉拉身上熱愛正義和自由、愛憎分明性格的由來,側(cè)面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的種種弊端,更為整部小說搭建起宏大的歷史背景,小說進(jìn)程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交替而行,因此達(dá)到一個新的思想深度。
2008 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頒獎典禮上,評委會對勒?克萊齊奧的致辭為:“將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險精神融入創(chuàng)作,是一位善于創(chuàng)新、喜愛詩一般冒險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對游離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性進(jìn)行了探索。”①參見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8/(諾貝爾獎官方網(wǎng)站)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8 was awarded to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 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 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此段文字充分肯定了作家獨(dú)特的寫作特點。異國文明、失落文明和落后文明,作家站在西方文明的相對面,反思所處的西方現(xiàn)代社會。對原始文明神話傳說的探索成為其作品不可缺少的部分。除了上文提到的《沙漠》,《墨西哥之夢》(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中對印第安文明傳說的涉獵;《巨人》(Les Géants)中羅列了三十多位女神的名字,這些神話人物分別來自不同文明的神話,北歐、印度、波斯、凱爾特、古巴比倫等; 《奧尼恰》(Onitsha)中兒子樊當(dāng)尋親之旅、父親尋找失落文明之旅與傳說中非洲梅洛埃黑女王尋找新城之旅三重交錯……這些都是勒?克萊齊奧作品中神話故事與小說現(xiàn)實交織的典型例子。
圖爾尼埃成名作《榿木王》(Le Roi des Aulnes)將主人公迪弗熱與基督教圣人形象交織一體,用意深遠(yuǎn)。中學(xué)時期迪弗熱通過同學(xué)第一次了解到圣克里斯托夫的故事。小說中作家用大篇幅文字轉(zhuǎn)述了中世紀(jì)古籍《黃金圣人傳》中的這一故事:“河水漸漸地上漲,孩子像鉛塊一樣重。沉沉壓在他身上;克里斯托夫向前游去,可河水還在繼續(xù)上漲,在他肩頭的孩子也越來越沉,難以支撐,克里斯托夫恐慌萬分,害怕送命……”②[法]米歇爾·圖爾尼埃:《榿木王》,許鈞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年,46-47 頁。
《黃金圣人傳》是一部中世紀(jì)古籍,由雅克?德?沃拉吉納在1261 至1266 間由拉丁語撰寫完成,講述了150 多位基督教圣人的故事。這其中就包括了圣克里斯托夫的故事。根據(jù)《黃金圣人傳》記錄,圣克里斯托夫是迦南人。他長著巨大的軀干,面目可怖。他很樂意伺候人,但這個人須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君主。于是他先后伺候了國家的君王和魔鬼。最后他意識到耶穌基督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在一個修道士的點悟下,他在一條河邊定居下來,馱往來的路人過河。一日,耶穌化成一個小孩讓克里斯托夫馱他過河。《黃金圣人傳》中詳細(xì)描述了這一情景。最終因為這一功績克里斯托夫成為了基督教圣人。
而作家小說的結(jié)尾,迪弗熱馱著從集中營中救出來的猶太小男孩埃弗拉伊姆在沼澤濕地中前行的畫面,從文字表述到情節(jié)安排都與上文圣克里斯托夫的例子極其相識。這樣的相識性不是偶然,作者的寫作意圖明顯:迪弗熱就是小說中的圣克里斯托夫。
隨著他的雙腳在半透明的水洼地里越陷越深,他感到小孩-本來是那樣的消瘦,那樣的蒼白-像鉛塊一樣重壓在他的身上。他向前走著,淤泥沿著他的雙腿不斷上升,每前進(jìn)一步,他身上的負(fù)擔(dān)就沉重一分。此刻,淤泥擠壓著他的腹腔,壓迫著他的胸膛,他必須以超人的力量才能克服這一粘人的阻力,可他依然堅忍不拔,因為他知道這樣都是正常的。他最后一次朝埃弗拉伊姆仰起頭,只看見一個六角的金星在黑暗的夜空中悠悠地轉(zhuǎn)動。(圖爾尼埃,2013:405-406)
對比以上兩個文本,除孩子重如鉛塊、河水慢慢上漲等情節(jié)一致外,“六角星”在猶太教中也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是上帝的象征。此時猶太男孩已化身為小孩模樣的耶穌。而迪弗熱馱著小男孩在濕地前行的描寫,文字充滿暗示性,極易將其與前文中克里斯托夫的事跡相聯(lián)系。互文的效果更突顯了迪弗熱神話人物般偉大的形象。
三、新寓言派寓意探究
新寓言派作品中人物設(shè)定、主要情節(jié)和小說背景等都或多或少具備某些象征意義。人物名稱、言行、主要情節(jié)的寓意不勝枚舉,就連小說中的事物、地名、人名、色彩等都蘊(yùn)含著某種寓意。《尋金者》中被兒時亞歷克西稱為“智慧樹”①[法]勒·克萊齊奧:《尋金者》,王菲菲等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3 年,3 頁。的一個高大的五椏果樹是其童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智慧樹的內(nèi)涵不言而喻,象征著圣經(jīng)伊甸園中的智慧樹。主人公伊甸園般的幸福童年正是圍繞這棵智慧樹展開。而亞力克西與愛人烏瑪相識后,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了一對鳥兒在天空中翱翔的情景:“在這個美譽(yù)邊際的世界,在黃昏里,窺視神秘的馬納納瓦上方兩只蒙鳥飛翔。”(勒·克萊齊奧,2013:266);“我看見兩只白鳥出現(xiàn)。她們高高的,在無色的天空,翱翔在風(fēng)中,盤旋在馬納納瓦周圍……它們安靜下來,一只鳥待在另一只旁邊,翅膀幾乎不動,仿佛兩顆彗星,望著地平線上太陽的光暈。”(勒·克萊齊奧,2013:309-310)鳥兒在空中翱翔的景象是主人公追求自由的心靈寫照。一對白鳥如同他和烏瑪般相互偎依凸顯戀人的親密。此時亞歷克西與烏瑪褪去人類的外衣,化身成天地間自由翱翔,相依相伴的白鳥。亞力克西與烏瑪?shù)膼矍樵谝粚B兒的形象中得到升華。 勒?克萊齊奧善于將符號、圖形和文字游戲穿插于作品中,從而表現(xiàn)某種詩般的寓意,例如《尋金者》中的星空圖形、《少年心事》的五角圖案等。少年蒙多原是一個不識字的流浪少年。灘上的老人用詩意的邏輯教會他26 個字母。蒙多(Mondo)的名字因此被解讀為“M 是一座山”、“O 則是夜空中的滿月”、“N 是人們在揮手致意”、“D 像月亮”。“‘好美’蒙多說,‘它有山,有月亮,有個人在向新月致敬,又有個月亮’。”①[法]勒·克萊齊奧 :《少年心事》, 金龍格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年,53 頁。作家對26 個字母詩意的描述不是單純的文學(xué)靈感發(fā)揮。從蒙多的名字中讀者即可讀到人物的本質(zhì)。蒙多無疑是自然的精靈的象征,反復(fù)被提及的月亮形象更突顯了其略帶憂郁的氣質(zhì)。作家的首部作品《訴訟筆錄》(Le Procès-verbal)中 ,主人公名叫亞當(dāng)。亞當(dāng)原是《圣經(jīng)》中上帝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人類,在伊甸園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用亞當(dāng)命名小說中這個與現(xiàn)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人物,更凸顯了其伊甸園亞當(dāng)般的非世俗性。
圖爾尼埃的短篇小說文字靈動而寓意豐富,被稱為“色彩繽紛的睿智”(柳鳴九,1998:148)。作品多描寫人物的日常,哲理寓意在生活中和盤托出。《阿芒迪娜》(Amandine ou les deux jardins)中假小子般的小女孩與淘氣的小貓,一次偶然的爬墻外出的探險,小女孩初潮的到來和小貓的懷孕,對主人公平淡生活的描寫實則蘊(yùn)藏對少女性成熟過程的象征意義。《皮埃羅或夜的秘密》(Pierrot ou les secrets de la nuit)中,面包師皮埃爾是黑夜的象征,洗衣女是陽光、白天的體現(xiàn),油漆匠則是五彩斑斕、炫目迷惑的代表。洗衣女被后者色彩的絢麗所迷惑,遠(yuǎn)走他鄉(xiāng),卻最終在失意中聽從了夜的召喚。黑夜自有秘密,表面上黑漆漆的夜空實際上是蔚藍(lán)色的,黑洞洞的烤爐是金黃色的。好一幅寧靜溫馨的畫面。
“現(xiàn)代小說即是對人類生存可能性的無限探索。”②Kundera Milan, L’art du roman. Paris : Gallimard, 1986, p.57.更深層面上,新寓言派的哲學(xué)思考正是對人類生存可能性探索的種種思考。內(nèi)延是對自我的認(rèn)知,外延是對人類價值觀的重新認(rèn)識。這其中又以圖爾尼埃寫作的思辨性傾向最為顯著。作家早年立志從事哲學(xué)教育事業(yè),大學(xué)期間潛心研讀大量哲學(xué)思想,哲學(xué)背景為其寫作思路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chǔ)。無論是流落荒島的幸存者(魯濱遜),還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迪弗熱),亦或流浪的移民(埃雷阿扎爾)③埃雷阿扎爾是圖爾尼埃小說《埃雷阿扎爾或泉水與荊棘》的主人公。作品講述了愛爾蘭牧羊人埃雷阿扎爾的一生。埃雷阿扎爾信仰虔誠,熟讀出埃及記。家鄉(xiāng)爆發(fā)饑荒迫使他帶著妻兒踏上逃荒之路。流浪中埃雷阿扎爾堅定地認(rèn)為自己即摩西,將帶領(lǐng)家人到迦南。小說多次通過互文手法巧妙地表現(xiàn)主人公即摩西的化身。例如圣經(jīng)中摩西率眾人穿過紅海,進(jìn)入沙漠;埃雷阿扎爾則帶領(lǐng)家人越過大西洋,在北美洲腹地的沙漠前行。摩西手持法杖,敲擊沙漠中的石頭便涌出泉水;埃雷阿扎爾的一根牧羊長杖幫助他在沙漠中擊退毒蛇。和摩西結(jié)局相似,埃雷阿扎爾最終并沒有進(jìn)入象征迦南的加利福利亞,他坐化于可遠(yuǎn)望到應(yīng)許之地的山上。,小說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更像是哲人的設(shè)定。
法國哲學(xué)家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當(dāng)思考成為證明存在的唯一途徑時,“我”的存在就不必拘泥于外界的定義。若我思考,則我存在。思考本身即可證實人的存在。身處不受外界干擾的荒島,魯濱遜是一個哲人,常常陷入無盡的思考中。他把思考的產(chǎn)物化作文字,記錄成日記。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也是由第三人稱敘述與日記形式的第一人稱敘述相結(jié)合。日記中,通過形而上的摸索,主人公找到了一條出路:“實際上一個時期以來,我就開始訓(xùn)練自己做到從自己身上不斷地把我所有的屬性一條一條抓出來——我是說所有的——就像剝蔥頭的皮一層層地剝。這樣,我就在我之外建立了一個個體,姓克羅索,名魯濱孫,身高六尺,等等。”(圖爾尼埃,2001:77-78)
姓名、年齡、社會身份,對此時的魯濱遜而言皆是一層層包裹在外的“洋蔥皮”,無用而累贅。它們代表了文明社會對人的定義和約束:人的存在即是由各種社會定義組成的。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定義的羈絆自我又如何呢?太平洋上的這座希望島為魯濱遜提供了擺脫藩籬的機(jī)會。
拋棄主觀局限性,魯濱遜終于找到對“自我”最本質(zhì)的定義:不再是流落荒島的棄兒,也不是開疆?dāng)U土的殖民者,魯濱遜即是自然的一部分。“自我”成為主觀形式與客觀存在(自然)的融合。借此,魯濱遜擺脫了現(xiàn)實社會的預(yù)設(shè)和限定,在廣袤的自然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根本意義。
“從今以后,總有那么一個我,飛來飛去,忽而落在人的身上,忽而落在島上,并使我時而是彼,時而是此。”(圖爾尼埃,2001:78)簡潔的文字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游離于蜉蝣之外,自由的“自我”。這個“自我”不是肉體形式的客觀存在,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作為主觀意識“我”的存在,是思考的產(chǎn)物,屬于形而上的范疇。一個“飛”字更凸顯了意識存在的輕盈和無拘束。我“忽而落在島上”“忽而落在人的身上”,于是我“時而是此”“時而是彼”。通過“我”化身成島一部分的奇幻描寫,魯濱遜的存在精煉成“我”這一主觀意識,意識是自由的,不受社會規(guī)則限制的,與它物“島”之間就不存在任何客觀差別。因此,主觀存在的“我”與客觀形式存在的希望島融合為一體。
通讀全篇,魯濱遜對自我的定義雖零散卻形成了一套哲思理論。小說中作家更借主人公的日記推演了這一理論:“人們自認(rèn)是認(rèn)識的主體,作為某一個個體走進(jìn)一個房間,他看、觸摸、感覺,總之,去認(rèn)識房間里所有的客體。”(圖爾尼埃,2001:85) 然而這樣衍生出來的對事物的定義只是對事物的人為限定,并不能代表事物的內(nèi)在本質(zhì):“它們內(nèi)在本質(zhì)所有的屬性——色,香,味,形”(圖爾尼埃,2001:85)。對魯濱遜而言,要想真正了解所身處的島以及荒島上的自我,只有拋棄人為的定義,將“我”作為一個意識主體直接與客體(希望島)重合。“魯濱遜就是希望島”(圖爾尼埃,2001:86)。
除了對自我的哲學(xué)性認(rèn)識外,新寓言派作品在潛移默化的情節(jié)描寫中還力圖對固有的價值觀進(jìn)行思辨性的反思。例如在語言方面:
一旦發(fā)現(xiàn)有喜歡他的人,他便走上前去,平靜地問他:
“您好,您想不想收養(yǎng)我?”
可能有不少人非常愿意收養(yǎng)他,因為夢多那圓圓的腦袋,油亮的眼睛很是逗人喜愛。可事情并不這么簡單。人們不能就這樣,這么快地收養(yǎng)他。他們開始向他提問題,諸如多大了,叫啥名字,住在什么地方,父母都在哪兒,可夢多不怎么喜歡這些問題。他回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
說完,他便跑開了。(勒·克萊齊奧 ,1992:5)
對于到處流浪,從未受社會教化、約束的蒙多而言,“您想不想收養(yǎng)我?”這一問句是蒙多與人交流的一種形式。蒙多并不在意其語義“所指”①現(xiàn)代語言學(xué)之父索緒爾提出“所指”的觀點:特定的聲音或形象在社會的世俗約定中被分配與某個概念發(fā)生關(guān)系,在使用者之間引進(jìn)某種概念的聯(lián)想。以索式為代表的現(xiàn)代語言體系,將語言看做一個結(jié)構(gòu)來進(jìn)行理性的分析。索緒爾因此被后世學(xué)者認(rèn)為是結(jié)構(gòu)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構(gòu)成了怎樣一個社會世俗的概念。而與之相反的則是人們的回答,諸如“多大了,叫啥名字,住在什么地方,父母都在哪兒”。顯然這里的問句是現(xiàn)代社會語言體系的體現(xiàn),即語言建立在龐大的結(jié)構(gòu)體系之上,每一個語音和字符都被分配與某一概念發(fā)生關(guān)系。“你想不想收養(yǎng)我”這一問句,必然引起對“收養(yǎng)”這一概念的聯(lián)想,從而人們進(jìn)入“收養(yǎng)”這一語境中,深入詢問相關(guān)的問題。掙脫了所謂理性分析中語音與語義間的限定,蒙多的語言更呈現(xiàn)出一種詩意的邏輯。而這一理論正是建立在虛空于社會限定性的語言模式之上,進(jìn)入了無限性的語言境界中。
現(xiàn)代西方社會,語言是表述周遭一切的工具。而文學(xué)中語言卻時常暴露出天性的不足。語言即是謊言,它既無法真正表達(dá)事物最本質(zhì)、潛在的特征,也無法完全詮釋人類內(nèi)心細(xì)微的感受。19 世紀(jì)末以來,對傳統(tǒng)語言的控訴引發(fā)了法國文學(xué)界多次革新。②其中包括19 世紀(jì)初20 世紀(jì)末以馬拉美為代表法國詩人在詩歌語言方面的探索以及20 世紀(jì)30 年代的超現(xiàn)實主義的潛意識文字寫作等。然而在西方理性主導(dǎo)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對語言的突破往往走向理性的反面:不明所以的癲狂或不可謂的秘境 之中。勒克萊齊奧對語言的探索是一次超越世俗的思考:借探尋失落文明之機(jī),超越西方現(xiàn)代語言的觀念,建立一套凌駕于文明社會語言體系之上的詩意語言理論。
在性別方面,圖爾尼埃在其多部作品中都談到了“雙性人”③1970 年,剛踏入文壇的青年圖爾尼埃在《新文學(xué)》上發(fā)表《心靈黑夜的閃光》(Des éclairs dans la nuit du c?ur)一文。文中作者生動地描述了柏拉圖《會飲篇》中遠(yuǎn)古先人陰陽同體的情景。人類本是陰陽合體的圓球。因為身體構(gòu)造完美無缺,使得人類無所不能。天神宙斯忌憚人的強(qiáng)大,便命太陽神阿波羅將人劈成了兩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從此男人與女人相愛就是為了尋找自己失去的另一半,恢復(fù)原始的完美狀態(tài)。作者又大篇幅引用對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jì)》的重新詮釋。亞當(dāng)和夏娃的墮落不在于偷吃禁果,而歸咎于上帝取走亞當(dāng)身上代表女性一面的肋骨,創(chuàng)造出夏娃,亞當(dāng)雙性合體的神性被破壞。顛覆性的思考正如文章題目,星星點點,是心靈黑夜的閃光,指引作家“雙性人”寫作的道路。長篇小說方面《榿木王》對“雙性人”表達(dá)深刻、富有哲理。而作家多部短片小說《亞當(dāng)家族?(La Famille Adam)、《小布塞出走》(Le petit Poucet)、《香水傳奇》(Légende du parfum)、《音樂跳舞傳奇》(Légende de la musique)都以“雙性人”為寫作主題。這一主題。作家試圖在小說人物身上同時植入兩種性別特征,從而改變性別對立的傳統(tǒng)立場。《榿木王》中主人公迪弗熱癡迷于雌雄同體的亞當(dāng)形象。他自認(rèn)是原始亞當(dāng)?shù)暮蟠A硗庾骷叶嗖慷唐≌f中“雙性人”形象特點分明,表達(dá)簡潔,人物設(shè)定一目了然,例如《亞當(dāng)家族》(La Famille Adam)、《小布塞出走》(Le petit Poucet)、《香水傳奇》(Légende du parfum)、《音樂跳舞傳奇》(Légende de la musique)。
《小布塞出走》中,主人公盧格爾(Logre)的名字讀音與法語中“吃人巨人”(L’ogre)同音。作者巧用這一點,暗示了盧格爾極具雄性氣質(zhì)的巨人形象。但顯著的男性特征卻掩蓋不了女性的另一面。“柔軟”、“溫柔”、“溫存”①[法]米歇爾·圖爾尼埃:《皮埃爾或夜的秘密》,柳鳴九等譯。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年,87頁。等形容詞強(qiáng)調(diào)盧格爾柔軟的女性氣質(zhì)。盧格爾的一切都是柔軟的,從金黃色的長發(fā)到絲綢襯衫,就連最具男性特征的胡子也充滿了柔性的美感:“他的胡子金黃、卷曲,像絲一樣柔軟光滑”(圖爾尼埃,1999:87)。盧格爾更是美麗的,高挑的身材、金黃色的頭發(fā)、藍(lán)色的眼睛、雪白的牙齒和嬉皮士風(fēng)格的裝飾。作者通過細(xì)節(jié)的描述,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位極富魅力的女性形象。“您漂亮得像個女人!”,(圖爾尼埃,1999:88)皮埃爾的回答是全文的點睛之筆。皮埃爾的窘困是真實的,在世俗范圍內(nèi),我們無法用準(zhǔn)確的詞來定義盧格爾。然而超出世俗局限,不簡單用“女人”或“男人”來定義盧格爾,男性特征之上綻放出的女性之美即是他本來的屬性。
性別顛覆的設(shè)想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大命題。傳統(tǒng)人類社會中男女性別的對立是絕對的。但在后現(xiàn)代主義時期,正如羅蘭?巴特試圖在兩性對立中找到平衡點的“中性”②法國符號學(xué)家羅蘭·巴特在《中性》(Le Neutre)一書中膽解讀圣經(jīng)中的情節(jié)。在作家看來,沒有被取走女性部分(肋骨)的亞當(dāng)是雌雄同體。巴特談到:“男性的活力與女子氣質(zhì)的融合,它意味著對立面的結(jié)合,這是一種理想的完美性,在性別構(gòu)成上簡直精妙絕倫 ”。“雌雄同體”的理論模型為巴特的“中性”思想奠定基礎(chǔ)。中性非陽性,也非陰性,它否定性別對立,試圖在性別對立中找到某種平衡。《S/Z》、《戀人絮語》、《中性》等著作中,都能看到作家在性別領(lǐng)域的這一解讀。理論般,學(xué)者們紛紛對傳統(tǒng)觀念提出質(zhì)疑,并試圖通過解構(gòu)、顛覆的手法來建立新的理念。傳統(tǒng)性別定義被解構(gòu),在男女性別的重構(gòu)過程中,新的定義應(yīng)運(yùn)而生。圖爾尼埃“雙性人”力圖尋找性別對立之上的統(tǒng)一,很好地呼應(yīng)了后現(xiàn)代主義性別顛覆的主題,實質(zhì)表達(dá)了作者回歸原始、超越性別沖突和探索存在多樣性的愿望。
四、結(jié)語
當(dāng)代法國文學(xué)界已充分認(rèn)識到新寓言派帶來的獨(dú)特寫作現(xiàn)象,然而對新寓言派的界定仍是眾說紛紜,各有側(cè)重。可見對新寓言派的認(rèn)識和界定還未蓋棺定論。如上文所言,新寓言派作為一個文學(xué)派別不是由作家們自發(fā)組織形成,它首先是被法國文學(xué)評家提出的,如此成因使學(xué)術(shù)界對其仍懷有不少質(zhì)疑。眾所周知,法國六、七十年代新小說派后再無代表性文學(xué)流派出現(xiàn),這與當(dāng)代西方文學(xué)界崇尚個體創(chuàng)作趨勢相關(guān)。被歸為新寓言派的作家們在寫作上不約而同的相識不是偶然,而是這個時代背景影響下的某種必然。文學(xué)評論界前輩的研究為后繼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種種因素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探討新寓言派文學(xué)作品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從深遠(yuǎn)意義上而言,對新寓言派的研究更有助于把握20 世紀(jì)后半葉以來法國文壇的最新發(fā)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