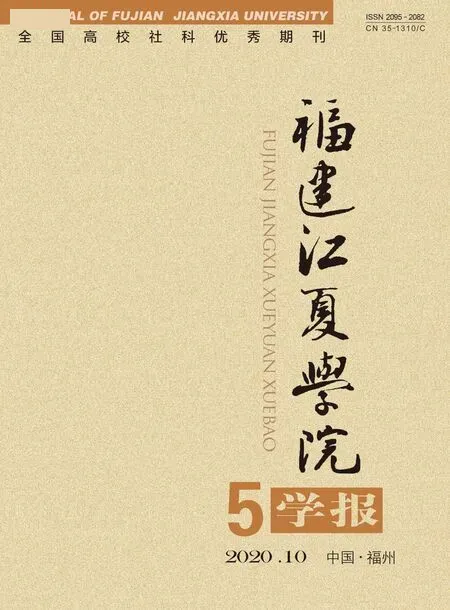傳統中國畫的品評理路及其內在邏輯
王 希
(聊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山東聊城,252000)
對中國畫品評觀念的研究是掌握中華歷史文化審美價值觀的重要線索。品評,指評定高下優劣。所謂中國畫的品評,即是對繪畫作品的藝術品質以及對畫家藝術境界的評判。在傳統中國畫學中,品評與鑒賞觀一直處于不斷地發展變化中。如畫學中最具影響力的品評標準的排序,即在宋代品評理論發展的成熟期,有關“逸、神、妙、能”與“神、逸、妙、能”畫品的定位差異,在不同著述中呈現出的標準之爭,究竟體現出何種價值導向?其背后又有怎樣的觀念動機?遵循著何種內在邏輯?在整個傳統中國畫品評理論的發展史中,繪畫品評標準隨著時代的發展又演繹出更加復雜多樣的價值導向,并反映抑或引領著中國畫的發展方向。因此,梳理其中的品評理路及其內在邏輯,是厘清歷史中多元復雜價值觀念的關鍵,對辨明真偽價值標準以及提煉中國畫的價值精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傳統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的三個歷程
將傳統畫學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畫品評理論進行提取梳理,可劃分為幾個重要的發展歷程:
第一個階段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的奠基時期。最突出的成就體現于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的“六法”,其為中國畫最早具有體系性的創作與品評理論的經驗總結,是中國畫品評標準中最具奠基性的重要理論。其后,南朝姚最著述《續畫品》,在其著述動因中表述到與謝赫的品評觀點有不同見解,只論藝而不分品第,開啟了后代無涉分品之體例。
第二個階段是唐宋時期,是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的成熟期。首先,有關品評標準的價值等級定位得到確定。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仿唐代張懷瓘在《畫斷》中的分品定位,將唐朝120余位畫家進行分類,設立神、妙、能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此外,另設“逸品”。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是第一部體系完備的畫史著述,其提出“自然、神、妙、精、謹細”五個等級,以及上中下三品,每品再細分三品,共計九品的品級劃分。宋人黃休復撰述的《益州名畫記》,具有重要的立言價值,其在畫論中不僅首次將“逸品(格)”定為最高品類,提出“逸、神、妙、能”的等級劃分,并進行了各個品類的話語詮釋,起到重要的歸導作用,引領了后代文人的價值取向。但這種品評標準并不是唯一的價值導向,如宋初劉道醇在《圣朝名畫評》中提出“六要”“六長”的評價標準,后按題材分為六門,每門分神、妙、能三品,每品之下又各設上中下三等,以對五代與宋初的畫院畫家進行評判。觀其品評對象與評價標準,側重于院體職業畫家審美趣味的價值定位。在宋徽宗時期,官方著述的《宣和畫譜》,則將“神”品置于“逸”之上,形成“神、逸、妙、能”的品級設定。在此時期,文人士大夫躋身畫壇,開始通過話語權的掌控將其文化審美價值觀念構筑于品評標準的價值導向中。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提出“人品即畫品論”“氣韻非師”的理論,開始在畫論中將品評標準的評判原則立足于繪畫創作者的人格才性上。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蘇軾提出“士人畫”與“畫工畫”的區別論述,將謝赫所建構的重繪畫性的品評標準體系進一步演繹,形成在“意理觀”基礎上,重神寫形的價值導向,由此開始了文人士大夫掌控繪畫品評標準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為元明清時期,是品評理路的轉型期。首先,元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元初趙孟頫提出“古意觀”“書畫同源”的主張,將前代尚“圖真”的“氣韻觀”進行品評理路的轉型,開啟后人在此理路轉型下的不斷探索。雖然在此種轉型的過渡中,尚有一些主張“圖真”理念的品評家,在當時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明初,李開先的言論,其著有《中麓畫品》,其體例與《古畫品錄》類似,均為先建立品評標準,后設畫品進行等級評述,對當時的“浙派”風格進行宣揚。但從明清以來繪畫流派的發展而觀,李開先提出的品評標準與審美取向,并沒有被后人所廣泛尊崇。明中葉,何良俊在《四友齋畫論》中提出“利家”與“行家”的區別,推崇趙孟頫、文徴明代表的文人畫,即體現出不同的審美價值取向。明代大行其道的言論是吳門后學董其昌的話語拓展,其在《畫禪室隨筆》中提出的“南北宗論”的價值導向,通過“崇南抑北”對文人畫、士大夫畫進行脈絡梳理,將文人畫提到主流地位。清代的品評理論呈現多元化的價值取向,“神逸能妙”的等級定位開始模糊。最典型的是黃鉞所著《二十四畫品》,設二十四種繪畫品格,分別為:“氣韻”“神妙”“高古”等。此著專論畫品,無涉畫家,僅從審美角度進行繪畫風格的標識與闡發,但其品格命名更多是隨感而發。如專設“氣韻”一品,并且其中許多品格類型均可以同時存在于一幅作品當中。清末秦祖永更提出了“有神而兼逸,有能而兼逸,有神與能兼善而仍無失為逸”的品評觀,“逸神妙能”的品第秩序又被打破,交融一體,這其中又呈現出品評標準的價值轉型。
由此,從對歷代具有代表性的相關中國畫品評理論的提取梳理中,可以發現中國畫品評標準建構的過程是何其的復雜。因此,從如此多元的價值觀念中真正把握其中的內在品評理路,則需從此中進行核心論斷的精準提煉與深度剖析。筆者在本文中將通過提出三個具有里程碑式的中國畫品評論斷,以此話語導向為研究中心,進行中國畫品評理路的梳理及其形成邏輯的剖析,分別為:第一,六法論;第二,人品即畫品論;第三,筆墨格調論。
二、法度的建構與形神觀的演繹
在歷代傳統中國畫品評類著述中,較早進行體系性經驗總結的文本,無疑是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謝赫在卷前提出的“六法”,不僅是重要的品評標準,更規范了中國畫的創作法則,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質的繪畫理論體系。縱觀后人的品評理論,雖有不同維度的側重演繹,但其本質精髓均未能出其右。
關于“六法”,謝赫歸結為:“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1]其中,氣韻在“六法”當中具有統領的作用。關于氣韻的解讀,歷代學者對此進行過多個維度的闡發。當代學者陳傳席認為,用氣去題目一個人,大都是形容此人由陽剛強健的骨骼構建出體格,顯現出的清剛之美,以及從此種形體生發出相對應的性格、精神、情調。用“韻”去題目人,指人的體態(包括面容)所顯現出的情貌狀態、風姿儀韻,以及由此引發的情調美感。“凡氣,必能顯現出韻;凡韻,必有一定的氣為基礎。二者雖可以有偏至,但不可絕對分離。”[2]
這種對氣韻的解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時期氣韻標準的形成,要結合魏晉時期整體時代語境中進行分析。氣韻的標準,不僅是在九品中正制的政治規則、重人物品藻的玄學之風、“以氣品文”的文藝思潮等大語境下,形成的話語闡釋,更是在畫學中承繼于前人繪畫理論發展之上,尤其是顧愷之“傳神論”“遷想妙得”觀念的進一步闡發。更為重要的是,氣韻的標準在此時形成為最高標準,也并不僅僅是對人物意象的精神氣度、風神境界的評判,更是對繪畫作品整體氣象意境與所傳達出的精神境界的總體評判。在氣韻作為最高標準,起到統領作用之后,謝赫在其下設置了用筆、造型、色彩、構圖、技法傳承五個法則的規約,對應于繪畫形式語言的維度建構:骨法用筆,是對畫家使筆技法與功夫的規約與價值評判;應物象形,指畫家主體對物象進行感通之后,對物象形式的塑造,即形神兼備的標準法則;隨類賦彩,是對物象賦色上的要求。隨類,顯示的是中國畫色彩觀上的規律用色、觀念用色的價值取向,即是對用色原則的規約與表述效果的評判;經營位置,是對畫面構圖上巧妙運思的要求與視覺空間營造效果的評判;傳移模寫,指對古人表達方式、技法運用的承繼品評。這五個具體維度的規約,構成了中國畫以氣韻為統攝的法度標準。
在謝赫對氣韻標準的建構中,有一個重要的維度規約,即應物象形,其規約了形神之間的關系。謝赫所主張的形神觀是形神兼備,即通過寫形以達到傳神。如其在評判第一品畫家張墨、荀勖時所用的言論:“風范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1]301對第二品顧駿之的評價是:“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1]301其對形與神的關系,并不是要舍形而取神。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對此觀念進行了深刻闡釋:“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3]其將形神兼備觀念下,對造型、用筆、氣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精辟的闡述,并又言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3]158無疑是對謝赫品評第六品丁光作品中所用的話語評判“非不精謹,乏于生氣”的進一步闡釋。
謝赫提出的氣韻觀,是重視主觀精神的意象性圖形觀。此圖形觀講求以形寫神,以表現物象的風神、氣度。重形神兼備的氣韻觀在生成之后不斷演繹,到宋代中后期高度成熟,并形成了意理觀。這種成熟的表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宋徽宗時代,統治者通過設立完善的畫學體系,將寫真觀念完美地貫徹于整個畫院的培養模式中,生成了造型精妙入神、色彩典雅高妙的宮廷院體畫;另一方面,蘇軾等文人在院體畫達到高度成熟的同時,對文人畫的發展也作出了進一步的創設與規約,尤其體現于其所主張的意理觀上。蘇軾的意理觀,重意理以寫神。其在《東坡評畫·凈因院畫記》中指出:“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常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4]
這段話鮮明地體現出宋代文人畫家所規約的意理觀:其一,超越常形的表面審視,要深入到具體物象的物理、物情、物態的生成本源,即對畫面所繪物象常理之上形神把控的價值評判。如蘇軾所推崇的文人畫家文同繪制的《墨竹圖》,是竹畫題材中最為經典之作。相較其后元明清人所畫之竹,其品格境界更高,重要的特質之一,即是合乎物性法度但又能超越法度。文同對竹子的物理、物情、物態進行過全面的觀察與把握,并將眼中之竹,化為心中之竹,是通過對竹子的物性情態把握,對竹桿、竹枝、竹葉的規律總結,再將心中之竹轉化為手中之竹,則是通過書法用筆的法度與內心情緒,進行理性與感性相結合的意象抒發。因此,文同之竹是在寫生的基礎上進行高度的提煉,更具態勢性情、更富有典雅崇高的品格。其二,指在掌握物象物理、物性的基礎上,進行主觀的畫理闡發,在繪畫創作中,體現為對繪畫法度的把握。如蘇軾所繪《枯木竹石圖》,其中的石頭、枯木的造型塑造均打破常規范式的自然平凡之態,但又合乎自然物象之規律,而賦予更多的情感抒發、主觀的畫理構思。其將石頭表現為近似螺旋狀的盤曲態勢,有一種蓄力待發之勢;枯木處理為拔地而起、先向右上方雄勁生發,其后又向左后方突然扭轉的突兀態勢,干枯的枝干似鹿角,其生長方向將觀者的視點引入畫面深處。在此中,蘇軾無疑將奇石、枯木進行了主觀性的特殊處理,先通過提煉出物象的物理規律,再根據畫者的畫理構思,以筆墨抒發意趣、托物言志。其三,指明能領悟到此層境界的畫家,一定是高人逸才,將畫者所具品格才性的評判提高到了重要地位。蘇軾在此不僅對形神兼備的氣韻理論進一步推演,發展為以提煉物象神髓,以重神寫形的意理觀,更將能把握意理觀精神的畫家,劃歸為高人逸士。此中,人品與畫品的關系也已經被鮮明地提出。
由此,從“六法”的體系生成,到意理觀的成熟,體現出魏晉到唐宋時期文人主導的中國畫品評標準的核心價值取向,從形神兼備到重神寫形的理路演化。其中,氣韻的評判標準,其主要脈絡是側重對畫內有形之氣韻,即繪畫性本體的評判。此中要明確的關鍵要點是,關于中國畫的繪畫性本體的評判,其此中有一個重要的思想觀念,即圖真。中國的圖真觀不同于西方古典繪畫重寫實的圖形觀。中國畫特有的圖真觀,是要畫者在深入掌握物理、物情、物態的基礎上,進行意象感知與境界創生的,即格物致知的審視之后,進行主觀思維的融造與升華重組,是極具有創作性的藝術思維方式,所以也稱其為形神觀。在宋代,這種思維方式已經發展到高度成熟的階段。到宋末,對這種形神觀的演化,也開始進入注重對作品之外畫家品格才性的評判階段。
三、畫外之品德才性與畫內之品格境界
在形神觀受理學觀念影響的演進過程中,重人物品藻的氣韻評判傳統也并未曾割斷,而呈現逐漸凸顯之勢,其品評維度即是指對繪畫創作者身份、品德、才性的要求與價值的評判。在宋代畫論中,郭若虛的“人品即畫品論”,最為鮮明地呈現出中國畫品評理路開始由畫內轉向畫外的品格評判。在其所著的《圖畫見聞志》中“論氣韻非師”一節,言:“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跡,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頤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5]顯示其將畫品的評判與畫者的文化身份、政治身份、人品才性相連。
其實,在郭若虛明確提出“人品即畫品論”之前,朱景玄、黃休復均分別對逸品進行品評,已經展露出對畫外品格的重視。朱景玄對逸品的提出,已將畫家高逸人格與逸品的繪畫品類相連接,但并未對逸品進行等級定位。黃休復則首次將逸品提升到最高的品類,將具有孤傲淡泊胸懷、超塵脫俗境界的文士品格與逸格畫品相對應,再次強調人格與畫格間的重要聯系,并在人物品藻論基礎上,提出“情高格逸”的畫外才情觀。后人沿著這一維度進行不斷的拓展。[6]
南宋鄧椿在《畫繼》中言:“畫者,文之極也。”對比五代荊浩在《筆法記》中所言的“畫者,畫也”,可鮮明地看到此中的重要轉化。鄧氏又言:“人品既高,雖游戲間,而心畫形矣。”[7]凸顯出畫家文化品格、心性修養對評判繪畫品格而言的重要價值,更直白地展現出畫品的評判由重繪畫性的本質屬性向重畫外文化性的轉換。
到元代,文人們則在“人品論”的維度上進一步予以闡發。湯垕在《古今畫鑒》中寫到:“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蕭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8]湯垕提出“胸次論”,指出以形似論畫為俗子之見:王維的畫之所以與庸史不同,是因其胸次的瀟灑使然。胸次的指代,無疑指涉畫者的精神層面,對應于畫家所具有的視域格局、人生境界而言。
元末楊維楨在《圖繪寶鑒序》中,也言“人品論”,但又較之前的畫品理論所不同,打破了封建綱常的身份局限,將書畫品格的高下與人的天質相連。“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則書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于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極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于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婦女,茍有天質,超凡人圣,可冠當代而名傳后世矣。”[9]在此,神妙之品出于天質的提出,指出高尚的天質品性,不僅只限于侯王貴戚、軒冕山林,婦女也可具有此品德,明顯打破了宋代以郭若虛、鄧椿為代表所提出“人品論”的局限性。
明代對氣韻的批判,重視畫者畫外文學才性上的功夫與修養的最著名論斷,無疑是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言:“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生,皆為山水傳神矣。”[10]其將氣韻分為天質層面的不可學與后天層面的可學。后天氣韻的培養途徑有讀書與行路。此言論最為后人所沿引。
清人中“人品畫品論”具有代表性的言論,首先是清前期畫家惲壽平在《南田畫跋》中提出隱的境界:“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11]“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11]152惲氏將逸品的產生歸結為畫者不受時風主宰的隱逸人格境界所創生,具有獨立個性風貌的作品,其實質是對逸格中畫外人格的一脈相承,重對逸品中畫家個性才情、精神境界的規約,其思想依然可上追莊子的虛靜觀。其次,清人“人品論”中的“氣節觀”漸趨受到矚目,成為書畫品評論中的重要標準。清中期,張庚在前人詮定逸格、注重孤高淡泊等胸懷品格的基礎上,著重以畫者的入仕行為、道德節操為評判標準,其在《浦山論畫》中指出:“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于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尚,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12]清后期,松年在《頤園論畫》則鮮明地指出“品學兼長”“后世貴重”,并提出“書畫清高,首重人品”[13]。
在畫品論中,以道德操守為重要的評判標準,與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語境有著密切的關聯。明清的政治更迭,對“貳臣”書畫品類的貶斥,成為一批士人思想中的評判傾向。雖然這種觀點并未具備完全客觀的學術性,也有一些文士在各自的論述中曾對“貳臣”的書畫成就進行藝術性正名,但書畫品類的評判中,對忠義節操標準的衡量,其實是側重于對藝術家藝術品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功用而言。當民族國家受到外族入侵時,這種意識則會越發強烈,尤其在晚清民族危亡之時,人品論逐漸演繹成民族氣節觀,如傅抱石、李苦禪等畫家均有相關的人品畫品論述。
可見,人品即畫品論,在畫史中首先強調的是特殊性,即先天特質、個性風骨,而早期這種天賦通常被冠以在王孫貴胄、高人逸士階層。隨著政治制度的調整、社會思想的轉化,封建綱常統治下思想的局限性逐漸變得開放。“天質說”“胸次論”等相繼提出,強調世人通過后天的學養孕化、人生閱歷的積累、視野胸懷的拓展,品格亦可提升,氣韻也可得到涵養。質言之,人品即畫品論,是氣韻觀中側重于對畫外人格、才性的評判。這種評判的標準自宋代始以文人劃定的“逸、神、妙、能”的品評等級定位發揮的影響最大。
但與此同時,此時期也有與這種品格定位不同的評判標準,即宋代官方的畫品標準,為“神、逸、妙、能”的等級劃定。這兩種評判標準的劃定,有爭議的地方即是逸、神兩品的等級位置。在宋代話語體系中,逸、神兩品均有共同點,即均是在形神觀思想上建構的兩種高標品類。此中,逸品的關鍵詞是筆減形具,即側重于以形寫神,強調在寫真的基礎上,進行更自由的意象創造,融入畫家更多的主觀情趣以及書法用筆的融入超逸;神品的關鍵詞是應物象形,即強調形神兼備,強調物象的客觀性,注重繪畫性本體和形色的技法表達。
逸、神兩品,其實質并無高下之分,均可代表中國畫的經典品格。這兩種品類的劃分標準,在后世的演繹中不斷被更迭前后地位,則取決于掌握話語權的評定者身份是院體官方還是文人士大夫,其實質顯示出話語權的歸屬問題。但逸品在后代的演繹中最具活力,隨著文人士大夫對畫品著述話語權脈搏的密切掌控,宋之后對逸品的評定,則多由畫內轉向畫外。由此,“人品論”品評風氣的生成,其實質是以畫面之外畫家的品德、才性為評判依據,注重對畫家人格氣質、文化修養、品格氣節、人生境界上的價值評判。這種風氣的盛行,一方面,推進了畫家對文學修養、品格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促使傳統中國畫的發展趨向主觀性筆墨意趣的情感抒發和文化情結的觀念表達。元代的筆墨格調觀,即是在這種內在邏輯下演繹生發出的結果。
四、筆墨意趣與氣韻格調
中國畫的藝術觀念在元代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折:由重繪畫性的圖真觀,轉化為重書法意趣的筆墨觀與重氣韻格調的古意觀。引領這次話語轉型的是文人士大夫趙孟頫,其在《秀石疏林圖》卷后自題:“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14]提出“書畫同源”的理論,并通過繪制《鵲華秋色圖》等作品,向世人展示其繪畫理論的實踐表征,標示著文人畫開始從對物象的三維空間的造型表現,轉向二維平面的筆墨表達,更傾向主觀意趣的抒發與氣韻格調的彰顯。趙孟頫又言:“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說也。”[14]255認為識畫要從畫面氣韻而觀,“古意”格調是高標的品格境界,只有通曉其道理的高人可明辨,標識著此時的氣韻評判是重整體畫面的格調境界而論。由此,開啟了從形神觀轉向筆墨格調觀的品評理路,并逐漸發展為元明清時期的主流品評標準。
元末倪瓚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15]倪氏的言論,表現其寫意觀,是要超越形似以寫逸氣。倪瓚的畫作以簡靜枯疏為特征,在構圖上常常以兩段景致為意象圖景,如以表現近景、中景,遠景留出空白,抑或是表現前景和遠景,中間幾乎留白,營造大面積的虛靜空間。景物設置上也僅僅以幾株枯樹、茅亭為表現對象進行干筆皴寫,整體意境簡淡空疏。倪瓚創造的這種境界也被后人視為“逸品”的典型代表。可見,倪瓚對“逸”的品格作用,不僅體現于其人格品性上的超逸表征,更在其繪畫作品的畫面實體中,通過筆墨意趣的塑造賦予了蕭疏荒寒的境界格調。
明人董其昌在《畫旨》中言:“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16]在《畫禪室隨筆》中言:“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習字之于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10]201在此,董其昌傳承趙孟頫“書畫同源”的理論,認為士人畫的線條筆法與草隸奇字書寫筆法相連,要以書法入畫,重筆墨趣味的抒發。董其昌對筆墨氣韻的重視,體現于其大量以仿制古人為題目的繪畫作品中。縱觀這些作品呈現出的筆墨意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古人筆法、墨法的形式法則,但更多流露出的是其自由個性的程式風格,其以筆墨自造而出的宇宙天地。
其后的清人畫家、理論家均對筆墨格調的研究格外重視,也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不斷演繹。如王學浩在《山南畫論》中記錄王耕煙所認為的士大夫畫標準為:“只一寫字盡之。”在其后,王學浩在認同此論的基礎上,言:“字要寫,不要描,畫亦如之。一入描畫,便為俗工矣。”[17]更是將書法用筆以入畫,成為評判士大夫繪畫的重要特質標準。
清代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對書法用筆用墨的使用精髓進行了高度概括:“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濕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是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18]又言:“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于筆,乃臻神妙。”[18]132方薰的言論涉及到筆墨觀的兩方面概述:一方面是在技術的層面,對筆墨功夫的畫法要求,即運筆之中要具備豐富的筆法墨韻的變化;另一方面是在畫道的層面,對畫法、畫理、物理、畫趣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精煉的闡釋,無疑是對宋代蘇軾物理、畫理、意理相互間作用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筆墨法度、理趣的提煉與創化。
清人王昱在《東莊論畫》中,提出“理氣與品格論”,首先言:“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19]其在人品與畫品論的基礎上,對人品品格的確定與筆墨格調的氣韻形成進行了闡發,強調正氣觀。又言:“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后可稱名作。”[19]348其中,闡釋到畫家要通過修煉心性、理正氣清,以立高尚人品,涵養浩然正氣,才能生成超逸品格的筆墨意趣,創作出傳世名作。亦可見,筆墨氣韻與人品格調之間的密切關系,即在品評標準上將筆墨本體與人品境界相結合,形成筆墨格調論。
可見,自元初趙孟頫提出“古意觀”及“以書入畫”的主張,通過繪畫創作進行觀念申發,將文人畫正式推上畫史的舞臺,重筆墨的氣韻評判開始成為繪畫品評的立足點。文人崇尚的筆墨觀也開始與古意趣味、簡靜格調、超然性情的氣韻格調相關。到明代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將傳統繪畫劃分為兩大脈絡,推出“南北宗論”,并使南宗成為正統,大行其道。清人畫家、理論家著力將筆墨氣韻觀進行深入微觀的闡發,筆墨格調觀逐漸成熟,并成為主導評價標準。氣韻的評判,則明顯地由畫內的有形氣韻評判,轉向筆墨評判與畫外無形之境的評判,即對繪畫性之外的書法意趣、形式風格體現出的文學修養與人格境界的評判成為主流。“逸神妙能”的品第秩序又被打破,清人黃鉞在《二十四畫品》中提出的二十四種繪畫品格,就自然地生成了。
五、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
通過以上對中國畫品評理路的梳理與內在邏輯的剖析,可以發現,“六法”一直是作為具有奠基性價值的品評標準,后代品評標準的發展均是從其不同維度進行演繹生發。但回溯畫史,其中有幾個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通過辨清其中的紛雜面相,更可對中國畫品評理路的形成勾畫出更加清晰的圖景,亦可從中更明晰地把握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
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的“六法”設立標準之后,其對畫家藝術成就進行立品定位的評判,卻受到世人的非議, 最具爭議性的,即是對顧愷之藝術價值的定位。姚最在《續畫品》中,對謝赫的鑒賞能力進行了批判,歸結為謝赫不能領悟顧愷之藝術中的風神氣度,與謝赫自身藝術的局限性有關。姚最對謝赫的藝術成就進行了這樣的評價:“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于氣連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20]可見,謝赫的身份其實是宮廷畫師,其對藝術的審美傾向側重于繪畫性。對于謝赫、姚最的不同觀點而言,說明藝術的評價受評論家主觀性思想傾向的影響。其后,李嗣真等人也認為謝赫的言論不公,應提升顧愷之的畫品地位。但此時期謝赫提出的“六法”仍為主導價值標準,如宋代郭若虛將“六法”的地位推為“萬古不移”。并且,通過流傳至今宋代之前的繪畫作品而觀,重繪畫性的圖真觀念是影響唐宋繪畫藝術導向的重要價值標準。
作為士大夫文人的蘇軾雖未有專門的繪畫品評類著述,但其通過對“士人畫”的話語闡釋,提出了“意理觀”的價值導向。此種觀念的形成,是受宋代理學精神主張的“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影響下的思想演進。簡言之,在“意理觀”中,意是對畫意、意氣的表達;理是在掌握萬物物性基礎上對畫理的把控,要求畫家有對形似進行提煉以表達物象神髓的能力。后世的學者們有的認為,蘇軾是寫意觀的代言人,但此時蘇軾提出意理觀的理念,其實仍是在圖真觀基礎上的延展。從蘇軾對王維、吳道子藝術評價的先后矛盾中可一窺:蘇軾早年高度推崇王維的“詩畫一體”,后又認為吳道子為“古今一人”,這種價值取向的轉化,最可見蘇軾的品評觀是受圖真觀深刻影響下形成的。意理觀的重神寫形是對形神兼備的進一步發展,即重物象神髓把控的同時,形似依然是重要的基礎維度。由此也呈現出藝術的多元評價標準中,被歷史抉擇的主導價值導向,一定是順應藝術本體規律的發展變化。由重繪畫性的形神兼備,到重意理觀的以神寫形,均是在圖真觀為主流的價值導向之下進行的取向演進,當其發展達到高度成熟的時候,藝術的進程必然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其價值取向的真正轉折點是在元代。
在元明清,隨著文人階層的全面介入,具有私人化性質的文人繪畫理論開始影響繪畫的發展。意理觀中尚意的取向,越易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人品論中對畫家人格才性、精神境界的評判,也上升為重要的品評維度,將繪畫性進行了地位上的顛覆。中國畫品評標準的氣韻評判,從對物象形神、意境氣脈轉向對文人意氣、筆墨品調的評判。文人諸種觀念的引入,將繪畫的獨立性打破,使繪畫進入到與其他領域整合的階段,詩書畫印四位一體成為常規范式,以致中國畫形式本體當中筆墨語言的陰陽虛實的組合、韻律情趣的抒發,成為繪畫表述的核心,筆墨的氣韻觀成為繪畫創作的追求。
至此,通過剖析中國畫品評理論發展中主導價值觀的演繹轉化,展現出當繪畫性本體發展到極度成熟之后,其畫外維度必然被重視與提升的底層邏輯。由此,畫內與畫外兩個維度共同作用、交替主導,形成了中國畫品評理論的內在發展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