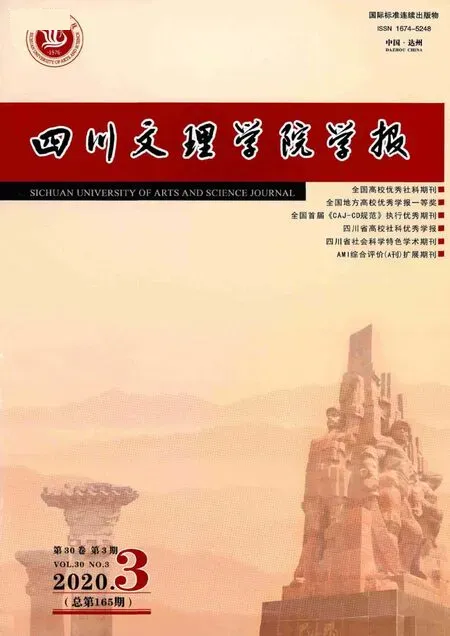中華文明第二期與禪宗美學(xué)的生命智慧
——關(guān)于中國美學(xué)精神的札記一則
潘知常
(南京大學(xué) 城市形象傳播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210000)
一、中國“無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
信仰的建構(gòu),在古老的中國,既引人矚目又道路坎坷。尤其是禪宗的思考,更是與眾不同。也因此,在研究禪宗與美學(xué)的種種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的時候,由于事關(guān)對于禪宗的思考的特定語境的準(zhǔn)確把握,無疑,也就尤其重要。
當(dāng)然,十分引人矚目的是,最初的中國,信仰建構(gòu)就已經(jīng)與西方世界殊異,不是“因宗教而有信仰”,而是“無宗教而有信仰”,成為古老中國的基本特征。
在中國,曾以“天”為宗。
眾所周知,在世界文明的歷史進(jìn)程中,唯有中華文明始終沒有滅絕,也因此,我們一般都把中華文明稱之為:“連續(xù)性的文明”,并且因此而區(qū)別于其它的“斷裂性的文明”,可是,為什么會如此?無可置疑,其中一定存在著某種巨大的向心力。或者,置身其中的中華民族一定默認(rèn)著某種價值、某一安身立命之處,這就類似于西方的絕對價值、終極關(guān)懷。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但西方民族必須回答,中華民族也必須回答。也因此,不難想象,在歷經(jīng)滄桑的古老中國的背后,也一定還存在著一個價值的“中國”,一個“中國的中國”。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中國之所以始終屹立于世界東方,一定也是有其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所談?wù)摰闹袊鋵嵅⒉皇峭暾闹袊皇钦鎸嵉闹袊亩种弧送膺€有四個地區(qū),卻很少涉及,它們是:西藏(含青海的部分)、新疆(含甘肅的部分)、內(nèi)蒙古、東北。必須提示的是,在這四個地方,都是很少見到孔廟的。而且,我們過去所談?wù)摰闹袊慕y(tǒng)治者,也不是全部的中國的統(tǒng)治者,而且也只是真實的中國的統(tǒng)治者的二分之一。須知,在中國,起碼有一半以上的統(tǒng)治者都是來自北方族群(包括隋唐的統(tǒng)治者)。換言之,中國之為中國,地點并不限于內(nèi)地,統(tǒng)治者也還有一半以上來自北方族群。何況,在中國的朝代中還有著元朝與清朝的客觀存在。那么,它們是怎么凝聚起來的?又是怎樣集中在了中華文明的大旗之下的呢?
例如,在中國,人們最為熟悉的,莫過于“逐鹿中原”。“中原”,似乎就是中國的麥加、中國的圣地。而所謂“中原”,我們知道,最早應(yīng)該是從洛陽開始,當(dāng)時,洛陽就被稱之為天下之中。著名的何尊上有一句銘文:“宅茲中國”。其中的“中國”,就是指的洛陽。最早的中國,也許就是從這里開始的。顯然,這里的“中”,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神圣范疇,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神性建構(gòu)。正是因此,才“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也使得中國的諸多民族都沒有例外地、也都孜孜以求地渴望融入中原。
顯然,融入中原,也就是融入中國故事、中國敘事,這“融入”,會使得執(zhí)政成本大大降低,也使得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強。這意味著,正是在中原,才蘊藏著極為優(yōu)質(zhì)的精神資源,也才存在著一雙神奇的“看不見的手”。它是中華民族最為內(nèi)在的向心力、最為強大的凝聚力,也是中華文明之所以得以無窮復(fù)制的文化基因,更是中華文明之所以得以世世代代連綿不絕的核心秘密。
換言之,“中原”之所以值得“逐鹿”,是因為它有著自己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不過,與西方不同,它不是通過“上帝”來呈現(xiàn)的,而是通過“天”來呈現(xiàn)的。或者說,在西方,是以“上帝”為宗;而在中國,則是以“天”為宗。“天“,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然而,嚴(yán)格而論,中國的“以天為宗”卻又很難被稱之為宗教。因此,對于“天”的敬仰,確實很難被稱之為宗教,但是,必須強調(diào)的卻是,與眾多的因此而導(dǎo)致的對于中國文化的否定性評價不同的是,我仍舊堅持認(rèn)為:“天”,卻畢竟是一種信仰。正是它的存在,才導(dǎo)致了“德‘的向前向上,導(dǎo)致了”德“的不斷提升。而且,”天“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中國的”無宗教而有信仰“的特色的形成。
托克維爾特別注重于去考察不同民族的“搖籃時期”,他認(rèn)為:“搖籃時期”昭示著“一些民族何以被一種似乎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們本身也未曾料到的結(jié)局。”[1]在我看來,中國也如此,與世界其它幾大文明不同,中國不是君權(quán)“神”授,也不是有宗教地進(jìn)入文明社會,而是君權(quán)“天”授,也就是沒有宗教地進(jìn)入文明社會。
這無疑是中國文化在信仰建構(gòu)路徑上的另辟蹊徑,以儒家為例,一般認(rèn)為,在孔子之后,儒學(xué)的拓展可以分為兩大不同的取向。一個是走向理性,以《大學(xué)》和荀子為代表,一直到宋代的程朱理學(xué),最終被推向了極致,另一個是走向宗教,以《中庸》《易傳》為代表。或者認(rèn)為,倘若以孔孟儒學(xué)為第一期,則第二期的儒學(xué)應(yīng)該是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秦漢儒學(xué),突出的是儒教的“外王”,關(guān)涉的也是公德層面,可以以子貢、子張、子夏、荀子、董仲舒、陳亮、葉適、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陳寅恪先生曾云:“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xué)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2]就是對第二期儒學(xué)的肯定。第三期的儒學(xué),是以心性為本體框架的宋明儒學(xué),突出的是“內(nèi)圣”,關(guān)涉的則是私德層面,可以以顏回、曾參、程朱陸王為代表。然而,無論如何,在這當(dāng)中,在信仰建構(gòu)的層面,儒家所做的探索,都無非是在以情感為紐帶的社群意識基礎(chǔ)上(這是出之于孔孟儒學(xué)的原創(chuàng))的外向拓展,也就是走向了以“敬仰”為紐帶的宇宙意識,這當(dāng)然屬于漢唐儒學(xué)的創(chuàng)新。人,生而不能離開社群,但是,同樣的是,人,也生而不能離開自然。人在一出生就置身社群生活的同時,也在一出生就置身天地宇宙,不難想象,正是因此,順理成章地,從秦漢開始,儒家的探索,在“社群”的基礎(chǔ)上,又注意到了“天地宇宙”。對于置身自然生命并且在自然生命中生生不已、共同精進(jìn)的期望,以及在敬畏與感恩中挺立主體價值,從天道以論人道,確實是在孔子、孟子那里都不曾思考和探索過的,也確實是儒學(xué)思考的新收獲。然而,在不論是“社群意識”,還是“宇宙意識”,卻都是出“無宗教而有道德“的思考——“無宗教”,是其中的主旋律。
至于宗教,在古老的中國當(dāng)然也不是沒有,但是,卻大多與信仰的建構(gòu)毫無關(guān)系,而只是建立在自然崇拜的基礎(chǔ)上的自然迷信。在其中,人的精神被自然奴役,人是不自由的,無意志無精神,被泯滅于自然,只知道自己是自然的,沒有價值,更沒有自由,以此,至多也只能被稱之為初始階段的多神教。土地爺、山神、河神、菩薩、狐仙、太上老君、關(guān)公,都可以請進(jìn)神龕,只要能夠帶來好處,就都無可無不可。可是,也正是因為多神,諸神之間的權(quán)能也就都十分有限,而且彼此矛盾,以至于甚至諸神資深都自顧不暇,又怎么給人類以強大的鼓舞?原則的相對和功能的有限必然使得這類的宗教成為功利的宗教。而且,有的時候,是“信”或有之,“仰”卻沒有,有的時候,則是“仰”或有之,“信”卻沒有,還有的時候,則是既沒有“信”也沒有“仰”。無疑,這其實不能被稱作“信仰”,而只能被稱作“崇拜”。與此相應(yīng)的是,既然如此靈活,那么,原則的力量、至高的力量自然也就蕩然無存。
在此意義上,在中國,儒家又被稱之為“儒教”,也就順理成章了。顯然,它區(qū)別于西方的“因宗教而有信仰”,它或許應(yīng)該被稱作“無宗教而有信仰”。
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無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中,也存在著不足。
就以中國文化中的“天“為例,作為宗教,無疑并不成熟。因為“天”其實只是一種低于自由意識的自然意識。借助于黑格爾對于文藝復(fù)興的批評,則是:在其中“單純的主觀性、單純的人的自由,即他具有一個驅(qū)使他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意志這件事,還沒有構(gòu)成正當(dāng)?shù)睦碛伞戳钜庵揪哂辛恕侠硇缘哪康摹@當(dāng)中也依然只有那種可容許的因素”,而且,也“只是按照它的內(nèi)容限于應(yīng)用在特殊的對象范圍之內(nèi)。只有當(dāng)這個原則被置于與那絕對地存在著的對象中,亦即置于對上帝的關(guān)系中來加以認(rèn)識和承認(rèn)……它才獲得對它的最高認(rèn)可。”[3]例如,當(dāng)年天主教進(jìn)入中國,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國禮儀”之爭。為什么會如此?就正是因為中國的祭天(還有祭祖、祭孔)。因為祭天(還有祭祖、祭孔),所以中國的儒教已經(jīng)超出了(道德)哲學(xué)的范圍,具備了一定的宗教性,但是,這里的祭天(還有祭祖、祭孔)又只能被稱之為低級而又低級的宗教性。顯然,這里的“天”毫無人格神的意思,只稟賦著道德性,不過,它的不足顯然不在“宗教”程度不夠,而在“信仰”程度不夠。換言之,“天”的不足恰恰是因為:在其中精神始終都并沒有意識到唯獨自己才是主體,因此卻轉(zhuǎn)而將自己隸屬于自然,誤以為自己是被自然所規(guī)定、所決定的,一方面已經(jīng)有所超越,也已經(jīng)稟賦一定的精神意義,另一方面卻又畢竟是此岸的,因此即便有意義,也僅僅是現(xiàn)世的意義。何況,加之自身的抽象程度畢竟還是不夠高,因此也就只能凝結(jié)為一種道德倫理,例如“民本”“國家”“公天下”等等。可是,也因此,在其中,信仰的積極意義也就仍然是有限的。精神性質(zhì)匱乏,自然意識凸出,導(dǎo)致了精神沉淪于自然,而且反而視自己為自然(如自然之天)。而在其中,精神卻不是自由的,精神對于自然的自由態(tài)度更是不可能出現(xiàn),而只有宿命態(tài)度。
至于在信仰中本應(yīng)充盈著的“神性”和“精神性因素”,也因此而沒有能夠在關(guān)于“天”的思考中被成功地剝離而出。對此,黑格爾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復(fù)予以討論。例如,在《宗教哲學(xué)講演錄》中,他指出:“中國的宗教可以稱之為一種道德的宗教(在此意義上,人們可以把無神論歸之于中國人)”[4]240“他自身中沒有立足點”,“人自身沒有內(nèi)在的、一定的豐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對他來說,一切外在者都是內(nèi)在者;一切外在者對他來說都有意義”,“與他有關(guān)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力量。”[4]244在《哲學(xué)史講演錄》中,他也指出:在中國,“主觀性精神的因素并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揮”,[4]126在《歷史哲學(xué)》中,他又指出: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的關(guān)于信仰的思考那樣,“‘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內(nèi)”的情況,中國“的宗旨只是簡單的德性和行善”,在其中,“我們無從發(fā)見‘主觀性’的因素”,“凡是屬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離他們很遠(yuǎn)。”[5]這也就是說,盡管它也被稱之為信仰建構(gòu),但是卻并不具備信仰之為信仰的根本內(nèi)涵。其中最關(guān)鍵的,就是精神因素的不夠突出。這就正如孟德斯鳩所觀察到的:“禮教里面沒有什么精神性的東西”[6]313“連一段表現(xiàn)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6]279總之,在其中充盈著的,也還僅僅是自然性、實體性的內(nèi)容。
我們知道,信仰之為信仰之所以為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人都不可或缺,完全就是因為,在其中,存在著的是人與理想、人與無限、人與未來的直接對應(yīng),也就是自由者與自由者的直接對應(yīng),它借助追問自由問題,殊死維護(hù)人之為人的不可讓渡的無上權(quán)利、至尊責(zé)任這一唯一前提,個人的存在,在信仰維度而言,其實就應(yīng)該是自由的存在。然而,這一切,在中國的“無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中都還暫時并不成熟。它更多地強調(diào)的,還是人與動物的不同。所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因此,人之為人,其實并不高于人,而只是高于常人。因此,只是“人圣”,而不是“神圣”,于是,也就不必去向絕對至善的理想、未來、無限敞開自己,更不必去以絕對至善的理想、未來、無限為標(biāo)準(zhǔn)來審判自己、懺悔自己,所謂“為仁由己”。而這也就必然遁入費正清等人提出的“既成事實就是合法性”。總之,既然具有某種超自然超現(xiàn)世的純粹精神生活——獨立和超越于自然意識和現(xiàn)世生活的精神生活在中國尚未出現(xiàn),既然對超感性的、精神意義的東西尚且知之不多,既然對主觀自由也尚且知之不多,那也就只好把“必須”當(dāng)做“應(yīng)當(dāng)”。于是,種種與現(xiàn)實價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的功名利祿之類,還仍舊被作為了性命攸關(guān)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人之為人,也不是馬丁·路德所謂“內(nèi)在的人”,而仍舊是“外在的人”,僅僅是“因行稱義”“因言稱義”,而不是“因信稱義”。于是,人之為人也仍舊是角色中、關(guān)系中的自己,而不是自由的自己、無角色、無關(guān)系的自己——哪怕是社群中的自己,也哪怕是宇宙中的自己。
二、“兩漢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
幸而,中國的“無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還并沒有結(jié)束,而是在上述基礎(chǔ)上繼續(xù)地艱難展開。
在2005 年出版的《王國維:獨上高樓》一書中,我曾經(jīng)從“大文明觀”的角度,中華文明的滄桑歷程,在2132 年的古老中國,可以具體劃分為兩期。其中,中華文明第一期圍繞著儒家思想展開。儒家思想初步解決了中華文明的根本困惑,以至于后人會感嘆:“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而道家思想則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但是,它的“天問”與“天對”畢竟只是圍繞著中國本土思想展開的,也畢竟沒有直面過中國文化以外的挑戰(zhàn)。
而中國文化的與西天的佛教的對話,則是本土思想與非本土思想的第一次的對話,是中華文明第二期。
毋庸置疑,佛教進(jìn)入中國,堪稱中國文化的一大姻緣,不但成功地使得非宗教的中國思想有史以來第一次中斷,而且成功地連接起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也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智慧。而作為對話的結(jié)晶,禪宗也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然而,盡管相對于儒家的“有”與道家的“無”,禪宗走向的是“空”,但是,“無宗教而有信仰”,卻仍舊是它的共同特色。
如前所述,中華文明第一期,已經(jīng)成功地開啟了“無宗教而有信仰”的中國特色的“到信仰之路”、“到自由之路”。但是,其中也確實困難重重。例如,因為不存在彼岸,因此就很難高揚某種超自然超現(xiàn)世的“精神性因素”,為信仰建構(gòu)所必需的那種對于自由的固守與呵護(hù),以及以超越本性、以無限、以未來為天命,乃至借助追問自由問題而殊死維護(hù)人之為人的不可讓渡的無上權(quán)利、至尊責(zé)任這一唯一前提,也很難得以實現(xiàn)。人的存在更很難成為永遠(yuǎn)高出于自己的存在,永遠(yuǎn)是自己所是而不是自己之所不是的存在。
例如,所謂“靈魂”,亦即自由存在的精神世界,就很難被切實加以關(guān)注。這是因為,在中國,所有的真善美都沒有完全放在彼岸的一邊,所有的假惡丑也都沒有完全放在此岸的一邊,因此也就并沒有被賦予一種絕對的、神圣的價值,于是,作為與彼岸相對的人也就沒有被賦予一種不可讓渡的絕對的、神圣的價值,而是僅僅往往被賦予了現(xiàn)實的“三不朽”而已,“靈魂不朽”與“靈魂救贖”,自然也就還是一個陌生的話題。與此相應(yīng)的,則是“現(xiàn)實關(guān)懷”與“憂患意識”。無疑,它們也絕對并非一無是處,尤其是在中國的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下,它們的維護(hù)社會正義、凝聚社會正能量的歷史貢獻(xiàn)更是不容否定。然而,究其實質(zhì),卻也不能不說,“現(xiàn)實關(guān)懷”與“憂患意識”畢竟還沒有完全進(jìn)入信仰的語境,因此存在的只是“信念”,而不是“信仰”。而且,也不是對于自我意識的體驗,而是對于外在世界的體驗。在“他自身中就沒有立足點”。[4]244“人自身就沒有內(nèi)在的、一定的豐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對他來說,一切外在者都是內(nèi)在者;一切外在者對他來說都有意義,都與他有關(guān)”。[4]245由此,作為統(tǒng)攝一切的終極價值的精神關(guān)懷、靈魂關(guān)懷也就遲遲未能到位。這樣一來,既然人的自然本性可以“自然而然”或者“順其自然”地生長為超越本性,那么,自然也就“人間即天堂”“人人皆堯舜”了。于是,精神的世界、靈魂的世界自然也就不會成為贖罪的煉獄、靈魂凈化所、未來靈性生活的預(yù)修學(xué)堂乃至滌罪所,精神的自由和靈魂的得救更自然也就并不重要,最終,當(dāng)然也就不是“靈魂救贖”而是“現(xiàn)實憂患”才會成為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
然而,“無宗教而有信仰”畢竟只是“無宗教”,但是卻絕對不是“無信仰”,因此,也就絕對不是對于精神的、靈魂的到信仰之路、到自由之路的否定。既然如此,那么“終極關(guān)懷”與“救贖意識”也就必然會成為必須。它意味著對于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被污染、被玷污的孜孜以求,意味著從絕對至善的理想、未來、無限的高度(因此才被象征地稱之為“彼岸”)地對于自身的重新發(fā)現(xiàn)。
在我看來,禪宗之為禪宗,其重大意義,恰恰就在這里。
相當(dāng)長時間以來,也包括我本人在內(nèi),盡管已經(jīng)意識到了儒家的立足于“有”乃至道家的立足于“無”,盡管都希望“物物而不物于物”,但是卻畢竟始終粘滯于“物”,即便是繼之的魏晉玄學(xué),轉(zhuǎn)而用人格理想取代道家的天之自然,堪稱十分可喜的進(jìn)步,卻仍然未能徹底解決,仍然是無法做到“應(yīng)物而不累”。到那時,我們也確實并沒有說清楚其中的根本差異,也就是:從“現(xiàn)實關(guān)懷”與“憂患意識”到“終極關(guān)懷”與“救贖意識”的轉(zhuǎn)換,換言之,從現(xiàn)實世界向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轉(zhuǎn)換。
然而,一旦意識到了上述根本差異,問題無疑也就顯而易見了。
簡單而言,莊子無疑已經(jīng)注意到了“有”與“無”的區(qū)分以及“無無”的問題(后來的玄學(xué),例如郭象,則干脆取消了“有”“無”問題),但無論如何,兩者畢竟都是“即有即無”,或者偏重“無”,或者偏重“有”。與佛教的對話之后所產(chǎn)生的禪宗,明快之處則是:“非有非無”。例如莊子的“齊物”是在有差別的基礎(chǔ)上的,因而并不否定萬物的存在,禪宗卻否定萬物的存在,結(jié)果就從道家的“同一”走向禪宗美學(xué)的“空”。又如莊子只是天人之學(xué),最高范疇為道,即自然(本性、本然、無為),而禪宗則是心性之學(xué),最高范疇為心,即空。這無疑也使得思想的發(fā)展更為深刻、深入。再如,僧肇、道信就發(fā)現(xiàn)莊子“猶滯于一也”。莊子提出的“游道”“入天”“見獨”“無待”“忘適”“無物”“無情”,都并非無懈可擊。“游道”是由于有“道”的存在,“入天”是由于有“天”的存在,“見獨”是由于有“獨”的存在。“無待”是因為有“待”的存在,“忘適”是因為有“適”的存在。“無物”是因為有“物”的存在,“無情”也是因為有“情”的存在。而禪宗的出現(xiàn),則使得這一思考從“無物”走向“無相”,從“無情”走向“無念”,從“無待”走向“無住”。還有,莊子對于“分別”的批判和對“無分別”的推崇無疑是十分深刻的,但卻畢竟還有缺陷。禪宗進(jìn)而從批判“無分別”又在更高的意義上回到了“分別”。所謂別即是別,同即是同(這與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點,例如巴什勒提出的“本體上的平等”,“接受和接收一切差異”相近),顯然就更為深刻。
事實上,禪宗所討論的,其實已經(jīng)不是現(xiàn)實世界的問題,而是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問題了。從儒家的“有”、道家的“無”轉(zhuǎn)向禪宗的“空”,對于禪宗而言,無疑也正是針對儒家、道家的對于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關(guān)注不夠徹底、不夠深刻而引發(fā)的反省。
三、發(fā)乎情,止乎覺
禪宗的產(chǎn)生,在中華民族的信仰建構(gòu)方面,無疑應(yīng)該是一個重大事件,也是一個重大轉(zhuǎn)折。
在其中,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當(dāng)然是惠能。最初,印度人普提達(dá)摩經(jīng)海上絲路從印度到達(dá)廣州,在廣州建寶林寺,被稱為“西來初地”。不久就從廣州到南京,會見南朝的梁武帝,孰料話不投機,于是他又“折葦渡江”,到了河南的洛陽,此后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燦,再從河南的洛陽轉(zhuǎn)至安徽的潛山,繼而,四祖道信再轉(zhuǎn)到江西的廬山,再轉(zhuǎn)到湖北的黃梅,其間,從黃河文化區(qū)域到長江文化區(qū)域的轉(zhuǎn)換清晰可見。然而,中華文明第二期的關(guān)鍵的一幕是惠能揭開的。因此,盡管他本人并不在乎歷史,但是,擁有他,卻畢竟是歷史的驕傲。正是因為他的出現(xiàn),后期的中國文化才再一次隆重上路,再一次整裝出發(fā)。從此,不再是“佛教在中國”,“中國化的佛教”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而且,惠能之后,源遠(yuǎn)流長的中國文化也不再是流轉(zhuǎn)于黃河長江之間了,從此,代表黃河的孔子、代表長江的老子、代表珠江的惠能并肩而立,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圣哲。通過惠能,禪的一瓣心香最終花落珠江。
首先,眾所周知,印度的佛教對于生命的看法是負(fù)面的,這與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儒家和道家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它畢竟仍舊是宗教的,也是有神論的。馬克思.韋伯指出:“印度所有源之于知識階層的救贖技術(shù),不論其為正統(tǒng)的還是異端的,都有這么一層不只從日常生活、甚而要從一般生命與世界,包括從天國與神界當(dāng)中解脫出去的意涵。”[7]然而,經(jīng)過禪宗的轉(zhuǎn)換,印度佛教的苦難意識被轉(zhuǎn)變?yōu)闃酚^的“禪悅意識”,印度佛教的以“無明”開場也被轉(zhuǎn)化為以“明覺”開場。總之,是從“有神的唯心主義”到“無神的唯心主義”。這意味著:在中國,即便是宗教,在本土也會被潤物細(xì)無聲地改造為非宗教,也會仍舊是走在“無宗教而有信仰”的道路之上,意味著中國的信仰建構(gòu)與宗教無涉。禪宗自稱“教外別傳”,并且以“別傳”來區(qū)別于傳統(tǒng)佛教乃至傳統(tǒng)宗教,正是對此的慨然宣告。
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是:從“是心是佛”到“非心非佛”再到“不是心,不是佛”。從禪宗開始,先驗的“覺”竟然下降為經(jīng)驗的“覺知”。其中的奧秘是以“心”為“性”。本來,在佛祖那里,“心”與“性”判然有別,但是惠能卻蓄意使之統(tǒng)一。如是,則成佛不再是走向彼岸,而是自我覺悟。性,不但是佛,而且還是主體的本覺與所覺,是一體的。結(jié)果,“佛性論”在中國轉(zhuǎn)變“佛心論”。于是,“空”成為“真空”,“有”成為“妙有”。最終,“平常心是道”就是必然趨勢,于是,佛教信仰進(jìn)在中國得以進(jìn)入了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這一次的進(jìn)入又與魏晉玄學(xué)不同,不但是從貴族、知識分子擴大到了市井百姓,而且,盡管禪宗與玄學(xué)都是通過“無”把外在束縛統(tǒng)統(tǒng)予以化解,從而回歸個體的生命愉悅,但是,魏晉玄學(xué)的目標(biāo)是緊緊抓住偶然的機遇,成就一個我,但是禪宗卻無此追求,只是當(dāng)下承受而已。
總之,禪宗所帶來的根本智慧,無疑就正是生命的超越的智慧。它從不引導(dǎo)人們離開具體而又單純的我——世界——佛,而是傾盡身心去啜飲生命之泉,這就必然超越有無、是非、生滅、得失,“用智慧觀照,用一切法,不取不舍”(《壇經(jīng)》)。并且,認(rèn)定時間即空間、瞬間即永恒、感性即超越、實即虛、色即空、動即停、生即死、有是有同時又是非有、無是無同時又是非無,“在不住中又常住”同時又無所謂“住不住”。主張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迷時為生死煩惱、悟時即菩提涅槃,現(xiàn)實與理想、短暫與永恒、有限與無限、“無明”與開悟,也如此。因此,妙悟是現(xiàn)象透處即本體、本體顯處即現(xiàn)象。從現(xiàn)象看,是不離有無;就本體看,是不落有無;從整體看,則是不離有無,不落有無。所謂“行住坐臥皆道場”“平常心是道”。
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覺”,當(dāng)然是其中的核心內(nèi)容。過去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儒)、“發(fā)乎情,止乎逍遙”(道),現(xiàn)在卻成為了“發(fā)乎情,止乎覺”(禪)。精神,開始超越了精神與自然的直接統(tǒng)一,開始返回到它自身,一種以精神自身為根據(jù)的自由精神,第一次得以在朝宗的溫床上加以孕育。盡管,這只是起點,也還并沒有達(dá)到絕對無限的內(nèi)在,但是,畢竟已經(jīng)開始不再作為自然的東西來加以對待,畢竟已經(jīng)開始把精神當(dāng)作精神,作為精神的精神自身也畢竟開始變成了精神的對象。超自然超社會的精神生活,第一次登上了中國的舞臺。
在這當(dāng)中,最為重要的,是成就了“妙悟”與“境界”。
關(guān)于“妙悟”,目前已經(jīng)有眾多的討論,我在《中國美學(xué)精神》中也已經(jīng)專門論及。然而,迄今大部分的討論卻仍然還是云里霧里,就“妙悟”談“妙悟”,往往被忽視了的,卻是“妙悟”的根本內(nèi)涵。事實上,“妙悟”之為“妙悟”,關(guān)鍵是從過去“神思”與“象”、與經(jīng)驗世界的直接關(guān)聯(lián),轉(zhuǎn)向了今天的與“境”、與心靈世界的內(nèi)在相通。它意味著:歷經(jīng)千年滄桑,中國文化終于尋覓到了進(jìn)入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的途徑。因為精神世界、靈魂世界不是一個可以把握的對象、一個可以經(jīng)驗的對象(否則事實上也就放逐了精神世界、靈魂世界),那么,怎樣去對之加以把握呢?“妙悟”正是因此而應(yīng)運誕生。這,就是禪宗所謂的“于念而離念”。
境界,是中西(印度)思想融會貫通的產(chǎn)物,沒有佛教尤其是禪宗思想中由“空”而引發(fā)孕育的“境”,中國人也許還一直都在喋喋不休地念叨著“意象”,也還一直都會停留在從莊子開始的心物關(guān)系之中,但是,因為本土思想與境外思想的結(jié)合,為信仰建構(gòu)提供了本體存在的根據(jù)。境界之為境界,已經(jīng)不是昔日中國人所喜歡說的什么“情景交融”,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的誕生。由此,精神世界的無限之維就被敞開了,人之為人的終極根據(jù)也被敞開了。我們知道,人是動物與文化的相乘,也是“原生命”與“超生命”的統(tǒng)一。其中的“超生命”其實就是人之為人的文化生命,亦即“靈魂”。境界的出現(xiàn),盡管首先是在禪宗領(lǐng)域,但是透過宗教的外衣,我們必須要指出的是,它體現(xiàn)的正是人的被文化化,是文化的從附屬層面一躍而成為本體層面。人的超生物性——也就是文化性占據(jù)了本體的地位。猶如有形存在的人置身的只是世界,無形存在的人所置身的,正是境界。世界,轉(zhuǎn)瞬之間全然成為了對人有所意謂的客體。當(dāng)此之時,作為人的精神無疑就亟待去自我表達(dá),境界,就正是人的精神的最高的自我表達(dá)。這正如馬克思所言:“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在理解”[8]8就是世界,從“主觀方面去理解”,就是境界。從生命“這個前提的內(nèi)容去研究這個前提”,是世界,從生命的“形式方面研究了前提”,是境界。[9]從“任何物種的尺度”出發(fā)的,是世界;從“內(nèi)在固有的尺度”出發(fā)的,則是境界。當(dāng)然,它并非“真理”,但卻是“真在”;它不同于“在”的“理”,是對應(yīng)于認(rèn)識,作為“在”的“真”,它對應(yīng)的是“生命”。而且,相對于“在”的“理”的“真理”,作為“在”的“真”的“真在”,也就是境界,才是“真實”的表達(dá),也是人的終極、人的精神、人的自由、人的超越的最高表達(dá)。
四、“有宗教而無信仰”
當(dāng)然,禪宗的探索也有其歷史的局限。這也就是說,迄至宋代,當(dāng)信仰形態(tài)的宗教最終被儀式形態(tài)的宗教取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的思想引進(jìn),卻又畢竟仍舊是喜憂摻半的。
中國的引進(jìn)佛教,究其實質(zhì),是有意無意中意識到了信仰的匱乏的必然結(jié)果,然而,信仰的建構(gòu)又談何容易,它意味著必須毅然跨越毫無精神性的自然意識,趨近超自然的精神世界,可是,兩者之間的巨大鴻溝,宛如二維空間向三維空間的躍升,這猶如鳳凰涅槃,也猶如脫胎換骨,無異一次精神的萬里長征。可是,來自西天的佛教無疑并不勝任,因為它自身也仍舊是自然宗教,在這方面,與中國文化并不存在質(zhì)的差異。其結(jié)果是,佛教進(jìn)入中國,歷經(jīng)“三武一宗”的四次劫難,而且大致跋涉了三個三百年:第一個三百年,是佛教進(jìn)入,第二個三百年,是禪宗興起;第三個三百年,是禪宗逐漸衰落。在這當(dāng)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的菩薩道思想逐漸離開了中國人的視線,佛教逐漸被儒家化。這就是禪宗的出現(xiàn)。所謂“教外別傳”,其實就是暗示著禪宗已經(jīng)脫離了印度佛教。由此我們想到,百年中,胡適、錢穆、柳田圣山都不約而同地用“革命”一詞來描述禪宗的出現(xiàn),錢穆甚至說,真正辟佛的不是韓愈,而是禪宗。其中的真正內(nèi)涵,正是佛教的逐漸淡出。
在這個意義上,玄奘去世與慧能出家的同時出現(xiàn),似乎就是一個歷史的征兆。從此玄奘就只活在《西游記》里,玄奘歷經(jīng)艱難取回的“西天”智慧、西天的信仰,也從此被束之高閣。有文化的玄奘從此輸給了不識字的慧能。
就以慧能與神秀的對比來看:神秀的偈句把“明鏡”與“塵埃”對立起來,慧能卻認(rèn)為,其實它們并非彼此對立,而是“心”之兩面。“明鏡”是心,“塵埃”也是心。萬事萬物,無論好壞、善惡、智愚,都是我們的心,因此,惠能第一次提出:關(guān)鍵在我們?nèi)ト绾斡谩靶摹薄_@樣,首先,惠能開創(chuàng)了“無神論的唯心主義”。全世界的宗教都是“有神論的唯心主義”,但是,惠能卻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宗教道路——“無神的唯心”。其次,慧能提示說:既然無“神”,這個“心”也就不在“神”,而在每個人的自身。這就是所謂“眾生是佛”, 每個人都原本就是“佛”,無需“成”也。只是我們自己把自己跟“佛”分開了,所以才要去“成佛”,但是,只要意識到自己就是“佛”,也就不需要去“成”了。最后,因此,所謂“佛”,就只是一個覺悟者。當(dāng)你意識到原來的所有人生問題都不需要去解答,因為它們根本就不是問題,于是,你就成為了一個覺悟者。無疑,這樣的看法,即便是在全世界,也是開天辟地的全新思想。中國人的思想由此而煥然一新。
然而,被禪宗改變的卻不僅僅是佛教,還有佛教的信仰。本來,佛教還是孜孜以求于現(xiàn)實的人心向絕對的佛性的趨近的,但是,禪宗卻把絕對的佛與現(xiàn)實的人心混同起來,例如,呂瀓就睿智地發(fā)現(xiàn),禪宗的真正奠基者道信所提倡的安心法門,所謂“道信的禪法”“與當(dāng)時倡導(dǎo)的‘他力信仰’是對立的”,“道信則強調(diào)以心為源,應(yīng)該憑借自力去做,因而有反對他力的性質(zhì)。”[10]而且,在中國浩如煙海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jīng)”的《壇經(jīng)》也刻意地強調(diào)自性自度、自性自修。馬祖干脆說:“平常心是道”,這意味著:連慧能的“迷”、“悟”之間的區(qū)別也不復(fù)存在,蘊含在西天佛教之中的信仰萌芽被有意淡忘。甚至,因為信仰的被消解,禪宗本身事實上就也被消解了。在基督教那里作為信仰的宗教,在禪宗這里變成了生活。佛教之中的“心”也被具體化為了“心性”。“佛”的宗教被改變?yōu)榛勰艿摹靶牡淖诮獭保胺稹钡男叛鲛D(zhuǎn)換為“心”的敬仰。虛無縹緲的“佛心”變成觸手可及的“人心”。于是,不再是盡從彼岸送來,而是“盡從這里出去”。成圣與成佛、修身與修行、仁愛與慈悲,科舉和成佛……都混同起來,事實上,從此,與儒家也就混同起來。無疑,轉(zhuǎn)而從“信仰”的建構(gòu)又回到了儒家的“道德”建構(gòu)的老路,這恰恰也正是禪宗的缺憾。
換言之,佛教的引入,倘若是意在中華文明的信仰建構(gòu),那么,則應(yīng)該是兩種可能。其一,從“無宗教而有信仰”進(jìn)入“因宗教而有信仰”,轉(zhuǎn)而借助于“宗教”的衣缽“來完成中華文明的信仰建構(gòu)。其二,進(jìn)一步固守”無宗教而有信仰“,那么,則應(yīng)該是擺脫宗教的衣缽,進(jìn)而在信仰建構(gòu)的層面做出全新的努力。然而,禪宗的出現(xiàn)卻恰恰未能令人滿意。它接過了宗教的衣缽,但是卻沒有進(jìn)而以之作為信仰的溫床,走的卻恰恰是”有例如王陽明哲學(xué)的誕生,例如《紅樓夢》美學(xué)的誕生,但是,倘若僅就禪宗本身而言,卻畢竟有所不足。
我們知道,就信仰的建構(gòu)而言,“精神”內(nèi)涵是一個重要的指標(biāo)。眾所周知,人之為人,僅僅只是一個未成品,生而有之的,只是與動物一樣的自然本性,所直面的,也只是與動物所直面的一樣的自然世界。幸而,這對于動物來說已經(jīng)是全部,對于人來說,卻只是局部,或者說,只是一半,而且是相對來說并不起決定作用的一半(盡管也很重要),另外的更為重要的一半,則是人類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亟待人類自己去創(chuàng)造的世界,也是真正拼盡全力去爭取。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提示:它不用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而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而且能夠“擺脫世界而去構(gòu)造‘純粹的’理論、神學(xué)、哲學(xué)、道德等等”,“不用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8]30意味著直接的外在自然世界的被主動剝離,每每把現(xiàn)實世界混同精神世界,把人的自覺意識混同動物的自覺意識,遺憾的是,外在對象作為他物,卻始終都是異己的,也始終都是每個人都須臾不可離開的,因而就也始終都在制約著自身,不但當(dāng)然毫無自由,而且更不可能把它作為一個自己在其中借以實現(xiàn)自身的對象來看待。而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則意味著:即便是不再憑借直接的外在自然世界,精神世界、靈魂世界卻依舊存在。何況,精神世界與自然世界的根本區(qū)別本來就在于必須能夠自由地對待對象,并且能夠在外部對象身上直觀自我,并且,還因此而穿越了直接性、個別性而進(jìn)入普遍性。
然而,在禪宗,卻盡管意識到了人類唯有借助精神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生活于自然世界,意識到了必須從精神本身來理解精神世界,但是卻也畢竟未能完全從自然意識中超拔而出,也未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這是因為,所謂自由包括對于必然性以及客觀性、物質(zhì)性的抗?fàn)帲约皩τ诔叫砸约芭c之相關(guān)的主觀性、理想性的超越兩個方面。禪宗敏捷地把握住了其中的超越性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主觀性、理想性的超越,由此,中華文明第一次不再關(guān)注脫離了自由的必然(例如儒家),而是直接把自由本身作為關(guān)注的對象(這無疑又是從道家“接著講”)。由此,自由本身成功地進(jìn)入了一種極致狀態(tài)(中華文明的思想本身也因此也進(jìn)入了一個全新的廣闊領(lǐng)域),但也正是因此,自由一旦發(fā)展到極致,反而就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不自由。恰成對照的是,西方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采取的態(tài)度是:自由地選擇(荒誕)。它勇敢地逼近這一危機,承認(rèn)生存的荒誕性,并且坦然地置身之中,在其中體驗著自身的本質(zhì)。然而,禪宗的態(tài)度卻是:自由地解脫(從“逍遙”到“覺”,即“解脫”)。結(jié)果,從莊子的“游”發(fā)展為禪宗的“證”(世界都成為象征,成為一個隱喻,于是才有所謂“看破紅塵”),這當(dāng)然十分深刻。然而,面對“生死怖人”的煩惱,它卻僅僅以“解脫”就取代了“煩惱”,“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愛心也同時被取代了。其結(jié)果,就是滑向“無可無不可”的掩耳盜鈴,這,又是我們亟待予以高度警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