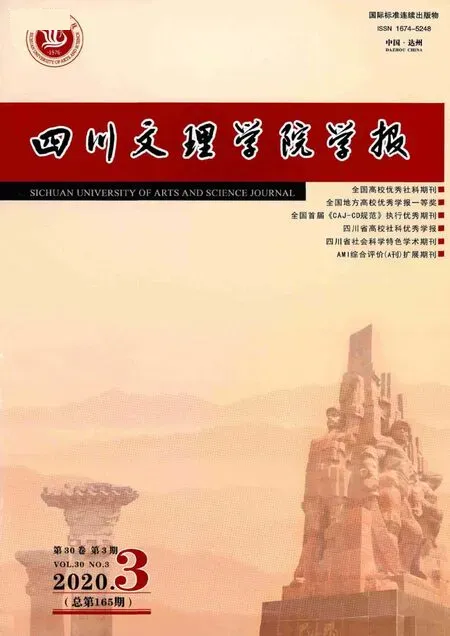“香菱學詩”中的詩歌賞析與創作
周天春
(中國石化西南石油工程公司井下作業分公司,四川 德陽618000)
《紅樓夢》作為一部經典名著,內容幾乎包羅萬象,成為后來人研究清朝風俗、飲食、建筑、服飾、禮儀等的百科全書。對于《紅樓夢》的評價與地位,筆者在此不做贅述。在第48 回《濫情人情誤思游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作者詳細講述了香菱師從黛玉學詩的過程,作為香菱的師父,林黛玉分別從詩歌的結構、立意以及格調三個維度向香菱闡明了如何去品詩,又如何去作詩。臺灣著名作家蔣勛稱贊說,“她(香菱)從一開始不會寫詩,到有一點生澀,到最后寫出了通仙的絕妙好詩的過程,絕對是文學教學、詩歌教學一個很好的范本。”
作為詩歌教學的范本,從林黛玉的指導與香菱的逐漸領悟中,可以看出詩歌賞析與詩歌創作都是一個循序漸進并不斷深入的過程。基于“香菱學詩”中的詩歌教學范本,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探討如何去賞析詩歌,如何創作詩歌。
一、從結構中認識詩歌
詩歌在我國古典文學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從“思無邪”的《詩經》與文辭華麗的《楚辭》開始,再到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詩歌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以不同的形式完成著自己的使命。也因為受詩歌的影響,在我國古典小說之中,詩歌也成為了烘托氛圍、促進情節發展的一種手段。這一點在《紅樓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那么如何去賞析詩歌、創作詩歌?作為師父的林黛玉開篇即言明:“不過是起承轉合。”這其實是在詩歌結構上的剖析,是一種對詩歌語言結構最直觀的觀察與認識,更是詩歌創作的技巧所在。
根據現存的文獻,“起承轉合”這個說法最早出自元代范德璣的《詩格》:“作詩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永。”到清代之后,學者劉熙載在其著作《藝概·文概》中,對范德璣的說法進行了引申,即:“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也,連起亦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顧兼趣合也。”時至今日,對“起承轉合”的釋義也無外乎這兩種。[1]
詩歌的“起承轉合”在于將文字、畫面、時間以內在的邏輯串聯起來:有“起因”再有“承接”然后“轉”最后以“合”收尾。這種結構在律詩中表現得較為明顯。
現在大部分學者的觀點是,詩歌的創作中“起承轉合”的方法基本是在唐代的律詩中逐漸萌芽與形成的,而再追其源流,那可能就要歸結于唐代的試帖詩了。對此,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金圣嘆這樣說:“唐人既欲以詩取士,因而又出新意,創為一體,二起二承二轉二合,勒定八句,名曰律詩。如或有人更欲自見其淹贍者,則又許于二起二承之后,未曾轉筆之前,排之使開,平添四句,得十二句,名曰排律。”[2]
金圣嘆所說并非毫無道理,中國詩歌發展到唐朝可以說到了一個頂峰,無論是詩人、詩歌的數量,還是對詩歌形式上的探索都讓后人難以望其項背。但是,如果再逆著詩歌歷史前進,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詩歌的“起承轉合”幾乎是與詩歌這個形式同時誕生的。
在上古詩歌《卿云歌》的“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在《詩經》中,在五言詩中,在七言詩中,“起承轉合”幾乎存在于所有的詩歌形式中。也有人說,“起承轉合”的結構成了固定的模式,有了定式,就有了局限性,但是這種結構上的獨特美學,卻讓其與詩歌這種文學像是水乳交融,互相成就。
在此,我們對于詩歌創作是否要嚴格遵循“起承轉合”的結構要求暫且不論,在后來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排律這種結構上的獨特性與可復制性,讓原本屬于詩歌的結構理論發展到明清慢慢脫離了詩的意味與至今被深惡痛絕的八股文聯系到了一起。[3-4]
但是,我們仍然要從黛玉的話中讀出更深刻的一層含義,那就是每一種文學體裁,無論是詩詞歌賦還是小品文辭,在其結構與形式上必然有著自己的特征。這種特征可能是獨有的,也可能是與其他文學形式共用的,但是,一定要看到的是,詩歌結構上的固化一方面是為內容服務,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區分于其他的文學形式。
詩歌只所以能夠被稱為詩歌,自然有著其不可取代的地方。在古代,詩歌通常以誦讀、吟唱為主,因此結構上的抑揚頓挫、高低起伏就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從賞析角度還是創作角度,從把握詩歌節奏上的變化與內容上的呼應上來說都是認識詩歌的第一步。
看看林黛玉怎樣講的:“……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這句話并不難理解,除了前面所說的“起承轉合”,節奏感作為詩歌的一大特點,也是詩歌創作訓練的基礎。
“平仄相對”就是詩歌的上句與下句的平仄要有變化。通俗來說,節奏與虛實、平仄對仗的形式,即聲韻。對于詩歌節奏感的訓練,是對入學兒童最基礎的教學,以音律、聲調、格律為主。因此,因而也誕生了大批有關聲韻訓練的典籍。明清已降,以《訓蒙駢句》《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為代表的啟蒙讀物的流行也說明了節奏感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
很多學者都認為,詩歌是我國古典美學的凝結,不僅僅是從詩歌意境上的理解,更是對“對仗”的詩歌結構的欣賞。對仗不僅僅是音律上的變化,也是內容上的呼應。例如《聲律啟蒙》中的“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不僅讀起來朗朗上口,而且內容上的對仗也延伸了詩的深度與廣度。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并沒有讓黛玉繼續和香菱解釋下去,而是讓香菱看前人的詩歌。因為如果要繼續說,律詩就單單對仗的手法就不是一兩句能夠解釋清楚的。在律詩的寫作中就由隔句對、續句對、偷春格、蜂腰格、起句對、末句對、徹首尾對、徹首尾不對等等特殊的對仗手法。[5]
香菱所做的第一首詩雖然并沒有得到黛玉的肯定,但是從仍然可以看到其詩中的“夜色寒”“影團團”“常思玩”“不忍觀”都做到了簡單的平仄對仗。這說明,香菱已經在對詩這種文學形式有了結構上的理解,只是還未徹底明白詩的內涵與韻味。
二、從立意中讀懂詩歌
從結構上認識了詩歌之后,林黛玉接著說:“……如若是有了奇句,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這句話乍一看來似乎是對詩歌結構上的否定,其實不然。林黛玉所言的核心是,結構固然重要,是認識詩歌與創作詩歌必須要打好的基礎,但是詩歌的目的是為了“言志”,結構說到底只是一種形式,是一種外在的表現,是“術”。
詩歌的好壞,立意最重要,而“立意”就是詩歌內容的集中體現。北宋著名文學家黃庭堅對于詩歌創作“立意”的重要性就有“不可鑿空強作”“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的說法。意思就是,詩歌創作也有內容可寫,在有了生活感受之后才能動筆,同時也要根據詩歌的內容與立意來評判詩歌的優劣。[6]
有內容可寫而不為了作文而作文,為了寫詩而寫詩,其實就是作詩著文要“言其志”要“源其情”。對于言志與源情的說法,早在《詩經》與《楚辭》等的創作經驗中就可見一斑,唐代王昌齡對于“立意”的內容在其《詩格》中云:“詩有三宗旨”,即“立意”。“立意”是詩歌之根本,“有以”“興寄”作為補充,強調了詩歌要感物起興、托物言志,一言蔽之,要有話說。[7]
從讀懂詩歌到創作詩歌,是一個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過程。林黛玉悉心講解之后便給香菱出了一道“考題”,香菱根據題目要求所做的三首詩也很好的佐證了詩歌的美在于結構與內容的相輔相成。甚至,立意若高了,結構有時候反而成了其次。
香菱以“月”為題,押的是十四寒的韻,所做的一首七言律詩,從結構上看,這首詩是合格的,但是黛玉卻做出了批評:“意思卻有,只是措辭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這其實就是對詩歌“立意”不高的批評,創作時只看到了客觀事物,而忽略了意與象的融合。
香菱聽取了黛玉的意見之后,所做的第二首與第一首想比,用到了“香欲染”“涂金砌”“淡淡梅花”“絲絲柳帶”,措辭更加講究,但是黛玉還說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了,還得另作。”“穿鑿”就是走了另外一個極端,只注重文字表面的華麗,以至于離題,沒有做到“不以文害意”。
將精力放在措辭上,往往就會被文辭所束縛,反而失去了詩歌本來要傳達的意境,因此在看完香菱第二首詩的寶釵才會說:“不像吟月了,……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聽完黛玉與寶釵的評價后的香菱很沮喪,因為作為一個初學者,香菱“自以為這首絕妙”,這就是對詩的內涵還未完全掌握的具體體現了。
同樣是寫“月”,同樣是押的是十四寒的韻,蘇軾的《中秋月》立意就顯得高了很多:“暮云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這首詩是蘇軾在宋神宗熙寧4 年中秋所作,當時其弟蘇轍到徐州來看望蘇軾,而在皓月之下兩人短暫的相聚之后便要分離,因此蘇軾所作這首詩,是在團圓之夜望著天上一輪滿月又將面對分離之時有感而發。他從對月亮的如實描繪開始寫,又因月的“團圓”聯想到人的“分離”,字里行間的悲痛如“清寒”一般“溢”了出來。在面對生離死別這個永恒的話題之時,蘇軾借月抒情,但并未一味悲觀下去,體現了詩人豁達的人生態度。這與香菱詩中文字堆砌出來的蒼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正如前文所說,詩歌的核心是“言志”,脫離了言志這個基調,文辭再華麗,技巧再高超,也算不得好詩。在明代中葉,曾經十分流行“雍容典雅”的臺閣詩風,與香菱第二首詩的風格極為相似:內容貧乏無味卻只在遣詞造句上下功夫。為此,明代的李夢陽掀起了復古思潮,其中的核心理論就是“格調”的論說,提出詩歌不僅是形式,更要注重立意。
較前兩首而言,第三首詩的進步是很明顯的:“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博得嫦娥應借問,緣何不使永團圓。”對于這首詩大家的評價也很中肯:“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
因此可以看出,立意的深度決定了詩歌的整體質量,評判詩歌的優劣,文辭只在其次,而重在抓住形象,有感而發,并能夠有所感悟,才算是一首好詩。
三、從格調中品味詩歌
在香菱作詩之前,林黛玉給了香菱一個推薦書目:“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
從王維到杜甫再到李白,林黛玉這位老師從詩歌格調中教香菱為何品味詩歌。香菱說自己喜歡陸游的“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卻被黛玉批評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念,一入了這個格局,是再學不出來的。”陸游的這句詩并非不好,對仗工整,內容也算“真切有趣”,唯一的缺點就是格調不高、格局不大,只是一些小情趣罷了。
“格調”是從詩歌“立意”中演化而來的更高層次、更深內涵的概念。唐代王昌齡對詩歌的格調作出如下闡釋:詩歌是從“意”到“格”,由“格”再到“調”的過程。而格調之高下,他在《詩中密旨》舉出了這樣的例子:“古詩:‘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此高格也。沈休文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此下格也。”[7]
因此,黛玉在給香菱講授如何創作詩歌的時候,并沒有止于詩歌的形式與內容,而是引入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格調”。從黛玉的推薦中我們也可以知道,無論詩歌的形式在歷朝歷代中如何更迭,王維、杜甫、李白三人的詩歌仍然值得我們學習,是因為三個人的詩歌中傳遞的是一種突破自身局限性而放眼看世界的大格局、大視角。剛開始讀詩,能夠品味出此三人詩歌里的深度與廣度,自己創作時候的格調自然不會低。
王維的詩歌用字簡單,卻詩中有畫,并大有禪意,能夠從淺顯的文字中讀出大智慧,十分適合初學者。香菱讀了之后針對“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一句詩有了自己的理解:“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字,竟找不出來。”這就是詩的格調,有著空間的廣闊和時間的長遠。格調高,立意自然就會深遠,在王維的詩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看破表層而追求內心深處從容之人的大境界。
杜甫的詩則是抱著一份對天下人的“仁愛”之心,秉持著與人民休戚與共的大愛寫就的。杜甫的詩被稱作“詩史”,就是源于他的大格局,能夠看到天下蒼生的悲苦,能夠切身去體驗這種悲苦。在杜甫的“三吏”“三別”中,我們看不到杜甫作為一個詩人的遣詞造句,只看到一個悲憫看世事之人發出了的悲鳴。文辭自然沒有諸如“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這樣的句子美,但是卻以格調取勝。
相比而言,李白的詩歌里則多了十足的想象力,這種不被自然規律所禁錮的想象力成為李白詩歌最大的風格。從格調上來看,李白的詩歌代表了一種獨立的精神,代表了在天底下自我成就的壯麗與瀟灑,帶著這份恣意遨游、上下求索的豪情而作出的詩歌,自然不會囿于文辭上的華麗。[8]
可以說,黛玉讓香菱所讀的三個人的詩歌在風格上各有千秋,但是在格調上都立意高遠。在黛玉看來,有了王維的詩歌的基礎,接著看杜甫的沉郁頓挫,再到李太白的浪漫豪放,“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詩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是個詩翁了!”有了這個基礎之后,香菱后來所做的詩歌也被大家夸贊“有意趣”,有格調,這與黛玉的教導分不開的。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或為了彰顯人物的個性,或為了烘托氣氛,或為了為讀者進行警醒,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詩歌,這些詩歌無一例外體現了曹雪芹的“詩歌創作”與“詩歌賞析”的偏好。這不僅僅表現在詩歌形式上要追求平仄對仗與起承轉合,還有有立意、有格調、有感情、有什么的意趣。通過“香菱學詩”,在黛玉與香菱在“教”與“學”之間的互動中,我們能夠看出曹雪芹自己對詩歌賞析與創作的理解,雖然有著個人感情色彩但并不失公允,不僅展現了作者自身的文學素養,也為后人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賞析詩歌、創作詩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