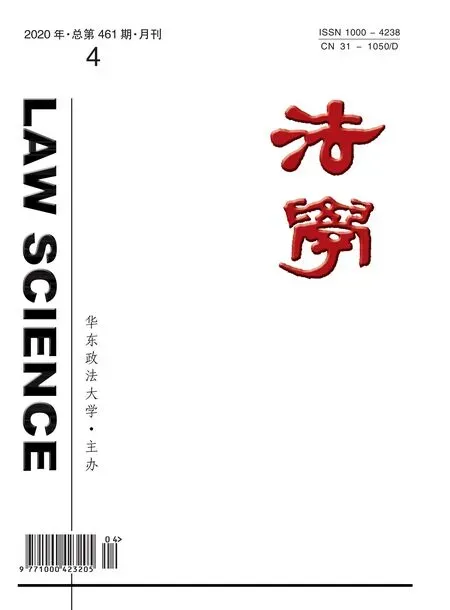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適用效力的邊界
●陳儒丹
一、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適用效力問題的產生背景
作為國家利益的安全閥,公共秩序例外制度,又稱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形成于國際私法與國際公法中。但是,與其在國際私法和國際公法中的活躍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WTO法中該項制度自1995 年被規定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第14 條〔1〕GATS第14條規定:“在此類措施的實施不在情形類似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服務貿易的變相限制的前提下,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成員采取或實施以下措施:(a)為保護公共道德或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措施……”GATS原文中對(a)款例外的注釋是“只有在社會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夠嚴重的威脅時,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2〕TRIPS公共秩序例外規定體現在三處。首先,序言中規定了“認識到知識產權屬私權;認識到各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標,包括發展目標和技術目標”。其次,第8條原則方面第1款規定了“在制定或修改其法律和法規時,各成員可采用對保護公共健康和營養、促進對其社會經濟和技術發展至關重要部門的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類措施與本協定的規定相一致”。此外,第27條第2款規定了“各成員可拒絕對某些發明授予專利權,如在其領土內阻止對這些發明的商業利用是維護公共秩序或道德,包括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避免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所必需的,只要此種拒絕授予并非僅因為此種利用為其法律所禁止”。序言、第8條第1款和第27條第2款〔3〕See Gregory Shaffer, Recognizing Public Good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ho Participates? Who Decides? The Case of TRIPS and Pharmaceutical Patent Prot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7(2), 2004, p.459-482.和《政府采購協議》(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第23條第2款中。〔4〕GPA對公共秩序例外的規定方式幾乎與GATS中的規定方式相同,其第23條第2款規定:“在遵守關于此類措施的實施方式不構成對條件相同的國家造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不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要求的前提下,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任何參加方采取或實施下列措施:為保護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或知識產權所必需的措施;或與殘疾人、慈善機構或監獄囚犯產品或服務有關的措施。”沉寂十年后,直至2006年,WTO爭端解決機構才在“安提瓜訴美國限制網絡賭博案”〔5〕See Panel Report, US—Gambling, WT/DS285/R, paras.6.463-6.487.中首次“激活”該制度。自此之后,其在WTO爭端解決中的適用逐漸變得頻繁,特別是于中國而言,在被訴時會較為頻繁地使用公共秩序例外進行抗辯。2007年“歐美訴華金融信息服務案”若未能達成和解則中國必然需要援引公共秩序例外進行抗辯,〔6〕See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DS372, DS373,DS378; Angela Wang, Will China Prevail Over the Current WTO?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nal, 2009, p.212, 215-221.2007年“美國訴華知識產權案”則明確涉及公共秩序例外,〔7〕See Panel Report, China—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adopted at 26 January 2009, paras.7.125-7.135, n.126;參見宋杰:《公共秩序、知識產權保護與中美知識產權爭端》,載《國際貿易問題》2008年第10期;Joost Pauwelyn, The Dog That Barked But Didn’t Bite: 15 Yea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t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0, p.14-15.2009年“美國訴華音像制品限制進口措施案”間接涉及公共秩序例外,〔8〕See Panel Report, China—Audiovisual Services, WT/DS363/R, adopted at 12 August 2009, paras.5.11-5.13; 參見彭岳:《貿易與道德:中美文化產品爭端的法律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2010年美國意欲訴華的Google退出市場問題也曾考慮援引公共秩序例外,〔9〕參見李晨:《google暴露WTO模糊地帶,中國應借機立法》,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3月9日,第2版;《美官員稱擬就中國審查谷歌向WTO投訴》,載新浪網2010年3月10日,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31317195997s.shtml.而中國準備加入的GPA在未來也極有可能引發公共秩序例外的適用。〔10〕參見蘇玲:《商務部:希望早日加入〈政府采購協議〉》,載《北京商報》2010年6月8日,第2版;《中國遞交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新提議》,載新浪網2010年7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721/09508335538.shtml.那么,這些WTO條款中規定的公共秩序特指本國(措施實施方)的公共秩序還是包含了別國(措施適用對象國)的公共秩序?可否為了維護被實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實施貿易限制措施?這些問題也可稱為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
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轄。域外管轄是為了本國利益,即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公共秩序而對處于外國的本國人或本國船舶實施管轄權。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則是指為了別國(被實施措施方)利益,例如,A國法律規定A國公民在B國旅游期間如有召幼妓行為,在其返回A國時將會被認為侵犯了B國的公共秩序而被A國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起訴。〔11〕See Nicolas F.Diebold, The Morals and Order Exceptions in WTO Law: Balancingthe Toothless Tiger and the Undermining Mo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7, p.70.很顯然,這樣一項措施將會限制B國的境外旅游服務貿易。〔12〕WTO所調整的措施并不僅僅限于民商法和經濟法,也包括一個國家與國際貿易有關的刑法與行政法,如美國訴中國知識產權糾紛案中就涉及了中國管制盜版的刑法和行政法。如果B國向WTO起訴,聲稱B國不認為召幼妓行為侵犯其公共秩序,那么A國是否還可基于GATS第14條第1款(a)項的規定使該項具有限制貿易效果的措施取得正當性呢?若答案是肯定的,則A國的限制貿易自由的措施違法性顯然會被削弱,敗訴率就會下降。對此WTO協定中未作規定,而“安提瓜訴美國限制網絡賭博案”也回避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
有學者認為:“制定國際貿易多邊制度的困難實質上在于如何區分下列兩種情況:一方面,一個非保護主義取向的政府不能避免某些國內政策附帶地產生針對外國競爭者的歧視;另一方面,一個保護主義取向的政府使用一個合法的目的作為設計能夠限制外國競爭的國內政策的借口。所以挑戰就在于,設計出對這樣兩種情況之間的區分反應靈敏的規則,使前者豁免,而又可以阻止后者發生。”〔13〕Aaditya Mattoo and Arvind Subramanian, Regulatory Autonomy and Multilateral Disciplines: The Dilemma and a Possible Resolution, 1 Jiel, 1998, p.303.WTO協定中所含的例外制度正是這類具有“過濾器”功能或“紗窗”功能的規則,其設計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國際自由貿易價值與成員國特殊利益價值之間的平衡,孔的大小決定了成員國自由裁量余地的多寡。如果例外制度的立法和司法趨于嚴格,那么被告自由裁量的余地減少,敗訴率就會上升,反之,被告敗訴率便會下降。
捍衛被告特殊的各種非貿易價值并因此使被告享有對貿易實施合法限制權利的例外制度散見于WTO各個具體的協議中。在諸多由例外制度予以保護的非貿易價值中,公共秩序價值可謂是一個較為重要的選項,因為“公共秩序是指對反映在公共政策和法律中的社會根本利益的維護,這些根本利益包括了法律標準、安全和道德”。〔14〕Supra note [5], paras.6.463, 6.466, 6.467.因此,若有關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例外的援引條件或適用規則都十分嚴苛,采取措施的一方將很難根據公共秩序例外獲得豁免降低敗訴率的話,則被告試圖根據其他非貿易價值例外降低敗訴率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具體到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上,需要以上述例外條款進行抗辯的爭議措施在適用過程中都有可能會關涉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對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認定與解釋則關涉具有貿易限制效果的爭議措施的正當性能否成立并因此取得豁免,如果能證明公共秩序例外不存在域外適用效力或者對其域外適用效力應該施加嚴格限制,那么其他例外亦當如是。
二、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適用效力問題的學術分歧
就GATS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而言,目前直接談及此問題的主要有Nicolas F.Diebold的文章,他認為應該拒絕賦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雖然關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問題幾無學者涉及,但是關于與公共秩序比肩而立的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討論則非常激烈,因為與人權和環境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及學者都希望將貨物生產國與人權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問題,如童工問題、以虐待動物的方式生產貨物問題及環境問題等,通過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規定納入WTO法系統中,通過借助WTO爭端解決機制促進人權主張的實現。從總體上看,目前這些學者的觀點可謂是非黑即白的。
(一)反對的觀點及理由
1.實施措施國與爭議措施的境外目標無法形成足夠強的聯系
Nicolas F.Diebold認為,根據WTO的司法實踐,域外適用效力通常跟域外的產品制造、加工及自然資源獲取的方式(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簡稱PPMs)聯系在一起。如同貨物必須經過生產過程、服務必須經過提供過程一樣,因此,提供服務的方法與提供貨物的方法是可以類比的。但兩者的不同在于,貨物的PPMs通常是發生在國外,而服務的提供則既可能發生在國外,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內,這完全取決于服務的提供模式。在GATS規定的4種服務提供模式——模式一跨境提供、模式二境外消費、模式三商業存在和模式四自然人流動——中,調整模式一和模式二的法律規則很有可能具有域外適用效力。例如,上述與模式二有關的這個例子,A國法律規定公民在B國旅游期間如有召幼妓行為,在其返回A國時將會被認為侵犯了B國的公共秩序而被A國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起訴。相反,在模式三和模式四的方式下,服務都在規制國境內提供,因此,就缺乏了潛在的域外適用效力。而且,Nicolas F.Diebold還認為,域外適用效力的形成必須建立在爭議措施的境外政策目標與實施爭議措施國有足夠密切聯系的基礎上。根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相關規定,該要求有被滿足之可能,因為以不道德的或者對環境有損害的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物理性跨越了國境,如在“美國蝦龜案”中,海龜是遷移的,會游入美國領海。與之相較,在服務的場合則很難找到相同緊密程度的聯系。事實上,模式二下的服務整個在國外提供并消費,與WTO爭端中被告境內發生聯系的只有消費者的住所和國籍,這樣一種聯系,緊密程度明顯不夠。
2.GATS的序言排除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
Nicolas F.Diebold認為,GATS的的序言規定“給予國家政策目標應有的尊重”,為實現國家政策目標,有權采用新的法規,這表明在通常情況下,GATS的例外條款不可能使旨在追求被告境外的政策目標的措施取得合法性,或者只有在存在一種非常強的聯系的情況下,至少其聯系強度要超過根據GATT情況下保護的客體與被告之間的關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15〕同前注〔11〕,Nicolas F.Diebold文,第70-71頁。
3.反對賦予公共秩序例外的鄰近概念公共道德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
Lorand Bartel反對直接賦予公共道德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認為生產者的不道德生產行為在貨物進口到進口國后可以導致消費者的不道德消費行為,因此,以保護本國公共道德的政策目標就可以阻止本國公民消費其他國家以不道德的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進而影響到出口國的公共道德,從而使措施獲得事實上的域外適用效力。〔16〕See Lorand Bartel, Article XX of GATT and the Problem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Case of Trad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3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02, p.353.Jagdish Bhagwati認為,WTO不適于解決這么復雜的問題,如果將貿易權利與勞工權利或者類似權利結合起來的話,制裁效果經常適得其反,那么其作用就像是炮艦外交政策的GATT制裁版,將置落后的國家于不利的地位。〔17〕See Jagdish Bhagwati, Afterword, the Question of Linkage, 96 Am.J.Int’L L., 2002, p.126, 132, 133.Diego J.Linan Nogueras、Claire R.Kelly、Dexter Samida等學者則認為,適用GATT第20(a)條時,允許WTO成員將自己的公共道德概念具有域外適用效力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既然公共道德的概念在不同國家存在差異性,適用這么一個主觀性的概念使其具有域外適用效力將會使整個GATT保證的具有互利商業性質的優勢置于非常危險的境地。〔18〕See Diego J.Linan Nogueras & Luis M.Hinojosa Martinez, Human Rights Conditionality in the External Trad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egal and Legitimacy Problems, 7 Colum.J.Eur.L., 2001, p.307, 328; Claire R.Kelly, Enmeshment as a Theory of Compliance,37 N.Y.U.J.Int’L L.& Pol., 2005, p.303, 328; Dexter Samida, Protecting the Innocent or Protecting Special Interests? Child Labor,Globalization, and the WTO, 33 Denv.J.Int’L.& Pol’Y, 2005, p.411, 426, n.108.
(二)支持的觀點及理由
學者持支持立場的觀點與理由如下。Salman Bal和Steve Charnovitz認為,既然WTO協定中的一般例外有適用于境外的情況,如GATT第20(e)條適用于外國犯人生產的產品的情況,那么公共道德例外也應可延伸而具有域外適用效力。〔19〕See Salman Bal,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Human Rights: Reinterpreting Article XX of the GATT, 10 Minn.J.Global Trade, 2001, p.62, 78; Steve Charnovitz, The Moral Exception in Trade Policy, 38 Va.J.Int’L L., 1998, p.701.Francisco Francioni則認為,如果承認公共道德例外具有域外適用效力的話,那么就應該是徹底的域外適用效力,也就是說,即使貨物生產或服務提供與公共道德無直接關系,只要該出口國或服務提供國的國家行為或國家秩序在進口國或服務接受國看來是不道德的,那么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就對所有原產地是該被認為不道德的國家的產品或服務發生效力。〔20〕See Francisco Francioni,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Free Trade, in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rancesco Francioni ed., 2001, p.1, 19-20.
其實,研析上述觀點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灰度的,在現實的復雜性與學界的認知之間存在需要被填補的鴻溝。
三、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適用效力問題的立法與司法解讀
有關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灰度就在于這個問題在立法層面上并無限制,司法層面上卻體現了對其的約束。
(一)GATS在立法層面并未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
WTO上訴機構于“歐盟荷爾蒙案”中認為:“將一個條約條款識別為例外條款,并不意味對該條款就應該采用嚴格解釋或者縮小解釋。對該條款的解釋仍應慮及上下文的意思和條款的目的按照通常文本意義來進行解釋,換句話說,仍應該按照國際法解釋習慣規則進行解釋。”〔21〕AB Report, EC-Hormone Decision, para.104.對GATS第14條第1款(a)項規定的公共秩序到底是否特指措施實施方的公共秩序,最有說服力的上下文可謂GATS第14條第2款之規定。
GATS第14條第1款(a)項相較于GATS第14條第2款的規定明顯少了特指詞“its”。GATS第14條第2款(a)項規定:“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a)要求任何成員提供其認為如披露則會違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to require any Member to furnish any information, the disclosure of which it considers contrary to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與之相反,GATS第14條第1款(a)項對公共秩序例外的規定是:“為保護公共道德或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措施(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morals or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比對該兩條文可以發現,第14條第1款(a)項少了兩個重要的詞——“it considers”和“its”。其中,特指詞“its”與本文所研究的主題密切相關,該字的缺失顯然不是疏忽所致,因為WTO協定的每一個用語都可以說是協商談判的結果,這表明至少從文本上看,GATS第14條第1款(a)項規定的公共秩序的概念在外延上并沒有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不應該簡單地將概念的外延縮小解釋成被告國家,即采取限制貿易措施的國家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說,不能因為是例外條款就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對概念的外延進行限縮解釋,排除掉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
(二)GATS注釋5和歐盟司法實踐證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
雖然GATS立法并未否定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但是根據GATS第14條第1款(a)項注釋5的規定,“只有在社會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夠嚴重的威脅時,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這表明公共秩序涉及社會某一根本利益,故一般需要效力級別較高的法律允以保護,通常這屬于國內公法范疇,也就是說,屬于國家主權行使之體現,意味著以保護措施實施對象國的公共秩序為名限制貿易似乎有干涉他國主權(尤其是他國內政)之嫌。歐盟和GATT的司法實踐所體現出的對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某種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此種考慮。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2條規定:“為證實由適用第三十一條所得之意義起見,或遇依第三十一條作解釋而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或所獲結果顯屬荒謬或不合理時,為確定其意義起見,得使用解釋之補充資料,包括條約之準備工作及締約之情況在內。”考察GATS原文中對(a)項注釋5的規定,“只有在社會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夠嚴重的威脅時,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該援引條件并非空穴來風,早在1975年歐洲法院關于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案的判決中就已經形成了完全相同的解釋。〔22〕See ECJ, Case 36/75 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 [1975] ECR 01219, para.28.
在1974年發生的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案中,歐洲法院首次對歐共體條約中涉及的公共秩序概念進行了司法解釋,但表現得十分保守,認為“每個歐洲成員有絕對的獨享的權利對本國的公共秩序的概念作出定義。公共秩序是與時空相關的概念,成員有權根據社會的演變而改變其公共秩序概念”。〔23〕Case 41/74, 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 [1974] ECR, 01337 at 01351.在一年后的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案中,歐洲法院的態度出現了迥異,認為“成員國可以自由決定本國公共秩序。但是,需要基于本國公共秩序減損條約項下的平等待遇和工人自由移動等基本權利的保障義務時,該公共秩序應該被嚴格解釋。此時,不存在不受共同體機構控制的成員國的單邊解釋。除非另一個國家國民的存在或者其行為導致對一國的根本利益構成一種真正的、足夠嚴重的損害,該國才可以限制另一國家的國民進入該國境內,停留或自由移動”。〔24〕Case 36/75 Rutili [1975] ECR 1219, p.28.也就是說,歐洲法院在1975年就已經形成了與GATS第14條第1款(a)項注釋5規定相同的限制性條件,即援引公共秩序例外必須要滿足兩個特別的前提條件:一是必須是對一個社會的根本利益的侵害;二是損害必須是真實的、足夠嚴重的。之后,在“MRAX案”和“Gattoussi案”等案件中,歐洲法院均一字不改地重申了該限制性條件。〔25〕Case C-459/99 MRAX [2002] ECR I-6591, p.79; ECJ, Case 97/05 Mohamed Gattoussi v.Stadt Russelsheim (2006),ECR I-11917, para.41; http://csdle.lex.unict.it/Archive/LW/EU%20social%20law/EU%20case-law/Opinions/20110614-014309_Conc_C_97_05enpdf.pdf,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在這些判決中,法院認為基于公共秩序例外實施的具有限制自由貿易效果的成員國措施會潛在地削弱歐盟的結構基礎,因此即使成員國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定義公共秩序的概念,該公共秩序例外對于歐共體條約旨在實現的貿易自由價值所造成的實質影響應該是法院允以嚴格控制的對象。〔26〕Se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World Trade Agreements: Using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HR/PUB/05/5, p.10-11.
鑒于GATS第14條第1款(a)項并未對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作出明定,但是,如上所述其注釋5規定的特殊援引條件源自歐盟的司法實踐的影響,所以若要確定GATS第14條第1款(a)項涉及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則就有必要參考歐盟在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上的司法實踐。
在歐盟的司法實踐中,與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相關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1974年發生的“Dassonville案”。Dassonville將一種名為Scotch的威士忌酒從英國進口到法國,然后從法國再進口到比利時并在比利時境內銷售。比利時主管機關因Dassonville未獲英國海關授權其在比利時境內使用Scotch該特定名稱的許可,違反了英國調整工商業貿易的法,故基于《羅馬條約》第36條規定的公共秩序例外起訴了Dassonville。Dassonville辯稱,比利時的措施具有類似數量限制的效果,違反了該條約第30條之規定。基于雙方的理由,本案的焦點問題其實在于:比利時主管機關具有貿易限制效果的措施能否基于保護英國的公共秩序而獲得合法性。
歐洲法院沒有審查比利時的措施是否與《羅馬條約》第36條規定的例外之一相符,而是采取了一條捷徑,即認為比利時的措施不能根據第36條獲得合法性是因為該措施在歐盟成員國之間形成了武斷的、變相的貿易歧視,因為對直接從英國進口到比利時的酒和從英國轉口法國進口到比利時的酒實施了歧視性待遇。
但是,該案的總法律顧問明顯意識到了爭議措施的域外適用效力這個問題,故認為政府要想根據《羅馬條約》第36條使其爭議措施獲得合法性,就只能是出于保護他們自己的公共秩序的目的,而不能是為了保護其他國家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說,如果是為了保護商業財產的話,那么只能是來源國,如英國,才有權憑借 《羅馬條約》 第36條,而不是進口國,如比利時。為了將其觀點論述得更加透徹,總法律顧問進一步認為,一個政府也不能因為要保護其目的國的公共秩序而限制貨物出口。總的來說,總法律顧問的觀點就是《羅馬條約》第36條只允許每個成員國僅出于保護其自己的國家利益才實施具有貿易限制效果的措施。〔27〕See Case 8/74, Procureur du Roi v.Benoit and Dassonville, 1974 E.C.R.837, 851, 860, 2 C.M.L.R.436 (1974);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oqp=&for=&mat=or&lgrec=en&jge=&td=%3BALL&jur=C%2CT%2CF&num=C-8%252F74&page=1&dates=&pcs=Oor&lg=&pro=&nat=or&cit=none%252CC%252CCJ%252CR%252C2008E%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true%252Cfalse%252Cfalse&language=en&avg=&cid=7948595,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61974CJ0008&from=IT,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
1977年,歐盟委員會的一個決定支持了總法律顧問的觀點。歐盟委員會認為,即使一個成員國禁止以殘忍的方法屠殺禽類,也不能因為這個理由就限制從低標準國家進口被殘酷殺死的禽類。換言之,歐盟委員會認為,對公共秩序的違反只能發生在該殘酷行為的實施地。從歐盟的法律實踐也可看出,基于《羅馬條約》第36條實施的國家行為應該只是出于保護本國的利益,而不能是為了保護其他國家的利益。〔28〕同前注〔19〕,Steve Charnovitz文,第725-727頁。也就是說,歐盟的法律實踐否定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由此也可以推出,即使賦予GATS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也必須要對該效力進行必要的限制。
(三)GATT司法實踐證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
Nicolas F.Diebold認為,基于保護被實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的爭議措施要取得合法性,必須在爭議措施的境外目標與爭議措施實施方之間建立起足夠緊密的聯系。很顯然,這一觀點混淆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與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轄問題。因為這兩者的利益維護對象是不同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是為了保護被實施措施方的利益,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轄則是出于維護措施實施方的本國利益。
在GATT的司法實踐中,雖未有直接與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相關的案件,但被廣泛討論、被認為是與爭議措施的域外適用效力相關的案例則有三個——美墨金槍魚案〔29〕“美墨金槍魚案”的起因是,適用拖網技術在東太平洋熱帶海域捕撈金槍魚時,容易傷害在習性上與金槍魚結伴而游的海豚。按照美國1972年《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的規定,捕撈金槍魚時順帶捕殺的海豚要控制在一定的數量內,否則要允以制裁。1990年美國政府根據法院命令禁止墨西哥的金槍魚及其制品進口,由此引發本案。、美歐金槍魚案〔30〕由于美國禁止金槍魚及其制品進口,涉及“中間國家”金槍魚制品對美的出口,1992年歐共體與荷蘭以同樣的內容提出了起訴,GATT專家組于1994年6月作出裁決報告。和美國蝦龜案〔31〕海龜是一種瀕危物種,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條約》(CITES)將海龜列為最高級別保護物種。漁民在適用拖網魚船捕撈海蝦時會順帶撲殺與海蝦結伴而游的海龜。美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海龜驅趕裝置(TED),為了推廣該裝置,1989年美國在其1973年《瀕危物種法》中增設了609條款,規定凡未能在捕蝦的同時放活海龜者,就禁止該國的海蝦向美國進口。1996年印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泰國聯合指控美國的禁令違反了GATT1994的第1、11、13條。。管轄權基礎是這三個案例的共同關鍵因素。領土原則決定了國家行使管轄權僅限于領土范圍,也就是說,一國無權在其他國家的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行為。〔32〕See L.Oppenheim, I International Law §144a (8th ed.H.Lauterpacht 1955); Stanley J.Marcuss and Eric L.Richard,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United States Trade Law: The Need for a Consistent Theory, 20 Colum.J.Transnat’l L., 1981, p.441-443.1927年常設國際法院在“荷花號”案中對該原則作出了一定的修正,指出管轄權不能由一個國家在其領土之外行使,除非依據來自國際習慣或一項條約的允許性規則。而普遍接受的不存在爭議的域外管轄的國際習慣只是指國家對其域外的國民和懸掛其國旗的船只行使屬人管轄權。〔33〕參見[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1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38頁;The S.S.Lotus, [1927] P.C.I.J., ser.A, No.10, p.150.
在“美墨金槍魚案”中,美國沒有辯稱其要保護的海豚在美國的領水范圍內,而是聲稱海豚在海水里游來游去是不屬于任何一個締約方管轄的全球共享資源,這使該案專家組認為美國無權采取措施實施域外管轄。本案中,美國主張保護其領土之外的在回歸線附近的東太平洋海域的海豚的政策是依據其對美國人和美國船舶的屬人管轄權,對此,專家組認為,美國的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美國蝦龜案”中,美國所爭辯的并不僅限于海龜屬于“全球共享資源”,而是“除了平黑類海龜(只限于澳大利亞周圍水域,并且其不屬于美國609條款設計的種類)外,所有種類的海龜,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或部分時間內都生活在美國管轄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域”。〔34〕朱曉勤:《從GATT/WTO爭端解決實踐看環境保護單邊措施的域外效力問題》,載《國際貿易問題》2004年第2期。對此,上訴機構認為,受保護的海龜與美國建立了充分的聯系,故可將其視為美國管轄范圍內的動物。
由此可見,這三個案例所要求建立的關系都不是爭議措施所保護的對象與爭議措施所適用對象國之間的管轄權聯系,而是與爭議措施實施方之間的管轄權聯系,也就是說,爭議措施必須是為了保護本國具有管轄權的人或物或其他利益標的,而不是為了保護其他國家的利益。實施措施國與措施的境外目標之間的聯系緊密程度決定的并不是GATT例外條款的域外適用效力取得規則,而只是域外管轄權的取得規則,即傳統意義上的效果管轄權的取得規則而已。〔35〕關于效果管轄的一個經典假設性案例就是甲國A國民站在該國領土上槍殺邊境對面的乙國B國民。從此角度我們也可認為,這三個案例間接地否定了對GATT例外條款的域外適用效力。
四、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適用效力的邊界建構
既然一方面GATS文本沒有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另一方面GATS注釋5規定、GATT的司法實踐及歐盟的司法實踐又證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的域外適用效力,那么隨后要解決的問題便演變為如何在賦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的同時允以適當的限制,即其邊界該如何建構?由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是基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負面效果容易造成對他國國家主權的干涉,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排除具有域外適用效力的貿易限制措施的不當性。
根據國際法律責任的一般原理,排除不當性的情況包括同意、對抗與自衛、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以及危難或緊急狀態。〔36〕參見《國家責任條款草案》第五章,A/RES/56/83,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2019年8月10日訪問。可見,措施實施對象國的同意是最有可能排除掉該措施不當性的理由。但是,事后的同意顯然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是事前的同意,而單邊的事前同意也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故此,最有可能排除掉具有貿易限制效果的措施的不當性的理由就是被實施措施方曾經作出的多邊性質的事前同意。換言之,如果被實施措施方與措施實施方在事前已經締結或參加了一項涉及公共秩序的國際條約,那么基于條約的善意履行原則,當一國未履行已經批準的條約義務時,原則上其他國家就有權糾正該國家的錯誤行為,〔37〕See Kyle Bagwell, Petros C.Mavroidis & Rober W.Staiger, It’s a Question of Market Access, 96 Am.J.Int’L L., 2002, p.56,73-74.包括通過實施具有貿易限制效果的措施維護被實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的方式來最終維護國際條約規定的公共秩序價值目標。
具體而言,可考慮允以下述4個條件的限制:一是國際條約必須是涉及公共秩序的;二是措施實施方與被實施措施方都屬于該條約的締約國;三是被實施措施方未履行維護條約規定的公共秩序價值的國際義務;四是措施實施方未從該項貿易限制的措施中直接或間接獲利。
關于第一個條件,國際條約必須是涉及公共秩序的滿足下列三種情況之一。首先,條約中已有明確規定的。試舉一個近似的例子作分析,旨在實現信息社會服務的自由流通的《歐洲電子商務指令》第3條第4款規定:“成員國可以采取措施減損有關信息社會服務方面的指令義務,如果滿足下列條件的話:(a)這些措施必須是(i)基于下列理由所必需的:公共秩序,特別是阻止、調查、偵查和起訴刑事犯罪,包括保護未成年人和反對煽動種族、性別、宗教、國籍歧視和侵犯個人尊嚴的斗爭……”〔38〕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這些羅列的價值就構成了指令參加國的國際公共秩序。該指令序言第(22)條規定:“為了保證對公共利益目標的有效保護,信息社會服務應該由服務提供國實施監管。有必要保證信息服務提供國的主管機關不僅為了本國公民的利益而且為了共同體公民的利益提供這樣的保護……”其次,條約中并未明確規定其目標價值是公共秩序,但是條約締約國的國內法如果將這些目標價值視為公共秩序以國家根本法或以嚴格法律程序進行立法的話,那么也可視條約所保護的目標價值構成國際公共秩序。最后,一些眾所周知的具有國際公共秩序性質傾向的國際條約,如國際勞工組織的童工指南和聯合國滅絕種族罪條約等,這些條約的性質如何可由條約設立的專門組織提供解釋性意見。
關于第二個條件,即措施實施方與被實施措施方同屬于該條約的締約國,這是比較容易被證明的,故而基本上無需作出解釋。
關于第三個條件,即被實施措施方未實施條約規定的國際公共秩序義務應由措施實施方舉證。如果當前與公共秩序有關的國際條約有執行機構的話,那么該執行機構就應該提供一份確認函來確認有義務履行條約義務的國家的履約情況。如果沒有執行機構,那么原則上WTO是沒有權限對該國際條約的規定進行解釋的,于此情形,被指責違反了該國際義務的國家必須違反的是條約中某一條非常清晰明了的無需解釋的規范(或條約義務)才行,否則,任何疑點利益都應該歸于被指責違反國際公共秩序義務的國家。〔39〕See Mark Wu, Free Trad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Morals: An Analysis of the Newly Emerging Public Morals Clause Doctrine, 33 Yale J.Int’l L., 2008, p.244-247.
關于第四個條件,若措施實施方沒有直接或間接從該項貿易限制的措施中獲利,則這個條件的舉證責任必須倒置,即應由被實施措施方提出措施實施方從該項貿易限制的措施中獲利的初步證據,由措施實施方證明其未從該項措施中獲利,若措施實施方不能證明這一點,就推定措施實施方從該項措施中獲利,該措施就不能根據GATS第14條第1款(a)項獲得正當性。如果措施仍然希望獲得正當性,那么就應該考慮WTO協定的其他規定。
簡而言之,如果賦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那么就應該基于這種效力所導致的干涉他國主權的嫌疑,而給予多邊主義的嚴格限制,嚴格限定此種效力的邊界。值得強調的是,如果措施實施國沒有任何協定依據而單邊主義地進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是經典意義上的干涉內政行為,這并非本文的討論范疇。本文由始至終關注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的討論語境不是單邊主義的,而是多邊(涵蓋少邊情形)主義的,是討論在多邊協定未曾明確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時,此種效力能否當然存在,效力的產生需要滿足何種構成要件或者說限制性條件的問題。例如,在GATS語境下,GATS成員對非GATS成員實施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或者反之由非GATS成員對GATS成員實施均是一種典型的單邊主義的域外適用,構成經典意義上的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只有措施實施國與被實施措施對象國均為GATS成員,且如上所述GATS條款并未明文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時,才涉及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邊界問題。
由于任何條約的權利義務都是一個讓步妥協形成的整體,爭端解決機構無權擴大或者縮小解釋,從而改變條約的談判利益格局。而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歐盟的機構,還是WTO爭端解決機構均或是回避這個問題,或是在多邊的語境下簡單套用單邊語境下的邏輯框架,或者只是簡單地給出一個否定觀點卻未作相應的論證,這些都在客觀上改變了談判形成的利益格局,改變了條約主導價值與共同體公共秩序價值之間的邊界線。
任何條約談判達成的共同體公共秩序的內涵和外延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出模糊性,有賴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得以逐步明晰與澄清,這也是一個共同體公共秩序觀的塑造過程。正是在此意義上,被實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措施實施方的公共秩序與條約所確立的共同體公共秩序在概念與外延上應該朝著逐步同一化的方向發展。由條約規定公共秩序例外成為公共秩序的一種憲法性機制,即公共秩序的一種多邊證據,在此種情況下,措施實施方基于維護被實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固然因域外適用效力而有干涉他國主權之嫌,但因多邊條約未明確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作為事前同意的證據,條約中公共秩序概念所蘊含的共同體價值底限的內涵在性質上是一種條約遵守行為,這就同時具備了執行條約中公共秩序義務的正當性。
五、結語
隨著全球范圍內經濟結構的改革和優化,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將逐步取代貨物貿易成為更加重要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力量,同時,政府采購也將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市場。各個國家服務法規發展程度方面存在的不平衡與國際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與各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政府采購協定締約國范圍的擴張與國內生產商及媒體對購買“國貨”呼聲的上漲之間的沖突,都使得公共秩序例外制度成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緩沖地帶”。
應當明確的是,公共秩序例外制度的適用結果既不能導致多邊貿易制度的崩潰或減損,又不能使國家在爭端解決機構的能動司法中被悄然剝奪WTO談判形成的并表現在文本中的權利。這個雙重目的的實現首先要依賴于對公共秩序的合理定位,〔40〕參見陳儒丹:《國家公共秩序還是國際公共秩序》,載《國際經貿探索》2012年第10期。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邊界的合理定位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學界在公共秩序例外及相鄰概念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問題上持有多種學術立場,既有反對意見,也有肯定意見,然而擱置這些非黑即白的立場,從立法和司法兩個層面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的灰度。在立法層面,GATS并未排除公共秩序的域外適用效力;在司法層面,GATS注釋5和歐盟司法實踐證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而且GATT司法實踐也間接證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慮及WTO協定的累加適用關系,GATT司法解釋無疑也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故此,在賦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適用效力的同時允以適當的限制才是對此種灰度的適度回應。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因干涉他國主權之嫌而被詬病為以公共秩序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為了防止此類情況的發生,必須對該公共秩序施以多邊主義的嚴格限制,即需要滿足以下4個條件,國際條約必須是涉及公共秩序的、措施實施方與被實施措施方都屬于該條約締約國、被實施措施方沒有履行維護條約規定的公共秩序價值的國際義務和措施實施方未從該項貿易限制的措施中直接或間接獲利。唯其如此,才能因為被實施措施方曾經作出的多邊性質的事前同意而排除具有域外適用效力的貿易限制措施的不當性。
中國應該支持并向國際社會宣揚并強化這種對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的多邊化或區域化的限制。因為在當前WTO框架體系風雨飄搖之際,單邊貿易保護主義開始盛行,或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或披著經濟制裁的外衣,泛化乃至濫用對公共秩序價值的保護顯然也是政策工具之一,所以對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適用效力施加嚴格限制,從防御的角度看對維護中國利益殊有必要。與此同時,應該對中國的國際角色有一個動態的認知,隨著中國的境外利益權重日益上升,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一個區域公共秩序觀的共識并維護這種共識具有相當的必要性。在此方面,歐盟的經驗已經驗證了這種區域公共秩序觀的形成對于區域發展的重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