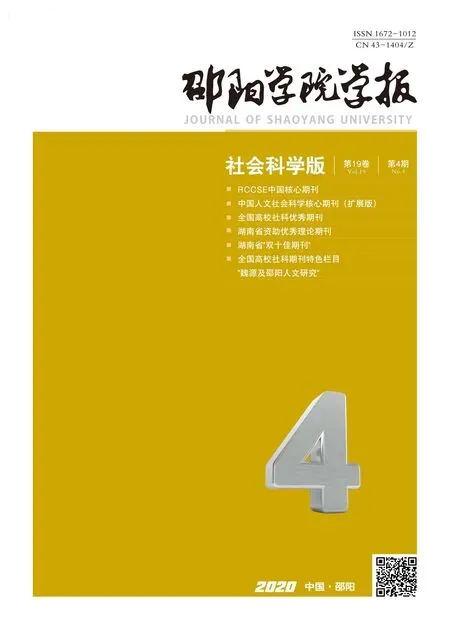程頤宗法思想的治道意涵
姚季冬
(邵陽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南 邵陽 422000)
北宋承殘唐五代之后,禮樂崩壞,秩序紊亂,重建禮樂秩序成為北宋儒者的使命。一個完整的禮樂秩序包含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然而北宋初期君臣著力點多在中央,地方禮樂不興,如蔡襄說:“宋興五十余年……朝廷禮文,罔不修舉。……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樂,專用法。”[1]卷二十二,507上有鑒于此,北宋中期的儒者們開始著力于地方禮樂秩序的建立,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在這一時代浪潮中,作為理學奠基者之一的程頤主動參與進來,提出了自己的宗法思想。學界對程頤宗法思想的具體內容和社會功能都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在研究方式上,或是將程頤宗法思想置于理學宗法思想研究中考察,或是將其作為宗族制度、家族制度研究的一部分展開,或將其置于理學、儒學脈絡中討論。對二程宗法思想進行獨立研究的成果不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1)在程頤宗法思想研究上,大體有兩種進路:一是將其與中國古代宗族制度聯系起來考慮,比較注重社會功能等外在內容。如邱漢生的《宋明理學與宗法思想》(《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62-73頁)即認為程頤將宗法提高到天理高度,這是前代所無的,有力地維護了封建統治。朱瑞熙的《宋代社會研究》(汝南:中州書畫社,1983年)、徐楊杰的《中國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馮爾康的《中國宗族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點,認為除了維護封建統治之外,保護地主階級的世代榮華富貴也是理學宗法思想的重要內容。國外學者不太使用“封建統治”之類的詞匯,因而其基本結論稍有不同,如日本學者井上徹的《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義角度所作的分析》(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則圍繞科舉官僚制展開討論,認為官僚身份世襲化是理學家主張宗法的目的。無論傾向如何,學者們在理學“宗法思想是服務于親族結合的觀念”這一點上取得了基本共識。另一種進路是從禮學的角度展開研究,比較注重程頤宗法思想的內涵。在具體研究中,有將其置于理學、儒學脈絡中研究的,如吳飛的《祭及高祖:宋代理學家論大夫士廟數》(《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4期,第28-38頁),林鵠的《宗法、喪服與廟制:儒家早期經典與宋儒的宗族理論》(《社會》,2015年第1期,第49-73頁)。有單獨研究二程禮學的,如王啟發的《程顥、程頤的禮學思想述論》(陳義初主編,《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9-154頁)、殷慧的《二程禮教思想的形成與沖突》(陳義初主編,《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4-204頁)等。上述兩類研究構成了二程宗法思想研究的主要內容,對本文有重要意義。除上述禮學進路的研究外,對二程宗法思想進行獨立研究的成果中,潘富恩、徐余慶在《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61-377頁)中的研究較有代表性。潘、徐兩位將二程的“齊家之道”歸納為四點:以法度齊家,嚴長幼尊卑之義、男女之別;樹立家長的絕對權威;治家必須從嚴;家長要言行身教。并對程頤復宗子制的思想做了梳理。二位先生主要是依據相關資料梳理二程的治家思想,但尚未對二程宗法思想的內核進行進一步挖掘。。對程頤宗法思想做治理層面的考察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程頤學術的落腳點和歸宿,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理學治理層面的含義。
本文將首先從地方禮樂秩序重建的角度對北宋地方治理思想做一概覽,以確定程頤地方治理思想的歷史語境;其次會對程頤宗法思想的主要特點進行分析,以確定程頤宗族治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最后會討論程頤宗族治理與天下治理的關系,指出程頤實質上將宗族治理定位為朝廷治理必要的補充。
一、北宋中期地方治理思想概覽
在正式討論程頤宗族治理思想之前有必要對其背景做一個簡單介紹,以明確討論的背景和語境。綜合考察,北宋中期對地方禮樂秩序重建的思考與實踐大體有三類:第一類是由政府來主持地方禮樂秩序的建設,其基本思路是將地方禮樂秩序視為政治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強調以政治的手段來建設社會秩序,在穩定的社會秩序基礎上,再追求禮樂秩序的建設。但正如趙秀玲指出的,在北宋的鄉里制度的實行過程中,負責具體基層工作的里正、耆長等職權和地位日益萎縮,在地方上能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小,基層治理也就愈發混亂。雖然有一些地方官提倡禮樂教化,但實際上禮樂秩序的建設根本無從談起[2]25-32。北宋政府試圖通過政治手段來建立地方禮樂秩序的效果并不好,歐陽修形象地描述為:“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強于一伙,天下禍患,豈不可憂?”[3]1159有鑒于此,王安石提出將保甲法作為地方政治、社會秩序建設的手段,但這離禮樂秩序愈行愈遠了。
成長于“文治”環境中的慶歷儒者試圖通過宗族治理來建立基層禮樂秩序,從而在地方上實現禮樂秩序的重建,是為第二類。其中提倡力度最大、影響最大者為范仲淹的義莊建設、歐陽修和蘇洵的族譜建設。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出于“敬宗收族”的動機購買義田、創設義莊,并訂立十三條義莊規矩作為保障。治平元年(1064)應范純仁的請求,范氏義莊得到朝廷的承認,其規矩有法律作為保障。范氏后人的努力使得范氏義莊不斷發展,成為宗族治理的典范。范氏義莊的社會功能是“通過義莊的濟貧措施,來達到儒家安定社會的理想”[4]192,即通過宗族治理來實現社會治理。大約與范氏義莊同時,皇祐至和年間(1049—1056)歐陽修和蘇洵先后進行了修族譜的活動,并希望能將此行為推行天下。歐陽修、蘇洵倡導族譜是希望達到“尊尊親親”的目的。實踐中,族譜和義莊互為補充,二者的結合成為宗族治理的典范(2)請參看王善軍:《宋代譜牒的興盛及其時代特征》(《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第124-128頁)。義莊與族譜這兩種方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可以說義莊是宗族的物質基礎,族譜是宗族的精神內核。范仲淹在《續家譜序》中說:“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后來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補編》,《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31-732頁)可見是先有族譜,方有義莊,義莊所服務的人群是以族譜的記載為準的。。
在政治手段和宗族治理之外,第三種建設地方禮樂秩序的思路是鄉約,在北宋以藍田呂氏鄉約為代表。鄉約與族譜、義莊等宗族治理類似,都希望通過基層的禮樂教化來建設地方禮樂秩序。但在治理對象的涵蓋范圍上,宗族治理僅限于宗族內部,鄉約則超出宗族之外,以實際的聚居規模(鄉、村)來確定地方治理的范圍。正是這種超出血緣關系的嘗試,藍田呂氏鄉約被稱作中國歷史上“一個破天荒的舉動”[5]27。但鄉約在北宋產生的影響其實不大,因而它對地方禮樂秩序的重建貢獻不大。
由于范仲淹、歐陽修等慶歷儒者在士林中的崇高聲望和義莊、族譜卓有成效的典范效應,北宋地方禮樂秩序重建的主流開始向宗族治理方向靠攏。程頤建設地方禮樂秩序的思路也大體延續了范仲淹、歐陽修、蘇洵的做法,同時又表現出自己的特點。
二、程頤宗族治理思想的特點
程頤屬于上述三類建設地方禮樂秩序思路中的第二類,這首先與他的家族背景、生活經歷有關。程氏一族頗有厚待族人的傳統,程頤之父程珦堪為典范[6]273-311。據程頤在《先太公家傳》的記載:
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等朝省,二十余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婚宦。……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瞻親戚之貧者。[7]650-651
程珦所作所為皆合義莊精神。程頤之母亦如此:“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孤幼,夫人存視,常均己子。”[7]653程頤在這種家庭中成長,必然受到影響,如尹焞說他“贍給內外親族八十余口”[7]346。雖然現存資料顯示程氏家族從未有過義莊行為,但這應該是出于條件的限制,而不是反對義莊(3)據李學如研究,義莊的實踐需要豐厚的財力支撐,因而義莊在北宋僅12例(李學如:《宋代宗族義莊述論》,《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6期,第40-45頁)。無論是程珦還是程顥、程頤都未曾顯達,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這種行為。如程頤在《家世舊事》中的記載:程羽為醴泉縣令時曾購買產物,以待久居。后程羽留居京師,但產物多在醴泉。程珦的四叔程逢堯留居醴泉(今陜西禮泉),其后人保管不善,“散失盡矣”,程頤也只能“思之痛傷”,無法贖回(見《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57-658頁)。。相比于義莊,程頤在宗族治理上更重視宗子法。
(一)立“宗子法”:宗族治理的制度構想
程頤曾簡短地回顧宗族制度的發展歷史說:
宗子法廢,后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7]162(4)此條又見《經學理窟·宗法》(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89頁)。《經學理窟》一般歸于張載,但張岱年先生在為《張載集》所作的序中指出,《經學理窟》“當是張載程頤語錄的類編”(《關于張載的思想和著作》,《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5頁),可見其中具體條目的歸屬仍當繼續考證。林鵠認為此條應屬程頤(《〈經學理窟·宗法〉與程頤語錄》,《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2期,第64-71頁)。我們雖不必持如此強的立場,但筆者以為程頤至少可以贊同此條的觀點。下引程頤論“管攝天下人心”“立宗子法,亦是天理”等條亦見于《經學理窟·宗法》,并做如是觀。
宗子法指西周式的封建宗法制度,譜牒指魏晉時用以作為選官和婚配依據的譜牒制度。程頤認為北宋社會“雖至親,恩亦薄”的局面正是宗法、譜牒皆廢的后果,因而相應的辦法就是恢復譜牒和宗子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7]85(5)在已確定的材料中,程顥未言及譜牒,而程頤屢言譜牒與宗子法,故程頤至少可贊同此條內容。另,本文引用《河南程氏遺書》中的內容時,如屬未明確表明歸屬的語句統一在引文前加“*”號,判定其屬于程頤的理由在腳注中表明。
雖然程頤確實勾勒了一個“宗子法行—宗子法廢—譜牒行—譜牒廢”的過程,并暗示了這是一個不斷倒退的過程。但他講的“明譜系世族”和“立宗子法”不能簡單地看作西周封建宗法和魏晉譜牒制度的復歸,而是他根據北宋實際情況所設想的兩種宗族制度:族譜制度與修改后的“宗子法”。對于族譜的作用,程頤并不否認,但其重視程度顯然不如歐陽修、蘇洵等人,這或許與他的家世背景有關。程珦在其自撰墓志中說:“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7]645可見程氏的族譜保存得較好。但這對“敬宗收族”似無太大的正面作用,程氏族人間亦多有不睦(6)就程頤自身來說,族人不睦之事多,舉其著者如先有族翁程逢堯為了族產猜忌其父程珦;后有族侄程公孫因利出賣,導致他編管涪州(前事見《家世舊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57頁;后事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61頁),這難免影響他對族譜之于“敬宗收族”的意義的判斷。。程頤認為能真正建立起宗族禮樂秩序的是“宗子法”,而不是代表小宗法的族譜、譜牒,這是他與歐陽修、蘇洵不同的地方。程頤認為小宗法會導致“親盡則族散”的后果,并非好辦法: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后祭其父。[7]180
需要注意的是,“親盡則族散”并非無的放矢。歐陽修、蘇洵編制族譜雖依循小宗法,只收五服之內的族人,但他們也都留下了合小宗譜為大宗譜的空間,即各房子孫各編其譜,待時機合適合編,即可為大宗譜。蘇洵還制作了《大宗譜法》作為范例。可見,小宗法實質上是從現實角度考慮的權宜之計,并非最終理想。而他們之所以采取權宜之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情見乎親,親見乎服,服始則哀,而至于緦麻,而至于五服”,即五服之外情盡服除,相視如途人,此為勢所必至(7)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蘇氏族譜》,《嘉祐集箋注》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頁,引文在第373頁。歐陽修以“斷自可見之世”為原則制作族譜,與蘇洵的理由實質是一致的,這代表了慶歷時期儒者的典型看法。。正是在這個地方,程頤和歐陽修、蘇洵產生了差別:五服之外皆如途人固是現實情況,但是面對這一現實情況,是認可五服之外的族人相視如途人的現實,還是改變這一情況呢?程頤選擇了后者,他推薦的辦法即大宗法。
程頤認為實行大宗法是天理內在的要求: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干,(原注: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7]242
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于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7]241
程頤將大宗法提高到天理的高度,認為大宗法是“自然之勢”。因此人要祭祀祖先,這是人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地方,應該得到踐行。從實踐上考慮,程頤大宗法的構想似不合實際(8)如茅星來在注《近思錄》的時候引用沈磊的說法,認為程頤大宗法并不能行于后世(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17頁)。朱瑞熙亦指出北宋一般只能實行小宗之法,即“五世而遷”之宗,程頤的大宗法近乎空談(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汝南:中州書畫社,1983年,第99-101頁)。,但若認為程頤僅是出于崇古的信念而推崇大宗法,似亦不合實際。其實,程頤的大宗法拋棄了西周式封建宗法的具體形式而保留了其精神,程頤想恢復的是同一祖先的族人之間的“親親”之情。為此,他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制度設計。
首先程頤重新定義了宗子: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而已。[7]179
程頤認為宗子主要是主持祭祀,這與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宗子是完全不同的(9)徐楊杰在《中國家族制度史》中把西周宗子的地位和作用概括為五點:占據統治地位,主持祭祀和占卜的權利,團聚家族、管理家族事物的責任,庇護家族的義務,處分家族成員的權利,統率家族武裝的職責(《中國家族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3-87頁)。可以看出,程頤對宗子的定義已經遠離了西周式的宗子。。程頤所以如此,是希望能說服“無百年之家”的后世中“至親恩薄”的人。程頤認為爭財奪利是“至親恩薄”的根本原因:“后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7]177在最根本的意義上,程頤強調宗子最好不和族人發生具體的利益糾葛,而主要負責主持祭祀,這樣人們接受起來便容易得多。為了說服世人,程頤甚至不要求祭祀的時候人人到場: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于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7]165
程頤認為在祭祀時支子“致其誠意”即可,而誠意的表達形式非常人性化:條件允許,支子從旁參與祭祀;條件不允許,支子則以物助祭,本人不必親自到場。唯一的強制要求是支子不可別立一廟去行祭祀之事。這是符合實際的考慮。正因如此,程頤強調“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7]179。所謂“收族”并不是要恢復西周封建宗法,只是別親疏、序昭穆、祭祀相及而已。
祭祀必定要有場所,因此程頤又特別強調家廟的作用,認為“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于此而祭祀也”[7]242。家廟就是實行祭祀的場所,每個宗族都應有廟:“家必有廟,廟中異位,廟必有主。”[7]241在家廟中的祭祀分為月薪之祭、四時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襧。至于家廟的具體數目,程頤認為并不是非常重要:“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7]167程頤對家廟和祭祀的相關論述在當時是較為激進的,對后世亦產生較大影響,成為比后民間宗族最重要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10)如常建華在《中國宗族社會》里面說家廟與祭祖制度是程頤宗法思想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方面(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應該說,程頤在宗族治理方面所提出來的大宗法、宗子法雖然在名稱上與西周封建宗法相似,但內容上有極大差異,不應將二者等同,更應將其看作北宋儒者為重建宗族秩序所做的努力之一。除了強調宗子法外,程頤宗法思想另一大特點是對修身和禮法的強調,實質是對“禮”和“理”的強調。
(二)修身與禮法:宗族治理的兩個核心
由于主張大宗法,程頤的“家法”涵蓋了同族所有成員,這是其特點之一: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兇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會不相見,情不相接爾。(11)《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二程集》,第7頁。龐萬里先生說凡祭祀與立宗子法都是“程頤的專門研究領域”(龐萬里:《二程哲學體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4頁)。程顥有對禘、袷的論述,雖然極少,但不能說沒有(如《遺書》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3頁)。至于宗子法,程顥確實無一言論及,故凡論宗子法的內容皆可視為程頤語。
程頤認為家法應該讓族人“骨肉之意常相通”,此即“收族”之意,這是溫情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嚴格的法度。其宗族治理思想的核心就在于“確立親族內符合道德的人倫秩序”[8]。
程頤認為家人之道是:“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7]884所謂“倫”實質就是“理”[7]182,就是“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禮”,如程頤在解釋《履》卦時說:“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7]749程頤希望通過嚴格的禮儀制度來實現宗族治理,讓族人相親相愛,從而建立良好的宗族禮樂秩序。換言之,在程頤看來,宗法本質上是“禮”(“理”)在宗族里的流行,其實質是上下尊卑有序的人倫,其表現形式為各種各樣的宗族禮儀規范,其效用是收族。可以說,宗法之中,上下尊卑之序是體,收族是用,而禮儀規范則是“體”的具體體現和實現“用”的必經之路。在這個意義上,程頤“立宗子法”實質上就是要求人們通過“禮”來治理宗族。程頤認為,若不能嚴格踐行禮儀規范,家道只是空談。程頤在解釋《家人》卦時一再強調:
治家者,治乎眾人也,茍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7]885
蓋嚴謹之過,雖于人情不能無傷,然茍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7]886
以嚴謹為本,以法度為尚,不毫無限度地顧及人情,這就是“正倫”,“理”自然在其中(12)這里遵從呂祖謙的說法:“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里已在矣。”(呂祖謙撰,呂祖儉錄、呂喬年編:《麗澤論說集錄》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24頁下)。所謂“法度”就是具體的宗族禮儀規范,若不能嚴謹地實行法度,不僅無法“正倫理”,而且無法“篤恩義”,所期待的收族效果自然就實現不了。程頤為了“正倫”曾煞費苦心地試圖制作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即使中間因被召入朝而中斷,也不曾放棄(13)《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240頁。為了避免枝蔓,有關程頤所制定的禮儀細節在此不多討論。大體情況可以參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中所收的各篇文章。亦請參看殷慧:《二程禮教思想的形成與沖突》(陳義初主編:《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4-204頁)。。
程頤認為要想“正倫理”,除了崇尚禮儀規范外,治家之人必須首先做到身正:“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7]888正身必須保有至誠之心:“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人自化為善。”[7]888至誠之心是正身之本,也成為“正倫理”的根本。于是修身便成為治家之人的義務和責任,也成為家道實現的根本,這可以看出理學家的特色。程頤說:
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7]888
一方面程頤認為家人相處不患不親,患在無禮法將親情限制在適度(中)的范圍之內,因此宗族治理應以禮為核心;另一方面程頤也強調了正身在宗族治理中的重要性,長輩失去尊嚴,晚輩忘記恭順,家道必亡。因此宗族治理必須以正身為本。程頤說:“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7]888威嚴即禮法之嚴謹,有孚即族人親親之誠心,有誠心方為正身,正身方可行家法。可以看出,在歐陽修那里只是略微提及的“尊尊親親”在程頤這里得到了理學式的發揮,威嚴以尊,其形為禮,其實為理;有孚以親,其本在誠,其體為理。誠以行禮,禮以固誠,二者又歸于天理。說到底,行家法去治理宗族,根本在于踐行天理(禮)。這樣慶歷一代儒者所冀求的宗族禮樂秩序就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不止停留在禮樂儀式和心理情感上,更得到了形而上的支撐和心性的保證。程頤宗族治理思想中鮮明的理學特色集中展現在這里。
總之,程頤宗族治理思想以恢復封建宗法精神的“宗子法”為制度依托,為此他進行了家禮的制作工作;在具體治理方法上,程頤強調正身以行家法,以正身為本,以家法的嚴格法度為核心,希望達到“正倫理,篤恩義”的目的。本質上是追求天理在宗族領域的流行。這是程頤宗法思想的理學特色所在。從治理的角度看,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宗族治理和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以及宗族治理和朝廷(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
三、地方治理與天下治理
程頤希望通過以禮為核心的宗子法來實現宗族治理,進而恢復社會秩序,那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第一,宗族治理作為基層治理的一種方式,它如何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秩序的恢復?第二,宗族治理作為一種宗族自治方式,它與天下治理(以朝廷為主)是什么關系?程頤認為宗族秩序的實現可以成就人才,進而化俗成禮,這是宗族治理對社會秩序恢復的積極意義,也是宗族治理對天下治理的貢獻。在此基礎上,程頤進一步強調,宗族治理本質上是一種自治,對于整個天下來說,它是朝廷治理獨立的、有必要的補充。
(一)化俗成禮與成就人才:宗法的現實意義
程頤認為得人是實現天下大治的必要條件,而人才不僅出于天性,更出于教化。在教化人才中,最重要的就是禮。圣人制作的“禮”對民眾有規范作用:
禮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節文之耳。[7]327
依李曉春的說法,程頤有一種“性體情用”的立場,即情是性接物之后所產生的,是性的發用。因為發用的不同,情有正有不正[9]183-188。出于人情的禮通過具體的禮儀制度來規范人的行為,從而規范人情,讓情的發用“正”,合乎人性,合乎天理。程頤認為禮儀制度的這種規范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有益的:“人欲之無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7]1006好的禮儀制度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成才,而人才的成就又可以促進禮儀制度的適時演進,人才成就與化俗成禮是一體兩面的。這正是程頤禮學思想的核心[10]194-204。因此需要恢復古禮的精神,制定出適時的禮儀。宗族禮儀制度當然只是整個禮儀制度的一個部分,但這是最基本的部分。畢竟,對個體而言,能為官的總是少數,多數仍屬于民;且為官者亦必有家,家為國之本。這樣個體大多數時候都生活在宗族的領域內,由此可見宗族治理的重要性。
就宗族內部來說,強調禮法的宗族治理可以收到成就人才的作用。程頤認為,一方面適時的禮儀可以讓人熏染,漸知禮義,如其自陳作“六禮”的目的:“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7]241另一方面也可以培養人的德性,成就人才。如其論祭祀,在所有宗族禮義中祭禮最為重要,程頤認為由宗子主持的家廟祭祀可以讓族人不生惰慢之心,“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7]165。人才的培養不僅在品德方面,其實也在才能方面。鄧小南在概括北宋士人心目中的“家法”的時候說:“士人之家的‘家法’,也并非僅僅行用于私家內室的原則。以敬奉祖宗的虔誠去對待國家事業,推治家之法意臨民,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理想狀態。”[11]62這個論斷對于程頤來說同樣適用。
宗族治理的意義還不止于宗族本身,它也是社會禮樂秩序的基礎,即化俗成禮。程頤認為宗子法可以讓人“順從而不亂”:
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后順從而不亂也。[7]242
宗子法能使人各有所統,各有上下尊卑之分,如此才能“順從而不亂”。這既是人才的成就,人人皆順其本分而行;也是風俗的改善,天下不亂。這里體現的價值觀,正如王啟發所說:“二程所看重的價值觀,確實有著維系親情,保障家族生活和社會秩序的意義。”[12]119-154可以說,程頤宗法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基層治理思想,他希望從社會基層(宗族)來讓上下尊卑之分定下來,保持基層的穩定,恢復基層的秩序,從而推至天下,恢復社會秩序。
(二)必要的補充:宗族治理在天下治理中的定位
程頤認為宗法制度有“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的作用,這體現了宗法、宗族參與天下治理的作用。然而在傳統政治思想中“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已經遠遠超出了宗族(民)的職責范圍,它是官的責任,是皇帝的責任。制禮作樂更是天子的職責,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宋代士大夫政治主體意識高揚,以天下為己任,故其希望在地方制作禮樂,程頤也是承其風而然。但士大夫制作禮樂與朝廷制作禮樂之間的矛盾是切實存在的:士大夫制作禮樂是否侵犯了朝廷的權威?這一問題是極嚴肅的,藍田呂氏鄉約引起的爭議體現了這一點。
呂大鈞推行鄉約始于熙寧九年(1076),至元豐五年(1082)呂大鈞去世為止,約五年半的時間[13]。藍田呂氏推行鄉約的目的同樣在于重建地方禮樂秩序,只是它超出了宗族的界限,處在“家”與“國”之間,屬于“士紳領導、民眾參與的一種民間組織”[14]18。因此呂氏鄉約曾引起廣泛的爭議,各種質疑中最嚴重的是:呂氏鄉約的實踐有地方士大夫與朝廷爭奪地方權力的嫌疑(14)鄉約引起的質疑實質上是超出血緣界限的地方權力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楊建宏認為“建立在鄉約基礎上的地方士紳權力場域觸動了以皇帝為首的國家權力場域”,因此它一出現就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楊建宏:《〈呂氏鄉約〉與宋代民間社會控制》,《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第126-129頁)。在這里,血緣界限是非常重要的邊界。。程頤與藍田呂氏往來密切,曾在元豐三年(1080)入關親見鄉約推行的情況。雖然在今存的各種資料中找不到程頤對鄉約的評價,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測程頤對鄉約這種處于“家”“國”之間的地方治理方式的看法。《遺書》卷十記有兩條: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7]114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于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7]115
程頤曾稱贊張載“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7]23,可見他是贊成張載禮教的。但從這兩條記載看,他對“關中”諸人的做法似不以為然。此時為熙寧十年(1077),呂大鈞已于上年開始推行鄉約,從“用禮漸成俗”“先自和叔有力焉”等來看,程、張所論或即指鄉約。從語氣上看,程頤對這種立足于“鄉”來建設良好社會秩序的做法似乎并不贊成。而且,程頤曾與呂大忠在書信中討論過如何面對現實法令與價值理想的沖突的問題,他說:
既為今日官,當于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茍遷就于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為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于法,眾亦不甚駭。[7]605
程頤認為儒者求有為之事當在給定的現實環境中積極發揮,務求合于義理,不必再另起爐灶。依此態度推測,程頤對鄉約似不會持贊同態度。
就治理思想而言,程頤與北宋大多數儒者一樣,關注點始終在朝廷,而不在地方(15)包弼德說:“第一代理學家和11世紀的其他思想家都是政治思想家,這是因為他們主張改變政府對社會運作方式是學術的目的。與之相反,在南宋興起的理學,則主張應該減少對社會的干預,而地方士人應該自發地采取更多的行動。”(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6-237頁)這是一個非常有洞見的觀察,程頤之所以對鄉約不敢興趣,或許正在于他的目光仍集中在政府(朝廷)身上,他對宗法的強調,也與此息息相關。。他對宗族治理的強調是在天下治理的框架下進行的。程頤認為宗法治理本質上只是朝廷治理的一個補充。
程頤在解釋《堯典》的時候強調唐堯治理天下的次序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這是《大學》修齊治平思想的反映。程頤認為,修身是治理的根本,但在實際治理活動中,齊家則是第一步:“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7]1035齊家不僅是第一步,而且直指天下大治的根本,即得民心:
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7]929
程頤認為立宗廟是得民心的諸種舉措中至大者,這就點明了宗法對朝廷治理的第一重意義:對王者而言,宗族治理實質就是朝廷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王者之治的起點所在。更重要的是,聯系到上一節討論的齊家之道中修身和禮法的關系,可以說在“修身—齊家—治國”的連貫過程中,宗族治理是修身和治國的中介環節——當然這是邏輯上的中介,而不是實踐中的。實踐中,修身、齊家、治國應是同時發生的。這樣,先秦儒家所強調的修齊治平思想在北宋得到了更為明確的闡發。
在北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程頤亦未忽略掉朝廷治理的另一主體——大臣。程頤認為世臣之有無與宗子法之廢立息息相關: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7]242
所謂“世臣”是指“累世修德之舊臣”(16)此為孫奭疏《孟子·梁惠王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一句中的“世臣”所說。北宋世臣出于故家,即不斷通過科舉等正規方式為朝廷提供賢能大臣的家族。因此很難說程頤宗法制度向往的是復辟門閥制度(王雪枝、仇海平:《宋代故家在北宋的發展軌跡及世臣的作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9期,第12-17頁)。,即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臣。世臣對朝廷治理能起到什么作用?張載說得很清楚:“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15]259張載這里說的其實就是宗法在化俗成禮和成就人才方面的作用,只不過重點放到了公卿上面。公卿們良好的宗族治理可以“立忠義”:一方面在宗族內部培養起忠義的氣節,從而錘煉人才;另一方面在社會上起到模范效應,帶動大夫、士、庶人的仿效(17)參見李靜:《論北宋的平民化宗法思潮》,《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80-85頁。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實踐次序而言,程頤的關注點并不在“平民”(無官身者),而是在王者與大臣身上,希望通過“巨公之家”的試行造成模范效應。但在理論上,程頤宗法思想確實有平民化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公卿的宗族治理和王者的宗族治理一樣,都是朝廷治理的內在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王者和大臣宗族治理之所以是朝廷治理的組成部分,這不是因為朝廷治理在本質上包含了宗族治理,而是因為王者和大臣天然地帶有了“官”的性質。如果拋開王者和大臣的身份性質來看,宗族治理和朝廷治理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治理方式。程頤自覺地把宗法限定在“家”的領域之內,如他曾因“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7]239而中止制作六禮的行為。這里的“私”指的是家、宗族,“公”指的是國、朝廷。程頤在宗族治理和朝廷治理之間劃了一條公私界限,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將宗法限定在“家”的范圍之內,從而將宗族治理定位為天下治理的補充。這樣可以避免出現藍天呂氏鄉約那樣的與朝廷“奪權”的境況。另一方面,程頤為宗族治理保留了自身的獨立性,也正是因為保留了宗族治理的獨立性,宗族治理才能成為朝廷治理的補充。
這種公私的劃分還有更深刻的意義,它首先是對北宋族權和政權復雜關系的反映。北宋時期,一方面族權和政權有分離的趨勢(18)參見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頁。需要指出的是,所謂族權與政權的分離是相對于漢唐時期世族制下族權和政權的緊密互動而言的,并不是說族權不再和政權發生關系。,另一方面北宋宗族建設主要由士大夫推動,士大夫們在進行宗族建設的過程中自覺地維護王朝統治,族權和政權以新的方式緊密關聯(19)北宋宗族組織對維護統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的發揮往往是從宗族自發開始的,由下而上的。關于北宋宗族組織的社會作用,請參看王善軍:《宋代宗族制度的社會職能及其對階級關系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第15-21頁);申小紅:《略論宋代的宗族自治》(《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第70-72頁)。。程頤對宗族治理在天下治理中的定位實質上就是族權和政權既相對分離又緊密相關的社會現象的理論反映。而當程頤將宗族治理定位成天下治理必要的補充之后,鑒于他作為理學奠基者之一的地位,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對后世產生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世宗族組織和國家政權關系的發展。此外,宗族治理獨立性的保留,也為士人保留了某種獨立和自由的空間,為士人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保留了空間——畢竟,無論何時何地,有人必有家,有家必有族。也就是說,宗族治理無關身份,是一定可以實行的。于是,當士人面對出仕的困境退下來之后,他便可以退回到家庭領域中來,一方面修身以俟時,一方面也參與家族治理,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在這個意義上,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出處原則得到了拓展:士人“窮”不再止于獨善其身,而可以齊家。士人活動的空間便被拓展了——學術向實踐轉化的空間得到了擴充。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北宋以后,士人在無法出仕的情況下往往選擇退回宗族去實踐自己所學,在宗族中構建起禮樂秩序,從而承擔起自己的使命(20)參見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6-215頁。從更宏大的視野來看,士人的選擇除了宗族之外還有書院、鄉約等。但在諸種選擇中,宗族是最根本的、所需條件最少的。。他們能這么做的原因在于,理學為“退”做出了理論上的證明——程頤的宗法思想恰恰是一個源頭。
綜上,在北宋中期恢復社會秩序的各種努力中,程頤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以禮作為核心,希望通過恢復宗子法和家廟制度來實現宗族治理。宗族治理在實質上是社會的基層治理,宗族治理的卓有成效就意味著社會治理的成功,社會秩序的恢復。程頤進一步討論了宗族治理和天下治理的關系,他認為宗族治理能起到化俗成禮、成就人才的作用,但宗族治理在整個天下的治理中只是朝廷治理的補充。當然我們應該同時看到,宗法對于天下的良好治理來說是一個有必要的補充,它的獨立地位并不因為朝廷的存在而消失,只不過應該嚴格區分宗法權力與朝廷權力的界限。我們可以說,程頤對宗法制度參與天下治理的思考體現出一種“共治”的思想:朝廷與宗族共同治理天下,政治與宗法共同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