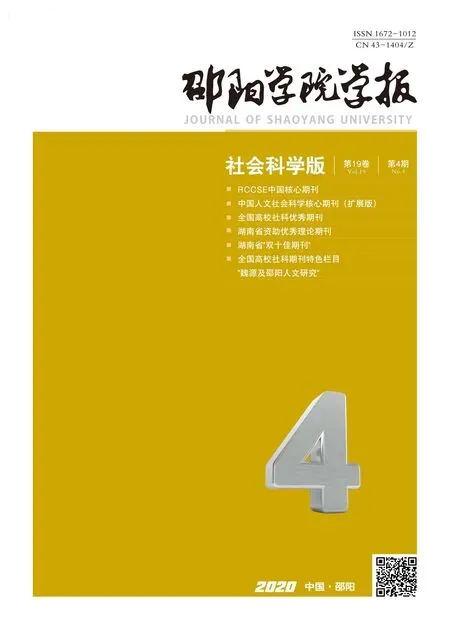論馬克思財產觀對洛克財產應得觀的超越
賀慧星, 向漢慶
(1.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2. 湖南工業(yè)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南 株洲 421007)
財產應得是人類幾千年發(fā)展始終關注的話題,也是近代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發(fā)展中無法回避的重要一環(huán)。對財產應得的不同態(tài)度決定了不同的邏輯進路,形成不同的財產應得觀。在各種可能的財產應得觀中,自由主義財產應得觀有其自身特色,占據(jù)了很大的市場,代表人物洛克認為財產是自然的延續(xù),在人從自然人向社會人轉變之前就已存在,因而僅需遵循自然法的原則給予其法律和社會地位上的確認即可。他在政治實踐中關注財產權與個體自由,認為只有建立絕對的自然財產應得體系才能克服社會生活中呈現(xiàn)的種種不自由,然而他在主體間的分配問題上陷入了泥潭,無法對社會的公平問題作出相應的回答。馬克思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提出以勞動為核心的財產應得觀。筆者認為,只有深刻理解馬克思關于財產來源的勞動本質的相關論述,才能真正在財產的自然應得和契約應得之外開辟一條正確的道路。
一、洛克財產應得觀的理論邏輯
作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洛克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政治思想、政治實踐以及對這些理論和實踐所做的理論辯護已經在其系列著作中得以呈現(xiàn)。其財產觀以及圍繞財產應得而表達的對自由的追求解決了菲爾麥財產所有權理論存在的不足,成為自由主義譜系的一大亮點。總的來說,洛克的財產應得觀從自然人格出發(fā),包括四個核心理念:(1)人從其自然性上看天然地具有人格以及基于這種人格的勞動能力,因而人是自由的。(2)勞動能力是財產應得的根本。只要個體運用自己的腦力、體力使得自然存在物對象化而脫離原有的自然狀態(tài),則該對象化的自然物即為該主體的應得財產。(3)財產權是人基本的自然權利,而不需要經過他人認可即可呈現(xiàn)其社會性。(4)有限政府的產生必要性和價值在于保護個體的應得財產,且政府的職權“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1]86。這四個核心理念集中詮釋了洛克的財產觀。其中,財產的自然性是基本屬性和原則,財產的所有權是整個財產應得觀的主體內容。要弄清上述四個核心理念在洛克財產應得思想體系中的邏輯關系,首先要把握貫穿于其中的“自由”這一主線。
在洛克的政治哲學體系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他對自由的闡述。總體來看,他的自由理念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狹義上看,洛克將自由當作一項與生命、財產等同一維度的具體權利。廣義上看,洛克的從自然理性出發(fā)闡述生命權、財產權、有限政府的正當性等理論旨在保障人的主體性,實現(xiàn)個體的自由。他論述財產應得也是以自然人的自由狀態(tài)為邏輯起點,以社會人的財產自由為主線,最終達到自由具體與抽象的統(tǒng)一。
當然,關于財產應得及其主線的具體闡述,洛克并非閉門造車,而是在其與菲爾麥的論戰(zhàn)中實現(xiàn)的。在洛克看來,菲爾麥父權制理念下的國王自然權力不過是上帝創(chuàng)世說或君權神授的高級形式,其專制理念彰顯無遺。菲爾麥利用基督教神學的教義闡述君權是神授的,君主享有財產的所有權。“人類不是生而自由的,因此不能有選擇他們的統(tǒng)治者或政府形式的自由;君主的權力是絕對的,而且是神授的,奴隸絕不能享有立約或同意的權利;從前的亞當是一個專制君主,其后的一切君主也都是這樣。”[2]8洛克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強有力地抨擊。他認為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個體缺少了基本的自由和生命權利,則財產權和其他政治權利無從談起,人的主體性地位也無法呈現(xiàn)出來。但他同時也指出財產權中的所有權性質表明財產并非像自由、生命那樣體現(xiàn)主體自我的同一性,而具有主體自我和他者的同一性,從而決定了財產權不具有自明性。
而要闡述清楚財產權的不自明性,同時將財產的應得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而非建立在契約或者同意之上,這是洛克必須要解決的理論難題。為此,他從經驗解釋和普遍法則兩個方面展開推理。就經驗解釋而言,如果要求全體世人都按照契約或同意的原則來達成一致,那么整個人類將陷入“上帝給予我們保存生命的無限物資,而我們卻餓死了”的“豐盛悖論”。遺憾的是,洛克的這種經驗解釋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財產應得的起源問題,這促使他不得不尋求一條更具普遍性的法則來論證財產自然應得的正當性。為此,洛克引入了勞動、勞動能力、勞動占有等相關概念來為財產的自然應得進行合理性論證。
洛克認為,勞動的特殊屬性在于勞動是通過手、身體來作用于對象之上,并使對象發(fā)生性狀的改變,將自在之物對象化為人化之物,而勞動過程中的手、身體與個體的人身權等自然法則直接相關,故而勞動是個人的。加之人類從自然界中獲取何種物品、怎樣獲取物品、采用何種方式獲取均與人的勞動能力有關。為此,洛克以土地為例進行論證。他認為,“上帝將世界給予人類所共有;但是,既然他將它給予人類是為了他們的利益,為了使他們盡可能從它獲得生活的最大便利,就不能假設上帝的意圖是要使世界永遠歸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我在這里把經過改良的土地的產量定得很低,把它的產品只定位十比一,而事實上更接近于一百比一”[3]21。在他看來,人類從土地中獲取財富并不是簡單地直接攝取,其根本不在于土地本身的肥沃與貧瘠,而在于人在土地上進行的耕地、播種、施肥、收割等系列實踐活動,并且人在越貧瘠的土地勞動,就越能體現(xiàn)勞動所帶來的財產的豐裕程度。這就是洛克的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理論。
但面對菲爾麥的責難,僅僅靠上述只言片語還無法解釋自然物品的公共財產屬性如何轉化為個體的私有財產,即私人財產所有權是如何從自然權利演化而來。洛克認為,勞動占有和混合論證能清晰地闡述上述問題。勞動占有是指個體對自身勞動具有自我占有權,那么通過勞動后獲得的財產(無論是共有狀態(tài)的財產還是私人財產)就具有天然的排他性。這一點已經在上文中洛克關于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理論中予以闡述,下面我們討論一下混合論證。所謂混合論證,指的是通過個體勞動與外部資源相混合而確立私有財產及其權利的論證[4]。洛克認為,“取出這一或那一部分,并不取決于一切共有人的明白同意……我的勞動使它們脫離原來所處的共同狀態(tài),確定了我對它們的財產權”[1]20。他的這種觀點表明,人類的勞動能夠有效區(qū)分財產的共有狀態(tài)和私有狀態(tài)。因為勞動的私人所有,使得一個處于原初共有狀態(tài)的東西若與人的勞動相結合就會改變其公共所有權,從而成為勞動者的私人財產,勞動者也自然地對這個東西享有一種排他性的權利。其他人未經勞動者本人同意而占有這個已經蘊含了勞動的東西,則是對該勞動者勞動的占有,這種占有行為在自然法面前是不正當?shù)摹2浑y看出,在洛克的理念和邏輯論證中,物品的公共財產屬性轉化為個體的私有財產是在自然狀態(tài)下通過人的勞動得以實現(xiàn)的,因而是自然性的,不需要經他人的同意和契約就能確立起來。至此,洛克通過比較嚴密的邏輯推理建立了財產的自然應得觀。
二、洛克財產應得觀的理論困境
洛克財產應得觀對近現(xiàn)代西方政治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其在自然狀態(tài)下所主張的勞動占有、有限政府等理論邏輯受到菲爾麥的指責,后者認為這僅是一種理想化狀態(tài),是洛克無法突破的理論困境。
第一,洛克的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理論未對勞動這一概念做必要的限定。洛克認為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和所有低等動物均為人類所共有,但人對自己的身體天然地具有排他性。人通過自己的雙手從事勞動所獲取的成果正當?shù)貧w其自身所有,即人通過勞動獲取的一切財產均可由個人自由支配。這種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觀點雖然指出了財產應得的道德性,但洛克卻未對勞動自身做必要的限定。他所討論的勞動也主要是指土地之上農業(yè)活動中的私人性勞動,對于私人勞動和一般勞動未做必要的區(qū)分,因而也無法說明國家何以能合法地享有私人勞動成果。
第二,勞動占有無法解釋土地自身的所有權問題。洛克闡述財產應得的過程中對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理解能證明個體勞動之后對自身所獲財富的占有權,但無法證明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天然屬于該主體,而土地是生產資料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要素,尤其對農業(yè)生產實踐而言更是如此,但洛克卻未對土地自身的所有權問題進行有效闡述。
第三,在財產應得觀的闡述中沒有處理好自由與平等之間的關系,過分注重個體自由而忽視了平等理念。洛克在許多論著中都將自由當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自然權利予以說明。他闡述個人自由的現(xiàn)實內容切實維護生命權、健康權和財產權等具體權利。其中,最基礎的權利是財產權。但他所闡述的財產權基于最初的自然權利關注到了具體的權利范疇,而不是抽象的權利。一些因土地而獲得的財產,由于不同的土地占有使財產權有所差別,進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政治權利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因為土地、森林等生產資料所有權歸資產階級所有,這使得勞動所得越來越向生產資料所有者集中,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平等程度越來越深。
洛克財產應得觀雖然有諸多不足,但其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頗大。盧梭就是典型案例。面對教會和普芬道夫追隨者的理論責難,盧梭汲取了洛克關于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理念,克服其財產的自然應得主張中存在的不足,主張財產的所有權應建立在契約或同意的基礎之上,形成影響后世的社會契約論。就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都謙虛地總結:“我一直試圖做的就是要進一步概括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傳統(tǒng)的社會契約論,使之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抽象水平。”[5]2盧梭雖然也從自然法出發(fā)論證私人財產的正當性,但他更注重個體之間在勞動中的平等地位,并且認為強力不能構成權利的第一要素。他認為,“強力不構成權利;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威才有義務服從。……既然任何一個人對他的同胞都不擁有天然的權威,既然任何強力都不可能產生權利,于是,人與人之間就只有約定來作為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了”[6]10。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在于盧梭認識到了武裝力量所帶來的強力及服從是不可取的,是非正義的。但他的理解也有偏頗。一方面,他在《社會契約論》中以森林中的強盜用槍來使別人服從為例,說明其沒有意識到除了顯性的強力之外,還存在隱性的強力,比如說資本、土地等帶來的隱性強力使得工人不得不與資本家簽訂協(xié)議來約定某些事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事實上,這種在帶有剝削性質的隱性強力之下作出的約定也是不正義的。另一方面,他以“約定的就是合法的”為由,指出任何人在約定基礎上的獲得都是一種應得。這種觀點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約定基礎上的應得可能是通過隱性的強力強行占有,因而也存在不正當?shù)目赡苄浴?/p>
三、馬克思財產的勞動應得對洛克財產應得觀的超越
洛克從財產的自然應得維度發(fā)展完善了自由主義財產觀,對自由和公正的理解助推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fā)展。但從理論論證本身來看,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對他理論上的批判在多個著作中均有體現(xiàn)。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洛克的財產權學說以及其他關于自由平等的言論并沒有真正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即使在部分理論中提及要給予工人一些勞動時間上的平等和勞動條件的改善,那也不過是類似于贊美封建社會勞動制度中合理成分的“死人復活”而已,其目的在于支持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神學。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應得觀不過是一套玩弄普通勞動者的把戲,只是“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xiàn)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起來”[7]670。哈巴谷作為圣經中的一個先知,本應受到譴責和批判,但洛克基于資產階級政權建設的需要,借助哈巴谷的名字、戰(zhàn)斗口號和衣服,使得資產階級能夠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tǒng)治。洛克通過看似正義的財產權學說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權理論,成功實現(xiàn)了由借助國王的招牌進行勞動成果占有向借民眾的名義進行勞動占有的轉變,加之“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條的實驗,醉心于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8]676,最終使得勞動成果被剝削階級占有,工人階級勞動時間上的自由則更加無從談起。為此,馬克思首先從理論上、然后在政治實踐中反對洛克的自由主義財產觀,提出自己的財產應得思想。當然,馬克思在批判洛克的財產自然應得理念時并非從抽象到抽象,而是有著抽象與具體相統(tǒng)一的內在邏輯。馬克思的財產應得理念不僅是指勞動者對財產在量的層面的所有,而且更強調質的意義上的所有,只有真正的勞動者才能共同享有勞動所獲得的財產,財產問題是一個關涉人的本質及其實現(xiàn)的重大命題。大抵而言,馬克思在財產應得問題上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勞動尤其是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是獲取財產的必要條件。勞動過程中的協(xié)作決定了財產應得的邏輯起點不是自然,而是真正的勞動。在馬克思看來,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是經過比較而提取出來的、為一切時代或幾個時代共有的生產特征。一般的生產是指生產活動“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8]686,即日常的生產活動。任何時候都不能割裂生產一般與特定時代的具體生產,生產一般“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別有不同規(guī)定的東西”,生產總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yè)、畜牧業(yè)、制造業(yè)等,或者是它們的總體,“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8]685。生產活動本身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不能將其僅僅歸結于自然主義和某種形式的契約。
一般的生產蘊含著人類物質生產過程中對生產三個要素的有機融合,而生產一般與特殊部門的生產恰恰就是分工與協(xié)作的另一種詮釋。無論生產一般還是一般的生產,都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協(xié)作。關于這一點,馬克思認可洛克的觀點,并將勞動中的共同協(xié)作理念予以深化。在馬克思看來,協(xié)作主要蘊含著兩個邏輯關系:一是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fā)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9]7。這意味著人在勞動中交往,在交往中合作。二是生產力不斷發(fā)展導致社會不同產業(yè)之間的分工,分工不等于分離,相反,分工更需要緊密協(xié)作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因為一方面,協(xié)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另一方面,協(xié)作可以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范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范圍的這種縮小會節(jié)約非生產費用(faux frais),這種縮小在馬克思看來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會帶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升。遺憾的是,這種勞動過程中的共同協(xié)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很難實現(xiàn),道德主體甚至在協(xié)作過程中受到資本邏輯的制約而使協(xié)作過程異化了。“一切規(guī)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xié)調個人的活動,并執(zhí)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個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10]384但是,一旦物質生產過程受到資本制約,從屬于資本的勞動協(xié)作進入生產領域,那么馬克思所倡導的協(xié)作過程中產生的管理、監(jiān)督和調節(jié)的職能就成了資本的職能,進而取得特殊的性質。一方面,伴隨著較大規(guī)模雇傭工人的協(xié)作,資本的指揮棒作用發(fā)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這就使得資本家所從事的指揮、管理工作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而且是一種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另一方面,雇傭工人之間的協(xié)作只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也就是說,雇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職能上的聯(lián)系和作為生產總體的統(tǒng)一存在于自身之外,存在于將其集合在一起的資本之中。這就使得雇傭工人勞動中的協(xié)作“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劃,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10]385。這種勞動產生的財產絕不可能為整個社會所共享,而只可能成為資本家的私人所有,因而需要對勞動過程中的異化予以理論上的批判和實踐中的消除。
要做到這一點,馬克思認為要消除勞動過程中的異化現(xiàn)象,從而為財產的共享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則需要“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xié)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0]874。這種個人所有制并非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的私有制,也不是東方公社中公有制的簡單重復,而是將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人民群眾是這種所有制的主人,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進而能夠自由地實現(xiàn)對所獲財產的共同享有。
第二,人民群眾對財產的價值訴求可以通過勞動予以呈現(xiàn)。馬克思指出,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和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具體而言,一方面人民的牧放人產生于人民群眾,所謂時勢造英雄,正是由于牧放人的主觀條件使其成為牧放人,但就其本質而言,牧放人就是人民群眾。另一方面,無論牧放人還是普通民眾,其價值訴求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以呈現(xiàn)。
那么,人民群眾究竟采用何種手段在勞動中實現(xiàn)自身價值訴求?馬克思利用“剩余價值”的概念對此進行了嚴密的論證。他通過考察工業(yè)革命以來英國經濟發(fā)展狀況后指出,在私有制社會中,勞動者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制約,整天在條件惡劣的環(huán)境中長時間工作,卻只能獲得勉強維持生存的微薄工資,他們創(chuàng)造的絕大部分剩余價值被他人無償占有。若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xiàn)狀,則需要首先成立勞動者同盟或統(tǒng)一的政黨,然后在該組織的領導下展開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一切剝削的政黨和制度,進而建立維護自身勞動權益、保障自身勞動成果的政權組織。由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建立勞動者的自由王國,實現(xiàn)財產真正從屬于勞動、財產歸真正的勞動者所有,從而在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彰顯人的本質。
第三,財產所得的價值旨歸在于人通過勞動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洛克雖然承認勞動創(chuàng)造了財產,但將其主要限定在生產領域,認為勞動在自然法則基礎上滿足了人的吃喝住用行,實現(xiàn)了自然人的基本需要。即使在部分場合將勞動上升到更高層面而使其具有某種道德屬性,也缺少必要的實現(xiàn)手段和路徑。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不僅是人與自然實現(xiàn)物質變換的手段,實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而且作為生活意義上的勞動,將人的本質(蘊含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本質)對象化在勞動的對象之中,使得勞動首先是生產勞動成為人的本質得以突顯的基本方式,從而使得人能夠在勞動中獲得最主要的財產——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能力,即通過勞動而最終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才是人參加勞動實踐的真正旨趣,使得人成為“人”。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這種論斷正是馬克思基于勞動是處理人與自然、社會及自身思維的過程的認識而得出的。只有在人的勞動目的論意義上才能真正認識到財產的源泉。這種認知解決了自由主義者無法真正詮釋的財產是“怎樣產生”和“何以產生”的問題,即“怎樣生產”和“為何生產”是由“生活意義”來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通過生產資料私人所有不斷占有工人的勞動成果,使得自身的財富看似得到了增長,實則在工人勞動異化的同時,使自身在剝削過程中受制于資本不斷增殖規(guī)律的制約而被束縛,從而深陷商品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的泥潭之中。而要走出泥潭,則需要站在整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高度,從“生活意義”上認識勞動、尊重勞動,如此其財產才是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