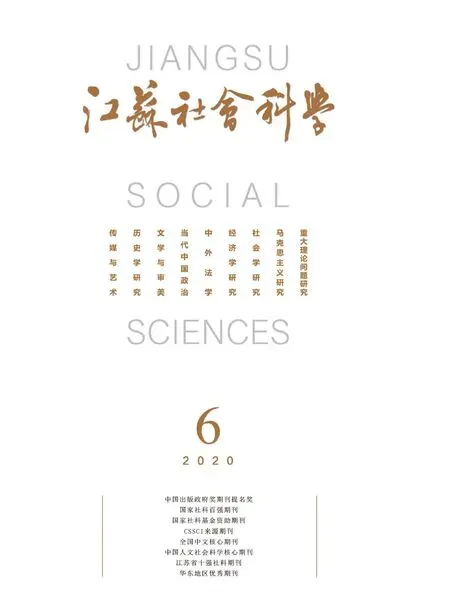騎士與圣僧:《堂吉訶德》《西游記》敘事藝術比較
劉愛琳 徐 偉
內(nèi)容提要 《堂吉訶德》《西游記》是西方“騎士”和東方“圣僧”的形象書寫。它們在各自由來有之的“騎士文學”和“西天取經(jīng)”的歷史規(guī)定下,不約而同地采用了“主仆”“師徒”的人物組合、游歷型的敘事結(jié)構(gòu),以及以諧寫莊的反諷范式,消解了小說文本的宗教宏大特性,實現(xiàn)了由宗教世界向世俗世界的轉(zhuǎn)向,助推了可資探究的世界文學的軸心時刻。
在東西方長篇小說發(fā)展史上,有兩部作品——無論從其在小說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還是對后世的影響來說——都是可以相提并論、并駕齊驅(qū)的,它們就是西班牙的《堂吉訶德》和中國的《西游記》[1]本文所據(jù)《西游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堂吉訶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塞萬提斯以厚重的歐洲中世紀騎士制度和“騎士文學”為書寫底色,將堂吉訶德塑造成圣徒和騎士的混合體,并把他的瘋癲與憂愁,鍍上了拯救基督教文明的色彩——“拯救道德價值淪喪、唯利是圖、正在毀滅的人類”,形成了烏托邦空想主義、難以墨守成規(guī)的行為,以及充滿彌賽亞元素的“堂吉訶德精神”[2]〔俄〕弗謝·巴格諾:《屠格涅夫的演講〈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與俄羅斯的堂吉訶德精神》,夏忠憲譯,〔北京〕《俄羅斯文藝》2018年第2期。。《堂吉訶德》人物形象的定格、故事情節(jié)的選擇,以及莊諧倒置的反諷美學,成為中世紀“騎士文學”的經(jīng)典表現(xiàn)。比《堂吉訶德》面世稍早二十多年的《西游記》,則以三藏取經(jīng)為依托,以弘揚佛法、調(diào)和儒道為基調(diào),借各色妖魔鬼怪,寫盡諸國萬象、三界善惡,用如椽大筆展示了圣僧取經(jīng)的宏大而奇異的情節(jié)故事。美國學者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中認為:“作為一部建立在現(xiàn)實觀察和哲學睿智基礎上的諷刺幻想作品,《西游記》的確使人聯(lián)想到《唐·吉訶德》。這兩部作品在中國小說和歐洲小說發(fā)展史中分別占有同樣重要的地位。”[1]〔美〕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第120頁。兩部小說以其不同的藝術空間,投射出了不同民族的文學書寫特色,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中西長篇小說體式在人物設置、敘事風格、美學特質(zhì)等方面近似或相近的藝術軌跡和審美追求,形成了十六世紀最后十年到十七世紀開始的幾十年的“世界文學的軸心時刻”。然而由于東西文化精神、社會理想以及作家創(chuàng)作立場等方面的具體差異,二者之間又有著一些不同。
一、人物設置:傳統(tǒng)敘事和傳統(tǒng)道德理想的代言
《堂吉訶德》作為西方文學史上首部較為成熟的長篇小說,其重要的標志就是塑造了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堂吉訶德和桑丘兩個人物形象;而《西游記》也以其豐富多彩、讓人過目難忘的人物形象見長,兩部作品在人物的設置安排上體現(xiàn)了異曲同工之處。吳承恩的《西游記》將故事本身置于從屬地位,突出故事主題和人物,“在對至少是主要圣徒——唐僧、孫悟空、豬八戒這三位實實在在的喜劇性格的塑造方面,充分顯示了他的創(chuàng)造才能。特別是后兩個形象與世界文學中著名的另一對互補角色——唐·吉訶德和桑丘·潘薩一樣使人難以忘懷”[2]〔美〕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第120頁。。兩部小說的敘事策略,都是以人物刻畫為中心,人物設置在類型化的框架中追求互補,人物面目清晰而不失多元,人物敘事描繪技法精熟,體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敘事觀念在人物環(huán)節(jié)的具體投射和賦形。
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傳統(tǒng)敘事的核心范疇。萊辛宣稱:“一切與性格無關的東西,作家都可以不顧。對于作家而言,只有性格是神圣的。”[3]〔德〕萊辛:《漢堡劇評》,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頁。在西方文學中,“從斯泰恩到普魯斯特,許多小說家都把對個性的探索選作了自己的主題”[4]〔美〕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第15頁。。在這一背景下,人物性格的典型論被傳統(tǒng)敘事理論廣泛接受了。就這兩部作品的人物功能來看,可以基本區(qū)分為背景人物和中心人物兩類。“背景人物”大都隨著故事推進和情節(jié)開展而依次上場,基本是作為情節(jié)鏈條的某個連綴環(huán)節(jié)和中心人物的陪襯而存在的。如《西游記》中許多神、佛、妖、魔的形象,這些形象看似荒誕不經(jīng),但他們的存在對于情節(jié)的構(gòu)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這些神佛妖魔本身也具備某種先天的面貌、架構(gòu)及精神內(nèi)涵。而“中心人物”則是貫穿始終、具有意義指代的一種人物設置。兩部作品的中心人物雖然在數(shù)量上并不相等,但在人物的作用、人物的搭配上卻有許多相似之處。性格互補、不可分離的主仆與師徒,是兩部小說人物構(gòu)成的典型符號。《堂吉訶德》的中心人物有兩個:一主一仆,即堂吉訶德和桑丘;《西游記》的中心人物有四個:一師三徒,分別是唐僧、孫悟空、沙和尚和豬八戒。從身份的屬性來看,這兩組人物分別是主仆關系和師徒關系,其中主人或者師傅即堂吉訶德與唐僧,是行動的主導者或執(zhí)行者,在整個人物關系和情節(jié)鏈條中起到了施動者的敘事主導或決定作用;而桑丘與孫悟空等人往往是追隨者,處于被動的行動功能層,他們對于敘事進程的影響,往往屬于一種促進或延緩,并不能從本質(zhì)上改變小說故事的進程或走向。
應該說,兩部小說人物的此種設置情態(tài),體現(xiàn)了作者的文心深意和藝術追求。由于一般的背景人物基本隨著相關事件的結(jié)束而退場,也就可以漸次隱藏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敘事意義,而主要由“中心人物”來觀照其中的意義。就中心人物的意義指向來看,主導人物往往浸透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意味,而背景人物往往代表著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背景人物和中心人物二者之間既是互補的,也是對立的,有著較為復雜的交集與沖突。比如,在堂吉訶德和桑丘的主仆關系中,堂吉訶德是行動的發(fā)起者,是桑丘的主人,他和桑丘的性格構(gòu)成了鮮明的反差。堂吉訶德是一個圣徒與騎士混合體,也是一個基督文化下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主義者,而桑丘則是一個腳踏實地、只知道衣食住行的現(xiàn)實主義者,也是一個充滿實用主義思想的農(nóng)民。兩人的口頭禪充分反映了他們個性上的巨大差異,如堂吉訶德的口頭禪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桑丘的口頭禪則是“有多少錢,值多少價”。而在《西游記》中,如果說唐僧是帶著西天取經(jīng)、弘揚佛法的理想主義情懷而走上西天取經(jīng)道路的“圣僧”的話,唐僧的三位徒弟則都是出于“贖罪”目的才成為其取經(jīng)的協(xié)從者。在主觀意圖上,他們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同道,有著客觀而鮮明的反差。悟空、八戒、沙僧都是因罪受難,他們走上取經(jīng)道路的初始動機都是出于逃脫懲罰或贖罪的現(xiàn)實目的。
一定意義上,主導性中心人物象征了文化思想秩序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潛隱著傳統(tǒng)倫理道統(tǒng)意義在敘事空間中的制導意義。從人物性格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兩部作品中性格相對穩(wěn)定、缺乏變化的人物形象,也主要是這些主導性的中心人物。唐僧的正統(tǒng)、古板、迂腐,近乎不近人情維持著自身的取經(jīng)訴求;而堂吉訶德近乎瘋狂、荒誕的騎士行徑,也主要是對某種已經(jīng)失去現(xiàn)實合法性的文化倫理理想的追求。在相當程度上,他們都是一些正統(tǒng)價值意識形態(tài)的維護者和承繼者。就此而言,他們構(gòu)成了整個人物形象的基本尺度,引導著他者向他們靠攏。比如桑丘,在和堂吉訶德騎士游歷過程中,他的性格和堂吉訶德有一個明顯不斷趨同的過程。他從出于或者能“弄個海島總督當當”而跟著堂吉訶德外出冒險的功利目的,到后來不計任何得失、死心塌地跟著堂吉訶德吃苦受辛,這其中堂吉訶德對他的感化和感召是非常明顯的。納博科夫在《堂吉訶德》中說:“堂吉訶德,一個英勇的騎士和理想主義者;桑丘,一個講究實際和膽小怕事的鄉(xiāng)巴佬,傳統(tǒng)沒有看到的是,這個咋一看是建筑在對照的基礎上的構(gòu)思,卻演變?yōu)槲┟钗┬さ南嗨脐P系,而這一構(gòu)思的發(fā)展,正是這部天才著作的精湛的成就之一。桑丘,在一定意義上,是堂吉訶德性格的變奏,這樣的相似性,在偉大的藝術作品里,幾乎可以說是不乏其例的。”[1]〔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堂吉訶德講稿》,金紹禹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127頁。在故事的最后,桑丘已經(jīng)超越了以前的自己,成為一個像堂吉訶德一樣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理想主義不似堂吉訶德的空中樓閣,而是建筑在現(xiàn)實的土壤中,在作者的筆下,他幾乎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結(jié)合得比較完美的人。又如孫悟空,它對唐僧也有一個不斷認同和馴服的過程。原本唐僧常常要借助于緊箍咒來控制孫悟空,而到后來,孫悟空已經(jīng)心甘情愿聽從唐僧的指派,甘心為唐僧赴湯蹈火;而豬八戒則表現(xiàn)出比孫悟空更大的變化。在取經(jīng)結(jié)束后,這樣一個充滿物欲主義和世俗精神的豬八戒竟然因“挑擔有功”從而脫俗入戒被封為“凈壇使者菩薩”,取得了僅次于唐僧與孫悟空的果位。美國學者余國藩認為:“豬八戒是像福斯塔夫、堂吉訶德以及桑丘·潘沙一類人的混合體,可以說,傳統(tǒng)中國文學中尚未有過這樣的喜劇形象。他的好色、邋遢及其貪吃,數(shù)百年來令人忍俊不禁。”[2]〔美〕余國藩:《宗教與中國文學:〈西游記〉的“玄道”》,樂黛云編譯,《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頁。這些都說明《西游記》與《堂吉訶德》兩書人物之間的同質(zhì)性。
顯然,借助類型人物的設置,兩部小說最終都將小說人物引向了社會文化倫理觀念的認同。相當意義上,這就使得不同時空、不同地域的兩部作品在敘事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相近之處。華萊士·馬丁說過,“敘事在傳統(tǒng)上一直提供對社會價值標準的肯定……起著指示歷史和社會變化的索引的作用”[3]〔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頁。。雖然說處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二者在基督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認同自覺性上有所區(qū)別,表現(xiàn)的深度也不盡相同,但對主流文化秩序的認同,對于精神力量的肯定,對于人格的倫理完善的追求和頌揚還都是一致的。固然這種傳統(tǒng)敘事的“意識形態(tài)要素”或許有著較多的歷史守成特征,但也不乏特定歷史時期作家獨特的人生體驗和文學認知,表現(xiàn)出了作家各自的人生思考和藝術創(chuàng)新。
二、情節(jié)安排:結(jié)構(gòu)的起伏與意義的開闔
《堂吉訶德》和《西游記》在情節(jié)安排上,都無法超越或者遺忘它們背后龐大的、具有規(guī)定性的“騎士”和“取經(jīng)”的固有模式。因此,《堂吉訶德》和《西游記》的敘事模式,都采用了游歷型小說的情節(jié)模式。它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以旅行作為小說的結(jié)構(gòu)方式,以中心人物的足跡所至構(gòu)成情節(jié)的多樣元素,沿線場景各異,場景變化多端,視角開闔多元,形成一種時序鮮明、段落清晰而又渾然一體的小說構(gòu)造范式。其中《堂吉訶德》一書,描寫了從貴族公爵府到外省小客棧、從鄉(xiāng)村到城鎮(zhèn)、從平原到深山的不同場景;《西游記》的場景更是琳瑯變化,縱向的上天入地,上到玉帝天宮,下到海底龍宮、地府;橫向的經(jīng)歷了一百多個充滿了異域風光的國家。清張書紳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言:“寫一天宮,寫一地府,寫一海藏,寫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閣筆,后世之所絕無。”從敘事藝術的傳承來看,《堂吉訶德》繼承了《奧德修斯》游歷小說的敘事技巧;《西游記》則在三藏取經(jīng)的歷史事實基礎上,體現(xiàn)了作者更多的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在敘事場景的變化組合和空間多元方面,表現(xiàn)了作者宏大的藝術想象和藝術表現(xiàn)力。
概括地說,《堂吉訶德》總的情節(jié)框架,就是堂吉訶德和桑丘主仆兩人通過行俠冒險,企圖實現(xiàn)或達成已經(jīng)成為過去時的騎士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境界;《西游記》總的情節(jié)框架則在于唐僧通過去西天取經(jīng)來尋求大乘佛教的真諦。表面看來,他們追尋的不是一類東西,但只要仔細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卻有著超乎尋常的一致性,即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完成某種神圣的使命為出發(fā)點,無論是前者的基督教的“救贖”,還是后者的佛教“普渡”,兩人在行事動機中,都充滿著崇高的理想主義精神。征途中經(jīng)歷的種種奇遇和與各種艱難險阻作斗爭的經(jīng)歷也是用來襯托主人公的堅韌與執(zhí)著,并以此建構(gòu)了小說的情節(jié)框架,他們的歸宿都是指向?qū)で笕松哪撤N終極價值的實現(xiàn),即基督文明和大乘佛法。
在游歷型小說中,阻礙游歷的因素一般有兩種:外在的阻力和內(nèi)在的阻礙。雖說兩部作品出自兩個不同的民族,但作者在作品中強調(diào)的都是:主體戰(zhàn)勝了外在的阻力,即戰(zhàn)勝了種種困難與考驗;克服了內(nèi)在的阻礙,即克服了自身的種種弱點。在游歷的過程中,堂吉訶德迷失于現(xiàn)實與幻想之間,經(jīng)常把幻想當成現(xiàn)實以至于做出很多錯誤的判斷,干了許多荒唐、滑稽、瘋癲的事情。在作品中,這個阻礙者是外部的因素,即宣揚中世紀騎士文化的騎士小說。是由于對騎士小說的熱衷才使得堂吉訶德分不清現(xiàn)實世界和幻想世界,以至于把風車當魔鬼去搏斗、把羊群當敵人與之拼殺、把囚犯當作是落難的騎士而奮不顧身地去解救,從而做出了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他自以為是英雄壯舉,卻給所有人帶來了更大的災難。而堂吉訶德所執(zhí)著的理想和他所處的社會的巨大差距又使得他在世人眼中成為可笑的喜劇人物。實際上,真正阻礙堂吉訶德實現(xiàn)理想的是其自身的原因。身處文藝復興時期的堂吉訶德還常常恪守著中世紀中期的價值觀和道德理念,他認為,要掃除社會不公,“莫過于游俠騎士和騎士道的復活”,這和時代存在著明顯的脫節(jié),形成了堂吉訶德與現(xiàn)實社會的強烈沖突。
而唐僧師徒的游歷魔障,一是前往西天取經(jīng)途中旋生旋滅的妖魔,一是師徒之間的旋滅復生的心魔。《壇經(jīng)》所謂“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故心魔實是取經(jīng)成佛的本質(zhì)障礙。因此,取經(jīng)師徒經(jīng)常迷失于善惡之間,以至于在是非之間會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阻礙了他們目標的實現(xiàn),而他們的迷失既是因為心魔,也就是內(nèi)心世界的矛盾和斗爭,也源自于他們和外部世界的沖突。唐僧師徒要面對的常常不僅是自身靈與肉的考驗,還有來自外部的各種阻力。在取經(jīng)的旅途上,他們經(jīng)常會和外在的邪惡勢力進行殊死的搏斗,途中所遇到的九九八十一個各色劫難,每一難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不同的考驗,而一關連環(huán)一關的、反反復復的八十一次考驗與磨難,正是師徒四人修成正果的“通關文牒”。《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四人取經(jīng)路上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劫難,都屬于外在的阻礙,但阻礙唐僧一行取經(jīng)的最主要的阻礙,主要來自于唐僧的“肉體凡胎”,以及由此而來的固執(zhí)、愚頑和是非不明,以及三個徒弟心中存有的各類無名心魔。
在游歷目標的實現(xiàn)上,《堂吉訶德》經(jīng)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過程。堂吉訶德在人生的最后階段徹底否定了一生的所作所為,最終帶著對自我的否定悲慘地離開了人世。臨終時他說:“我從前是瘋子,現(xiàn)在頭腦靈清了”,“現(xiàn)在知道那些書上都是胡說八道,只悔恨已遲”。他臨終前要求燒毀所有騎士小說,而且要求他的外甥女不能嫁給讀過騎士小說的人,否則將得不到遺產(chǎn)。他終于在無法承受的哀痛中告別了他的幻想世界,恢復了理智,命歸黃泉了。堂吉訶德否定了他的癲狂的騎士行為,也告別了驅(qū)動他行為的所謂騎士文明和騎士文學。魯迅曾說:“堂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錯誤。錯誤的是他的打法。”[1]魯迅:《〈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后記》,《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頁。其實,塞萬提斯用堂吉訶德的瘋癲行為、與時代的脫節(jié)以及精心選擇的“大戰(zhàn)風車”等典型書寫,是在宣告了“騎士文學”的終結(jié)。而《西游記》中的唐僧師徒則歷經(jīng)千辛萬苦,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天竺國,面見了如來佛祖,又將真經(jīng)原路護送回東土,因此受如來冊封。一部“西游”,以師徒都得道成為佛菩薩而呈現(xiàn)出一個看似圓滿的結(jié)局。
兩部作品中體現(xiàn)出的相似情節(jié)安排,既有各自民族小說傳統(tǒng)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也源于兩位作家對社會的進步和理想的實現(xiàn)給予的高度關注。應該說,通過創(chuàng)作來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是吳承恩和塞萬提斯的共同選擇。但兩位作家在創(chuàng)作追求上又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塞萬提斯是因為對當時流行于西班牙脫離現(xiàn)實的騎士小說深感不滿才創(chuàng)作的《堂吉訶德》,他以為借助于騎士小說這種體裁,可以“借題發(fā)揮,放筆寫去,海闊天空,一無拘束”[2]〔西班牙〕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楊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頁。,目的“無非要世人厭惡荒誕的騎士小說”。這樣的一種創(chuàng)作追求和創(chuàng)作目的決定了他在情節(jié)的安排上必須通過堂吉訶德的悲劇來否定已經(jīng)過去了的騎士制度和騎士的行俠冒險。效果也正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樣,自這部小說問世后,騎士小說在西班牙文壇上從此銷聲匿跡,被徹底地“掃除干凈”。不但如此,那個騎著瘦馬、挺著長矛的堂吉訶德騎士,則成了“堂吉訶德精神”的顯性象征。今天來看這部小說,《堂吉訶德》的思想內(nèi)涵和社會意義遠遠超越了小說作者的預期。而吳承恩的《西游記》,則利用由來已久的唐僧“西天取經(jīng)”的故事,借助降妖伏魔的小說結(jié)構(gòu),出入三教,諷喻當世,使得小說文本既包融特定宗教和哲學的深刻內(nèi)涵,也飽含社會批判意識和人文情懷,更不乏濃郁可喜的大眾情趣和民間氣息。“將金丹玄道轉(zhuǎn)化為《西游記》這樣精彩而好讀的作品,作者無疑是第一流的天才。”[3]〔美〕余國藩:《宗教與中國文學:〈西游記〉的“玄道”》,樂黛云編譯,《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頁。《西游記》小說所構(gòu)建的宗教象征體系,以及廣闊而深遠的人間社會矛盾體系,如佛教的“心猿意馬”、道教的“金公木馬”隱喻系統(tǒng)、三教混同的社會系統(tǒng)等,形成了小說宏大而多重的闡釋空間。
三、美學效果:傳統(tǒng)敘事詩學的守常與新變
《堂吉訶德》與《西游記》的文本,充溢著浪漫反諷(Romantic Irony)的美學效果。兩部小說,在敘事與表意、想象與現(xiàn)實、主觀與客觀之間,都包含著有意無意的反諷敘事。《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為了寫出優(yōu)秀的作品,他必然既是創(chuàng)作性的又是批判性的,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既是熱情洋溢的又是講求實際的,既是訴諸感情的又是訴諸理智的,既是下意識的靈感所激發(fā)的又是清醒自覺的藝術家。其作品旨在描述世界,然而又具有虛構(gòu)性;他覺得有責任對現(xiàn)實做出真實或完美的描述,但又知道這是難以完成的”[1]〔英〕D·C·米克:《論反諷》,周發(fā)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頁,第118頁。。而《西游記》的文本世界,也同樣體現(xiàn)出了浪漫反諷的美學追求。
悲劇色彩和喜劇色彩的交織,悲劇人物和喜劇人物的纏結(jié)構(gòu)成了這兩部作品的共同特點。首先從整部作品的美學風格上來講,《堂吉訶德》應該是一部以喜劇的形式表現(xiàn)悲劇內(nèi)容的作品,而《西游記》則是一部以正劇的形式展開敘述,但卻充滿了喜劇色彩的作品。“中世紀理論把美降低到完善、合乎比例和光彩奪目。圣托馬斯說,三件事是美所必需:首先是善,不完善的東西是丑的;其次是正確的比例或說和諧;最后是光彩,因為我們把任何有鮮明色彩的東西都叫做美的。”[2]〔荷蘭〕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劉軍等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頁。但《堂吉訶德》一書打破了這個最低的美的三要件,諸多的敘事要素是充滿喜劇色彩的,如堂吉訶德和桑丘主仆兩人在外貌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鮮明對比所產(chǎn)生的喜劇效果,兩人因為性格的巨大反差和對生活認識的截然不同致使他們在相處中所產(chǎn)生的摩擦和對話中充滿的喜劇元素,堂吉訶德因為對生活認識的偏差而帶來的行動上的失誤所造成的喜劇效果等等。正因為這樣,《堂吉訶德》在問世的很多年里都被當成是一部喜劇作品。但《堂吉訶德》一書的喜劇要素是表層的,悲劇精神才是這部書的精髓,也是我們?nèi)鏈蚀_認識堂吉訶德形象的關鍵所在。
如果說堂吉訶德的喜劇色彩是觸目可及的,那么他的悲劇色彩則要我們用心去體會。堂吉訶德的悲劇體現(xiàn)在他和時代的不合拍上。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卻處在一個理想主義精神不斷失落的時代,所以他的心靈是寂寞的,他的精神是不被理解的,他屢屢被周圍的人作弄,還被周圍的人視為小丑和可笑的人,堂吉訶德和同時代人在對話時所產(chǎn)生的巨大的錯位和誤讀,這些都揭示了理想主義、信仰主義的失落和它們在當代所面臨的尷尬處境。這種尷尬,形成了“事實”明顯糾正“表象”的悖論情境,因此,海涅把《堂吉訶德》視為“關于靈與肉的反諷性寓意作品”[3]〔英〕D·C·米克:《論反諷》,周發(fā)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頁,第118頁。。當然,堂吉訶德的悲劇更體現(xiàn)在他行動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錯位上。無疑他的理想也就是他行動的動機和目的都是很高尚的,但是他的手段卻使得他的理想永遠只能成為一個無法實現(xiàn)的夢想,甚至注定他會永遠走著南轅北轍的路,這也注定了他只能成為一個悲劇人物,而且這之間的矛盾使得他的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更顯得可悲可嘆。堂吉訶德最后的結(jié)局,則進一步增加了他的悲劇色彩。他臨終前的自我否定,使他的一生成為了一個永遠無法回頭的錯誤,有了無法糾正的遺憾。如果上升到作品的形式和內(nèi)容的高度,我們可以說《堂吉訶德》是一部用喜劇的形式敘述悲劇內(nèi)容的長篇小說,這樣一種悲喜交錯的美學風格增加了作品的層次和容量,也是使這部長篇小說獲得了和它的長度相匹配的厚度。《堂吉訶德》完成了宗教世界向世俗世代的轉(zhuǎn)型,成為西方十八世紀“浪漫反諷”小說作品的開山之作。
《西游記》的美學風格,就是小說文本之中無處不在的奇幻之趣、童真之趣、義理之趣、諧謔之趣、反諷之趣,小說作品呈現(xiàn)出了整體意義上的“滑稽之雄”的美學追求[4]李劍國等主編:《中國小說通史·明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4頁。。在《西游記》一書中,人物形象的多樣性,紛繁復雜的場景和變幻多端的情節(jié),構(gòu)成了其多姿多彩的美學風格。但在《西游記》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美學風格是正劇和喜劇。從大的方面來看,《西游記》講述了一個正劇的故事,而作品也是采取了正劇的敘述方式,唐僧師徒歷經(jīng)千難萬險、克服無數(shù)困難去西天取經(jīng),并最終獲得真經(jīng)。這是一個帶有一定神話和理想主義色彩的美好故事,而作者是帶著堅信無疑的正劇的敘事風格來敘述的,獲得的美學效果也是正劇的。心誠志堅、而又庸弱迂腐的唐僧,帶領著三個頑劣不堪的“妖徒”,進行神圣無比的取經(jīng),本身就構(gòu)成了一個巨大的反諷情境。《西游記》一書,情趣橫生,活潑生動、奇幻兼具的部分,也是最能體現(xiàn)作者的想象力、最受讀者喜愛的部分。小說高超地將作品“人物”的動物性和人性雜糅一起,聚焦“猴頭”“夯豬”的形象特質(zhì),刻畫出了文學世界中極具喜感的孫悟空和豬八戒形象。如豬八戒是全書最大的笑點,也是喜劇元素。在外表上作者賦予他豬一樣肥胖、丑陋、笨拙的特質(zhì),而在個性上他也像豬一樣貪吃、好色、慵懶,充滿了世俗的欲望,取經(jīng)也意志不堅,稍遇挫折就想重回“高老莊”,是佛家所謂無明凡夫的典型。西天之行的神圣目的與他參與其中的世俗目的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顯明的反差,這也注定他常常成為隊伍中其他成員的笑料、成為讀者的笑料。對這個充滿世俗精神的人物,作者一方面給予淡淡的諷刺和挖苦,一方面也給予寬容的理解,這樣就使得這部作品更多人間的煙火氣,也更增加了讀者的親切感。正是以豬八戒這個喜劇元素為出發(fā)點,使得這部作品的喜劇要素不斷擴展,如豬八戒和孫悟空之間“對立”、豬八戒娶妻、八戒偷吃人生果等等。圍繞著豬八戒這一人物,作品的喜劇要素在情節(jié)發(fā)展和矛盾沖突中得以延伸。豬八戒“喜劇性格的基本特點就是主觀與客觀的悖謬,他經(jīng)常表里相背、弄巧成拙、欲蓋彌彰”[1]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頁。,構(gòu)成了小說的“浪漫反諷”。
《堂吉訶德》和《西游記》,都是中外文學史上浪漫反諷的杰作。它們都是悲喜因素的對立與結(jié)合,體現(xiàn)了多元化、多層次的美學效果,給閱讀者和闡釋者帶來不同、多感的審美體驗。這兩部書通過堂吉訶德與桑丘、唐僧與孫悟空等之間二組對比互補關系,通過場景的變化來展示全景式的社會現(xiàn)實,擴大作品的表達容量;通過人物、情節(jié)的安排使讀者獲得多種審美體驗,以進一步吸引讀者。這些都是在長篇小說成長成熟期作者擺脫了純粹的敘事模式后所做的嘗試。《堂吉訶德》和《西游記》也從一個側(cè)面印證了雖然處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中,但東西方長篇小說也能在一些方面呈現(xiàn)出相同相似的發(fā)展軌跡。兩部作品的美學意義,就在于從不自覺的創(chuàng)造向創(chuàng)造性自覺的過渡,從天真向感傷、從非反思向反思的過渡,從再現(xiàn)向表現(xiàn)的過渡[2]〔英〕D.C.米克:《論反諷》,周發(fā)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頁。。
《堂吉訶德》和《西游記》兩書,在基督文明和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小說作者無法擺脫“騎士”和“取經(jīng)”的固有框架,但他們在不同的時空之下,一致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通過比對鮮明的“主仆”“師徒”人物角色,世俗而非神圣的典型情節(jié)的選擇,特別是以詼諧之法寫莊重之事的美學追求,各自完結(jié)了“騎士”和“取經(jīng)”此類宏大敘事的歷史使命。在文學的歷史上,完成了宗教神圣向世俗世界的板塊移動。《堂吉訶德》和《西游記》各自所蘊含的文學美學價值值得學界投入更大的精力去挖掘和研究,而比較視閾中的兩者比較,或許可以洞見不同時空、不同文化、不同種族背景之下,世界文學創(chuàng)作的共同努力和普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