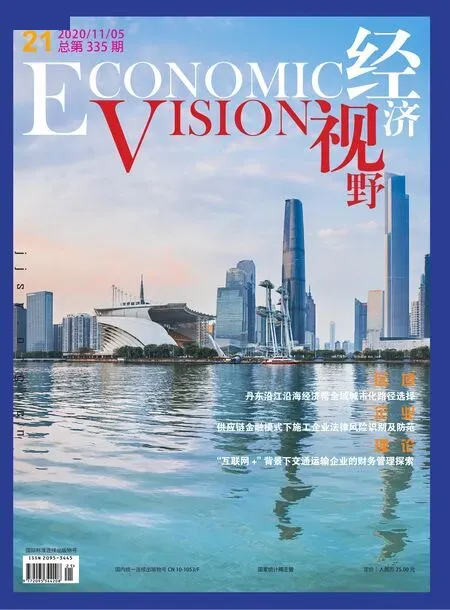稅負結構的合理化與財稅改革探討
□ 文| 程英麗
引言
近年來,稅負問題已經逐漸成為全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話題,主要因為稅收不僅關系著國家與地方的經濟發展,而且也與不同階層民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所以社會大眾對稅收問題尤其關注,并進行深入的討論,實際上這屬于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目前雖然不同學界針對稅負問題有著不同的觀點、立場、立論基礎及方法,但是也獲得了許多共識,如不能將稅收負擔和非稅收入負擔混為一談、不能將宏觀稅負與企業稅負同等看待等。從現有關于稅負問題的研究來看,多數是從宏觀稅負或企業稅負角度來提出稅制改革的建議,對于稅負結構合理化的關注較少,應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稅負的結構,這樣有利于人們進一步認識稅負結構,也有利于問題的發現、原因的分析以及改進建議的提出。
稅負繳納結構與稅制改革的關系
稅法規定了企業單位與個人的稅收繳納義務,從納稅人角度來看,可通過對稅收繳納結構來分析單位、企業及個人在稅收繳納上的比例結構。而由于我國有許多種稅收種類,且納稅人在繳納過程中所遵循的稅法規定也不同,所以先從不同稅種的繳納結構開始分析。
目前我國共有18個稅種,除了企業所得稅不涉及個人繳納以外,其他稅種都需要有單位及個人共同繳納。比如,個人所得稅的繳納,實際上也有單位繳納的一部分,主要因為單位在支付勞動者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時,也需要進行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另外,部分稅收除了企業要繳納以外,個人也需要進行繳納。所以需要根據不同稅種去對繳納者的數量或繳納金額進行衡量,以此對稅額貢獻結構或不同繳納者的分布結構進行分析和考察。比如,對于車輛購置稅多數是由個人進行繳納,所以屬于以個人貢獻為主的稅種,可由此結合相關的數據及方法對全部稅種的繳納結構進行計算,從而獲得單位和個人的稅額貢獻結構,換句話說,就是在分析不同稅種的繳納結構基礎上,將這些稅種看作是一個整體,由此進行分析從而獲得總體的稅負繳納結構。
實際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企業等單位稅收繳納是我國稅收的主要來源,個人直接繳納的其實并不多。盡管近年來隨著稅制的改革變化,個人直接繳納的稅額呈現出上升的趨勢,除了個人所得稅和車輛購置稅以外,個人還會涉及到房產稅、契稅等稅費的繳納,但是總體上仍然是企業等單位繳納貢獻較多。而這樣以企業等單位繳納為主的稅負結構,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公眾稅收意識及稅負痛感,也會導致稅收相關的法律規定和制度執行局限在小范圍群體中,難以實現稅收的“公共性”,這實際上也違背了稅收的公平性。所以,對于稅制改革的方向,應著眼于“公共性”這一方面,盡量擴大稅收涉及的范圍,讓更多人尤其是普通群眾真正對稅制改革的思路、目標、原則及產生的影響有充分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充分的討論,只有在獲得廣大民眾尊重且支持的稅制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稅負繳納結構與稅制改革有著密切的聯系,應保證稅負繳納結構的合理性,在改革過程中,應將稅負繳納結構與最終分配結構兩者重合進行考慮,適當增加在繳納貢獻結構中個人直接繳納部分,適當減少企業等單位在繳納貢獻結構中的比例,從而促使稅制結構能夠充分體現出稅負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稅負分配結構與群眾利益的關系
保證稅負分配結構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是廣大納稅人正當訴求,因為稅負分配結構指的是稅負最終歸宿結構。一般情況下,個人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負繳納結構與分配結構基本一致。但是相比較于個人繳納結構部分,由企業等單位所繳納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環保稅等,其最終歸宿結構并不體現在企業之間的分配,而會表現在個人之間的分配結構,如由企業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雖然繳納者為企業,但是最終承擔的并不是企業,而是與企業相關的投資者或勞動者。
現階段企業經營者在企業稅收管理上,會通過各種方式或手段將企業所得稅轉至不同個人身上,如通過提高產品價格或服務價格方式,將稅收轉移至消費者;通過壓低進貨價格或服務價格的方式,將稅收轉移至供應者;通過降低員工勞動報酬的方式,將稅收轉移至勞動者等。
除了上述這些情況外,在企業無法將稅收轉移出去時,最終由企業投資者個人承擔,所以實際上企業所繳納的稅收大部分是由不同的個人承擔,但是采取何種的負擔轉移方式無法獲得確切的結構,換言之就是無法明確獲得企業繳納稅負如何在個人身上進行分配。但這并不意味著與最終分配結構無關,無論是怎樣的情況,稅負的分配結構始終都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因為稅負最終都會落實到個人身上,所以需要關注稅負分配結構的合理性,從而保證稅負結構的合理性。而這就需要稅制改革關注到不同群體所負擔稅收的合理性,如果只是在稅負繳納結構合理上考慮稅務征收機構與納稅人繳納的便利,而忽視了最終的負擔群體,忽視了不同群體利益分配的合理性,那么無疑這一項稅制改革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為此,在進行稅制改革過程中,應將改革重點放在稅負的分配結構的合理性上,對于不同稅種的稅收政策制定,先要考慮稅負的分配結構的合理性,并將其作為引領改革的方向以及判斷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據。而對于稅負的分配結構的公平性,應遵循“量能負擔”這一原則,一是要強調具有納稅能力的人都應負擔稅收,除法律明確規定以外的個例;二是強調納稅能力較高者應比納稅能力較低者所負擔的稅收更多,而并非是相反;三是要強調相同納稅能力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收。雖然理論基礎上具有充足的說服力,但是如何在實際中運用則充滿了較大挑戰,比如如何衡量不同人之間的納稅能力?是否一個人的收入比另一個人高,則說明其納稅能力較高?等等。這些問題也對稅負分配的公平合理產生影響,所以在未來稅制改革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這些問題,這對保證稅負分配公平具有重要的意義。
稅負結構與政府支出結構的關系
由于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性涉及到不同群體的利益分配,因此政府支出結構也與稅負結構的合理性有一定的聯系,在稅制改革時,需要將這兩種結構放在一起考慮。具體而言,理論上稅收是向全社會群體進行普遍性的征收,理應由全社會群體享有公共支出項目;而對于向部分特殊社會群體征收的特殊項目,也理應用于與這種稅收目的相符合的公共支出項目中,如煙草消費稅的征收,相關支出應用在控煙禁煙活動中。這樣的財政原理才容易被納稅人理解和認同。
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政府公共支出結構并沒有實現與稅負分配結構的一致,兩者之間未能建立起合理的邏輯關系,從而導致合理的稅負結構與合理的支出結構不能實現有機結合。為此,在今后的稅制改革過程中,除了要考慮稅負的分配結構的合理性,也要充分考慮支出結構的優化,只有實現收支兩個結構的合理性,才能夠真正地實現財政的公平。比如當前我國面臨較大的扶貧壓力,根據收支合理的基本要求,個人所得稅應用于特困人群的扶貧救濟支出,為此可以在個稅改革過程中通過采取統一的比例稅率,以此簡化稅制,并提高籌資效率,從而實現收入分配整體的公平性。
結語
總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稅制改革應從稅負高低問題向稅負結構合理性方面的轉變,以此促使財政收支一體化發展,這樣才能夠保證財稅制度更好地滿足未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