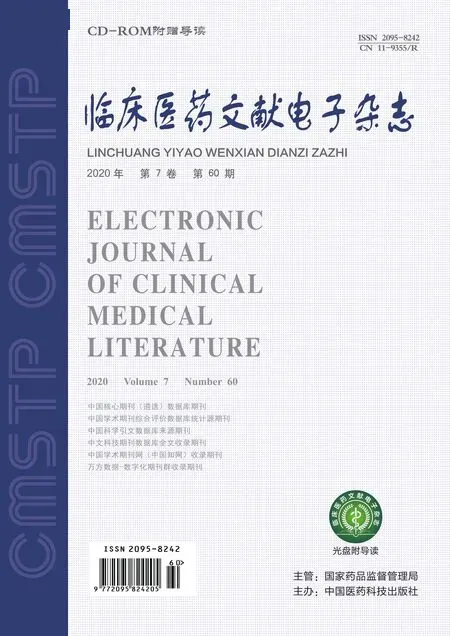藏藥藥性理論的藏藥方劑組方規律研究
旦正才旦,徐曉珊
(青海省藏醫院,青海 西寧 810007)
近年來,隨著藏醫藥在臨床中不斷推廣和普及,醫學領域也逐漸重視藏藥方劑的規律研究,在現階段,大概存在1000種藏醫常用的藏藥方劑,而通過中醫藥理論難以有效解釋藏藥方劑組方的相關規律[1]。深層次探討藏藥方劑的組成原則,針對藏藥藥性理論總結出組方的基礎規律及具體方法,是促進藏醫藥發展的基本要求。
1 藏藥的治療機理
藏醫提出藥物的治療機理是藥物性、味、效進行滲透和作用的結果,藏醫在臨床實踐中所依循的基本準則在于藥性、藥味、藥效及疾病的“對治”,認為藥物、疾病均具備其“性”,且源于五元,在藏醫經治體典著作《四續》中表示:“對治藥物仍由五元生,身、病、藥物渾然為一體”,這闡述了藏醫所秉持的“對治”原則,同時是藥物依據效、味、性、功能配方的根本依據。此外,藏醫強調藥物的八性、六味、十七效,其中“味”占主導,而“效”與“性”呈因果關聯,彼此為“對治”關系,疾病“對治”則可愈,反之則導致病情加劇,具體的論述在著作《四續》中詳細解讀。
和傳統中醫相比,藏醫的“對治”原則與其有著巧妙的相似之處,尤其是中醫學中提出的熱者寒之、寒者熱之、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等理念;但是也存在區別性,譬如藏醫中的熱與寒不僅代表藥性,同時代表病性以及身體體質,切勿混淆理念。
另一方面,在藏醫“本質性能”理論中又有進一步劃分,共包括祈愿功效、對治功效、緣生功效、生地功效、顏色功效、同形功效、氣味功效、同類功效等8類,重點分析了藥物由于外在顏色、形態結構、氣味不同而發揮出程度不一的功效。在中醫中,也主要通過藥材的色澤、形狀、氣味等進行鑒別。
2 藏藥方劑組方的基礎原則
在部分醫藥文獻報道中發現,藏醫組方存在一定規律與原則,被相關學者整理為“主仆原則”,也就是組方中對于主病主證發揮關鍵治療效用的藥物為“主”,譬如針對熱證治療的冰片系列方劑,而促進“主”藥提升藥效或是輔助削弱“主”藥毒性的藥物為“仆”。在藏藥組方時還存在差異性的君王、王妃、大臣、士兵藥等,和中藥學中的“君、臣、使、佐”配合應用相比,其兩者涵義具有一定差別。藏醫中的“君藥”通常表示方中“主”藥,“臣”藥為其之臂,“君王”藥與“大臣”藥在方中具有主導地位,應該均可歸納為“主”藥;而“士兵”及“王妃”藥則主要針對主藥的性、味、效進行配伍。此外,和中藥方劑配伍組成基本原則的區別還表現于,在不少情況下藏醫方劑會結合藥物功效強度將治療同類疾病的同種藥物進行分類,包括君王、尊主、大臣、庶民藥,譬如,“冰片”是熱性疾病臨床治療中效果最為顯著,也是藥效強度最大的藥物,因此把“冰片”視作主藥的一系列治療熱性疾病方藥作為君王藥,紅花則排其次,以其為主藥進行組方的系列熱性疾病治療方藥為臣藥。基于此,在藏醫組方中,應當對疾病進行合理診斷,明確疾病性質,探尋疾病發作的主要因素(主因及誘因),同時充分掌握藥性與疾病屬性之間的聯系。同時,在給藥過程中必須結合疾病屬性來判斷所使用藥物的效、味、性進行組方。譬如,藏藥中的“八味沉香丸”多用于治療“隆病”,其主要遵循了“異性對治”原則。此外需注意的是,在藏藥藥性理論和中醫理論中,對藥物寒熱屬性上的理解具有顯著差異。
3 基于病性和藥物的藥性、藥味與化味組方
由著名藏醫學家宇妥·寧瑪云丹貢布所著的《四部醫典》提出,引起疾病的重要因素主要在于赤巴、隆、培根發生紊亂,而在進行疾病診療時,需調節“三因”,促進其實現平衡目的。通常隆與培根的紊亂在“三因”中屬寒性病癥,針對寒性的隆與培根病,藏醫主要采取具有溫熱性質的藥物治療,而赤巴紊亂歸于熱性疾病范疇,常通過寒、涼性質藥物實施治療。在藥味方面,藏醫認為各類藥物味均具備不同功效,同時其作用發揮均存在差異性,分別對治不同疾病。比如,具備甘、苦、澀味的藥物可治療赤巴病,具備酸、甘、辛、咸味的藥物能夠治療隆病,具備辛、咸、酸味的藥物可治療培根病[2]。依循三化味理論,化味酸可對“培根”和“隆病”進行治療;化味甘可對“隆病”和“赤巴病”進行治療;化味苦可對“培根”與“赤巴病”治療。為此,藏醫遣方給藥通常以此作為依據,甘味可提升元氣及體力,促進患者身體堅實,能夠醫治“赤巴病”和“隆病”,改善腎虛、體虛及咳喘等。
4 基于病性和藥物性效組方
五源理論在藏醫藥學中具有重要作用,和三因及“味性化味”理論存在緊密的關聯性,根據藏醫歸類藥物的五源理論,即把藥物歸類至五類:水、土、火、風、空類,藏醫強調五源在交互作用及不斷運動中構建出宏大的物質世界,繼而闡釋人體病理、生理及藥物。并結合五源相互作用、衍生、變化及推進的關系進行抽象地歸類與推演,以此了解事物的結構形式及運動方式,這是一類體現系統性的邏輯思維模式。同時,藏醫學中提出五源中的每源均具備對應源功,提出土性藥物可發揮重、柔、溫、穩、潤等6種功效,起到強勁筋骨的作用。藏醫在進行臨床治療的過程中,結合“對治”原則,能夠把相近或相同性效的對治藥物配至同個方劑中,例如“隆病”存在輕、糙、涼、動、堅等特點,在進行該病治療時則可充分使用具有重、柔、溫、潤、穩特性的相關藥物加以對治。
在文成當智,貢保東知,東改措[3]等學者的《四部醫典》用藥規律——“味性化味”理論的科學內涵分析一文中提出,藏醫認為五源的不停運動及互相作用構建出各色的物質世界,包括病理、人體生理及藥物等。通過推演五源之間相互演變、影響、滋生及發展的關聯性,以此來闡釋事物的運動模式和結構特征,是一類系統化的邏輯思維方法。此外,藏醫將“疾病產生于五源,治療藥物亦由五源生”作為原則,解釋人體的生理、三因、病理、用藥等。并提出五源中不同源均有對應的功效,且權重依次減小。
5 基于藥物功能與病性組方
在臨床實踐中,藏醫積累了長期的藥物對治經驗,比如采取牛黃、冰片、紅花、綠絨篙、竹黃、白檀香等治療熱病,利用麝香、鉤藤、烏頭、鐮形棘豆等進行解毒,通過甘青青蘭、藏茵陳、唐古特烏頭、波菱瓜、藏木香等治療赤巴病[4]。在《四部醫典》醫治熱性肝病的方劑相關資料整合中,通過Cran R統計軟件完成頻數統計以及關聯規則研究,發現熱性肝病方劑治療中出現最高使用頻數的十味藥物為:天竺黃、藏紅花、印度獐牙菜、丁香、訶子、牛黃、兔耳草、渣馴、鴨嘴花、檀香,這提示藏醫在臨床實踐時一般結合藥物的功能完成組方加減,針對性診治相應疾病。并根據藥物功效進行組方,分為兩類,包括調理和峻瀉,用于404種疾病治療。
4 結 論
藏醫藥學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不斷更新對疾病知識的認知和理解,建立了一套藏藥藥性理論,促進自身掌握治療疾病的方劑組方規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藏醫各級文獻參考中的大部分方劑均無藥物劑量規定,這可能在于藏醫在臨床用藥時既需針對患者的實際情況加減藥物,還需結合患者的病情變化明確各類藥物的劑量,而藏藥的使用規律與指導原則為后人推廣藏藥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本研究所提出的藏藥方劑組方規律僅建立于漢文文獻的研究前提上,認識還不夠深入,仍需更加系統、全面地對相關藏文醫藥文獻進行分析,以獲得更加準確的藏藥方劑組方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