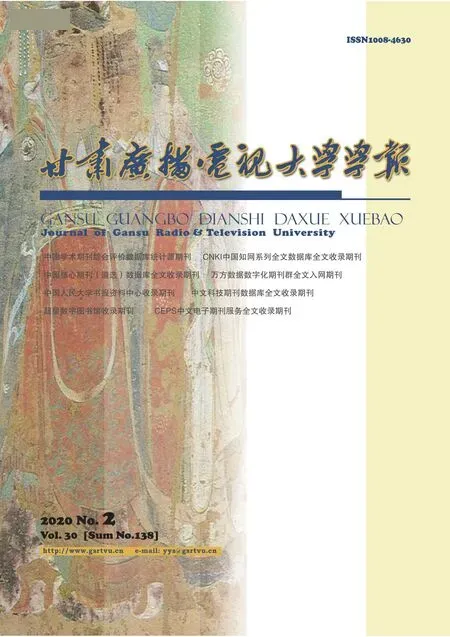互聯網平臺勞動關系認定的思考與完善
——以眾包配送為例
楊坤直
(上海師范大學 哲學與法政學院,上海 20023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飛速發展,新型的商業模式不斷涌現,餓了么、美團、閃送等眾包配送平臺應運而生。這些平臺的出現滿足了人們新的消費需求,同時也為社會公眾帶來了更多元化的就業機會。目前的平臺配送多采用眾包模式以化解運力不足的困難,眾包配送員已經成為外賣配送的主力軍。所謂的眾包配送模式是通過互聯網平臺以整合社會閑散勞動力,從而滿足更多兼職崗位的需求。在外賣眾包模式中,騎手只需要在APP系統注冊,由餐廳商家出錢派單,騎手在APP系統中搶單配送,進而完成配送任務,獲取相應的收益。由于此類從業者的收入跟平臺的配送單量、配送時效、客戶滿意度等要求相掛鉤,而平臺對于上述要求同樣有著嚴格的把控標準,這使得很多從業者為滿足平臺方的嚴格要求,減少了對自身以及他人安危的考慮,以致增加了外賣配送過程中存在的安全隱患[1]。因此,有必要分析近年來所產生的一系列涉及眾包勞動關系認定的案例,思考我國現行法律對于這類從業者是否予以保護以及保護是否充分,并探析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遺憾的是目前的眾包配送模式雖然已經發展成熟,滿足了多數人的就職需求,但這并未能改變眾包從業者的法律保護現狀,這類從業者普遍無法獲得勞動關系的認定。我國勞動法對勞動關系認定的標準沒有進行具體規定,在現有涉及眾包勞動關系認定糾紛中,我國各地勞動仲裁機構或法院仍然會謹慎地依據《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①(以下簡稱《通知》)以確定眾包物流平臺與注冊騎手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其第一條對勞動關系認定的三大從屬性的內容進行了大致規定,即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②[2]。由于該《通知》是2005 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所頒布的部門規章,其中較為籠統的條款內容難以適用于新型的眾包外賣配送模式,加之眾包外賣配送的服務性質以及平臺刻意的防范意識使得這些從業者一旦受到傷害就可能無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的司法實踐提出了挑戰。
現有的涉及眾包勞動關系認定的案件中,很多法院并不認可從業者與眾包平臺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甚至也不存在勞務關系。在于建新訴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一案③中,一審與二審法院均認為“于建新在快遞業務選擇、工作時間和報酬分配等方面均不受同城必應科技公司管理和支配,且勞動工具亦未由同城必應科技公司提供,因此于建新與同城必應科技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亦或是勞務關系,同城必應科技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不應承擔賠償責任”。雖然這樣類似的否定性判決還有很多④,但無法否認的是眾包配送從業者在適當的情況下需要得到法律的認可,認定其與平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這有助于保障其合法權益,實現勞動法的基本價值和立法初衷。而在李相國訴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一案⑤中,法院在論證了眾包模式下李相國需要依賴此工作維持生計,其能夠接單的數量以及交通工具的選擇上沒有其他選擇可能性,而且所完成的任務要完全遵照平臺方的要求[3]。法院最終認定李相國與同城必應科技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或許是考慮到本案判決結果可能會對眾包配送模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法院在論述中補充道:“本案的判決并不代表所有注冊的閃送員與同城必應科技公司之間均具有勞動關系。”可見在眾包配送模式的包裝下,現行法律的籠統化規定為司法裁判帶來了分歧,導致裁判結果不一致,損害司法權威,同時也難以保障特定從業者的合法權益。
二、問題的分析
互聯網平臺勞動關系的判斷離不開對傳統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的分析,以及其判定理論核心內容的研究。學界通說認為,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在于從屬性的判斷,以此來區別雇傭、承攬等其他民事法律關系[4]。正如史尚寬所言,“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謂當事人之一方對于他方在從屬的關系,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乃為特種之雇傭契約,可稱之為從屬的雇傭契約”[5]。由上述定義可知,勞動契約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勞動者的從屬性。
(一)我國勞動關系認定標準
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的擁有方,與其勞動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勞動者在提供服務、給付勞動時,必然與其所提供的勞動力一同進入高度服從用人單位管理和支配的從屬關系之中,進而受到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工作內容的安排、工作時間及地點的控制、工作任務的質量與進度的監督,具有極強的人格上的從屬性[6]。所以,在傳統的勞動關系下,該人格從屬性是用以區分勞務關系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勞動法用來判斷從業人員是否屬于勞動者以及能否給予法律特殊保護的重要考量因素[7]。
通過分析上文的案例可知,在實務中,法院通常對從業人員是否受用人單位指示、管理、監督,是否接受工作安排、服務時間以及是否受勞動規章制度的控制等方面重點考察,由此可知,我國勞社部發布的《通知》采用“主體資格+從屬性”,即“構成要件”式的立法來認定勞動關系,該種形式突出體現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要求;換句話說,只有在從業人員與用人單位同時滿足了主體資格、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四個條件的基礎上,才能認定他們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此外,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⑥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六條和第三十九條第二款⑦規定了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除了上述所列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一律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般證據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換言之,由從業人員對勞動關系存在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
(二)美國勞動關系認定規則
大陸法系國家判定勞動關系是否存在采用的是“從屬性”標準,而英美法系國家則采用“控制說”標準。在美國,勞動關系的認定以及雇員身份的判斷主要存在兩個體系。
第一個體系是1935 年《國家勞動關系法》所使用的普通法標準。該標準強調雇主控制或者是有權控制雇員提供服務的工作細節,如果雇主享有對雇員的控制權,則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若雇主一方缺乏控制權的存在,則勞動力提供方是獨立承包商,而非雇員[8]。美國的《國家勞動關系法》規定,判斷服務提供者是雇員還是獨立承包商,應該考慮十個因素,一是雇主對工作細節控制的程度;二是個人從事的是否為特定的職業或業務;三是特定職業所需的技能;四是報酬支付方式;五是雇用的時長;六是哪一方提供工具;七是職業的種類;八是工作是否是雇主常規業務的組成部分;九是當事人是否認為他們之間成立了勞動關系;十是雇主是否從事商業。其中沒有哪一項因素具有決定性,在對勞動關系進行認定時仍然需要對所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但是在該標準下,雇主的控制程度是相對重要的因素,雇主對雇員的控制程度并不是指實際行使了多少控制權,而在于雇主保留了多少可供行使的控制權。
第二個體系是加利福利亞州美國地方法院(簡稱加州模式)所確立的“Borello”規則[9],該規則規定的八個因素,應在認定雇員身份時予以考量,一是服務提供者是否從事特殊的職業或業務;二是該特殊職業所需技能;三是雇主是否提供工具以及工作地點;四是報酬支付方式,按時間還是工作量計算;五是個人所提供服務是否屬于雇主的日常業務;六是職業的種類,是否需要在專家的指導或監督下進行;七是提供服務的時間長度;八是雙方是否相信他們正在建立勞動關系。可以發現,“Borello”規則制定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與上文的普通法標準在很多因素上都是重合的,因此,在判斷勞動關系是否存在以及認定工人是否具有雇員身份時,綜合考慮工人與雇主雙方的所有相關事實是有必要的。
此外,在很多時候,可以將上述兩個體系同時適用于同一案件。例如在Lawson 訴Grub Hub 一案中(2017 WL 2951608),加利福利亞州美國地方法院首先分析Grub Hub 的控制方式及其對Lawson的控制程度,進而運用普通法標準初步認定雙方之間存在雇主與雇員的勞動關系。到這里,這個案子并沒有結束,美國地方法院繼續考量“Borello”規則中的八個因素,后來發現了其中三個不利于認定Lawson 為獨立承包商的因素,一是雙方認為他們之間建立起獨立承包商關系并簽訂相關協議,這看似是Lawson與Grub Hub達成的獨立承包商的合意,進而可以作為法院認定兩者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但是根據加州的就業測試標準,該書面協議不具有確定性;二是Lawson 自己提供設備、不需要穿Grub Hub 的服裝;三是Lawson 在Grub Hub 工作時也在為其他相關公司提供服務。對以上三個因素的判斷,并不能從法律上否認Lawson 的雇員身份,因為加利福利亞州法律規定了認定勞動關系的表面證據規則(616 F.3d 895),即只要原告提出表面證據,證明其為雇主提供了服務,法院便可認定原告的雇員身份,若被告提出原告是獨立承包商的請求,則其需要提出相反的證據予以充分證明。最終,加州法院認定Lawson屬于Grub Hub的雇員。
基于對比分析可知,我國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認定主要依賴于對從屬性的判斷,法院在審理互聯網勞動關系案件時,均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與組織從屬性上逐一考量,三者均符合的從業人員才能被法院認定其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由此可知,我國對互聯網勞動關系的認定仍然采用傳統的較為嚴格的認定標準[10]。上文所提到的美國認定勞動關系的兩個體系,其中每個體系所包含的各個因素都不具有決定性,即使普通法標準中雇主對雇員的控制程度是相對重要的判斷因素,美國法院依然要綜合考慮其他九個因素。此外,對于“Borello”規則中有而普通法標準中沒有的因素,加州法院在審理本州勞動關系認定案件時也將予以考慮,但是兩個體系均沒有規定所有因素必須同時滿足的要求。綜上,從勞動關系認定的多因素規則以及表面證據規則的規定來看,美國更加注重對雇員利益的傾斜保護。
三、改進與完善建議
互聯網平臺用工所呈現出的靈活性與傳統的用工模式具有很大的差異,我國勞社部于2005年發布的《通知》是以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經濟發展為基礎,并且制定者無法預見未來的經濟形式以及就業形態,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完備性與滯后性。此外,2018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其發布的《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2010-2018)》中也同樣提到了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遇到的挑戰,其中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難以完全適應不斷涌現的新經濟形態下的就業要求”。盡管如此,《通知》所確立的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規則并沒有過時,因為其內容反映了勞動關系認定的本質——從屬性的判斷,因此不用完全推翻和顛覆。但是,勞動關系的認定規則的確需要緊跟時代的腳步,做到與時俱進。
第一,增加勞動關系認定的因素,綜合考量多因素應用于個案。不同的商業模式會產生不一樣的用工形式。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用人單位對從業人員管理、監督的方式與程度也會發生改變。包括服務提供者的工作時長、是否具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報酬發放的方式以及計酬的形式、服務工具由哪一方提供、服務超時是否有懲罰、平臺如何評價從業者的服務質量以及是否處理消費者對平臺工人的投訴等,都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借鑒美國勞動關系認定的多因素規則,在我國現有的主體資格和從屬性的基礎上,增加對眾包配送職業種類、工作時長、工作地點、計酬方式以及監督方式等因素的判斷,并在個案中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并且,不把其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作為決定性的判斷因素,同時摒棄傳統《通知》里所傳遞出的“同時具備以下情形”的要求。因為平臺不同,其對從業者的用工形式或許就會不同,即便是同一平臺,對自己平臺內不同類型的從業者的用工形式也會有所差異。因此,在判斷平臺與眾包配送從業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時,應對多個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第二,擴大從屬性判斷的內容,將算法控制納入其中。根據傳統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只有在用人單位對從業者進行實地管理以及從業者遵守用人單位制定成文的勞動規章制度時,才能謂之為組織從屬性中用人單位對從業人員的管理。對于互聯網平臺用工而言,由于它的靈活性,平臺從業者每日奔馳于大街小巷,并不像傳統的從業者一般在用人單位提供的固定辦公地點從事勞動,這看似沒有受到平臺的管理與控制,實則不然,平臺在用戶的訂單詳情頁設置對其工人的星級打分機制,實時對平臺工人的服務過程和服務質量進行監督;對于提供服務超時以及被用戶投訴的平臺從業者,互聯網平臺制定了相應的懲戒措施,建立起“用戶+平臺”的雙重監督模式。由此可見,雖然平臺對從業者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管理,但是,在新經濟發展的潮流下,平臺只是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實施管理與控制,即運用算法進行遠程監督。綜上,對認定勞動關系的從屬性判斷的內容應予擴大,尤其是組織從屬性的內容,將用人單位利用算法對從業人員進行管理控制納入其中,以適應新經濟的發展。
第三,注重對從屬性判斷的實質解讀,而非浮于表面。當前的網絡平臺用工具有極強的靈活性,主要表現在平臺從業者可以自主選擇其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以及是否提供服務——接單或者拒絕接單,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些表現往往就是法院否定從屬性,進而不支持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是,就像上文所論述的一樣,認定勞動關系是否存在,不應以某一個或幾個因素決定,而是應該全面考量所有因素,不能僅僅因為平臺從業者工作時間、地點的靈活性和選擇提供服務的自主性就簡單地否認勞動關系的存在,要對從屬性判斷的實質進行解讀。正如前文所述,平臺是否通過算法實施控制、管理、監督的內容,同樣也是法院在認定勞動關系存在與否時應該考量的因素。總而言之,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平臺通常會采用更加隱蔽和復雜的方式對從業人員實施控制管理。因此,需要透過不同的新型商業模式以及平臺對其從業者的管理方式等表面現象,對從屬性的內容進行實質判斷,不應局限于平臺從業者靈活的工作方式以及可供自由選擇的服務就輕易做出判斷。
第四,借鑒美國的表面證據規則,分情況地適用于具體個案。具體而言,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平臺從業者,他們往往缺乏與平臺主管談判的能力,即便在工作過程中遭遇權益侵害,也無法通過其他正當程序尋求救濟,同時,這些平臺從業者完全依賴該平臺的工作以維持生計。對于這類服務提供者,法院可以在審理涉及勞動關系認定案件時適用表面證據規則。正如美國法官Chhabria所言,對勞動關系進行認定時應當遵循勞動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以及它意圖保護的工人。我國勞動法旨在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對于上述所列情形之下的平臺從業者,法院可以適用表面證據規則以判斷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這樣既可以實現勞動法傾斜保護勞動者的意圖,又不至于過度加重平臺的舉證責任而阻礙新經濟形勢下平臺的自由發展。
注釋:
①勞社部發【2005】12號文。
②《通知》第一條: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是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是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③(2019)京02民終5483號。
④(2019)京0106 民初15893 號、(2017)蘇0213 民初8149號。
⑤(2017)京0108民初53634號。
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十三條規定,因用人單位作出的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的勞動爭議,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⑦《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第六條和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與爭議事項有關的證據屬于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單位應當提供,用人單位不能提供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