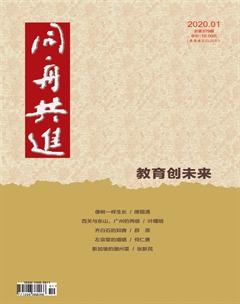齊白石的知音
薛原
齊白石老人晚年得到了很高的禮遇,可以說是中國畫家能夠得到的最高禮遇了。但即便如此,在老人身后,齊白石和他的藝術還是受到了批評和貶斥,如說老人的藝術是腐朽的,是不能代表新的藝術方向的,在人格上也被非議,如說老人吝嗇,眼里盯著錢之類。當然,這一切后來都反了回來,齊白石和他的藝術已被公認是中國畫在20世紀的典型代表。
關于齊白石節儉,有許多逸事,例如從鎖著的柜子里拿出已經發霉的點心給客人吃,等等,不勝枚舉。在繪畫上,更有一些逸事,例如:1950年代初,有書畫雅好者請齊白石作畫,當時齊白石仍按潤例收費,按尺幅大小明碼標價,而且在潤格幅度內,一幅畫畫幾只蝦幾只蟹,老人心里都有數,一般不會多畫。但西泠印社2009年出版的一本齊白石冊頁《花鳥草蟲冊》里卻有兩幅都是破例,一幅是墨蝦,一幅是雛雞。老人畫完了兩只蝦和三只雛雞后,正要題款,但在場的求畫者又求老人在畫上再添些什么,老人沒有說話,意思大概是再添就得加錢了……最終老人還是加了,不過他是在兩幅畫的右上角各“吝嗇”地添了半只蝦和半只雛雞,邊畫嘴里邊嘟囔著說,這些添筆算是送的。這兩幅冊頁,后邊添加的半只蝦和半只雛雞,與整體的效果看,還是能看出是“多余”的,但也多了幾分情趣和神韻。
齊白石屬于大器晚成的典型。他12歲開始學木匠,27歲開始拜師學習詩文書畫和篆刻,并以賣畫為生。定居北京后,結識了陳師曾。在陳師曾的鼓勵下,齊白石有了晚年的“衰年變法”,閉門多年專攻寫意花鳥,形成自家面貌,獨創了紅花墨葉的兩色花卉,以及濃淡幾筆的蝦和蟹等。
1917年夏,55歲的齊白石為避兵亂,又來到北京,在琉璃廠南紙店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到了齊白石的篆刻印章,特去拜訪,相談甚歡,成了知音。陳師曾擔任教育部的編審員,擅長寫意花卉,在北京已是有盛名的名家。齊白石從行篋中取出借山圖卷,請陳師曾鑒定,陳說齊白石的畫格是高的,但還有不到精湛的地方,并題詩一首:“襄于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束紙叢蠶寫行腳,腳底山川生亂云。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正如論書喜姿媚,無怪退之譏右軍。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用齊白石的話說,陳師曾是在勸說他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齊白石后來說,這次到北京,結交陳師曾做朋友,是他一生可紀念的事。當年在北京,更多的文人名家是瞧不起他的,不僅由于齊白石的木匠出身,對齊白石的繪畫作品也是看不起的,譏諷齊白石的畫粗野,題詩也不通。所以,得到陳師曾的激賞,對齊白石來說,是很值得紀念的。
1922年,齊白石60歲。那年春天,陳師曾應邀去日本參加畫展,陳讓齊白石預備幾幅畫,交陳帶到日本去展覽。結果陳帶去的齊白石的畫都賣了出去,且畫價甚高,齊白石的花鳥畫每幅賣了一百銀元,山水畫更貴。這樣的畫價,在當時的北京是難以想象的。齊白石為此賦詩一首:“曾點胭脂作吉花,百金尺紙眾爭夸。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這次日本展覽之后,齊白石在琉璃廠的畫價也一天天高了起來。用齊白石在自傳里的話說:“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對于早逝的陳師曾,齊白石老人的確是永遠忘不了的,還一點也不“吝嗇”筆墨,一直到晚年不斷寫詩題畫,紀念著這位當年對自己有鼓勵和推介的友人,如在《題陳師曾畫》一詩里,齊白石寫道:“君我兩個人,結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貴。牛鬼與蛇神,常憶腕底會。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我言君自知,九泉勿相昧。”在《齊白石詩集》里,粗略翻覽,就有十余首有關陳師曾的題詩。如《師曾亡后,得其畫扇,題詩哭之》《見陳師曾畫,題句哭之》等,滿紙充滿“哭君歸去太匆忙”的紀念之情。
自1946年以后,齊白石的藝術雖然在題材上再無多少創新,但筆墨設色卻越來越老辣樸拙,被譽為燦爛晚霞。1949年后,白石老人的生活更是安逸,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禮遇。毛澤東在1950年3月邀他入中南海賞花敘誼。徐悲鴻在出任新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后又續聘他為名譽教授,在1953年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還刊文《祝賀畫家齊白石九十三歲壽辰》,如此評價說:“齊白石的作品是從對自然景物精神的觀察中來,具有形神兼備真實生動的特色,從他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楚看到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勤樸不倦的勞動熱情,和對生活景物的細膩精心的觀察能力,以及表現景物的那種富有精煉創造才能的匠心。”同年,中央文化部授予齊白石老人“人民藝術家”稱號……老人的心情和繪畫更是隨意賦形,成就了晚年燦爛的繪畫生活。
用李澤厚在《紀念齊白石》里說,齊白石的構圖、畫境、筆墨,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國意味、中國風韻。它的確代表中國,民族的東西。它是民族的,卻并不保守。
至于說齊白石的為人,那些看似逸事、實為美談,其實并非說老人吝嗇。對待知音,白石老人是毫不吝嗇的。齊白石和他的藝術,已經成為我們精神生活的滋養。
(作者系文史學者)